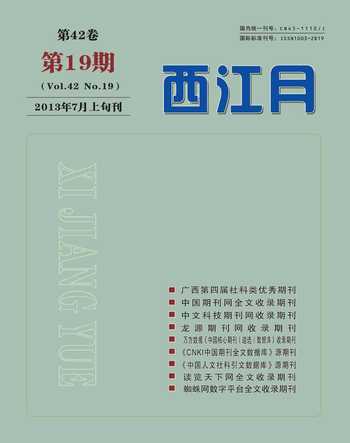“女巫”亦“女神”
左丽萍
【摘 要】母性形象贯穿于曹禺的戏剧创作中,他所创作的母性形象既有传统美德化身的女神形象,又有罪恶的施使者即女巫形象,“女神”与“女巫”两极对立的形象体现了曹禺对女性复杂文化心态和审美判断。《原野》中的焦母,正是其作品中的一位典型母亲,本文就试图从原型批评的角度,解读焦母这个女性形象,以此观照曹禺女性的审美取向,以及女性形象模塑中男权文化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原野》;女性原型;神话;集体无意识
按照荣格的说法,在人的意识或无意识之下潜隐着一个为人类所共有的集体无意识,他说:“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都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有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变迁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i集体无意识不是通过个人经验取得的,而是我们从远古的祖先那里继承或者也可以说是“遗传”下来的。在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的巨大心理能量往往是通过一些既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荣格将其称为原型(archetypes),女性原型就是这些原型中的一种。
原型批评将女性原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可怕的母亲,指的是女巫、妓女、妖女、荡妇等,她们代表的是黑暗、凶险、支离破碎、死亡恐怖性的无意识。第二种是伟大的母亲,她们体现出的主要性格是包容、善良、关怀,与出生、温暖、保护着、生长、相关,她们像大地养育万物一样充满母性;第三种指的是精神伴侣、精神的化身,公主或神圣母亲的形象,体现抱负和心灵上的完成。在《原野》中,具有男性般的智慧和机智、拥有财产和绝对权力,同时又对儿子和家庭极尽爱护的女人——焦母,正是前二者的结合体。
一、恶毒的女巫
在人类社会的生存空间中不变的两性关系构成生物最基本的两元立,随着母系氏族社会让位于父系氏族社会,男性的强大和女性阴柔遵循生理法则被固定和传递下来男尊女卑,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当女性冲破男权社会制定的家族伦理规范,追求自我和超越男性的强势时,往往被视为妖魔,而成为千人所指的罪人,即女巫。
曹禺的《原野》中焦母就是这样一个妖魔化的女性形象,自丈夫去世后,她成为了焦家的最高权力人和钱财的掌握者,拥有强大的女性主体权威。她的身上俨然没有传统女性所具有的温柔软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明显男性气质的性格:刚强,智慧和力量。首先,焦母的出场便初显了她的强硬。在作品的序幕中,通过白傻子之口,就预先形成了一个暴力性的女性,白傻子说到:“焦大妈,她说,送…送晚了点,都要宰…宰了我。你…你要是把她的斧头抢走,她也宰…宰了你!”难以想象,这些词语在描述一个年老的妇人。其次,在与儿子,儿媳妇金子三人的关系中,又显示出了焦母的控制欲和权力意识,她对儿子有近乎变态的控制欲,极力的破坏他的婚姻,不予余力的对儿媳金子进行狠毒的咒骂和压迫。而在钱财方面,焦母亦是独揽大权。儿子在外工作所赚的钱,均被焦母掌握,甚至在焦大星外出时,他还需要焦母的支助。最后,在与仇虎的冲突中,又变现了传统观念中女人不该具有的智慧。如在作品的第二幕,当焦母得知仇虎已经回来准备复仇时,她没有表现出一丝的软弱和逃避,而是直面仇虎,并技巧性的与其周旋,稳住仇虎的复仇情绪。而后,她又暗中通知了稽查队,试图将仇虎送回监狱。从这一系列的安排和行动中,可见看出焦母身上所具有的魄力和智慧。
上述的三个方面,都表现了焦母的一种男性的强势,但这种强势,与处于父权制度下对女性的要求和审美相悖的。曹禺作为男性作家,在对焦母的塑造上,必然会无意识的渗透共同的心理遗传,即对女性创造力的恐惧,而最终演变成了焦母的女巫原型。曹禺几乎把焦母这个形象塑造成了一个具有某种妖性的女性,如在作品第一幕中,焦母引诱金子说出其生辰八字,而后用人形木偶对金子进行诅咒,同样的在第三幕中,当自己误杀孙子后,焦母进行了招魂,这些近似远古时期女巫作法的仪式,使得焦母俨然成为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女性。虽然焦母以权利、金钱对男权社会提出了反叛,但最终还是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二、伟大的母亲
中西方神话中有众多的女神,如中国的女娲、姜螈、嫘祖,西方的该亚、瑞亚、赫拉、皮拉、夏娃等,她们的共同特征是:善良、包容、坚韧、忍受人类的苦难,生育繁衍后代,妻性、母性、女性是她们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她们都是人类母亲的符号。当世界一片蛮荒的混沌状态下,她们辛勤理家,辛劳耕作,筚路蓝缕,用自己柔韧而坚韧的身躯,开拓奋斗,担当家族和人类命运领袖的调遣周旋重任。这些女性神话都表现出对原古先民人类母亲的敬重和仰慕。
虽然焦母以其“恶毒”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有人称其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个人物。”但她在维护家庭和保护儿子这点上,又可以说她就是焦大星生命中的“女神”。母性所特有的爱护、无私奉献和对家人的维护在焦母的身上都有所体现。
首先,焦母在对待外人上虽是极尽的狠毒,但对自己的儿子却是显现出普通母亲的慈爱与呵护。在《原野》的序幕中,焦大星即将远行,焦母嘱咐儿子到:“记着在外头少交朋友多吃饭,有了钱吃上喝上别心疼。”在这里,焦母脱去了外面那层攻击的外衣,恢复到了内在的正常母亲的身份。上面的那段嘱托,是日常生活中,母亲送别儿子时的最典型的情境,然而正是这种平常性,反映了她与天下所有母亲的一个共性——对儿子深沉的爱和关心。(下转第32页)
(上接第30页)又如在第一幕中,当睡梦中的孙子因不安而苦恼时,焦母暂时放下了对儿媳金子的争吵,转而对孙子耐心的安抚,作品中对她的行为和言语有细致地描写:她走到摇篮旁边,把孩子抱起来,悲哀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又轻轻拍着孩子的背。此时的焦母,俨然是一位慈爱的奶奶。焦母的母性,不仅仅表现在这日常生活的言语和动作细节中,更体现在当家庭亲人遭遇外敌灾难时,显现出的如女娲一般无私奉献和甘愿为子孙受难的品质。在作品的第二幕中,仇虎回来向焦家复仇,焦母得知这个消息后,她选择了独自面对强大的敌人,她说:“我倒是想报官,不过看见了大星,我又改了主意。我不想我的儿孙在受阎王的累,我不愿小黑子(焦母的孙子)再叫焦家下代人恨,仇易结不易解,我为什么要下辈人过不了太平日子。”可见,焦母所有行为的准则是以保护儿孙,维护焦家的安全为前提,而全然忽视了自我生命的考虑。这是远古以来人们对母亲的的一种共识:保护和奉献。
所以,无论曹禺把焦母塑造的多么恐怖阴暗,但其作为母亲,都不可避免的具有母性。这种母性,是深沉民族心理长期积淀的结果。中国神话中关于女性崇拜的神话比比皆是,这些神话母爱的圣母文化传统在心理上制约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更激发了那些受传统文化影响下作家的潜在创作。美国学者卡罗·吉里根在《男性生命周期的女性》一书中说到“在男性的生命周期中,女性形象和地位是哺育者,抚养照看者,贤内助,人际关系的协调人。”也就是说,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更强调的是其依赖性和救助性,即母性。中国的女性,无论她是什么角色,都必须有母性的倾向,她们用她们的付出建构属于男性的神话世界。焦母具有所有女性身上所具有的生命活力,与生俱来的母性情怀,给身边贫血、脆弱的男人以怜悯、宽容和支撑,成为他们精神上的栖息地。
可见,作为男性作家的无意识中存留着远古时代所遗传下来的对女性的共同的心理:一方面,他们渴望着女性的保护和爱,视女性为提供安全和能量的大地,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女性的创造力感到恐惧,从而把女性妖魔化、异化,把女性看成是堕落的夏娃,引发灾难的潘多拉。人类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关于女性的话语就是以男性本位为规范的女性话语,由于男性本位的规范,男性作家在建构女性形象时,必然会以男权的规范来建构。概括起来说,以“女神”和“女巫”为两极的女性文学类型均是人类社会进入父权制时代之后的产物,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期望。现今,人类几千年来所遵循的父权制文化传统并未消失,以男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评估更是根深蒂固地沉积于人们的头脑之中。焦母身上所具有的恶魔母亲原型和大地母亲原型的双重特质,正是男权文化视角下对女性的审美判断的体现。
注释:
①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和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1]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和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
[3]平原.女神与女巫:曹禺的母性意识[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04).
[4]郭思辰.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扭曲——试论欧洲文学中的女巫形象[J].科教文汇,2009(04).
[5]吴景明.女性崇拜意识与曹禺童年的“性别错位”[J].北华大学学报,2000(1).
[6]曹禺.曹禺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