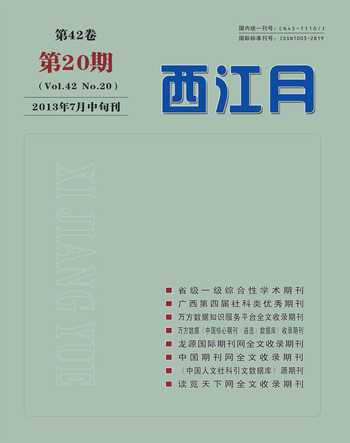先锋文学影响下的麦家小说创作
程浩
【摘要】如果将麦家的作品是一幅幅精美绝伦的油画,文学传统就是这画作的基础与“底色”。在此基础之上,便是他所借鉴和吸收的各种文学艺术营养。这些营养,有的来自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有的是新时期以来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贯穿其作品思想与形式的“先锋文学”风采。
【关键词】先锋文学;麦家;艺术手法;思想主题
麦家曾在专访中亲口承认,先锋文学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说是无法避免的。的确,上世纪80年代走上文坛的麦家,在那个文学“先锋”盛行的时代,面对那巨大的艺术及思想影响力、感染力及号召力,麦家不仅无法避免其影响,而且还主动、有意识地吸收、借鉴其有益的文学与思想营养。
一般认为,先锋文学是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与新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遭遇后,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合谋性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及90年代初蔚为大观。其开创性、反叛性、实验性、前瞻性等主要特性,与新时期以来,尤其是80年代起大量传入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的鲜明特点一起,被麦家大量吸收,并表现在其作品的叙事形式与思想主题等方面。
读麦家的小说,有关先锋文学的最使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主要集中于他笔下作品的叙事形式技巧方面。其中一些特点,之前论述麦家创作的“悖论”性精英意识时已经有所涉及,如叙述故事时的“元叙事”方式,这是从马原开始,几乎所有先锋小说家都曾经使用过的叙述方式,在麦家的作品《充满爱情与凄楚的故事》、《四面楚歌》甚至是《解密》中对发现失踪的容金珍的地点的前后不一的描述中,都可以见到这一叙述方式的身影。又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而采取的“迷宫叙事”方式,这一在麦家及诸多先锋小说家的导师,阿根廷人博尔赫斯笔下被充分发扬光大的故事叙述方式使麦家钦佩不已,并主动沿用。《风声》在“谁是老鬼”这一悬念引领下展开了一系列惊险的故事。谁是老鬼?他(她)有如何成功避开敌人的重重机关?他(她)的前世为何?未来命运又将走向何方?陈二湖、林婴婴等人身上也汇集了一个又一个悬念,对于他们的前世今生和命运浮沉的关注和对真相的求知欲,将他带入一个又一个悬念迭起的叙事迷宫中。除了叙事的迷宫性,《风声》还通过精心的结构组织与故事建构,营造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杀人游戏”,一场荡气回肠的“逃逸游戏”,文本与故事的“游戏性”在此一览无余。除此之外,《飞机》中由儿童视角出发描写成人世界的陌生化手法的大量使用,结尾对叙述者“我”纵身跃下的过程和中途“我”的见闻的夸张性描写,都与先锋小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叙述视角、叙述者的转移与变化方面,《解密》、《风声》、《暗算》等作品都有充分的体现,第三人称叙述者常常走进故事层,参与故事内容,叙述视角也常常发生变化,由故事人物从第一人称角度展开讲述,并采用访谈录等形式,充分体现了叙述方面的先锋、实验色彩。凡此种种,充分代表了麦家创作在技巧形式方面对传统叙事的背离以及对先锋性、现代性技巧的吸收与融合。
除了形式技巧,先锋文学的思想主题与价值观还深刻地影响了麦家作品中故事的中心思想。先锋文学及新时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创作中,很多作品体现了一种具有一定文化规定性的“超验思维”,即“在文学创作中追求永恒的确定性,往往以确定性社会真理为创作的终极目的,并且整个创作都围绕这一目的展开。”从《狂人日记》对封建势力的批判,《阿Q正传》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到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红色经典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的光明前景与伟大优越性的歌颂,长期以来文学作品的主题体现的都是高度理性的,被政治历史束缚了的“非文学精神”。个体真实人生体验、生命之思往往被抛弃、被压制,得不到认可。新时期起始阶段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虽然有所突破,但更多的仍是对既有“超验思维”语境中产生的文学主题的反思、纠正与局部突破,仍未彻底摆脱原有的思维惯性。直到先锋文学的出现,“体验思维”才真正开始打破“超验思维”的一元垄断局面。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地关注平凡、普通的民众和日常的生活,问题和语言方面也日益丰富、多元、现代。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高度个人化本位的,追求多远观念共存发展的具有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特征的思维模式,”作家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内心体验为本位进行创作,它使文学更加人学化,拉近了文学与活生生的人的内心世界的距离。在这种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与情感的思维模式下创作的文学作品,更加关注与描写个体的命运经历与转折,体现人的生命体验与存在之思,使作品主题在关于人生人性的哲学化思考方面达到一定的高度。
这种事关生命与人生体验的思维方式,显著地作用于先锋小说的创作,也深刻地影响着并突出地表现在麦家的作品中。纵观他的创作,经常流露着他对人生人性、生命命运与存在的个人化的深刻思考。比如《暗算》中通过对黄依依、阿炳灿烂到极致却转瞬即逝的生命轨迹的描写以及对他们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死因的交代,使故事表现出对生命荒诞的深刻感悟。又通过对陈二湖为红墙而生,最终又死于红墙,终生无法远离其一步的“毒瘾”似生命历程的交代,与黄依依的遭遇一道,引发对生命价值的形而上思考。《杀人》中,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的“我”带女儿回家祭奠父亲,本已无心寻仇,竭力想避免冲突,但最终仍然难以避免因过失杀人而锒铛入狱的结局,而最终杀人接口的幻灭又使“我”这一行为顿时失去了所有意义,“我”的入狱,似乎只是上辈恩怨延续的结果,是冤冤相报的宿命使然。这种人物坎坷命途上随时可能不期而遇的的偶然性的意外与巧合相对照,构成一组必然与偶然的人生悖论,所有这些都使人顿生面对生命时的无奈。《四面楚歌》中,没有人能真正理解阿今,在彰显时代话语环境的同时,也体现了阿今心中充溢的人生孤独感与迷惑无助;《充满爱情雨凄楚的故事》中,裙的哥哥竟然以生命为砝码将自己的妹妹当做诱饵,在他眼中,至亲的妹妹就如同待宰的羔羊,人性的疯狂与险恶在貌似正义的革命与战争名义的笼罩下显露无疑。
作为一个成熟、系统的文学艺术与思想体系,先锋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形式到内容再到主题思想,全面而又深刻。难怪在麦家心中,这一思潮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入、广泛而又难以避免。在它的示范与熏染下,麦家在作品创作艺术与思想表现上,充分展示了先锋的印记。
【参考文献】
[1]麦家.暗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麦家.解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麦家.风声[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4]麦家.黑记[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5]麦家.麦家自选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6]焦明甲编.新时期先锋文学本体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