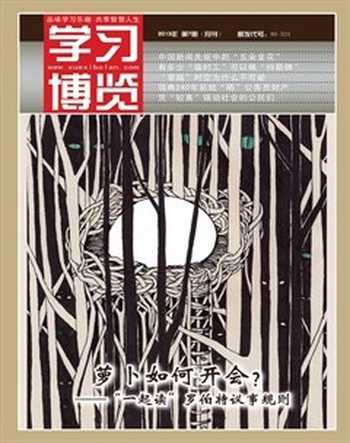市场的道德正义性
张维迎
自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以来,有关市场经济制度优劣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拥护者和批评者之间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市场拥护者主要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证明市场的优越性,把道德制高点留给了市场批评者。结果,给普通人留下的印象是: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但不利于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市场竞争有利于富人和强者,不利于穷人和弱者;追逐利润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导致贪婪和道德堕落。普通人似乎只能在物质主义右派与道德主义左派之间选择。
这样的印象当然是错误的。作为经济学家和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阿瑟·布鲁克斯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坚定捍卫者。他的新著《通往自由之路》的独特性在于,作者不是从效率的角度,而是从社会正义和道德的角度捍卫市场经济。作者认为,自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个人幸福来自“获得的成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就是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实现卓越);自由企业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让人们各尽所能获得成功,使人活得有尊严;自由企业制度也最有利于人类同情心的彰显。市场经济制度给普通人带来最大的幸福,因而是人类创造的最道德、最公平的制度。
本书对自由市场制度优越性的论述不仅基于逻辑推理,更基于经验事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本书有关个人慈善行为的部分。美国是最市场化的国家,美国也是最慷慨的国家。美国每年的慈善捐款加起来大约3000亿美元,超过芬兰、葡萄牙、秘鲁等国的GDP,其中四分之三来自私人捐款,四分之一来自公司和私人基金会。70%-80%的美国家庭每年都做慈善捐款,平均捐款额超过1000美元;50%-60%的美国人每年都提供自愿者服务,平均接近50小时。以人均算,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捐款和自愿者服务时间接近美国,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
美国人为什么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原因不仅仅因为美国人富有。富人确实给出更多的捐款,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的众多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按占收入的比例计,美国工作的穷人的捐款比例高于富人和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慈善行为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政府作用的信念高度相关。相信自由企业制度的人比相信大政府主义的人更慷慨,无论用捐款还是自愿者服务时间衡量都如此。以对收入分配的态度为例,1996年,不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的平均慈善捐款4倍于持相反观点的人,这一差距与教育水平、收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无关。其他非货币形式的慈善也如此。平均而言,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提供的自愿者服务远小于持相反观点的人。2002年的调查显示,与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多的人相比,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少的人更少愿意献血、更不愿意为陌生人指路、更不可能返还收银台多找的钱,也更不可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和金钱的帮助。这些大政府主义者在约会中也更可能不守时间。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原因在于,主张大政府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无关;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每个人的责任。这表明,大政府主义者更可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缺少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心。这一点令人震惊,但真真切切。中国的观察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茅于轼教授是坚定的市场主义者,但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他也是做慈善活动最早、最多的经济学家。从创立农村小额贷款,到创建富平家政学校,再到创办乐平基金会,无不彰显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爱心和同情心。他做慈善事业的口号是:赚穷人的钱,帮助穷人赚钱!赚穷人的钱意味着你必须满足穷人的需要,为穷人服务;帮助穷人赚钱意味着帮助他们成功,使穷人脱贫变富。
这本书是针对美国的背景写的,但对今天的中国具有更大的针对性。当今中国,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反市场的人总以道德高尚自居,使得大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更有市场。但观察表明,道德宣言不等于道德行为。凡是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高,道德水准就高;凡是不按照亚当·斯密的理念、不搞市场经济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较差,道德水准就比较低。比如中国和美国,就再显然不过。
理念决定现实。阿瑟·布鲁克斯《通往自由之路》一书,有助于澄清人们的一些认识误区,坚定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信心。我相信,这本书值得所有人一读。
(摘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