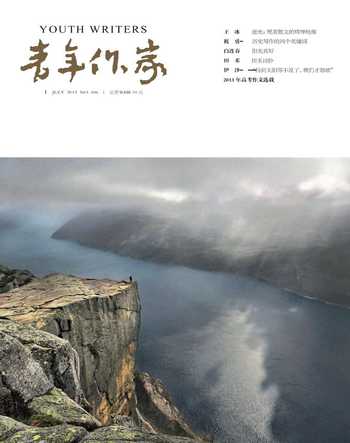祝勇印象
宁肯
最早听到“祝勇”的名字,我还在一家广告公司,与文学已多年无缘。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刚刚认识了苇岸,他让我重新认识了文学,我们开始交往,他到城里来我们见面,他有什么活动叫上我,其中一次是散文活动,苇岸提到了祝勇。那次活动在北大的蓝月亮酒吧,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人,主要是诗人、散文家,有几代人,可惜祝勇没来。我记得应该是1997年秋天,或稍晚一些,当时我觉得祝勇挺个性的,这么重要的活动居然不来!我的感觉上一直留有这么一直模糊的很难准确的印象。但印象就是这样,常常它是错觉的代名词,待真正见到祝勇,发现是个爽快而且如此年轻的帅哥,为人非常明朗,简直可以一鉴到底。
我喜欢这样的人,喜欢看上去一鉴到底但又有极其丰富层次的人,喜欢因为这些层次或深入这些层次,而越来越感到他实际上是个深不见底的人,甚至你会消失在这些迷人的层次中。有些人正相反,看上去满脸深刻,老成持重,深不可测,实际上拿竹杆试试,很浅;这且不说,还净是石头、泥,所谓深度不过是浑浊与多种霉。祝勇与此正相反,在他身上你不可能闻到霉味的东西,阴阳怪气的东西,云遮雾罩的东西,煞有介事、忧心忡忡、角色混乱的东西。祝勇是一个很敞开的人,在北京作协,祝勇、凸凹、华栋我们经常凑在一起,一到年终总结开会,晚上吃完饭,就互相找,聊聊,谈谈,有时徐小斌和林白也会加入进来,大家主要是聊文学,聊书,聊一些现象。总之,我们都是一些敞开的人,我们互相欣赏各自的敞开,而这其中祝勇是一个能够增这种敞开亮度的人。他总是去肯定,说,对,你说得太对了,就是这样。我特别爱祝勇这样说,因为我能感到他这样说时是洞悉了某种东西了的。实际上我们经常互相这样说,这也是我们常在一起的原因。我们也就争论,不可能没有,但即使是在表达异见时祝勇也是清晰的、明朗的、优雅的,一如他阐释的内容。
因为同为“新散文”写作者,我们有着更多的讨论。说起“新散文”,某种意义上说,祝勇对“新散文”在理论上的梳理与确立,功不可没。中国正经的文学流派不多,所谓“正经”是说有创作群、有理论、有自觉、有阵地、有影响,这方面朦胧诗堪称翘楚,散文界是“新散文”。“新散文”自1998年在《大家》正试登场,出现了一批迥异于传统散文的文本与作者;1999年《散文选刊》推出“新散文作品选”,配发了主持人语称:“作为一门古老手艺的革新分子,新散文的写作者们一开始就对传统散文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它的主要是表意和抒情的功能、它对所谓意义深度的谄媚、它整个生产过程及文本独立性的丧失,以及生产者全知全能的盲目自信,等等,无不被放置在一种温和而不失严厉的目光审视之下。”尽管有此精要的描述,并有文本,但当时并未产生新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直到2002年祝勇写出长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对“新散文”进行了阶段性总结,“新散文”才真正的风生水起,引起轩然大波,被历史正试确立。此文着眼于文体,列出了长度、虚构、审美、语感等四项指标,论证了“新散文”所不同于制度散文的特质。祝勇意气风发而又不乏理性地说:“纸上的叛乱终将发生,迟早有人要为此承担恶名。但是,对于一个健全的文学机制而言,背叛应是常态而非变态,因为只有背叛能使散文的版图呈现某种变化,而不至于像我家窗下的臭水沟一样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一个无比浅显的道理。散文叛徒们与‘断裂主义者的区别显而易见:后者的利刃斩断过去,而前者的道路通向未来。”
说如同国外的一些文学流派往往理论与创作集于一身,祝勇不仅是“新散文”理论的旗手,也是创作上的主将,他的长篇散文《旧宫殿》体量上堪称长篇小说,是“新散文”标志性的作品,亦是他自身理论上的实践。《旧宫殿》将长篇小说的结构、语感、话语方式、解构、戏仿、互文等诸后现代观念引入散文,其文本的反讽叙事与历史本身的严酷叙事构成了相互对照与指涉,既消解又批判,既颠覆又建构,突破了单向维度,其丰富多声部的形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对历史与现实的个人姿态。个人,是“新散文”的基点,变是必须的,但无论怎么变都不能离开这点,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是“新散文”的秘密,也是一切文学流派应有的秘密。祝勇深谙于此,这也是我们关系的基础。
祝勇的写作远不止“新散文”,他的写作涉及思想、学术、小说、评论、历史、艺术、旅行、电视——一出手就捧回一个“金鹰”奖。他现在的工作身份是“故宫学”学者,这是一个难描述的人,当祝勇嘱我写此文时,我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我长他十岁,他已著作等手,出版的书不下四五十本。得了“金鹰奖”后我曾担心他在电视领域走得太远,毁了自己——电视可毁了不了人,结果一个转身他又回到散文上。一次他跟我谈了一个想法,想写一个艺术系列的散文,用今人的文化视角比如写写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韩熙载夜宴图》,诸如此类,问我《十月》可否做个栏目,做上一年。我觉得太好了,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有时当编辑就是这样,朋友交到位了,好稿子自然来了。几乎当即拍板,并大加鼓励,果不出所料,读着这些“预设”文本,不仅对祝勇的担忧消失了,而且觉得这是祝勇新的起点,至少在散文创作上是里程碑式的作品。祝勇的许多“痕迹”都体现在这个系列里,小说的,思想的,“新散文”,学问的,历史的,甚至电视的,我感到惊异,感到祝勇在“整体”地浮现。于是有了《故宫的风花雪月》这个专栏。今年,有散文出版传统的东方出版社开始为祝勇整理和出版文集,《故宫的风花雪月》就是其中一部。祝勇依然是一鉴到底的清晰,然而他清晰的层次又是让人如此的迷失,难以把握。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深不可测,是敞开,而又没有尽头,我以为这才是一个作家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