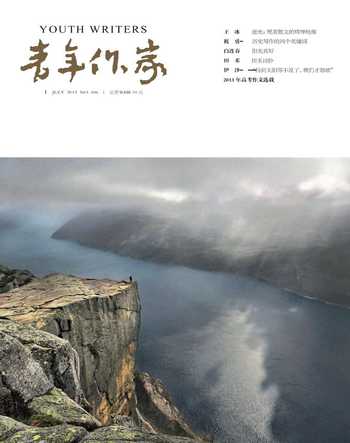“待到太阳等不及了,我们才怒放”(节录)
我被委以信任,因诗歌的
兴衰发展
至少我被委以的信任,是因它
衰亡的部分
——查尔斯·布考斯基
我与至今尚未谋面的美籍华裔人文学者刘耀中先生建立通信联系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起先是他在严力主编、纽约出版的《一行》诗刊上读到我的诗作后写信给我,他在信中称我为“中国的金斯堡”,令我青春的虚荣心得到巨大满足,写作上也备受鼓舞。他在后来的信中总要夹寄一份他发表于海外中文报刊介绍西方文学、哲学大师的文章复印件。他系统介绍的这些大师有我了解的,有我并不十分了解的,甚至还有我压根儿不知道的;最吸引我的还是他在评述这些大师时所动用的知识系统和丰富材料,是我在一般国内学者那里读不到的。刘耀中先生当时已是退休的年龄,而我大学毕业走进社会不久,我们靠通信建立起来的私人友谊真有点“忘年交”的味道在里头。介绍艾伦·金斯堡的那篇文章,是他在我的请求之下写的。他在该篇文章的结尾处还写道:“去年西安青年诗人伊沙来信说,他很感谢我寄给他的那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巴利迈尔斯著的金斯堡传记,他希望我写一些关于‘被打垮的一代的扫描及对金斯堡一生的介绍和评价,承蒙器重,特写此文以答谢!”
刘先生在信中提到的那部名叫“GINSBERG:A BIOGRAPHY”(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的金斯堡传记,是他在1994年寄赠与我的。这部英文原版书寄达之后所激发的是我妻子老G将它译为中文的兴趣与冲动。当时国内的出版社似乎正处于刚刚懂得必须掏钱购买版权而又普遍买不起的阶段,出版几乎无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老G开始翻译这本书,我的前同窗和当年在大学校园里活跃一时的前女诗人,深知金斯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很像是情话:“大不了我就当翻上一堆资料吧——供你私人使用的资料。”
第二年——即1995年,在刘耀中先生的一封来信中,他夹寄了一篇介绍美国诗人Charles Bukowski(查尔斯·布考斯基)的文章。这是我此前一无所知的一位诗人,但这篇文章却叫我没法不激动:因为文中所引他诗的片断,也因为他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和他的人生态度,甚至包括他在美国文化中的际遇和地位。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注定要和我有点关系的诗人,正如我在1986年初读金斯堡时的直觉一样。在我的急切要求下,刘耀中先生很快寄来了一本布考斯基出版于1981年的原版诗集PLAY THE PIANO DRUNK LIKE A PERCUSSION INSTRUMENT UNTIL THE FINGERS BEGIN TO BLEED A BIT ( BLACK SPARROW出版社)——这本宝贵的书是他在加州格伦底尔城的一家旧书店里购得并转送与我的,书的扉页上还留有上一位读者的阅读心得,他(或她)用英文写道:“我能说什么呢?大师……生日快乐1983”。
老G在看完这本原版诗集后对我说的话与当年顾城的姐姐在看到《今天》时对顾城说的话有点相似,她说:“他写你这种诗。”——正是这句话使我急切地想把布考斯基的诗变成中文,与妻子合译布考斯基的建议也正是由我在当时提出的。说干就干,那年7、8两月,我们共同翻译出布氏诗作24首,其中23首后来陆续刊发于《西藏文学》《女友》《倾斜》《中国诗歌》《诗参考》《葵》及台湾《创世纪》《双子星》、香港《前哨》等10余家海内外中文刊物——其中既有期发量两百万份的大众读物,也有非正式发行每期印数只有几百册的同仁诗刊——这便是布氏诗作在中文世界里的最早现身。也正是自那年起,我在中国当代的诗人圈中开始听到有人谈论“布考斯基”这个名字,并听到越来越多的赞誉之声,我知道由我和妻子老G一起提供的这个译本并没有辱没大师的名字。
接着是老G眼里只有她这个“作品”的漫漫七年。
七年中,我怀揣一份美国诗歌的地图,反复阅读着布考斯基。最终,我给了他“四星半上将”的军衔,而在我眼里,在此之上的“五星上将”也只有华尔特·惠特曼、T.S.艾略特、艾伦·金斯堡三人——如此评判势必会带入一个诗人在文化和历史语境中的作用与影响来考虑;而若回到一个诗人纯粹的写作内部,布考斯基就该被追授他没有得到的那半颗星。也就是说,那么在我眼里,布考斯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金斯堡出生于1926年,布考斯基出生于1920年,后者甚至比前者还大6岁。考虑到他们大体上属于一代人以及诗歌走向上的大体相近,我对前辈论家爱将他们放在一块比较的做法基本认同。布考斯基35岁开始写诗时,金斯堡已快爆得大名了。一个是写得晚,出道更晚;另一个则在勇敢地当了一把文化逆子的同时,也旋即成为时代的宠儿。金斯堡是随着一个大时代的到来应运而生的诗人;布考斯基则是一个天生的边缘诗人,与他所经历的任何时代似乎都格格不入。金斯堡一生中的大半时光,都是在世界最著名诗人的优越感中写作的;布考斯基则始终在一种大体不得志的落魄感中写完了自己的一生。《嗥》是金斯堡一生的顶峰,也是平生难越的一座高峰,他后来的写作都是在为如何超越自己而不断的努力中;布考斯基则属于渐入佳境的一种,极为多产,泥沙俱下,越写越好,貌似不经意,却暗藏智慧,他的巅峰十分自然地出现在他的晚年。
以下所述是我身为诗人更为隐秘的心得:金斯堡是“史诗”书写者、时代的代言人,他最为擅长或者说真正写得好的是《嗥》《美国》《卡第续》这类长诗或类长诗;他的短诗写得并不十分好,他的短诗都写得太“大”——我指的是他还是习惯动用“史诗”的架构和站在高处的语势来写。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那本《艾伦·金斯博格诗集》在得到时尚青年热买的同时,也让真正的诗人十分失望,这一方面有翻译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金斯堡的短诗远不具备你印象至深的《嗥》的水准。布考斯基则正好相反,他是日常的、边缘的、个体的,他没有也无意建树金斯堡《嗥》式的文化里程碑,他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自己人生片断和生活细节信手拈来的好功夫,使他成为短诗高手;他不是传统意义的短诗营建者(讲求精致的那种),恰恰40~80行的中等篇幅是他更能发挥才华的一个空间,他善于把篇幅意义上的“长诗”做“小”——我指的是往人性的细微处做去。在这个篇幅之内,在这个世界上,我尚未见到过比他更好的诗人。与布考斯基相比,我以为金斯堡写的是真正知识分子的诗歌,真正社会精英的诗歌——我加个“真正”是为使在中国被严重歪曲与异化的两个概念还其本义;而布氏本人则体现为一种真正的平民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的作品充满着美国平民生活的强烈质感并将诗中的个性表现推向极端。金斯堡诗歌的先锋性太过依赖于一个大时代的背景;布考斯基则是绵长的,他的先锋性即使对美国对整个西方诗歌而言,也一直绵延至今。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布考斯基对我同辈以及后辈诗人的影响。我把后来的译作在网上发布后,这种影响变得立竿见影。显然,布氏的影响已达中国年轻一代的诗人,已达中国诗歌的生力军,这种影响目前正在升温,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他更多的诗被译成中文,这种影响将变得愈加广泛和深入。这种影响的发生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在文化的压力(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和某种光环的笼罩(“诺贝尔奖”及其他)下获得的,诗人们喜欢他——一个酒鬼,一个糟老头——仅仅在于:他的诗实在太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