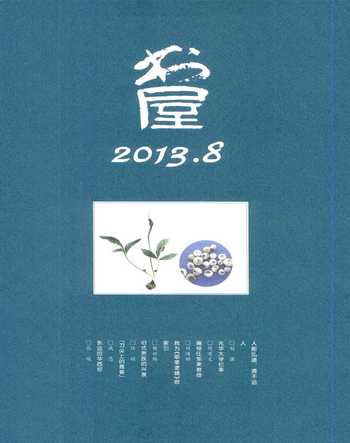四月不沉默
胡燕青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此,我没有格外兴奋的感觉。十多年来,我只在等待一个人拿这个奖,他就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 觟mer,1931— ,因为他的译名很长,下面有时简称“托马斯”)。去年我终于愿望成真,兴奋的感觉至今仍在,这种偏爱无疑是任性的。这几年来,我在香港浸大开设的新诗创作课,都以他的短诗做教材(主要教《黑色明信片》、《哀歌》和《四月与沉默》几首)。暑假前在校园碰见一个写作很不错的学生,他说已经借去香港所有大学和公共图书馆里的托马斯作品集,不自觉地迷上了这位瑞典老人。但是,把Transtr? 觟mer读成Transformer(“变形金刚”)的同学也大有人在,诗毕竟是小众的。
好些年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都是诺贝尔奖的头号大热门,赔率极低(竟然有很多人拿这个去赌——这世界无奇不有)。去年最热的反而不是他,而是叙利亚的阿多尼斯。诺奖公布那天,我七点正就凑到电视机前看新闻。果然,他成功了,我高兴得当场大叫起来。其实,他一直在“让赛”。1974年,瑞典学院把文学奖一次颁给两位瑞典作家,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让桂冠落在瑞典作家头上了,不免惹来闲言。可能为了避嫌,其后主办单位矫枉过正,从那时起一直没给瑞典人(甚至北欧人)颁发这个奖——三十七年来,这是第一次。
首次接触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是在1981年与《诗风》众学长一同编辑《世界现代诗粹》的时候,那时读到胡国贤转译的《轨道》,已经深受吸引。后来陆续读到董继平和李笠的翻译,又主动寻找英语的译本,发现这位诗人打动我的力度,甚至比爱尔兰的叶慈和意大利的蒙塔莱更厉害。但阅读英译之后,我也发现托马斯两位中译者似乎不完全明白托马斯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关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
因此,当我读到瑞典汉学大师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 )的中译,心里很兴奋,这当然也拜诺贝尔文学奖之赐。如果不是托马斯得奖,我肯定,愿意出版新译本的人不会出现。毕竟,奖项公布时连欧洲许多评论家都不大清楚这获奖人是谁,我估计托马斯的中国读者比欧洲读者更多。
马悦然老先生已经八十九岁,与托马斯相识接近五十年。他的中文甚好,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弟子,译本所见,古文固然难不倒他,平仄、格律,七言和五言诗的重音、断句,他都熟悉。最重要的是他认识托马斯,且是他的好朋友和知音。
《巨大的谜语》一书,包括托马斯最近的两本诗集The Great Enigma和Sad Gondola里面的诗。苏格兰诗人若彬·费尔顿(Robin Fulton)也出版托马斯作品英译,马悦然告诉我们,费尔顿的英译本是最好的。如果不是他提示,我们怎能在众多的英译本中找到最好的来读?马悦然也柔和地比较了他的译本和若彬·布莱(Robert Bly, 1926— , 美国诗人)的翻译,丰富了我的视野。马译本很轻巧,虽然是精装,但不重,可以带着上街,小小的三十二开,让人有手持珍宝的喜悦。
马悦然老先生是非常认真的译者,他的谦卑和对文学、学术的认真,更使人敬佩。他对翻译的看法,更让我感动非常。他说:“据我看,译者实际上应如奴隶一般工作。译者应该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和译文的读者负责任。”为此,他对托马斯诗歌里的重音和轻音做了深入的研究。托马斯模仿日本俳句写成的短诗,他也翻成5-7-5的俳句基本形式。俳句的十七个音节,在中文里本来不必执著,但能做的,马悦然都做了。即使是托马斯自己,以俳句形式创作时也没有完全按照日本人的传统来写(例如诗中没采用“季语”,如以“红叶”写秋天等),但马悦然却尽量在格式上努力。
1990年,托马斯中风,那时他只有五十九岁。中风后的他,失去了右手和语言能力,他是钢琴家,失去右手太痛苦了。瑞典作曲家就为他创作专门用左手弹奏的曲子,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马悦然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就为马演奏,这种情谊增强了诗人和译者之间不可多得的心领神会。1996年,托马斯出版了《悲伤的凤尾船》,里面有两首诗写他中风之后的感觉,其中一首,正是我常用来做教材的《四月和沉默》(April and Silence)。马悦然说,这是诗人“对他的命运的慷慨之叹”。这首短诗,凝练自然,意象精深而充满想象力,完全是托马斯的风格:
《四月和沉默》
荒凉的春日
像丝绒暗色的水沟
爬在我身旁
没有反射
唯一闪光的
是黄花
我的影子带我
像一个黑盒里的小提琴
我唯一要说的
在够不着的地方闪光
像当铺中的
银子
(马悦然译文)
这个作品是托马斯中风之后写的。北欧的春天迟来,但到了4月,总应该开始了。但是,触景伤情,尚未年老就中风的托马斯难免经历长时间低沉,无法借助语言和音乐表达心中的感情,对一般人来说尚且十分难受,何况是钢琴家诗人呢?“我的影子带我 / 像一个黑盒里的小提琴”,是一个两层的复杂的意象。“影子带我”一语,美国诗人布莱翻成“影子载我”(I am carried inside my own shadow),“像一个黑盒里的小提琴”,两种译文都透明地呈现出诗人的才华。“影子带我”是第一层的比喻,表示诗人无法脱离身体的牢笼。但是,天才的脑袋总是装载着多得无法尽用的隐喻。散文家如钱钟书,小说家如张爱玲,心里的喻象就源源不绝,托马斯当然也一样。“影子带我”仍嫌不足,就再来一个“像一个黑盒里的小提琴”。这种两层意象也是余光中常用的,例如他的短诗《蛛网》就是一例:“暮色是一只诡异的蜘蛛/蹑水而来袭/复足暗暗地起落/平静的海面却不见踪迹/也不知要向何处登陆/只知道一回顾/你我都已被擒/落进它吐不完的灰网去了。”蛛网固然是暮色的喻象,但暮色也是晚年的喻象。学生问我:“你怎么知道?”我说:“‘落进它吐不完的灰网去了中的‘灰网就是老人的白发。”同学听了大大惊叹。托马斯呢?连用两层比喻,意犹未尽,又再来另外一对:“我唯一要说的/在构不着的地方闪光/像当铺中的/银子。”说不出来的话,原来并非躲在远处,乃在眼前。刚好就在一臂之遥处(“构不着的地方”)逗引他,因为不远,所以追寻;“当铺”一词,同样是“构不着的地方”的喻上喻。“当铺”指出那里面的“银子”(布莱译成“家传银器”)本来是诗人自己的,如今近在咫尺,却无法赎回。马悦然先生指出这首诗和诗人中风两者之间的关系,对解读此诗非常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马悦然所译的另一托马斯著作《记忆看见我》。这本书于《巨大的谜语》半年后面世,是托马斯六十岁时所写的回忆录。书一开始,他就说:“‘我的一生,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看见前面一道光线。仔细看,那光线真像一颗有头有尾的彗星。彗星的头,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决定生命最重要特征的幼年。我努力回忆,努力钻进那时代。可是在这浓密的地区中移动很难,很危险,我感觉到我会接近死亡。再往后,彗星越来越稀疏,有越来越宽的尾巴。我现在处于尾巴的后端。我已六十岁了。”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一方面为其“魅力没法挡”的彗星之喻所吸引,一方面给清简自然的中文所震慑。这真的是老外的译笔吗?没多久书就读完了,那是因为马悦然实在译得好,我像在读一本小小的精彩的中文原著。托马斯写他的童年和少年——父母离婚,海员外公填补了父亲的位置。他母亲是教师。小小的托马斯记得的第一个感觉,是三岁时一种“骄傲”之感。但到了学龄,他因为没有父亲而被嘲笑,老师告诫同学不得因此欺负他,越帮越忙地把他推向更痛苦的处境。受强壮的同学欺凌,托马斯抵抗无效,“(我)终于想出一个叫他失望的方法:完全放松。他接近我的时候,我假装灵魂早就飞走了,只留下一具尸体,他可以随意拿一条没有生命的破布甩在地上,这很快就叫他厌烦了”。从一开始的“骄傲”之感到一条“没有生命的破布”,年幼的托马斯经历了自我形象的坠落,心灵渐渐变成诗人灵感的园圃,但这同时让他的心智暴露于危机之中。
少年时代的托马斯终于崩溃了。他患上了抑郁症和惊恐症,也许还在思觉失调的边沿上耽待了好久,“一种不发出光芒而发出黑暗的探照灯把握捕获”。整个冬天,他落入强大的恐惧之中,直到夏天的太阳再度升起。他说:“我的存在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疾病。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医院。”在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经历幻听、幻视。但他又说:“这也许是我最重要的经验。”这一章,在书里命名为《驱邪》。我们很难说这不是托马斯创作的启动器,以及他寻求亮光(他诗里相当重要的意象)的原动力。后来,他的集子中有几首写默想祷告的作品,都写得特别深刻。
马悦然为了让我们更了解托马斯的成长,把他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出版前的作品也翻译成中文,辑录在书后,并且加上解说。对我来说,这实在无量功德。如果不是他,我怎样才能读到那些分散发表于各文学刊物的作品呢?
老实说,《巨大的谜语》和《记忆看见我》两本书拿在手中,我实在欢喜得很。在我心目中,托马斯是当今世上最优秀诗人,他是瑞典人,他的国度遥远,语文文化都是我“够不着”的,幸好他有这位举世知名的汉学家朋友马悦然,以“奴隶”的谦卑为我们细细翻译。我终于能够读到托马斯的最佳中文译本,一步一步走近他的心灵了。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著,马悦然译:《巨大的谜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