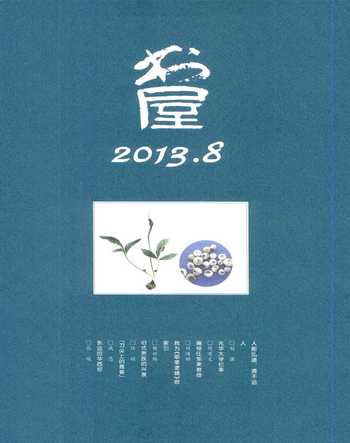闲话陋室和《陋室铭》
陈华东
烟波浩淼、汹涌澎湃的扬子江自西而东咆哮直下,过江西湖口后日益宽阔。在大江的西沿岸,有一座小有名声的历史文化古城,那就是刘禹锡笔下的“陋室”所在地——秦制历阳,古谓和州,今称之为和县,隶属于安徽省马鞍山市。而古县城所在地,至今称谓仍沿用古称的历阳。据《南畿志》载:“历阳本秦县,项羽封范增为历阳侯,即此。”除县城历阳镇外,还有两个名镇值得一提:一是乌江镇,因系叱咤风云大英雄西楚霸王项羽的魂归之处而闻名遐迩;一是裕溪口镇,因系长江航线大型货运口岸和淮南铁路终点而成为交通枢纽,而正缘于此且又与芜湖隔江相望,此镇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划归芜湖市管辖。
安徽和县是一座有着两千余年的古县城,堪为人文荟萃之地,惜因历朝历代时有发生的战火兵燹所扰,而使原本甚多的文化遗存累遭毁损。回首历数,保存至今的(当需数度修缮)尚有陋室、孔庙、霸王祠、镇淮楼、文昌塔、西梁山、鸡笼山和香泉等处名胜古迹。言及此,不由地顺势提上一句,1980年初冬,在和县龙潭洞考古时掘出一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后,此处即被定名为和县猿人遗址,1998年初,经国务院批准,“和县猿人”遗址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该说此一发现,确实为研究南北方古人类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以及探索长江流域广袤地区的文明进化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千百年来,源于陋室而有一篇自古流传至今的《陋室铭》,可谓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然《陋室铭》中所提及的陋室位于何地?现状又是如何?且如今世传之言又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安徽和县、河北定州和湖南常德之说,对此,恐非尽人皆知。另则,举凡读过《陋室铭》者,认为这是唐代思想家著名诗人刘禹锡(772—842)的名篇,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说提出了质疑,且其考证言之凿凿,有根有据,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意见相左的情况。缘于此,不才笔者亦意欲忝列己之浅见而泚笔作书,以作聆听这场讨论的入场券。至于为何将题目言之为“闲话”,乃因史料短缺、辨别乏力、考证不足而难以加以肯定判断是也。既然如此,撰写此文只求在引用几家之言后再附上几句不成熟的感言而已,故以如是之题而力求为之。
先说陋室。据史料所载,刘禹锡笔下的陋室坐落在安徽省和县城东的半边街,坐北朝南。当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刘禹锡二次遭贬领任和州刺史之时,当地官绅极力要为刘禹锡兴建豪华官邸,然被其断然谢绝,并赋诗一首以作警励:“比屋茕嫠辈,连年水旱并。遐思当后已,下令必先庚。”嗣后,只在官署后圃小山脚下建一简陋之室,自谦为“陋室”,以作起居、议事乃至行文论道之用。
因有“陋室”,继而有《陋室铭》这篇千古绝唱的文字问世,并于存世后不久,即唐文宗宝历年间,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因情所致而书之并勒石成碑,尔后惜因兵燹废圮,陋室及其碑文遂而无存。明正德十年(1515),时任知州黄公标扩建陋室,补书《陋室铭》碑文,并在园内建有多处小型亭阁,诸如“半月池”、“舞鹤轩”、“迎熏亭”、“万花谷”等,蔚为大观。后随岁月流逝而遗存下来的,则是清乾隆年间时任知州宋思仁重建的陋室三幢九间室。再后至民国六年亦即1917年,和州知事金梓材重修陋室,岭南金保福又在东侧建一碑亭,补书《陋室铭》碑文一方,后虽断但犹存。此外据传,刘禹锡在和州任内,不但撰写了千古名篇《陋室铭》,而且还留下了《历阳书事七十四韵》的长篇韵文。
在笔者童年时期的记忆中,当时的陋室未见开放,家乡百姓也就无缘前往瞻仰。日伪时期,陋室成了日寇的兵营;民国时期,陋室成为县党部所在地;而在解放后,和县公安局长期设在这里,直至改革开放初始之时方迁出。1985年,当地政府接受政协委员联名提出的议案,而由省、县拨款按原貌再度修葺陋室,以纪念刘禹锡这位旷世贤才的唐代清吏。至此,业经历朝历代多次修缮而保留至今的陋室,现已开辟为刘禹锡纪念馆,其主室正门门楣上的“陋室”两个大字是著名诗人臧克家题写的。迎面照壁上刻写的则是“政擢贤良,学通经史,颉韦颃白,卓哉刺史”十六个大字,其中的“韦”系指韦应物,“白”系指白居易,以此概括表达了后人对刘禹锡的崇高敬仰之情。主室正中塑有刘禹锡立像一尊,庄重肃穆,上悬一横匾,亦书有“政擢贤良”四个大字。1986年,和县陋室即被定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再说《陋室铭》。一旦提起这篇脍炙人口的铭文,不得不对过往历史作出一点简要回顾。唐顺宗永贞年间,时任户部侍郎的王叔文及其搭档王伾,联合了时称“刘柳”的刘禹锡(时任监察御史)和柳宗元(时任礼部员外郎)等八人,在刚刚继位的唐顺宗的大力支持下,对政治启动变革,即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的现状,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即史称的“永贞革新”,颇得民心。然而可悲的是,历史上举凡力主改革变法者,如用现今的话语来说,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不到一百五十天的“永贞革新”之举,终因唐顺宗逊位而夭折了。至此,王叔文被赐死,王伾亦在遭贬后染疾身亡,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同样遭贬而到边远地区担任司马,成为“逐臣”。这就是史称的、广为人知的“二王八司马事件”。随后二十年间,刘禹锡几经辗转,在多处担任刺史之类的官职,再无昔日的辉煌。如前所述,直至唐穆宗长庆四年,刘禹锡出任和州刺史,世上遂有如此这般的陋室,以及随之而问世的千古绝唱《陋室铭》。
理应思忖的是,面对亦诗亦画的陋室,岂能没有文字加以优美赞许而让后人到此访古时为之探幽欤?于是乎,陋室主人刘禹锡撰写了《陋室铭》,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这篇格调清新、明快简约、超凡脱俗、意境深远之华章。试问,“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廉青”和“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之句,难道不是主人钟情于陋室而发自内心的真实写照?!对于这篇简短的散文,后人一致认为,此文乃系作者以借物明志的表现手法,从而表达他那不追名逐利和坚守节操的高尚情怀,以及不求闻达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调为其旨趣的。
但是,《陋室铭》是否出自刘禹锡之手?溯千年而至今,却另有一说。
所谓陋室之谓,一般地说,不是专指而是泛称,任何时何地,即便是豪宅,主人亦可谦称为陋室。如若由此着眼,称之为陋室者可谓多矣哉。缘于此,有心之人当从古籍中仔细稽考对比后,势必会提出一个问题:刘禹锡建于安徽和县的“陋室”是否就是《陋室铭》中所描述的“陋室”?或者说,《陋室铭》是否为刘禹锡亲撰抑或他人之作?前文已提到,千百年来,当民间将刘禹锡和《陋室铭》早已联系在一起之时,学术界有识之士却能对此定论提出质疑以期谋求真相。应该说,这是彰显学术自由争论的一个可喜现象,理当值得称道的。
由此,笔者即饶有兴趣地研读了几篇针对《陋室铭》作者提出质疑的文章,同时又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一经综合后而深感将所接触到某些少量而又散见的不同看法加以罗列归纳,尽管涉及面不大,亦恐不失为一件有意义之事耳。有鉴于此,故而为之。
其一,北宋真宗年间高僧释智圆,生前曾有专著《闲居编》五十一卷于生后仁宗年间刊行而存世。在论及《陋室铭》时,著者认为,以仙、龙自比,有狂妄之嫌,不符刘禹锡行文风范,故而谓之曰:“俗传《陋室铭》谓刘禹锡所作,谬矣……”。如此一说,恐系对《陋室铭》作者提出质疑的最早声音。对此论断,笔者因缺乏相应史籍资讯而难以佐证,当姑妄信之。不过有一点,举凡读过《陋室铭》者,似乎看不出作者在文中隐含自比仙、龙之喻。诚然,愚此一谫陋之议,亦恐谬误之言。
其二,经查阅得知,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的《文苑英华》、清嘉庆十三年(1808)开始辑纂的《全唐文》,以及清同治年间朱澄《结一庐剩余丛书·刘宾客文集》等著名相关史籍,确实均未收录《陋室铭》。但有研究者就此著文称,当刘禹锡为母守丧返居洛阳时其婿崔生索文,曾取其四分之一为集略,时有可能未将《陋室铭》选入;旋即又称,《刘梦得文集》原三十卷,《外集》十卷,宋初散失十卷(顺便插上一句,宋刊本《刘梦得文集》仅存的第一卷至第四卷共四卷,现藏北京图书馆),源于此,当不排除《陋室铭》在散佚之列的可能性。
其三,多少年来,不管是教科书抑或评述文章,但凡提及《陋室铭》时,无不认为这是刘禹锡的一篇传世佳作,对此,无需一一列举。然代代相传的古籍中载有《陋室铭》者,却仅见于《古文观止》,其他重印的相关古籍(包括《刘梦得文集》)亦从未见其收录。但据笔者所知,也有例外,比如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配画古文名篇赏析》一书,在其收录《陋室铭》一文的简介中,其首句则以肯定的口吻写道:“选自《刘梦得文集》。”这是此书编者的笔误抑或经考证而得到的认定,笔者就不得而知了。顺便说一句,简介中还说刘禹锡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那就显然有误了。
其四,笔者最早接触质疑《陋室铭》作者的是初中同窗呼安泰写于十年前的一篇文章,题为《刘禹锡与〈陋室铭〉》,文中某段曾作如是阐述:“首先,《陋室铭》这篇散文,千余年来,仅见于《古文观止》,连刘禹锡自编的《刘梦得文集》中也未选入;再者,刘多次召集‘和州父老于‘陋室议事堂,共商抗灾大计,岂能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句呢?作为立志革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刘禹锡,其一贯思想表现与《陋室铭》中所流露的消极、颓废情绪,毫无相同之处。”当时笔者读到此段时,觉得呼兄之言颇具参考价值,但存有两则疑点,一是《刘梦得文集》或称《刘宾客文集》及其“外集”虽未收录《陋室铭》,但不能仅凭这一点而否定刘是该文的作者,似应作进一步征信印证,以求确凿无误才是;二是不管《刘梦得文集》是刘的自编抑或后人编纂传世,一时疏漏亦乃自古至今在所难免之现象。三是呼文所说的《陋室铭》流露出来的只是“消极、颓废情绪”的看法,而这样独具别意的看法,似乎与学界的共识大相径庭。
其五,南京一位专门研究刘禹锡的大学教授曾对《陋室铭》一文本身进行剖析,认为通篇缺乏逻辑,拼凑成文。这位资深学者以《陋室铭》开篇两句作为例举,认为违反常理,岂有仙居矮山龙游浅水之理?一经比对,此议则与释智圆之说如出一辙。仅此一点,足以表明了这位专家否定了刘禹锡是《陋室铭》作者之说。然众之所识,其开篇两句,乃行文时常用的排比法,即乃一种形象的比喻,放在文首,颇具点龙画睛之效。这位学者仅从生活常理出发而予以否定,恐有失之偏颇之嫌。
其六,青年学者段塔丽在《〈陋室铭〉作者辨析》(《文史知识》1996年第六期)一文中曾侃侃言道:“由于《古文观止》选编者审核不精,漏收或误收古人作品,以及所收文章与作者名不副实等情况更是不乏其例,而将《陋室铭》一文题名刘禹锡所作,就是其中一典型例证。”为了印证此一结论,作者在此文中列出三大理由。如将其简略,则可概括为:一是当刘禹锡贬任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时,曾撰《竹枝词》十余篇,《旧唐书》本传中有所提及,但并未提及《陋室铭》,而《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则称朗州风俗陋甚,这就与《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之“陋”的含义大相径庭。二是遭贬后的刘禹锡常靠文字来渲泄因政治上的失意而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与郁闷,这是他在朗州写下十多篇《竹枝词》的主要原因和动机之所在,而这与《陋室铭》一文中所抒发的豁达乐观的高雅情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三是遭贬之官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可能纵情地与鸿儒“谈笑”而与当地官吏随意“往来”,焉能有《陋室铭》这样的文字问世呢?既然否定了刘禹锡是《陋室铭》的作者,故在文章结尾,段君经仔细研读两《唐书》后而认定《陋室铭》的作者乃是唐文学史上不见经传的崔沔。纵观段君此篇佳作全文,可谓依之有据,言之有理,但其出发点则是将所谓的“陋室”认定在朗州了(有湘籍作家专文对此论证,此处就不引用了)。殊不知,刘禹锡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先贬连州后又贬任朗州司马。回京一段时日后又二度遭贬,当赴任和州刺史时,已是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相隔十八年,处境有所变化。如果朗州不是“陋室”的所在地,那么辨析《陋室铭》是否为刘禹锡之作则要从另一个方向去探索论证了。
其七,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在《〈陋室铭〉作者质疑》(《文学遗产》1996年第六期)一文中写道:“据《新唐书》卷一二九《崔沔传》,谓《陋室铭》乃崔沔所作。今按《崔沔传》篇末云:‘沔俭约自持,禄廪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该文随后又云,“崔之生平及作《陋室铭》事,始见于颜真卿所撰《崔孝公陋室铭记》……接下来便细写崔氏撰《陋室铭》及刻石经过:‘为常侍时,著《陋室铭》以自慰。……。”经查阅,1921年商务版《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崔沔小传(亦源自《新唐书》)对此采信而有同样记载。吴老在该文中又接着写道:“我们说此《铭》为刘禹锡所作固无确据,即使说是崔沔所作,亦不免有启人疑窦之处也。”且又认为:“总之,鄙意以为,今所见《陋室铭》实不类唐人作品。如确信其为唐人手笔,则宁信其作者为崔沔,亦不宜属之刘禹锡。”此一结语,展现了吴老治学严谨的风范。对此,窃以为,既然《崔沔传》与《崔孝公陋室铭记》均提及了崔沔撰写《陋室铭》,那么仅仅八十一字的全文理当顺势引用并予以评介才是。据崔沔、刘禹锡年谱,崔早刘九十九年,果能如此,一经引用,《陋室铭》到底为何人所撰之问就有定论而不会引发歧义了。
综上所述,从明正德十年扩建陋室并补书《陋室铭》碑文,乾隆年间重建陋室,乃至民国六年重修陋室且又补书《陋室铭》碑文一方等史籍记载来看,依愚之浅见,《陋室铭》所论及的“陋室”的确切所在地,和县之说,似应予以采信。而若此一采信得到确凿证实的话,那么撰写《陋室铭》的作者,仍应是刘禹锡而不是早他一百年的崔沔。当然,这还是一家之言。应该说,在尚无确凿的考证而能作出足使诸家均能接受的定论之前,仍属悬案,故其尘埃落定之期望,恐尚待时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