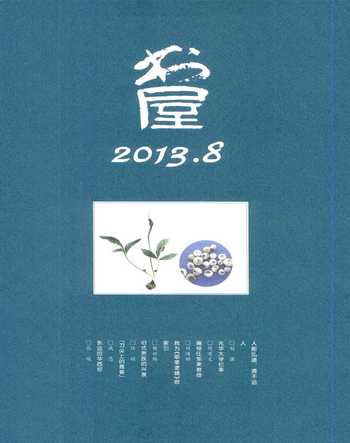“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张宝明
公元前479年,也就是鲁哀公十六年,孔子辞世……鲍鹏山在《孔子传》行将收笔时将其传主比喻为“千秋木铎”,并以夫子“自道”的口吻对“无道也久”的社会发出预言:“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侑》)言简意赅,在中国这块广袤无垠的罗盘上,夫子毕其一生、不舍昼夜,为我们华夏历史文化勘定出了美轮美奂的思想磁场。从此,一代又一代后学朝圣的故事一直在路上。如果说一部西方文明史是对柏拉图注解的历史,那么作为东方文明史东道的我们也不能不是对孔子注解的历史。中外古今,元典从来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逾越的祭碑。无论我们走多远,我们都会时时回眸凝望:毕竟,我们在回答要到哪里去之前必先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当下,传承与创新的命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究竟该传承什么?失去那余音袅袅的“木铎”,我们不但无法确证自己是谁,而且也难以找到回家的路。
沿着鲍鹏山的笔墨,孔子重新向我们走来。尽管沧桑、坎坷、颠簸甚至流离之路曾经让我们在千年风雨中惨淡曲折,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回归正途、直趋灯塔的还是孔子那振“道”发“义”的“木铎”。在技术、专业、信息满天飞舞的今天,也只有“木铎”才能点燃岌岌复岌岌之人文薪火的火种:走上“道”,再出发。在没有想好路怎走之前,这时的“道”比“路”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传承和复兴的地位绝对不亚于创新和开拓。因为一旦失“道”于人,人再将“路”走歪,代价将沉重而惨痛。这,历史一次又一次地给出了残酷的证明。好在我们唇枪舌战,为“大学精神”争来争去之时,鲍鹏山携着孔子来了。阅读《孔子传》,它至少省却了我们在浩如烟海之经典中打捞“大学何大之有”的定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几千年前的孔子早就想到了,而且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大学三项功能之前重点加上了以“道”为中心的“文化”传承。鲍鹏山跟着夫子的“木铎”振动出了几圈晕轮:“大学学习的目的,是要弘扬一个人伟大高尚的德行。”“大学”是指一种学问。这种学问的目的,简言之就是“学大”,学着让人大起来:
简单地说,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就是君子之学。它不是培养人的专业技能,甚至也不是灌输一些静态知识,它立足于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让人学会对世界上纷纭复杂的事物做判断,同时培养人的高贵品格和气质,养成人的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成人;不是为了一己谋生,而是要为天下人谋生,谋天下太平,争人类福祉!可见,“大学”的内涵,至少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对于技术的学习,而是提高德行,是养成人格,然后改造社会,这是大学的最根本含义。
毋庸讳言,在经典和注解之间,难免产生张力。这种张力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存在,这可以说时时有、事事有、人人有。张力,如果不是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必要的张力”。问题是我们的注解如何在回归的前提下缓解、化解甚至消解这一紧张。乍读这本书,如果不与其“天时地利人和”,那就不只是张力的问题,至少部分的大学校长就会把它当成胡言乱语甚至疯人疯语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理解的鲍先生“木铎”声中的“不是”判断并不是不需要,而是要先声夺人,一再强调“道”的独一无二地位。笔者以为,在还原经典却无法无缝对接的情形下,我们至少可以不是“只为了”。比如大学不是不需要“培养人的专业技能”,也不是不考虑就业,但那并不是唯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要铭记的是:价值比知识更重要,品质比技能更重要,“成人”比专业更重要,一言以蔽之,前面有一“道”风景线无法逾越。
孔子有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论语》)纵观孔子的一生,横竖都将探究宇宙人生的大道作为自己一意孤行的使命,始终将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作为臻于至善的人生目标。他既没有迷官(场)丧志,也没有玩(器)物失志。“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出了其出“道”早,将一生奉献给学问、真理的少年大志,“志于学”即是“志于道”的开始。在一个现在大多数少男少女争相“卖萌”的时代,这样的立志打破了“道之不传久矣”的局面。从其对弟子子夏关于“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的谆谆教诲中,我们便能领略其担当道义、心系天下、志存高远的公共知识分子情怀。在齐、鲁、卫、陈、楚诸国并立的年代,他没有流于某一国,也没有滞留于某一地,更没有投于某一人,他的道一以贯之,无论何时何地,都以情怀布“道”,“天下为公”的大同信念在牢牢存储在了孔老夫子随身携带的移动硬盘里,物化在振聋发聩的“木铎”里。
在夫子那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与生俱来,如同充盈着暖意和爱意的太阳,尽管云层可能不时遮挡住其光辉,但其光彩照人的放射却不舍昼夜。道义的担当从来如此:不但心中有道,还要乐于布道。谁都知道,心中有道是第一步,行走在布道的路上是第二步,可这第三部也是最难的一步则是如何在泥泞荒蛮、荆棘塞途的崎岖险径中一直走下去。更何况,他不只是流萤相伴,他要经常要在沿途的歧路中回答那些对自己膜拜有加的弟子们的质询。如果是一位厌世、避世的隐者也就罢了,弟子们恰恰跟的是避地、避国、避人却不避世的大道担当者!风正劲,夜正冷,路在何方?老夫子周边的小夫子的接踵而来追问也是充满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老师,“君子亦有穷乎?”“君子亦有穷乎?”这里的“穷”,不仅仅局限于金钱上的穷困,更多指的是人生挫折、事业坎坷与政治上的穷途末路。这句话翻译成白话:老师啊,您不是常说我们这些沿着崎岖陡峭山路担当大道、寻求真理的人会达到辉煌顶点吗?为什么我们在世间还会如此困厄而一筹莫展呢?
平时我们看到的性格直率、心中充满阳光的学生子路这次提问非同凡响。可以说是一次最有问题意识的发言,真正代表了孔老先生得意门生的水平。因为子路之问问出了一个千年秘密,也是中国几千年哲学史上、伦理学史上的一个大命题:一个人既然按照至高的道德准则去行事,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为什么回答总是否定的?是啊,弟子们可以问这问那,甚至问一些鬼神之类的看似刁钻的问题,那些提问并不难回答,但“君子亦有穷乎”这问题恰恰戳到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囧处。我不好推断孔老师当时有没有有辱尊严的情绪反应。要知道,今天摊上这样的直逼人心的富有挑战性问题,老师们大抵是要一句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乎?”你小子是不是觉得跟导师跟错了,从现在开始,你我不是师生,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历史有据,夫子淡定,再淡定,最后还是淡定!当子路一肚子带着怨气去质问老师时,老师却一副气清神定的姿态:“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回答的简单明了、意味深长。其含蓄的底蕴被几千年后怀抱原典的鲍子悟道并一语道破:“君子本来就应该是常常走投无路的。”不,准确地说,鲍鹏山不是一语道破,这里还有更为精彩的阐释与言说:
道德并不能保证道德之人人生顺遂。希望通过实行道德来保障自己顺遂,更不是人的最高境界。
如果你认为做个君子处处都能够够行得通,到处都能受欢迎,那我告诉你,错了。恰恰相反,君子正因为他讲道德、讲原则,他追求进取却又有所不为,所以他常常是被制肘的,时时是被雍阻的,往往是行不通的。”
在这两段对孔子悲观而又崇高的注解中,让人至少让笔者悲喜交加。在前一段,我不禁想到“五四”时期批孔先驱陈独秀的话:“道德不是用来责人的,而是用来律己的。”这些的确是对道德极其透彻的理解。而后一段话,我想起了新儒家冯友兰的一句话,中国哲学就是“接着说”和“如何说”的问题。对鲍鹏山而言,他显然接住了这样一个大命题,而且将孔子当时欲言又止、想说而又没有说完的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年的孔子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的呢还是要把这个话题故意甩给诸如像鲍鹏山这样的夫子?毋庸讳言,我本人同意鲍鹏山的“半醉”:“君子以成人为最高追求,小人往往不择手段地去追求成功。君子当然也追求成功,但是,君子在追求成功的时候不以人格的丧失作为代价,在成功和成人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一定选择首先保有人格尊严。而小人正相反。”这话我还有另一半:乱世和宁世截然两端。一心寻求公平、正义和大同理想的孔子啊,不正是想通过他和弟子们努力让“乱世狗”成为过去吗?他老人家清楚:未来的安康社会,“宁世人”必将以道德准则、法律规范行事,那时的世界才真正变成了我们一再期盼的美好人间。这一点,也是作者在《自由与道德》一节中点破的那样:“真正的道德人格一定是自由的人格;真正的道德人生是自由的人生;真正的道德社会一定是自由的社会。孔子,以其一生的修行,告诉了我们道德与自由的这种关系。到达这种境界的人是宽松的、从容的、愉悦的、自由的,又是合乎道德的、体面的。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和道德的结合。”及此,也许,子路及其同学的问题不言自明矣!
“君子固穷!”孔子的淡定回答,不止说他老人家已经在回答之前习惯性地捋好了思路,而是说他对道义担当、寻真求理过程中人在囧途的凄凉、惨淡乃至迷茫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满载一车的星辉,义无反顾地走在寻求希望之光的旅途上,渐行渐远,因为他心中有梦。这个梦不是鲁国梦,也不是齐国梦,也不是卫国梦,而是行大道的中国梦、世界梦、天下梦。仰望天空,那“梦”在孔子的心中是星星,是月亮,更是太阳,这个梦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稍不如意而掉头回传,也不会在大祸临头也时“斯滥”!这样说,从孔子一路风尘后的彼时彼景中可以证实。在“仁者担当”一节,鲍鹏山这样描述孔老师及其弟子在陈、蔡两国之间陷入孤境、穷困潦倒的尴尬情形:两国大夫们围追堵截,将一批匡世济民、理想远大、仁慈博爱、德行高尚之有担当、有追求、有信仰的布经传道“君子”队员团团围住,一心传(大)道、布(圣)经的师徒一行陷入了千年之迫、万年至窘之中。我想子路此时的一肚子的怨气很有代表性,号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圣人被弄得灰头土脸,竟然落魄到斯文扫地的这步田地,何至于此啊!正是在这个关节上,孔子抚琴吟唱:“君子固穷!”这可能是自古及今无人能比的“中国好声音”。如果此道不是一以贯之,这一“声”就难以让人信服,更难以让叫“好”经久不衰、延绵千年。
“志于学”,乐以忘忧;“志于道”,不知老之将至。将“学”与“道”统一起来并作为毕生的追求,孔子用一生的坚守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这个统一不但改变了中国文化史,而且改变了包括政治史的整个社会系统。学统、道统、政统,在孔子“志于学”的影响下开始分离,出现了一批带有公共知识分子性质的士大夫,这比西方早了几千年。学术独立是第一步,这一步开启了一个独立的职业,不再依附于政治;“君子不器”是第二步,这一步又有进一步的分离,它将以学术为职业的“稻粱谋”士人与道义担当的士大夫区别开来,开启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先河。学问与道德、知识含量的多少与人文关怀的高低从来没有必然的关联。一个化学家或物理学家可能只埋头生产化学武器或核武器,而且追求的目标是杀伤力越大愈好,这样,他可是一个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专家,与孔子所说的为谁的“道”是两码事情;民国时期的王闿运可以是一代学问宗师,但他为袁世凯称帝写的颂歌则是金钱作祟。这里的知识、学问与人文、道德构成巨大反差。回眸历史,我们有怎么能不平添几分对夫子的敬仰?
先人已逝,逝者如斯。孔子临终前唱出的最后一首歌还在这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死了,子孙还在,绝学不绝。我想,无论是对过去的“先人”还是对当下的“来者”,借用《孔子传》的精神:理解比崇拜更重要,同情比仰慕更需要,因为古往今来的圣者都曾活在“当下”过,寂寞圣哲之间的对话从来都是穿越时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