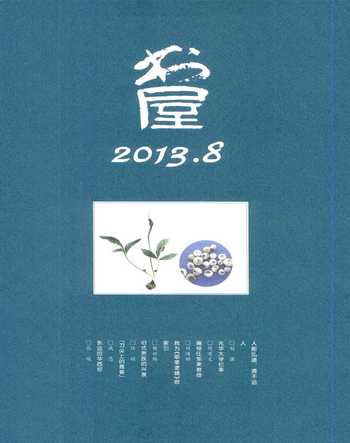“秀才遇到兵”、 “一适之妙”与 “诗穷而后工”
刘克敌
一
1929年7月24日下午,陈寅恪与赵万里欲去景山故宫博物院分院查看陈列之清帝画像。当时他们均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且佩戴有该院的徽章,理应可以出入,不料却遭到守卫士兵的阻拦,用陈寅恪书信中原话就是“大声呵止,形色狰恶”。虽然两人据理力争,仍然被拒之门外,甚至要动手殴打两人。后经博物院职员出面,陈寅恪才得以入内,但其徽章却被该士兵撕烂。为此,陈寅恪向傅斯年写信让他要求有关方面严惩该士兵,并应傅斯年的要求以史语所的名义写信给故宫博物院,要求将该名士兵开除。不过最后处理结果如何,现存书信中没有下文。
可以想见,此事对陈寅恪刺激较大,且不说作为知名学者教授他不该受到如此粗暴对待,即便是普通人也不应如此罢,这就应了那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老话了。无独有偶,鲁迅当年在途经香港时也曾遭到海关检查人员的无理搜查,他随身携带的书箱被翻得一塌糊涂。更令鲁迅气愤的,是船上的茶房将这野蛮的检查归咎于鲁迅,说鲁迅太瘦了,所以他们怀疑鲁迅是贩鸦片的。而鲁迅对此也无可奈何,也只有事后写一篇杂文发发牢骚而已。而且,这样的事似乎不只中国文人遇到,法国大文豪卢梭的文章写得很漂亮,但他却不善言辞。一次他经过一个小镇,受到一个市民十分粗鲁的羞辱,并且引来很多人围观。粗鲁市民的亢奋让围观者兴高采烈,他们毫无例外地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着卢梭受到羞辱。卢梭当时极为难堪,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反驳,只好逃之夭夭。更让他难过的是,当他想出足以反驳对方的话语时,他离开这个小镇已经很远。
但假如我们处于他们的情境中,又能怎么办?是的,你可以愤怒,可以体会到那种刺痛你尊严、伤害你人格的羞辱感,只是你没有办法反抗:不仅因为它很快就消失,不仅因为你无法用语言为自己辩解,而且因为新的羞辱和烦恼又一次产生。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会一直在意这样的羞辱,因为它太短暂太平淡也太频繁。对于很多人而言,这只不过是在其无聊和单调的生活中激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只不过是像被蚊虫叮咬一口那样短暂的疼痛。在我们内心深处,几乎感觉不到它曾经发生过,因为太多次这样的羞辱已经让我们麻木。当然,也许它不会完全消失,如果你真是对这样的羞辱特别敏感的话。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对所有这样的羞辱都敏感都在意都无法忍受,我们又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是苟活,而是像一个“人”一样的活下去。
可是,陈寅恪、鲁迅和卢梭不能!他们的疼痛不会消失,因为他知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疼痛,而且是全人类的疼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伤害他侮辱他的那些人。诚如鲁迅评价宝玉所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贾宝玉的悲凉,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的不幸与死亡。而陈寅恪等人的感慨,也正如此。他知道肉体的死亡诚然令人悲伤,而精神的麻木愚昧更加可怕。
二
陈寅恪喜读书自不待言,而且对“误书”有自己的见解。1929年10月3日,在他致傅斯年信中曾用此典故:“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诸人索取可乎?‘求之与抑与之与纵有误读,亦有邢子才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之妙也。”“误书”一词出自《北齐书·邢卲传》:“有书甚多,而不甚讐校。见人校书,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且误书思之,更是一适。”这里陈寅恪不仅仅是展示出自己幽默的一面,也由此看出他对伪、错之材料的态度。其实,早在留学海外时,陈寅恪就开始运用新方法,从新的角度处理常见甚至伪旧材料以锻炼思路、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如针对别人提出的为何要读老而旧的英语语法书的疑问,他的回答是:正因为它老才读。又陈寅恪曾经指出:“尝谓世间往往又一类学说,以历史语言学论,固为谬妄,而以哲学思想论,未始非进步者。如易非卜筮象数之书,王辅嗣程伊川之注传,虽与易之本义不符,然为一种哲学思想之书,或竟胜于正确之训诂。”
1935年,在给学生讲“晋至唐史”第一课时,陈寅恪为说明该课要旨,也曾专门讲到怎样对待旧材料与新材料及二者关系的问题:“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要戒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更有进者,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古人的言论和行事。……言,如诗文等,研究其为什么发此言,与当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事,即行,行动,研究其行动与当时制度的关系。”
1953年陈寅恪曾以《周礼》为例,再次指出怎样对待旧材料的问题:“《周礼》中可分为两类:一,编撰时所保存之真旧材料,可取金文及诗书比证。二,编撰者之理想,可取其同时之文字比证。”
综合陈寅恪上述观点,可看出他认为所谓新与旧、真与假都是相对的、互相可以转变的。旧的或假的材料并非全无价值,关键在于研究者取何种角度。其次旧材料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新材料,但当时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假材料若确之其假,则已经成为真的“假材料”,有其特殊的利用价值。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代表了那时的水平,反映了那一时代之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这些对今人仍然有借鉴意义和利用价值。最后,即便这些材料前人虽已用过,但材料本身往往具有多个层次,或从不同角度看即有不同的内在价值,可以进一步挖掘。在学术史上,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而陈寅恪自己更是在扩大材料的使用范围及巧妙运用旧、假材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范例。
三
“诗穷而后工”是历代文人一直信奉的格言,与“大凡物不平则鸣”一起,差不多成为分析文人何以能在困窘中发奋创作的最好解释。自然,不能不提及的还有司马迁那段足以流芳千古的名言:“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如果说历代文人还有什么可以为自己的困窘生活辩解的话,也许就是这些理由了。遗憾的是,很多文人忘记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其实还说过一段:“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养活,还要奢谈什么仁义道德,岂不羞耻?
所以当我从陈寅恪书信中读到文人的另一面,即他们对舒适的生活条件和安逸的创作研究环境之向往时,就真切感到了陈寅恪的坦承与可爱。1942年,处于颠沛流离状态中的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愿望:“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做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对此,今人钱文忠认为,这实际上与陈寅恪的一个重要思想有关,就是说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不是嘴上喊喊、手上挥挥的标语口号。钱文忠为此举陈寅恪1919年与吴宓的一段对话作为补充说明:“陈君又谓‘……我侪虽事学问,而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做官以及作教员等,绝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据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所记,抗战时他在昆明期间,应邀写其那部著名的《国史大纲》。为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钱穆的友人为其在郊区一座寺庙觅得一个住处,那里山清水秀,人迹罕至。钱穆到后十分满意,竟然一住就是数月,期间除了偶尔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基本上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后来陈寅恪等人去看望他,虽然也对此地风景秀丽表示艳羡,但陈寅恪却说如果让他长期生活在此地,他非发疯不可。看来陈寅恪虽然学富五车,倒不是耐得住寒窗寂寞之人。而学术研究是否能有成就,虽然和环境有关,但最重要的显然还在个人努力。
如果说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那么是否创作就不一定如此呢?老托尔斯泰的生活条件在他那个时代应该是足够舒服,但老先生却还是能写出一部又一部的经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真正是在困窘中写出其杰作的,这说明日常生活状况确实影响作家的写作,但只要作家还能有机会和有能力写,是否写得出杰作其实和其生活环境没有太多关系。写到这里,其实可以说鲁迅就是陈寅恪的同道。他在《碰壁之后》中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哪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来诉痛苦的。”1927年后,鲁迅移居上海,与许广平的结合以及孩子的出世,让鲁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鲁迅书信和日记中,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对这样生活的满足。在其日记书信中,有很多关于鲁迅对稳定舒适生活的描述以及鲁迅对这种生活的迷恋。例如鲁迅对请客的讲究——如果没有好馆子,宁可不请客。对看电影的迷恋——每年竟然可以看数十次之多,每次一定要买最好的座位,而且要全家人坐汽车去……
然而,对舒适日常生活的向往,是否影响鲁迅、陈寅恪等大师的伟大?是否影响他们为那些生活在黑暗之中人们所发出的启迪和呐喊?是否可以因此责备他们有些虚伪?似乎不能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