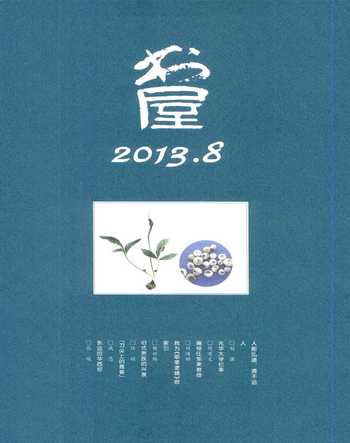日本书纪(二)
潘德宝
明治汉学者
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学者たち》,1998;《明治の青春》(续明治の漢学者たち),2009,东京:研文出版。
町田三郎《明治时期的汉学者们》及其续篇《明治的青春》大多以汉学者为中心展开论述。日本研究汉学者的著作其实颇多,如吉川幸次郎编著的《东洋学的创始者们》(讲谈社,1976)、礪波護和藤井讓治编著的《京大东洋学百年》(京都大学出版会,2002)、陶德民《明治汉学者与中国》(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等。其中《京大东洋学百年》多为名家论名家,如我最感兴趣的是兴膳宏论吉川幸次郎,犹如杜甫写李白,实在令人心动;陶德民教授则讨论重野安绎、西村天囚、内藤湖南三人的中国观,颇多新见史料,论述引人入胜。因为这些著作中部分论文已经翻译成中文,读者自可查阅。另外,李庆教授《日本汉学史》对汉学家的介绍相当完备,该书出版以来,已经取代了同类研究。
相比之下,町田三郎这两种著作,在规模和视野上并没有特别之处,不过,作者的关注点倒是值得介绍。《明治时期的汉学者们》(本书大陆尚未有中译本)一书首篇《明治汉学备忘录》一文,将明治时期四十余年的汉学分为四期,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重心:第一期从明治元年到明治十年,主要表现为汉学的衰退与启蒙思想兴盛;第二期为明治十年初到明治二十二、三年间,主要为帝国大学古典讲习科与斯文会的活动;第三期为明治二十四、五年间到明治三十五、六年间,表现为东西哲学的融合与关注日本学;第四期为明治三十七、八年到明治末年,主要表现为日中学术综合、汉文大系面世。这里以事件为中心而展开的汉学史的划分,是值得思考的。
明治十二年(1879),综理东京大学的加藤弘之向文部省提案设置古典讲习科,但未获得允许。明治十四年(1881),再次建议而获得许可。明治十五年(1882),附属于文学部的“古典讲习科”成立,主讲“国学”,而后设立“支那古典讲习科”,讲授“汉文学”,至明治十七年(1884),分别改称为“国书课”、“汉书课”。当时招生名额计四十名,而明治十六(1883)年第一届报名人数达一百六十名。
该书《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的人们》一文,通过学生的回忆,重建“古典讲习科”的历史场景,指出明治维新以来,硕学凋零,汉学命脉几乎断绝,而“古典讲习科”具有承前起后的巨大作用,虽然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犹如民国时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但同样在学术史上有巨大影响。在我看来,网罗中村正直、三岛毅、岛田重礼、井上哲次郎等人进入“古典讲习科”的教授阵营,其实就是让古典学研究进入现在学术体系,更何况“古典讲习科”还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其对汉学的意义当然重大,作者因此而视为此一时代汉学发展的重要事件,自然很有说服力。
《关于汉文大系》一文介绍了明治四十二年(1909)至大正五年(1916)间刊行的大型丛书《汉文大系》的情况。该丛书由富山房出版社社主坂本嘉治马提议,服部宇之吉编集,解题者有重野安绎、星野恒、小柳司气太、安井小太郎、冈田正之、岛田均一、儿岛献吉郎、井上哲次郎等一批汉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者。该丛书共二十二卷,计三十八种,选目可谓是中国古典知识系统的基本图书。刊行这一丛书,通过精审校注、详细提要解说,介绍了中国古典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幕末以来日本汉学成果的集大成,作者还说明了该丛书也吸收了当时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一丛书具有世界汉学的里程碑意义。
《明治的青春》一书也是以汉学者研究为中心,不过视野较前书为广,个别论文的论述更为细致,如《久保天随的日本汉学史研究》一文比较具体集中在汉学者的汉学史研究。该书中《福冈的汉学》一文的视角比较少见,一般认为福冈人尚武重商,而作者则以人物为经,以教育为纬,展示了日本汉学的地域传播特点。
明治汉学
三浦叶,《明治の漢学》,东京:汲古书院,1998。
《明治的汉学》书中《明治汉学的盛衰》一文,与町田三郎《明治的汉学者们》对明治时代汉学发展有着不同的认识,了解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学术史划分,有助于整体把握明治汉学的发展。町田三郎侧重于事件为标志的划分,而三浦叶此书则侧重于汉学与洋学的此消彼长的竞争状态。
作者指出,明治初期延续幕府而来的汉学素养尚存,至明治五年(1872)政府发布《学制》,取缔私塾,汉学开始衰退,至明治八九年(1875—1876)间,以汉诗文为主的几种杂志刊行,可见汉学已成欧化背景下的一种潜流。明治十五年(1882),东京大学设古典讲习科,地方上三岛中洲的二松学舍、岛田篁村的双桂精舍、蒲生褧亭的有为塾等也开始发力,京都的草场船山、大阪的藤泽南岳等墪生达到三四百人,汉学在洋学盛行的背景中也仍有一定势力。直至明治十八年(1885)森有礼主政文部省,推行极端欧化教育,私塾衰退,汉学衰微。
明治十八年后,汉学首要任务是反欧化宗教、道德,针对提倡欧化的《国民之友》杂志,汉学者们也创办《日本人》提倡国粹主义。明治十九年(1886)东洋学会、东洋哲学会创立,一时之间东方哲学研究兴起,当然,这也是在欧化背景下展开的。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变化,学者也开始在中国史学研究上开始用力,至明治二十八年(1895)儿岛献吉郎《东洋史纲》、三十年(1897)市村瓒次郎《东洋史要》、三十一年(1898)桑原騭藏《中等东洋史》等刊行,一时风头颇盛。从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汉学其实是欧化思潮刺激下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该书对明治以前并非“不知有汉”,其实是侧重于“学”的逻辑,这与李庆教授《日本汉学史》从明治时期开始书写,具有相近的“汉学”范畴观。
该书还特辟四章来交代明治时期的各种汉学观,其中第一部第五章《启蒙思想家的汉学观》尤其值得细读,作者详细列举了新岛襄、内村鑑三、中村敬宇、福泽喻吉、西周、加藤弘之、中江兆民、西村茂树、井上毅的汉学观,他们的汉学观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汉学的发展。第六章还介绍了明治时期文人学者如高山樗牛、大町桂月、田冈岭云、山路爱云的汉学观。汉学史著作中回顾汉学观,这对学术史写作很有启发意义。
该书对明治时期中国文学的研究并不特别深入,只是介绍了当时几部中国文学史,作者认为这些中国文学史之作可能是受到了日本文学史写作的启发。众所周知,这些日本汉学者的中国文学史对中国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有一定影响,可惜目前关于日本文学史写作与中国人编写中国文学史之间的联系,少有人发掘。作者对这些“文学史”的介绍颇为简略,倒是相关几篇文章对这些文学史的作者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如第二部第一章主要是论述“赤门文士”,第二章直接讨论儿岛献吉郎,相关资料都值得注意。
关于“赤门文士”,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并不多。作者称这批“赤门文士”为新汉学者,他们都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关于东京大学的学科发展,可参见东京帝国大学所编的《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东京帝国大学五十年史》等论著),校内的“赤门”为其重要标志。这一学科的毕业生中,汉学科有:藤田丰八、狩野直喜、桑原騭藏、白河次郎、久保天随、铃木虎雄等;国文学科有:大町芳卫、武岛又次郎等;国史料科有:笹川种郎、幸田成友等;哲学科有:姉崎正治、蟹江义丸等;汉学科选科有:田冈岭云、小柳司气太等;哲学科选科有:西田几多郎。这一批赤门文士其实就是后来汉学界的中坚力量,其实值得从教育史、汉学史等多角度作一个群体研究介绍给中国学界。
虽说此书出版已有一段时间,其中所论今天看来似乎也失去了前沿性,比如作者在书中概括出明治汉学的四个特点:一为洋学的影响;二为学风较幕府时代更为自由活泼;三为明治汉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四为汉字研究。看起来在卑之无甚高论,但作者引证的材料却仍值得关注,如在第三点中作者指出明治时期,很多汉学家用汉文来翻译西方作品,不但有文学作品,甚至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被中江兆民翻译成了汉文《民约译解》,这一现象似乎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足够重视。
汉学与洋学
岸田知子,《漢学と洋学:伝統と新知識のはざまで》,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0。
三浦叶的《汉学史》从汉学与洋学的关系角度下考察汉学,其所谓的汉学,几乎可以说是西方学术体系下的产物,是“洋学”所催生出来的一门学问。但汉学与洋学的关系还存在着另一种形态。岸田知子这本《汉学与洋学:传统与新知识之间》描述了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前的“汉与洋”的关系。
该书所谓的洋学,其实是指幕府时代的兰学,更具体地说是从荷兰人那里传来的医学。医学在日本学术史上的意义,可能与地理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相近,这些知识传入之初,可能是作为传统学问、技术的一种旁证,但它们所具有的强大实证能力,对传统知识人的认识世界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传入中国的地理学打破了中国人的天下观,而传入日本的荷兰医学,也具有类似的作用。
从文化交涉的角度看,它们是如何进入传统东方学术体系的呢?岸田知子该书《洋学者与汉学》一文列表统计,指出当时很多学者是用汉文来吸收兰学的。笔者所见《重刻解体新书》就是以汉文写成的医书,虽然书中加了假名训读,若当时读者不深通汉文,恐怕是无法接受西方医学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所谓兰学要搭上汉学的车才能进入日本,而明治时代汉学要进入现代学科体系才能发展,这时洋学成了搭载那辆的车,这之间的变化很值得深入深思。
不过,岸田知子该书属于普及性质,对于学术史和思想史角度的阐发是不足的,该书介绍了中国的五行与兰医中的四元,介绍了幕府时代兰学学习的情况,介绍了当时日本学者如何运用朱子学中格物穷理的观念来接受兰医,但总体上来看,仍多属于介绍性的文字。我希望读到是“汉学”观念映照下的“洋学史”,这在中国和日本似乎都没有理想的著作。
近代日本的汉文学
村山吉广,《漢学者はいかに生きたか》,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
本书的主体当然是八位汉学者的传记,也许题目可以译成《汉学者传略》,不过全书第一部分有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明治以来的汉文学情况,倒是可以与其他的汉学史著作参看。该书中《明治的汉学》一文就非常不同于三浦叶的写法,三浦叶侧重于学术性的汉学研究,相比之下,本书作者的“汉学”则侧重于汉文学,他认为虽然明治时代洋学盛行,可汉诗文创作也非常发达。作者认为明治中期可以说是“爱好汉诗文”的时代,社会上层人士倾倒于汉诗文,甚至流传有“现在参议都是书生”的话头,他们出口即为汉文,出手即是汉文调的文章,当时较为流行汉文和汉文直译体。其次在现代新语词的形成中,当时学者往往援用汉语词汇,甚至借中国古典语词创制新词。对明治汉学两种不同的论述,正可以丰富我们对明治汉学和汉文学的认识。
该书中另有一篇《大正昭和的汉学》,描述了孤军奋斗的汉诗文作家,但将历史追溯到甲午中日战争,认为日本战胜以后,国民心态急剧膨胀,报纸杂志上的“汉诗栏”渐次衰退,终于消失,而汉诗文作家也迅速减少。作者所举例的汉诗文作家仅聊聊数人,如国分青厓以批判时事的“评林诗”闻名于世,而后就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几位毕业生,包括久保天随和铃木虎雄等人。至于在汉文学的形态上,则已大不如明治时期的前辈了,他们开始以日语翻译汉诗,当时称为“汉诗和译”,著名的有土岐善麿、佐藤春夫、井伏鳟二等人。
《战后社会与汉学》一文从仓石武四郎说起(仓石武四郎也有《本邦汉学之发达史》的讲义,似乎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仓石武四郎关于训读的观点,在本书作者的笔下,成了汉学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汉学开始蜕变成东洋学。这一转变并非只是一个名词上的变化,而是整个学术体系的调整。
欧美汉学和中国国学研究,似乎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甚至在研究方法上也可以互通有无,其区别看起来只是研究者的身份不同。但从学科体系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研究对象往往从时间上分,如先秦思想、唐宋文学、明清史等,虽然国学研究的定义言人人殊,但最大的共识应该是在时间上;而欧美汉学研究往往从属于东亚系,是作为区域研究而展开的。换言之,国学是历史研究,而欧美汉学则是地理研究。而日本汉学却近于中国的国学研究,日本汉学转向东洋学,事实上就成了历史研究转向地理研究,虽然他们也还是关注古典中国,但论述的前提却转换成了当下。本书作者认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东洋学界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凌越欧美汉学自不待言,很多成果连中国学者都不能无视,可惜未作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