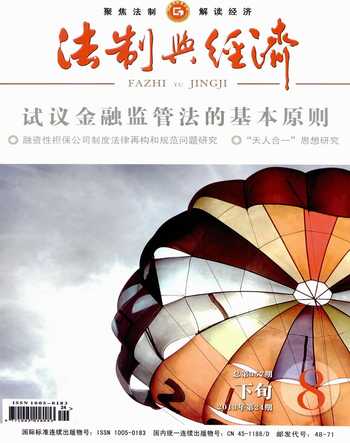濒危物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研究
[摘 要]濒危物种在近几十年时间内的迅速消亡与人类的不合理开发活动有密切关联,人为的环境污染破坏了濒危物种原有生存栖息环境。通过赋予濒危物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创设与之相配套的濒危物种诉讼代理人制度,促使环保团体参与到濒危物种保护事业中来。以濒危物种成为诉讼主体的形式,突破原有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思想的法律制度安排,由濒危物种去捍卫其作为生态系统一员所应当享有的、与人类相同的尊严与权利,对保护濒危物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濒危物种;原告资格;环保团体;公益诉讼;代理人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濒危物种是指所有由于物种自身的原因或受到人类活动或自然灾害的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野生动植物。环境污染、生物栖息地的破坏使得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过度消耗的状况十分严重,这也意味着针对濒危动植物的相关法律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如何去遏制濒危物种消亡的速度?能否通过赋予濒危物种相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使得身处灭绝边缘的濒危物种能由相关环保团体作为其诉讼代理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阻止人类肆无忌惮的开发行为?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之立法现状
因受法律二元结构论——公法、私法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一直被视为典型的“私诉”,法院要求由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而将诉讼划分为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类型,其背后的法理是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学说、国家主权理论。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国家是社会公益的代表,人民将部分权利自愿让渡给政府,因而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场合,则由国家代表公共利益,向法院起诉,而按照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私人利益”只能由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而司法机关则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但这一传统诉讼结构,在面对现代社会中日趋复杂的权利结构,很多权利因其主体的复杂性,导致其难以区分究竟应属“私权”或是“公权”,反映的究竟是“公益”还是“私益”,因而使得环境权益难以受到诉讼机制的保障。①根据我国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意味着我国第一次将环境公益诉讼纳入法制轨道,这对于传统诉讼理论是一种突破。从实践层面而言,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对于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有着积极促进作用,这对于传统诉讼理论中所强调的“直接利害关系”理论是部分的突破,使得部分机关组织认清自己在环境保护中所应肩负起的责任。但我们仍应该看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更多的是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实践中,究竟哪些“相关组织”符合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要求?哪些法定机关有代为起诉之资格?依旧需要不断进行细化研究。
三、濒危物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设定之理论依据
赋予濒危物种诉讼主体资格是种际公平理论在诉讼法上的体现,根据日本学者山村恒年教授的观点,自然与人类有着共同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现代法律如果将人类的尊严作为其基底的法律价值加以承认的话,那么也应将作为人类生物学、精神的生存基础的自然作为人类以内的东西予以承认其基底的法律价值。②对濒处灭绝生物的生命价值的尊重,赋予其诉讼资格,使其能够通过法律的手段寻求自身生命权的救济,所体现的正是人类对于自然价值的尊重。传统诉讼是以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为原告,而环境公益诉讼则与传统诉讼之间存在差异,环境公益诉讼将公益的促进作为其要件,诉讼真正的目的并非单纯的寻求个案救济,而是敦促政府或受管制者积极采取某些促进公益的法定作为,判决的效力未必局限于诉讼的当事人。③关于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设计,我们应当看到其与传统诉讼之间的差异,看到两者在诉讼目的之间的不同,尤其在进行环境公益诉讼这样具有浓烈公益性质色彩的诉讼制度时,不应为传统法律制度思维所囿,而是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针对部分反对意见所认为的,在原有诉讼制度中濒危自然物不存在诉权的观点,斯通教授的反驳很有说服力。按照斯通教授的见解,我们可以仿照公司法破产重组制度中为公司设定托管人的方式来为自然物设定代理人。我们在处理无行为能力人(如植物人等)的相关法律问题时,采用的方式是由其或基于法定或基于指定而产生的代理人,代其参与诉讼活动。从现有的诉讼制度来看,诉讼的主体资格所要求的是当事人的权利能力,而非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因此,以自然物不具备表达能力为反驳理由难以经得起推敲。斯通教授认为,像不能说话、没有意识的国家、公司、婴儿、船舶、自治城市和大学等都被赋予了法律资格,既然这样,我们也可以赋予自然物以法律资格,并为他们设定保护人和代理人。④
四、立法构想——濒危物种原告代理人制度的架构
反对将自然物纳入诉讼主体的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物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一旦赋予自然物诉讼主体资格,对现有的司法制度将是巨大挑战,需要耗费巨大的司法资源,同时,因为自然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着语言沟通的障碍,如何为其选定代理人?代理人又如何行使其代理权?代理权范围如何界定?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是否是自然物真实意思表示?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立法构想中回答。
从美国和日本有关自然的权利诉讼实践来看,其主要形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代理人(监护人)模式,即以环境保护团体或个人作为自然物的代理人为原告,具有无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的地位和作用;二是信托人模式,即由团体或个人作为自然物的受托人,成为原告;三是自然物及其受托人作为共同原告模式;四是准无权利能力财团的模式,即管理人保护团体作为代表人。⑤通过对美、日两国的司法实践的考察,认为采取代理人模式较好。
赋予自然物以自然资格,与其说是法律技术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类法律观念的问题。在法律实践中,早已有“人”以外的主体成为诉讼主体,比如在英美海商法中就认定“船舶”具有法律上的人格。而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群体内部中对于存在沟通交流障碍的群体,比如未成年人、精神障碍人等,针对这些存在意思、意志表达与表示障碍的人群,法律并未排除其诉讼资格,并为这一特定群体设计了监护制度和代理制度,可以看出,诉讼资格更多强调是一种权利能力,而非行为能力。法律能够为无意识的植物人设定监护人,同样可以为濒危物种设计相应的代理人制度。针对数量有限的濒危物种(我国珍稀野生动植物名录中濒危动物植物共计279种),在有限的诉因(有灭绝的威胁)的前提下,授予濒危物种原告资格,并不会导致任意的自然物起诉任何人造成的任意损害的情形,不会因滥诉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
关于濒危物种代理人的选定标准,可以借鉴美国学者科罗拉多州法学教授Burke的观点。Burke教授认为:在EAS中增加一个动物诉讼条款符合国会颁布的ESA的目的,并且国会有权这样做,而且这也符合法院解释原告资格的原则。在具体实施中,可以通过有原告资格的动物原告的“亲密朋友(next friend)”实现。美国最高法院也在司法实践中描绘了作为“亲密朋友”而应具备的条件。第一,“亲密朋友”必须充分解释为什么他代表的是当事人而非代表自己;第二,“亲密朋友”必须显示他真实地致力于保护他所代表的当事人的利益。⑥在人类代表濒危物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亲密朋友”理所当然的是代表该濒危物种,而非代表其自身。“亲密朋友”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中,不仅仅要求其有致力于此的决心,更应当对其的资格能力进行相应的限制。作为濒危物种的代理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与科学上的专业知识,能够适当有效地代表濒危物种参与诉讼活动,具备维护濒危物种权利的能力。具体到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最适合充当濒危物种的“亲密朋友”应当是环保团体。环保团体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具备相应的环境科学与法律知识,具备维护濒危物种权利的诉讼能力。我们应当认识到并非所有的环保团体都能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中濒危物种的代理人,法院应当对能代理濒危物种提起诉讼的环保团体进行指定,防止缺乏资质的环保团体作为诉讼代理人损害濒危物种的权利,这也是防止滥诉发生的一种手段。在美国自然物权利诉讼中,环保团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与美国团体制度发达、制度相对健全的国情有关。
关于诉讼代理人所作出的代理行为是否符合濒危物种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常识、经验做出基本判断,因为濒危物种提起公益诉讼的诉因在于其生存受到巨大威胁,而排除这种威胁所表现出的现实紧迫性必然能够为外界所知晓,因此环保团体代濒危物种提起诉讼,请求排除这种威胁,合理性可以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面对着帕里拉属鸟栖息地被绵羊破坏的情形,直接威胁到帕里拉属鸟的族群存亡时,此时由环保团体代其向法院提起诉讼,必然不存在与自然物真实意思不相一致的情况。
五、结语
环境法作为一门充满了创新的法律学科,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对传统的挑战,而这一次次的理论上的突破,都是人类在文明进化演变过程中对于自身在自然与社会关系中定位的不断反思,是人类一次次对于终极关怀的追寻。赋予自然物权利,尤其是赋予濒危物种诉讼权利,挑战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对于法律秩序的既定安排,这将改变人们传统法律体系中将人类外化于自然的传统思路,而是要求将人类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将人类置于与其他生物相同地位,赋予濒临灭绝险境的物种,能够通过诉讼之方式,寻求救济的权利,通过赋予濒危物种原告资格、设计濒危物种诉讼代理制度,使得环保团体能够以更加直接高效的方式参与到濒危物种的保护工作中,这对于一个国家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民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参与都有着积极意义。
[注释]
①傅剑清:《环境公益诉讼若干问题之研究》,载《环境法系列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②陈泉生:《论环境时代宪法对其他生命物种权利的尊重》,《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
③曹树青:《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进路探寻》,《海峡法学》2010年第2期。
④陶建国,张维新:《美国“自然的权利”诉讼》,《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11月,总第95期。
⑤吴勇:《环境公益诉讼的另类视角:自然物种诉讼》,《法学论坛》2009年第1期。
⑥严厚福:《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确立——扩大“合法权益的范围”还是确立自然物的原告资格》,《北大法律评论》2007年第8卷第1辑。
[作者简介]章楚加,南京大学法学院2012级环境与资源法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