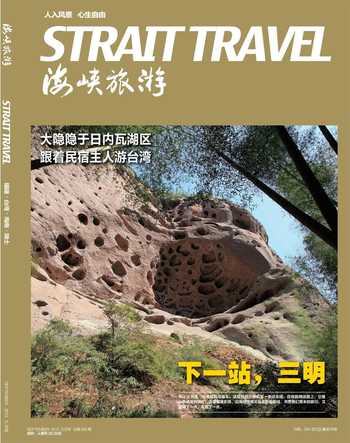一碗不起眼的切仔面
陈淑华
当那一碗切仔面上桌时,我实在无法相信它有如此醇厚的味道。
前阵子,天热,胃口跟着给缩小了,那时候便想来一碗面,特别是街头的面。记得小时候,生了病,没了食欲,大人总会轻声地问,要不要吃面啊?1970,甚至更早的1960年代,彰化街头卖的面,有名的“猫鼠面”或“黑肉面”,都是一碗小小的,摆明了是点心的模样。回到祖父母的家乡,古都台南的担仔面,小巧的更非日常三餐的吃食,是台南在地人垫肚的小食,也是我们这些随着祖父母返乡小孩的美味犒赏。
好长一段时间,在又是犒赏又是抚慰的滋味包裹下,我无法辨别这些面食的真正味道所在,只知1980年代末,从彰化北上以后,台北街头小摊的面,大大一碗,阳春面不说,切仔面吃来竟也是阳春般的淡而无味。
阳春面,一团白色生面下锅煮熟捞起,置入碗中,淋上大骨熬的热汤,乍看宛若阳春白雪浮现,因而在江南一带得名。但这样一碗光面,一碗清清如也的清汤面,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出现在台湾街头,却因着煮面人大多是外省籍老兵,又有了外省面之名。
切仔面(台语发音tsh'ik-á-mī)亦是一碗清汤面,只是黄色的碱面取代了外省面的白色面条,而摆在面摊上的黄面还是熟面,等客人点了,一把抓来放入笊篱(竹漏杓)中,置入滚烫的热锅,抖动几下,让面均匀受热,随即提起倒扣入碗中,利落的动作中切切声响,切仔面之名不禁也喊出口,然后如同阳春面般淋上大骨汤,伴着豆芽韭菜,以及一小杓油葱酥,豪华者来点肉燥的切仔面便上桌了。
如此切仔面出现台湾街头至少一二百年,说来彰化的猫鼠面和黑肉面,以及台南的担仔面都是切仔面。早年的切仔面都是挑担出卖,一百多年前,在出不了海捕鱼的日子,台南的洪芋头向漳洲老乡学得一手煮面技法,开始沿街挑担卖切仔面度小月,最后他将面担停在台南水仙宫前,黄昏时刻,写着度小月的小灯笼傍着担仔一挂,洪芋头的切仔面卖出名了,曚昽光线下,“担头”特别显眼,于是度小月担仔面成了招牌了。
近百年前,彰化的陈木荣也在午后三四点开始挑担出来在离观音亭不远的地方卖切仔面。陈木荣生肖属鼠,身形又恰好瘦小而行动敏捷,他切的面让人垂涎,到猫鼠(台语老鼠的发音)那边吃面的口语传开来了,“猫鼠面”随之诞生了,让无名的面担仔有了名字。1945年后才出现在彰化街头的黑肉面,亦因第一代老板的外形,黑黑胖胖而得名。
回味这些曾经丰富我的童年滋味的切仔面,台南的担仔面,源自漳州风格,大骨汤头中浓缩着虾子的精华,而这一切就在上桌前的那一杓肉燥,香菇、绞肉伴着剁成末的虾肉,调以五香和酱油,慢炖而成,味重而浓,加上那一尾火红的鲜虾,让这一碗切仔面溢出原本朴实的面貌。而彰化的猫鼠面或黑肉面,虽没有台南担仔面的华丽样子,但以蛤蜊取代虾子,自有一种清新的台湾风味,特别是那一杓肉燥,隐入汤中成为熬汤的材料,化浓烈于无形,看似清清淡淡,却在时间之火的催化下层层发散,让蛤蜊的鲜味如打水漂儿般,在猪肉的甜味中涟漪无穷,最后甚至让人忘了它也是一碗切仔面。
二十多年的台北居,切仔面几乎无所不在。在许多或幽静或嘈杂的巷弄,不管无名或有名的面摊或小吃店,从琳琅满目或寥寥无几的菜单上,抬头望去,总少不了切仔面,但舌尖历经台南虾味与彰化蛤味汤面锻炼的我,对它总提不起劲,甚至视而不见。没想到,这几年来,却有人以这种寻常到几乎让人忘了它的存在的切仔面,做为让地方发光的特点。
新北市芦洲切仔面节已经热烈地举行过好几年。在日本殖民台湾的末期,周乌猪于芦洲涌莲寺庙口摆担卖切仔面,二次大战爆发,受战火波及难以为继。战后,1946年,他的徒弟在庙门口重操师父的旧业,继续切面维生,半个多世纪过去,芦洲一个小小的地方竟密密麻麻出现了四十多家的切仔面担,到底从周乌猪传下的切仔面,藏着怎样与众不同的口味?可以让它繁衍滋生出如此的局面,甚至一度让人以为芦洲是台湾切仔面的发源地?
那天一访芦洲的切仔面店,终于恍然大悟。切仔面上桌,一团黄面突出汤中,绿色韭段漂浮,明明就是朴实到不行的模样,但面条一吃,汤一喝,却比想象中大骨汤头煮成的切仔面有味。抬头一望,店里卖着各式黑白切小菜,三层肉、嘴边肉、猪心、猪肝、猪舌、大肠、生肠等等,莫非这些猪肉、猪内脏就是汤头美味的来源?果然从周乌猪传下的切仔面店,强调他们的汤头是以猪大骨加三层肉与嘴边肉炼成。
位于淡水河下游西岸的芦洲,原为一处沙洲,从雍正年间开发以来,一直以农业为主要产业,涌莲寺慢慢的也成为一农产品集散地,来来往往的庄稼人,偶而在这里吃到一碗不仅止饥又充满猪肉精华的清汤面,搭一二份黑白切的小菜,一天,甚至再来一季的力气都有了,怎能不为它着迷呢!显然芦洲切仔面从忠于乡野原味的道路找到了突围的力道。
就在我惊艳于芦洲切仔面时,没想到,经台北桥,过了淡水河,进入台北市,来到大桥头,卖面炎仔的切仔面蕴含的力道更猛,怎么有如此厚实的汤头,喝到最后竟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滋味浮现。摊上的黑白切,同样有各式猪味,除此竟还有白切鸡肉与鸡下水(内脏),一问,过去竟还卖有鸭肉。这不是囊括了家里拜拜的牲礼吗?在过去贫穷的岁月这可是过年过节才有的滋味啊!而今都俱现在那一口汤中。
卖面炎仔自十七、八岁开始在大桥头附近大稻埕一带挑担卖切仔面,至今传到第三代,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一府二鹿三艋舺”,大稻埕在艋舺衰退之后,于1860年代随着台湾开港后而崛起,在茶香岁月中一度茶行林立、商贾云集。而大桥头做为台北桥的东端,1960、1970年代,许多从台湾中南部涌向北部谋生而群居在桥西端三重、芦洲一带的人,便以它做为踏入台北这个繁华都市的第一站,当时在桥下还有所谓临时工派发市场。卖面炎仔的这一碗切仔面既要满足来自淡水河另一边劳动人口的力气需求,也经得起大稻埕殷富人家的刁嘴考验。
比起芦洲的切仔面,藏在西安街宁静住家中的卖面炎仔切仔面,长相更加不起眼,面条伴着大把的韭菜条散在汤中,家常到让人几乎不相信它有这样的实力。但它就是有,才能让当地人以它当早餐,做为每一天的开始,还有来自各地慕名的客人不断涌向它。
好醇好厚的汤头,喝到尽头竟衬得韭菜更加的清香,不一会儿面条便滑溜的下肚了。我想以后除了彰化街头飘着蛤仔味的切仔面,我也会惦着这一碗不起眼的切仔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