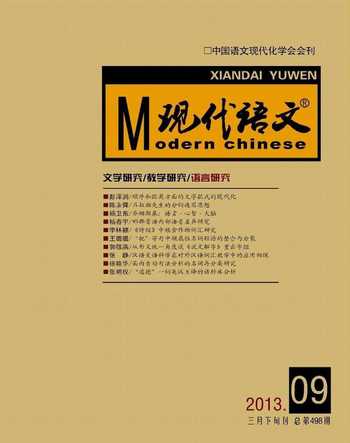浅谈判断古代汉语宾语语义角色不可依据翻译
摘 要:古代汉语宾语语义角色作为古代汉语动宾语义关系研究的一种结论,其研究方法具有特殊性。由于古今汉语词汇层面的差异,现代汉语的翻译并不能作为判断古代汉语宾语语义角色的最终依据。
关键词:古代汉语 动宾关系 语义角色
古代汉语动词和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非常灵活,在语法研究中经常被讨论,到目前为止成果颇丰,共识颇广。学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结论一般都在两个角度上展开表述,一个角度表述为述语活用,如“使动”“意动”“为动”等;另一个角度表述为宾语的语义角色,如“对象宾语”“工具宾语”“目的宾语”等。
以上两个角度不仅仅是表述的侧重点不同,而且还有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当结论要表述为述语活用时,人们一般都通过将古汉语的例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来观察其特征,如翻译为“使之如何”时就是“使动”,翻译为“以之为如何”时就是“意动”,翻译为“为之如何”时就是“为动”,可以说翻译中添加的介词“使”“以”“为”都成了判断述语活用类别的标记。而当结论要表述为宾语语义角色时,不少学者同样采用翻译后观察译句介词标记的方法。那么,究竟翻译能否作为判断古汉语宾语语义角色的标准呢?
类似的方法在现代汉语宾语语义角色判断中是奏效的,只不过现代汉语采用的是变换而不是翻译。如“吃大碗”,须先变换成“用大碗吃”,根据介词标记“用”来判断宾语“大碗”是工具宾语。但是,在古代汉语宾语语义角色判断上,可能会有问题。下面通过几个具体的例子进行分析。
(1)夏四月丙子,享公。(《左传·桓公十八年》)
(2)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3)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孟子·离娄下》)
(4)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诗经·墉风·桑中》)
(5)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左传·闵公二年》)
(6)宾之以上卿,礼也。(《左传·桓公九年》)
孙良明(2008)认为,例(1)中“享公”的宾语“公”是“目的”角色,原因是“享公”在古注中被解释为“为公设享燕之礼”。以介词“为”作为目的宾语的判断标准是符合我们的经验的,然而这种做法的危险却暗藏在“为公设享燕之礼”这一释译中。“为公设享燕之礼”作为一种释译,本身是准确无误的,但从语法学的角度来看,它却是宽泛的。由于动词“享”的词义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没有词汇化为另外一个更加通俗易懂的词,因此后人在释译“享公”时,一般都使用带介词短语的分析性形式,以求文从字顺。实际上,若不考虑文从字顺,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的翻译——“设享燕之礼接待公”。这样一来,“享公”的语义结构跟现代汉语的“接待某人”“款待某人”没有实质区别 ,其宾语都是典型的对象宾语。
杨伯峻、何乐士(2001)认为,例(2)中“衣其尸”的宾语“其尸”是“替做”角色,原因是“衣其尸”可以被翻译成“给其尸穿衣”。如同例(1),这个翻译是宽泛的。在历史发展中,“衣”的及物动词用法既没有被保留下来,也没有词汇化成另外的词——现代汉语中找不到一个表示“给某人穿衣”的及物动词来对应上古汉语作及物动词的“衣”,因而在翻译“衣其尸”时只能使用带介词短语的分析性形式。然而,上古汉语有一些名词的动词用法却比“衣”更幸运,比如:“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蛊”本义是一种毒虫,也是一个名词,但它在这个句子里的动词用法却在后代词汇化为一个双音节词“蛊惑”。于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蛊文夫人”不是“给文夫人施加蛊惑”,而是“蛊惑文夫人”。相比之下,“衣其尸”其实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宾语“其尸”就是一个较典型的受事。
例(3)中的“简驩”被杨伯峻、何乐士(2001)认定为“对向”角色,原因是“简驩”可以翻译成“对驩简慢”。与前面两例同理,由于现代汉语没有动词与古汉语的“简”相对应,因此只能采用带介词短语的分析性形式。但就古汉语的动宾结构“简驩”来讲,宾语“驩”应该是对象宾语。
例(4)“期我”的宾语“我”被孙良明(2008)认定为“与事”角色,原因是郑笺释此句为“与我期乎桑中”。《说文解字》释“期”为“会也”;段玉裁注:“会者,合也。期者,邀约之意,所以为会合也。”可见,“期我”翻译为“约我”同样是恰当的,宾语“我”是对象宾语。
例(5)“先之”和例(6)“宾之”的述语是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这两种情况下的宾语被王克仲(1989)划在“间接受事”中,和作为“直接受事”的典型受事角色相区别。这似乎符合我们的经验,因为在人们的理解中,动词的“活用”本就是变通的、间接的,在翻译时通常也需要加介词“使”和“以”,因而“活用”动词的宾语自然不是直接的受事。但是,恰恰如同前面的两个例子一样,人们又一次掉进了翻译的陷阱。刘又辛(1983)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主要从翻译的角度分析,意即古代汉语很多“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已经词汇化为双音节动词,所以这些古汉语的“活用”翻译成“使之如何”“以之为如何”都没有必要,因为它们可以由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来对译。这个看法很有价值。比如“止臣”,完全可以翻译成“阻止臣”,而不必翻译成“使臣止”;“尊贤”,完全可以翻译成“尊重贤人”,而不必翻译成“以贤人为尊”。这些“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一旦被如此对译,就现了原形,恢复了施受关系的原貌,宾语就不至于被当作“间接受事”了。但蒋绍愚(2001)指出了一些无法找到恰当的动词来对译的动词。比如“先之”和“宾之”,它们似乎只能翻译成“使之先”“以之为宾”。但我们认为,虽然在翻译时作此番分析性的调整是无妨的,而在理解动宾语义结构的时候,它们跟“止臣”和“尊贤”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宾语的语义角色上,不论它们在对译时采用上述哪种手段,使动用法带的宾语都是较典型的受事宾语,而意动用法带的宾语都是对象宾语(即一种典型性较低的受事宾语),它们都不应被划入“间接受事”。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词汇层面的差异决定了古代汉语的翻译不可能像现代汉语的变换一样准确地显示动宾语义关系,揭示宾语语义角色。翻译是用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去转述古代汉语,以此为依据是一种“以今律古”的做法。翻译只可作为判断古代汉语宾语语义角色的参考,而不可作为最终依据。
参考文献:
[1]蒋绍愚.使动、意动和为动[A].语苑集锦——许威汉先生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刘又辛.使动、意动说商榷[J].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2).
[3]孙良明.汉魏晋人对谓词结构中名动语义关系的分析[J].古汉语研究,2008,(2).
[4]王克仲.古汉语动宾语义关系的分类[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5).
[5]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修订本)[M].北京: 语文出版社,2001.
(徐欣路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
——兼谈立体化古代汉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