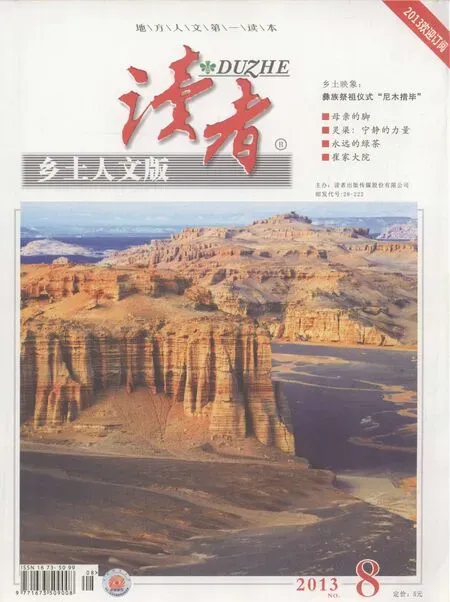奶奶的『飞鸡』
图/沈骋宇
文/老特务头子
奶奶的『飞鸡』
图/沈骋宇
文/老特务头子

奶奶是从我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喂鸡的。
鸡苗都是奶奶一只只亲自挑选的,公母各半。她常说:“3岁看大,7岁看老,人物一理。眼里没精神,再怎么养都是瞎货。”每次喂食,奶奶给母鸡单独喂一份,管够;给公鸡只喂一半的量,手脚慢的、脖子短的、不会支棱着小翅膀往前挤的统统吃不饱。等到那些小鸡仔长到半大的时候,那些小公鸡们的身板就拉开距离了,这时候,奶奶隔一阵子就叫大爷把最孱弱的那只拎出来杀了,给我和我哥打牙祭。
经过奶奶自创的末位淘汰制考验,最后那只一路打拼下来的公鸡,不论是体格还是精气神,都已经完全脱胎换骨,跟普通的公鸡彻底划清了界限。它的眼神犀利无比,充满傲气,只需睥睨一下就吓得那些外来的鸡屁滚尿流;它的步履扎实沉稳,甚至连饭后游园都像是在阅兵式上踱着方步对群臣颔首致意。最关键的是,经过长期的征战,它的翅膀得到了充分发育,华丽的羽毛在它的身上已经不再是可笑的装饰。它,已经成为了一只货真价实的“飞鸡”。
最开始,我还只是看到它时不时飞到院墙上俯瞰它的领地,后来有一次,它竟然当着我的面从地上飞到屋顶瞭望远处的麦场。当我还没舍得把这个神奇的事件跟我哥分享的时候,它又在一个傍晚,拍打着翅膀掠上了院子里那棵十几米高的梧桐树。整个飞翔的过程是那么优雅从容,把正围坐在树下吃晚饭的一家人惊得目瞪口呆。
它只吃奶奶喂它的小米和苞谷,“用膳”的时候,它那成群的妻妾都必须垂首肃立,咽着口水等它吃完才能“上桌”。后来,它开始变得桀骜不驯,并且像藏獒一样只听命于每天给它喂食的奶奶,就连我和我哥从它的领地经过时,都要时刻提防它的攻击。为了防身,我和我哥进出自家院子都得随手拎一根竹竿。有一天,我喝了凉水,闹肚子,情急之下忘了带竹竿。等到我猛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它已经悄然摸到我的身后,正准备在我屁股上啄几个窟窿出来。好在我急中生智,右手抽出皮带,权当软鞭使将出来;左手拎着裤子,且战且退。未几,我哥闻声接应,方解我茅厕之困。
终于有一天,它闯下大祸,把大姨家刚满3岁的小外甥女给啄花了脸。气急之下,奶奶随手抄起一根木棍就向它抡了过去。出人意料的是,它竟然呆立在那里纹丝不动。奶奶连打三下,最后一下打中了它的脑袋。我一直坚信,照它的身手,完全可以轻松躲过奶奶的绝杀,然后一飞冲天,飘然而去,凭借一身绝世武功,无论是在麦场也好,在田头也罢,招集一群部下,继续当个鸡王不是什么难事。可能是它到死也不肯相信,奶奶会真的杀它。
依旧是大爷操刀,将它剥皮洗净,它的尸身上露出了一块块硬实的肌肉,下锅爆炒了十几分钟,肉硬是不烂,后来又加水炖了好久,才盛盘上桌,那种充满嚼劲的口感令我至今难忘。不久之后的一天深夜,奶奶突发中风,抢救过来之后落下了半身不遂的毛病。病好之后,奶奶时常架着单拐、拖着僵硬的右腿蹭到院门口张望。后来,她再也没养过鸡。
(易小鱼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