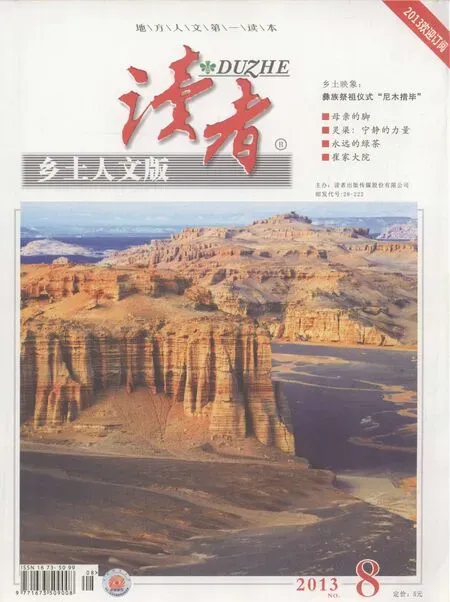我讨厌我身上的汗味
文/周海亮 图/邵晓昱
我讨厌我身上的汗味
文/周海亮 图/邵晓昱

我知道我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汗味。我还知道,那气味很难闻。
现在是黄昏,我挤上一辆12路公共汽车,从东城去西城。我喜欢12路公共汽车,它是小城所有公共汽车中线路最长的一趟车。每天我都要往返东城和西城,清晨与黄昏,12路公共汽车伴我穿越小城。有时我甚至嫌这段行程太短。我喜欢站在车上,打量这座城市的街景。
我讨厌一些作家把我们描述得很可怜,偏偏现在的作家大多喜欢这样写。在晚上,在睡觉之前,我喜欢翻翻杂志。我翻杂志绝非有什么作家梦,纯粹是因为无聊。我常常被杂志里的那些农民工的故事所感动,我对他们心怀怜悯。但我与他们不一样,我不想让别人怜悯,并且我真的没有让他们怜悯的理由。事实上,除了偶尔的伤感、恐惧、孤寂与无所适从,我过得挺快乐。
我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只要有一瓶白酒、两包咸菜、一根火腿肠,我的夜晚就是快乐的。我一边喝酒一边打量街景:我喜欢坐着轮椅的老人、挺着啤酒肚的男人、挎着坤包的女人、踩着滑板的孩子;我喜欢路灯投下的光影、汽车溅起的污水、男人打出的酒嗝、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我喜欢马缨花的香味、流浪狗的气味、汽车尾气的味道、女人随风飘过的香水味。城市里,一切都是美好的。我喜欢这个小城。
可是我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汗味,这让我非常难堪。
清晨,我用冷水将身体冲洗了一遍又一遍。从西城去东城的公共汽车上,我非常自信。我挤在人群里,身体轻轻地晃,轻轻地晃,这让我想起母亲的摇篮。我迷恋这种感觉,我愿意被这种迷恋所欺骗。
可是黄昏,当我裹着一身臭汗回来,我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我尽可能地躲开人群,尽可能离他们的身体远一点,再远一点。然而,我仍然会看到他们厌恶的表情。他们或扭过脸去,或捂住鼻子,或打开窗户,或干脆下车。每当这时,我都感到非常尴尬。仅仅有一次,一身臭汗的我被挤到一个女人的身旁,那女人看看我,非但没有面露厌恶,还冲我笑了一下。那一刻阳光明媚,我认为全世界的花儿都在那一刻开放了。
我常常想,假如我不必流汗,我就会像城里人一样,每时每刻都干干净净,或许我还会往身上喷点儿香水,淡淡的,甜甜的,若有若无的,丝丝缕缕的,仿佛站在槐花丛中。那样的话,我会靠近每一个城里人:老人、孩子、男人、女人。我喜欢漂亮女人,我喜欢靠近她们。喜欢靠近她们,仅仅是因为她们让我感到幸福。
现在我被挤到一个小角落里。本来我站在门边,可是乘客越来越多,我努力与他们拉开距离,就退到了角落里。然后,一个男人挤过来,我看到他的嘴巴里镶着一颗漂亮的假牙。他看着窗外,突然锁紧眉毛,扇动鼻翼。他扭过脸来,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他的表情,让我极不自在。
“你身上的味儿?”他问我。
“我刚干活回来……”
“我是问,是不是你身上的味儿?”他有些不耐烦。
“我住西城。”我说,“工地上不能洗澡……”
“真啰唆。”他近在咫尺地盯着我的鼻子,似乎随时可能将我的鼻子咬掉,“我问你,是不是你身上的味儿?”
“是……”
“真是没素质。”他冲我瞪瞪眼睛,“离我远点!”
我非常想离他远点,非常非常想。可是那时候,我早已被挤得动弹不得。
“车上太挤。”我低下头,说,“等再过几站,车里腾出地方……”
“那你快下车!”他说,“这么小的车厢,被你弄得臭烘烘的。”
“可是,我得到西城才能下车……”
“我让你下车!”男人冲我吼叫起来,“你想把大家都熏死?真他妈没教养!”
我不敢再说话,更不敢再看他。车厢里静悄悄的,我知道大家都在看着我。我还知道,那些眼神太复杂:怜悯、好奇、漠然、愤怒、幸灾乐祸、兔死狐悲……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我还知道,他们并非都是城里人,我相信,他们中间,至少有一半人刚刚来到城市。
我理解他们。他们没有必要帮我,他们也厌恶我的汗味,如同我也讨厌别人的汗味。世界上,所有难闻的气味都让人不舒服。
我下了车,一声不吭。我是走回宿舍的,路上,我买了一瓶白酒、两包咸菜、一根火腿肠。8站路,我走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不是我走得慢,是我太累了。可是我并不恨他。城里人都爱干净,我也爱干净;城里人都讨厌汗味,我也讨厌汗味。就是这样。
我只恨我自己。因为我的身上,总有一股难闻的汗味。
(吴雅琴摘自新浪网周海亮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