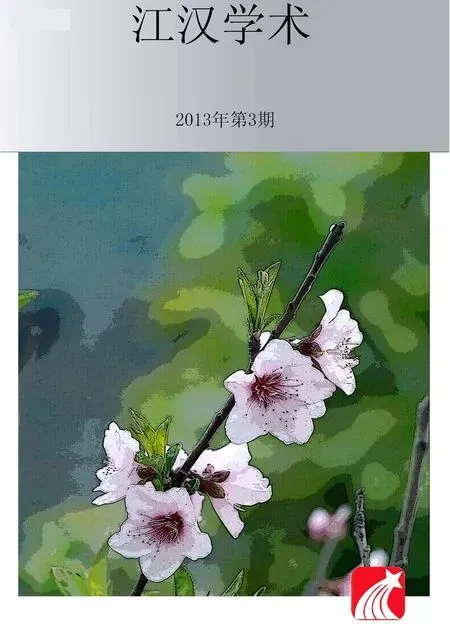新诗格律理论研究:进展与问题
——以刘涛《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为例
西 渡
(清华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84)
新诗格律理论研究:进展与问题
——以刘涛《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为例
西 渡
(清华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84)
现代格律诗学是现代诗学的核心和前沿问题之一,关涉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相关理论问题。在新诗诞生后不久,格律体新诗便和自由诗一起成为新诗的两翼,在彼此竞争、相互依存中共同推进了新诗艺术的精进。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现代格律诗学缺乏系统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不少以现代格律诗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问世,但这些著述和论文的成绩却还不能尽如人意。其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多集中于某一时段或某几个诗人、学者的格律理论的研究,缺乏对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的整体把握,或者虽有心做贯通新诗史的研究,但限于见识和材料掌握的程度或者囿于门户之见,存在重要的遗漏甚至偏见、谬误;二是理论把握能力不足,对现代格律诗学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和范畴概念缺乏系统梳理与辨析,以致不但没有在理论上对现代格律诗学建设有所推进,甚而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概念的认识上从已取得的成果后退;三是问题意识不够,对现代格律诗学牵涉的现代诗学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意识和理解,更无庸说做出高屋建瓴的阐释;四是没有在文献掌握和发掘上下苦功。以刘涛新近出版的《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为例,可探讨当下新诗格律理论研究在文献等方面的进展以及相关论述和判断上的不足。
新诗格律;现代格律诗学;新诗史;《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
新诗形式的探求是与新诗诞生同时开始的极富挑战性的理论与实践过程,这一过程迄今已持续近百年。格律新诗的探索虽然要稍晚一些,但从陆志韦1923年在《我的诗的躯壳》[1]一文中提出“有节奏的天籁”开始,这一过程也已持续整90年。陆氏之后,以新月诸人为中心的新诗形式运动成为格律新诗的第一个里程碑。此后,格律新诗便和自由诗一起成为新诗的两翼,在彼此竞争、相互依存中共同推进了新诗艺术的精进。相应地,新格律诗学(或曰现代格律诗学)也就成了现代诗学的重要部门,而且显然是其中牵涉最广、问题最多因而也是理论难度最大的部门。实际上,现代诗学的核心和前沿问题,包括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等,几乎都首先尖锐而集中地反映在现代格律诗学中。因此,现代格律诗学的探索历程不仅是新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广义的现代诗学中最前沿和最具活力的部分,其中不仅反映了新诗理论探索的履痕,而且突出显示了整个现代文学理论探索的层理和脉络。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现代格律诗学却一直缺乏系统研究。近年来,虽然有不少以现代格律诗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问世,也有以此为题做博士论文的,但这些著述和论文的成绩却还不能尽如人意。在我看来,在现代格律诗学的研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多集中于某一时段或某几个诗人、学者的格律理论的研究,缺乏对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的整体把握,或者虽有心做贯通新诗史的研究,但限于见识和材料掌握的程度或者囿于门户之见,存在重要的遗漏甚至偏见、谬误;二是理论把握能力不足,对现代格律诗学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和范畴概念缺乏系统梳理与辨析,以致不但没有在理论上对现代格律诗学建设有所推进,甚而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概念的认识上从已取得的成果后退;三是问题意识不够,对现代格律诗学牵涉的现代诗学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意识和理解,更无庸说做出高屋建瓴的阐释;四是没有在文献掌握和发掘上下苦功,一点有限的材料你有我有,螺蛳壳里做道场。令人欣喜的是,最近读到了刘涛先生的新著《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2]一书。这是一部精心撰写的巨构,在我所说的上述诸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刘氏此书煌煌四十余万言,不仅文献材料繁富、多新发现,而且视野开阔、见识透彻,抓住了现代格律诗学的诸多关键关节和问题,并能在此基础上对百年现代格律诗学的进展做出富有洞见的历史清理,可谓新时期以来现代格律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创获。
一、以文献为基石
刘氏此书最显见的一个特点就是文献材料的宏富。全书上及新诗初创,下及新世纪前十年,凡此期间关于现代格律诗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搜罗殆尽。在此书之前,刘涛就出版了一本现代文学文献考佚的专著《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3],收入现代作家、诗人散佚诗文七十多篇,在现代文学文献考佚上取得突出成就。为了掌握现代格律诗学的相关文献,刘涛多年来下了很大的苦功。在此书后记中,刘涛自己交代,其材料准备工作2006年前后便已开始。为了查找相关文献,刘涛多次南下上海、镇江,泡图书馆,拜访相关学者,所下功夫至大且深。为撰写此书,在广泛搜罗、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刘涛专门撰集了近十万字的现代诗学论文目录(1917—1949),供自己随时翻阅参考。这大概是关于现代诗学论文的一个最完备的目录,本身就有学术和出版价值。以往关于现代格律诗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新月诸公,至多及于朱光潜、林庚、何其芳、卞之琳等人,此外便鲜有道及。这种研究状况致使现代格律诗学的整体面貌模糊,人们对它的前世(它的发生)今生(它的最新进展)都缺乏足够认识。刘涛此书可以说完全改变了这种粗枝大叶的研究现状。本书论及与现代格律诗学有关的诗人、学者,仅列名于目录的就多达38人。而在“《少年中国》诗人群的探索”、“《文艺杂志》同人的形式试验与探索”、“新时期的新格律探索”等章节下还涉及相关诗人、学者二十多人。全书论及的学者、诗人超过六十人,重点论及的即达四十余人。全书引用文献仅有关专著就达二百多种。在关于现代格律诗学文献材料的掌握上,刘涛此书毫无疑问属于首屈一指。
文献上所下的苦功带来了学术上的丰富创获。此书论及六十多位诗人学者,除少数大家比较熟悉外,梁实秋、王统照、潘大道、唐钺、刘梦苇、饶孟侃、于赓虞、陈启修、刘大白、梁宗岱、徐迟等的现代格律诗论都是近期才为学界所注意的,吴世昌、张世禄、程千帆、高名凯、孙毓棠、常风等与现代格律诗学的关系则是刘涛此书的新发现,胡乔木、许霆、鲁德俊、许可、丁芒、柳村、骆寒超、丁鲁、程文、程雪峰等人的现代格律诗论则可能是首次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对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刘涛此书在文献材料上也有新的拓展和发现。譬如林庚一直是现代格律诗学研究的热点,但以往的研究在材料上都限于其已经结集的诗论文章。刘涛此书则不仅利用了解志熙先生所发现的林氏散佚诗论,而且自己对林氏格律诗论也有重要考佚成果——首次发现了林庚刊于《厦大学报》1943年第2期的15000余字的长文《新诗形式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林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格律诗学思想的认识。再如叶公超和孙大雨究竟谁先提出“音组”说,过去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刘涛通过查核叶公超《论新诗》发表前罗念生、梁宗岱、朱光潜、周煦良等引证孙氏有关音节文章,发现均未提到孙氏有“音组”名称,而孙大雨首次提出“音组”概念的莎士比亚《黎瑘王》译序并非如孙氏自己所说发表于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2期(1931年4月20日),而是首发于重庆《民族文学》第1卷第1期(1943年7月7日)。这番细密的查证肯定了卞之琳关于叶公超提出“音组”概念早于孙大雨的看法,从而了结了一桩学术公案。此外,对罗念生、柳无忌、张世禄、程千帆、高名凯、孙毓棠、常风等现代格律诗学思想的研究,也都依赖于作者对其散佚诗论的发现。
文献的宏富带来了此书视野的开阔。从时间范围上说,此书上及现代格律诗学的胎孕期,考察了它和白话—自由诗学的渊源,下及新世纪,关注到它最新的进展,把百年间现代格律诗学的发生、发展、演进、转折的种种现象作了全面梳理。而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7年迄今的现代格律诗学的进展情况,作为整体的历史存在,过去学界鲜有道及,可以说正是刘涛此书让它们首次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研究对象来说,不仅包括了闻一多、孙大雨、林庚、朱光潜、何其芳、卞之琳等现代格律诗学的中心人物,也纳入了很多以往一直处于边缘、不为学者齿及的边缘人物,如李思纯、饶孟侃、梁实秋、刘梦苇、罗念生、柳无忌等等,更可贵的是还把新诗界以外的一些学者——如王力、张世禄、程千帆、高名凯、吴世昌等语言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有关现代格律诗学的成果纳入研究范围。正是这种开阔的视野为此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保障。
二、整体观与问题意识
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全局观和整体意识。刘涛认为,现代格律诗学是中国传统汉诗形式被破坏之后一种普遍蔓延并逐步加剧的“形式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形式重建”的产物。它是一种“正在生长的诗学形态”,“正处于生长、发育、变异之中”,“新诗形式重建问题没有解决,则此‘新形式诗学’将一直持续,因而,围绕新诗形式重建与再造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的一切努力,皆可纳入‘新诗形式运动’与‘新形式诗学’的范围内予以考察”。[2]1-2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刘涛对于“现代格律诗学”的全局观和整体观。由此,“现代格律诗学”就不是某些诗人、学者出于个人兴趣与偏好而发生的若干彼此孤立的关于新诗格律的探讨,而是现代汉语诗歌寻求自身形式重建的一个有机的、持续的历史进程,并因而具有自身孕育、发生、生长、发育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一有机的、内在的过程也不断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能改变其内在的生长机制,而只是作为其生长的环境因素发生作用。本书显在的任务是梳理新诗诞生百年来“现代格律诗学”渊源、流变的历史进程,其潜在和隐含的目标则是揭示这一历史进程的内在生成过程及其隐秘的机制。
在这样的整体视野下,现代格律诗学“生成——转换的大脉络和发展——演进的大阶段”[4]4乃如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一样豁然显露,而其前后左右的关联与差异也得以纤毫毕露地显形。刘涛在吸收解志熙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现代格律诗学从一种独特的新诗观念,到成为一种与白话—自由诗学相抗衡的新诗理论,再到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新诗学的生成过程,把现代格律诗学从萌芽、产生迄今的百年历史分为七个阶段:从1917年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并提出“增多诗体”的主张到1925年刘梦苇发表《中国诗底昨今明》为滥觞期;从1926年4月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副刊·诗镌》发起新形式运动到1932年7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1932年9月柳无忌等主编的《文艺杂志》相继停刊为生成期;从1935年底梁宗岱等人在天津《大公报·文艺》编辑“诗特刊”到抗战开始为发展期;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艰难求索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开始为大发展时期;从1977年臧克家发表《新诗形式管见》到1990年代初为复苏与总结期;从1994年雅园诗派诞生到2010年丁鲁《中国新诗格律问题》出版为总结期。以上七个时期构成了全书七章的基本叙述框架,而其叙述的动力则是把现代格律诗学视为一种生长的诗学形态的整体史观。
刘涛关于现代格律诗学的上述历史断期和命名未必都为定论(例如把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称为现代格律诗学的大发展时期就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将1977年到2010年的最近时期以1994年为界断为两个时期也不尽合理,尤其把1994年以后的阶段称为总结期更值得商榷——“总结”似乎带有“终结”的意味,就与作者一直强调的“现代格律诗学”的未完成性相抵牾),但无疑体现了作者试图把握历史进程的努力,也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洞见和学术胆识。在这一叙述框架下,现代格律诗学不再是一堆散漫的、凌乱的材料,而是一个有机的生成过程,从而让历史的内在逻辑在叙述中得以显形。例如,把1917年到1926年《晨报副刊·诗镌》创刊之前的一个时期视为现代格律诗学的滥觞期纳入现代格律诗学的考察范围就很能见出作者眼光,有助于认识现代格律诗学与初期白话诗的形式危机的内在关联。过去谈新诗格律多始于《晨报副刊·诗镌》的创刊,至多上推到陆志韦《渡河》的出版,这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格律诗学与白话—自由诗学的渊源关系,从而掩盖了现代格律诗学作为新诗形式焦虑的产物这一根本属性。而把1935年到抗战开始的一个阶段视为“以京派为主体的现代格律诗学的发展期”,充分关注了以朱光潜、梁宗岱、叶公超、林庚为首的京派诗人、学者对现代格律诗学的贡献及其承上启下的关节作用,正如解志熙在此书序言中所称赞的,“超越了学界既往的看法,显示出独立思考的学术胆识”[4]4。对“十七年”格律诗学的关注,也显示出作者的独立判断力。依我个人的看法,把“十七年”视为现代格律诗学的“大发展时期”,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这一段关于新诗格律的讨论固然极多,但理论上的进展并不多——孙大雨、林庚、王力的格律理论在上一阶段其实已经形成,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主张则没有超越朱光潜、孙大雨已有的成果,这一阶段的理论进展主要体现在卞之琳的说话型节奏和哼唱型节奏的区分和参差均衡律的发现。但此一时期确实是现代格律诗学发展、转换的一关键期,其牵涉的问题甚广,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民族形式问题,新诗传统问题,传统与现代、新诗与旧诗、自由诗与格律诗的关系问题,至今仍然在各种场合的诗学论争中不断复现。所以,对这一时期进行独立考察确有其必要和合理性。我想理解了此一阶段所发生的这些论争和问题的性质,也就理解了当今诗坛的泰半。在“十七年新形式诗学”一章中,作者对上述问题都有很好的梳理。1977年以后的新诗格律理论则是此书首次纳入学术视野。刘涛此书第一次总结了这一时期新诗格律理论的主要进展,显示了作者超前的学术眼光和理论自信。“新时期的新诗格律探索”和“以‘雅园诗派’为主体的新诗格律探索”两章无疑是本书的重要创获。当然,由于鲜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这两章存在的问题也是全书各章中最多的,此待后文讨论。
此书还有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在论述中,作者始终把新诗格律视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由此也就把现代格律诗学的历史转化成了一部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史。在作者看来,所谓现代格律诗学主要就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视觉和听觉的关系问题,节奏的成因问题,齐言与齐顿的关系问题,建行问题,“半逗律”理论的评价问题,说话式节奏与歌唱式节奏问题,语言与诗歌形式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历史的梳理是本书叙述的显在线索,那么以上问题的展开就构成了本书叙述的内在线索。应该说,刘涛列举的上述问题确实抓住了现代格律诗学的关键。本书探讨现代格律诗学近百年的历史进程,涉及相关学者、诗人六十多人,中间包括众多的事件和现象,而全书的叙述脉络清晰,条例分明,这一内在的叙述线索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述问题意识不但使本书的叙述获得内在动力,而且在辨析研究对象的格律理论时,也总能帮助作者抓住其核心思想,从而恰如其分地总结、分析他们对现代格律诗学各自的独特贡献和问题、不足。作者对闻一多格律主张包括其隐含的理论问题的辨析,道人所未道,解志熙先生在序言中已道及。在分析叶公超的格律思想时,作者抓住了叶氏对音义关系的探讨和说话的节奏两个主要贡献;对孙大雨,着重阐述其音组理论;对李广田,则以其形式理论和对新诗散文化的批评和剖析为中心;对何其芳,主要介绍其“现代格律诗”的命名和主张;对卞之琳,着重阐发其说话型节奏和哼唱型节奏的区分和“参差均衡律”。事实上,作者的问题意识所带来的思想锋芒和理论见识,我们可以从他对各个研究对象的格律思想的辨析中不断领略到。在对朱光潜、林庚格律思想的辨析中,尤可见出作者的学术功底、判断力和理论思辨能力。
在探讨朱光潜格律理论一节中,作者以《诗论》为中心考察了朱光潜格律理论的主要思想。在这一考察过程中,作者牢牢把握了朱氏格律思想的核心和创新之处:一是从学理层面为诗歌格律辩护,探究其哲理的和历史的根源(“形式实质同一说”、格律的“自然律”与“规范律”、声律运动的历史的因果线索);二是对诗歌音乐性质的辨析,诗、乐的异同;三是音顿理论(四声与节奏关系的研究,顿的性质和作用,韵与节奏的关系)及其与同时或此前相关声韵理论的异同。事实上,即使在朱光潜这样的大家面前,刘涛也没有放弃提问和独立思考。在考察朱氏以“形式实质同一说”作为格律的理论依据时,作者及时揭出了其中的内在矛盾:“形式实质同一说既可证明诗有其与散文不同的形式,同时由于形式与实质有绝对的同一关系,这样一来,每首诗为了表达其独有的实质,就必须自创一格律,决不能因袭陈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诗的格律。……因此,为了弥补其理论上的缝隙,他对自己的‘诗的形式起于实质的自然的需要’的观点又做了否定,认为‘形式与实质并没有绝对的必然关系’。这不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吗?”[2]144在指出朱光潜格律学说这一内在矛盾之后,作者接着介绍了朱氏在《谈美》一书中提出的格律的“自然律”与“规范律”,并指出它正是朱氏弥缝上述内在矛盾的努力,从而揭示了两者的逻辑联系。最后,以语言学家张世禄对《诗论》的批评作结。张氏的《评朱光潜〈诗论〉》一文既肯定了《诗论》的总体成就,但也对《诗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提出商榷,指出了朱氏有关声韵与诗歌节奏关系的若干缺失。在这一个过程中,作者引领我们从多个角度考察朱氏的格律诗学,从而更为完整地理解其格律诗学体系。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揭示出朱氏格律诗学的现实关怀:“朱光潜全部诗学活动建立在对于传统的依恋与皈依的情感基础之上”,其中饱含朱氏对中国文化传统“送终绝命”的忧心[2]135。从朱光潜这样一个以西学为根柢的学者著作中读出这种忧心,充分见出作者眼光的敏锐。
对林庚形式诗学的批评见于本书第三章第四节和第五章第三节。“半逗律”和建行理论,一直是探讨林庚形式诗学研究的重点,本书也以主要篇幅介绍了林庚这两个独创性的理论。但对它们的评价,作者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审慎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在第三章第四节,作者指出,“林庚形式诗学中,最易招致批评的地方,是他对于诗行字数过于机械的限定,以及新音组字数过长(五个字)所导致的诗行过长。字数限定过死,虽然外形整齐,但又失去了参差错落之美。……诗行变长,是否就是诗歌发展的趋势?很值得怀疑”[2]199-200。第五章第三节又指出,“林庚的理论体系对于‘民族形式’的理解过于拘泥,且有等音计数之嫌,其九言诗不过是传统‘七言’体的放大,在实践中的操作性与有效性到底有多大,值得作进一步观察”[2]306。但对林庚的理论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留有余地:“林庚的理论作为与‘音顿’或‘音组’不同的理论体系,是对后者的有益补充与竞争……新诗形式建设,仍然处于初期探索阶段,任何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在其合理性没有被历史和实践完全否定之前,都有其存在价值,林庚的建行理论,由于其所具有的理论代表性、原创性及诗性特色,就更应该得到认真的对待。”[2]306-307这种判断就显得既有理论主见,又不失审慎。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关注了林庚的半逗律和建行理论,而且注意到了林庚早年关于自由诗性质及其与现代性关系的探讨以及林庚对于诗歌“形式哲学”的探讨。其实,林庚在现代诗学上最大的贡献不在其半逗律和建行理论(正如刘涛所说,它们多半将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而在其“形式哲学”上的诸多新发现。林庚关于诗歌形式的容易说、跳跃说、解放说、普遍说至今仍然是关于诗歌形式性质的富有启发和独创性的界定。刘涛称之为“林庚作为诗人对于诗歌‘形式哲学’形而上的诗意感悟”,并给予很高评价:“由于诗人这种天马行空、洒脱不羁的直观感悟,林庚的诗歌形式哲学,才焕发出其独特魅力”,“这也是学人纯粹学理性的研究所无法取代的。”[2]195这种独立判断无疑显示了作者思考的深入。
三、 不足与局限
当然,此书也非完美,无论是结构安排还是在某些理论判断上都还存在可商之处。结构上最大的问题,是未能结合具体作品对现代格律诗学及其实践进行说明,此点解志熙在序言中已经指出,这里不再赘述。在理论视野上,我觉得本书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对新诗和现代性的关系关注不够;另一是对当代诗歌状况比较隔膜,进而导致对当代诗歌包括对当代格律诗学进展的某些评价和判断出现失误。我认为这也是目前一些研究新诗格律理论的著作普遍存在的问题,故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
对新诗和现代性的关系,作者是有相当意识的。在讨论林庚、何其芳、卞之琳和新时期格律诗学时,对此论题都有所涉及,可惜都未深入。更为遗憾的是,在“结语”部分总结现代格律诗学的核心问题时,也未将新诗、格律新诗与现代性的关系列入。可见,作者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够。正是由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它对现代格律诗学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是规定性的),导致作者对新诗和现代格律诗学的一些命题的理解和判断存在偏颇。其实,新诗与现代性的关系是新诗学或现代诗学核心的核心,也是现代格律诗学面临的主要理论挑战和理论难题。可以说,现代诗学、现代格律诗学的其他问题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或发生的。事实上,新诗的发生就是基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渴望和追求。在胡适的新诗设计中,现代性既是动力,也是目标。白话—自由诗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其合法性和新诗史主流地位的。因此,格律新诗要取得在新诗中的合法地位,就必须回应新诗现代性要求对它提出的挑战。而且格律新诗从它被提出那天起,从陆志韦、闻一多、徐志摩,到朱光潜、梁宗岱、叶公超,一直到林庚、何其芳、卞之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而当代格律诗学之所以变成自说自话,在当代诗歌创作实践中寂无回响,其根源就在于未能对这一挑战作出有效回应。本书未能对此线索有所总结是一大遗憾。
此外,由于未能充分理解新诗的现代性追求,作者对新诗与旧诗的关系、自由诗与格律诗关系的某些判断也存在可议之处。对新诗与旧诗的关系,作者的认识大致来说是清醒的。针对所谓“古新结合”的“新声体诗”和丁芒的“自由曲”,作者指出,“这些古新结合的作品,是否属于现代格律诗,还是值得慎重考虑的。因为,它们毕竟更接近旧体诗词,不应作为新诗来看待”[2]370,显示了敏锐的判断力。但对1930年代京派形式诗学、1950年代民族形式诗学的批评,就显得过于看重其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向往,进而将他们与骆寒超、吕进等人的“新诗二次革命论”视为一脉,无意中忽略了前者对现代性更加坚执的追求。其实,何其芳、卞之琳的格律诗学在民族形式的外表下掩藏的是对现代性的渴望——民族形式不过是他们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应对策略。而吕进等人所谓的“新诗二次革命论”对此显然缺乏自觉,因此,也就不可能对新诗建设有积极的贡献。艾青1940年代提倡“散文美”,也从根本上关乎新诗的现代性追求。诚如解志熙序言中所说,艾青之强调散文美和胡适强调“自然的音节”、叶公超强调“说话的节奏”、卞之琳强调“说话型节奏”一样,“实际上也就是主张用散文的句法来建构新诗的诗行诗句之节奏”[4]10,而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获得新诗的现代性活力。作者在相关论述中将“诗的散文美”简单理解为“散文化”,不免有买椟还珠之嫌。同样由于对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关注不够,在自由诗和格律诗关系的理解上,作者有时不免表现出某种本质主义倾向,不自觉地把格律视为诗的本质属性,并进而作为判断新诗是否成立的依据:“骆寒超指出新诗没有成立,其根源就在于‘没有一套规范原则来使自己定型’。确实,新诗要发展,要真正与旧诗词竞争,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格律(形式)问题。”[2]403书中多次流露出对骆寒超等人“衔接传统、重建诗体”观点的同情,并把弥合文言与白话、新诗与旧诗、自由诗与格律诗的二元对立模式视为目前新诗发展的趋势。“衔接传统、重建诗体”的努力固然值得同情,突破诸种二元对立模式也是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这种努力和愿望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有利于新诗自身的现代性的展开。只有在此前提下,这种努力和尝试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就会妨碍新诗自身本质的实现。实际上,新诗与旧诗的竞争,主要是基于现代性的竞争,新诗的成立并不依赖建立一套规范原则来使自己定型,而主要依赖其自身的现代性的确立和展开。用诗人臧棣的话说,新诗和旧诗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系统,新诗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美学空间的自我生长。新诗和古典诗歌传统的联系,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发挥积极作用。[5]一个新诗人,尽可以从古典诗歌传统中去获取他的语言资源、题材甚至诗意感受,但是其作品的价值却取决于他对新诗现代性的推进和贡献上——这个推进主要体现在新的意义、新的诗意的发明和发现。因此,现代格律诗学所追求的形式重建必须以有利于新的意义、新的诗意的涌现为标准,而不是相反。
该书存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对当代诗歌状况的隔膜。在谈到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状况时,作者多次使用“危机”、“失范”(原书误为“示范”)、“失控”、“迷途”等判断,例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自由诗越来越处于强势状态,新诗的形式由示范(当为‘失范’)到失控,新诗声誉在一般民众眼中越来越不佳”[2]15;“新诗日渐加剧的危机状态”[2]16;“当前诗坛面临严重危机,诗人自娱自乐,读者越来越少,向歌诗传统回归的声浪越来越高”[2]40;“90年代现代格律诗的发展,一方面带有与自由诗竞争的意味,一方面也带有试图通过形式重建,以改变新诗危机状态,引领新诗走出迷途”[2]368。这些判断都颇成问题。事实上,从1970年代末朦胧诗兴起以来的三十多年,是新诗史上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最多、总体成就也最突出的时期。我以为这个时期新诗的突出表现有三:一是新诗在这个时期终于完全摆脱了对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依傍,从模仿转入了创造;二是伟大的诗歌抱负开始在优秀诗人心灵中生根;三是创造活力纷呈。总之,这个时期的新诗体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也许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新诗的南北朝时期,它虽然还没有达到唐诗那样的充分成熟,但却是一个诗歌的可能性不断被发现和激发,一个朝向未来蓬勃生长的时期。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推翻这种主观的判断。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1994、1995年分别开始印行《舒婷的诗》《海子的诗》,其后十多年间,前者发行了三十多万册,后者发行了二十多万册①。这样的发行状况可以说是诗歌离民众越来越远,声誉越来越坏吗?更重要的是,众多诗人和读者对新诗的感情真正称得上热爱,这种热爱是与一般人们对旧诗的喜欢完全不同的。旧诗和读者的关系是知识的和趣味的,新诗和读者的联系却是性命相关的。我们以生命和新诗发生联系,而仅仅以趣味和知识与旧诗发生联系,其间意义的轻重高低,是不难判断的。但如果把上述的危机判断移之于格律新诗,倒是大致符合实际状况的。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确乎成了自由诗的一统天下,写格律诗的优秀诗人绝无仅有(张枣大概就是仅有的例外),优秀的格律新诗也难得一见。但这种危机只属于格律新诗,而不属于作为总体的新诗——个中缘由确实值得现代格律诗的主张者和实践者认真探讨。如刘涛此前所说“由于自由诗越来越处于强势状态……”[2]15,似乎自由诗的强势就是新诗危机和声誉不佳的原因,这种判断恐怕更难成立。由于对当代诗歌的基本判断存在这种误差,也导致该书对新诗整体成就的判断出现偏差。在该书结语中,刘涛不仅对新诗已取得的成果表示怀疑,而且轻易同意了骆寒超关于新诗还没有成立的结论,我以为是该书的一大硬伤。
对当代诗歌状况的隔膜,也导致该书对现代格律诗学在当下的进展状态出现某些误判。刘涛认为,1990年代现代格律诗有两个标志性的重要事件,一是雅园诗派的诞生,一是“新诗二次革命”口号的提出。对前者,刘涛评价说,“雅园诗派是新诗历史上第二个大的现代格律诗派,它的出现,说明20世纪的新诗格律探索,进入又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2]15;对后者,刘涛认为是对“胡适革命的再革命,对诗体否定的再否定,由诗体破坏走向诗体重建”,“诗体的由破而立,由分到合,这一个‘圆’划了整整一个世纪”[2]403。对两者的评价都偏高。其实,所谓雅园诗派既缺乏优秀的诗人,也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优秀的作品,实难与当年的新格律诗派相提并论。事实上,“雅园诗派”的大部分作者对诗与新诗的性质都缺少基本认识,其作品很少具备基本的诗的质素。骆寒超等提出的“新诗二次革命”在我看来也是不通之论。如果以“诗体重建”、“重续传统”为“再革命”,这个再革命自新诗诞生以来不就一直在发生着吗?何须等到百年后由某人事后诸葛亮似的重新提出?而且本书研究的不就是这个“形式重建”的理论探求史吗?尤应引起注意的是,骆寒超的“二次革命”论建立于新诗还没有成立的判断上。这是对新诗史的严重误判,其判断依据则是其本质主义的格律观,以为诗的本质寄托于格律,新诗没有定型的格律则意味着新诗尚未成立。由于这样一种格律本质主义的诗观,骆氏既不能充分认识胡适新诗革命的文化和美学意义,也不能认识新诗诞生以来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轻易认同了骆寒超等人的上述观点,刘涛便以1994年雅园诗派的成立为界,把新时期以来现代格律诗学的探求断为两个时期,并把1994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称为“以‘雅园诗派’为主体的新诗格律探索”,把骆寒超视为这一时期“首次打破自由诗体与现代格律诗体的二元对立,对自由诗体与现代格律诗体的形式规范作了细致总结、规范、限定和阐发”[2]378的主要诗论家。这些判断都有待商议。当然,骆寒超在现代格律诗学上自有其贡献,但他重建诗体的具体主张却多有漏洞。骆寒超认为新诗节奏是推进式的,旧诗节奏则是回环式的。这个判断若纯从比较视野来看大体不差,但若细究,则还有可议之处。事实上,从《诗经》到楚辞已经发生从回环式节奏向推进式节奏的转换,到两汉五言诗的成立,这一转变过程已告完成,而近体诗则是在总的推进式节奏的基础上,在声律上重新引入了一点回环式节奏的因素。从回环式节奏向推进式节奏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诗脱离音乐的节奏向语言的节奏转变的过程。朱光潜的《诗论》对此过程已经揭示得很清楚。骆寒超认为回环式节奏要在新诗的形式建设中唱主角,把新诗的形式重建寄望于回环式节奏的复归,实际上是从语言的节奏向音乐的节奏倒退,违反了诗歌进化的规律。事实上,推进式节奏乃新诗命脉所在,新诗以现代性为核心的诗意的发明和发现主要有赖于此。令人可悲的是,不少诗人和新诗格律的倡导者在这个问题上长期陷于迷思,总是试图在新诗中复活旧诗的音律和节奏。这是忘记了新诗自身的文学和美学使命,也忘记了新诗音节和旧诗音节的语言基础已有巨大不同。我认为,这正是格律新诗陷于衰微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 《舒婷的诗》《海子的诗》发行量是笔者在2011年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编辑的颜炼军、王晓谈话中得到的信息。
[1] 陆志韦.我的诗的躯壳[M]//渡河.亚东图书馆,1923.
[2] 刘涛.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索——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刘涛.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解志熙.《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索》序言:精心结算新诗律[M]//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索——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J].文艺争鸣,1998(3).
2013-03-31
西 渡,男,浙江浦江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中国计划出版社编审。
I052
A
1006-6152(2013)03-0049-07
责任编辑: 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