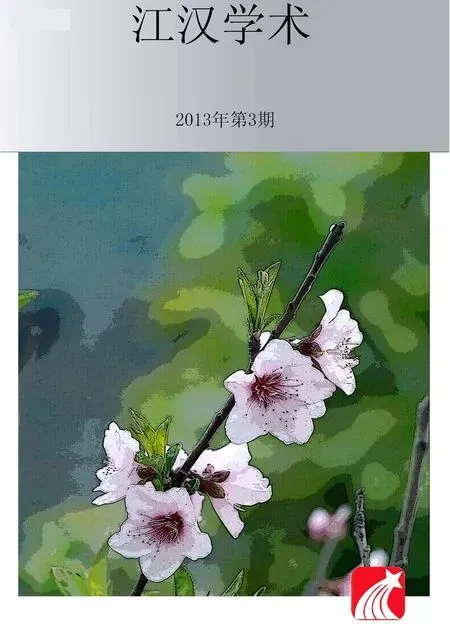迎向诗意“空白”的世界
——论现代汉语新诗咏物形态的创建
颜炼军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杭州 310012)
迎向诗意“空白”的世界
——论现代汉语新诗咏物形态的创建
颜炼军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杭州 310012)
现代汉语新诗自诞生起,就不再拥有古典诗所依靠的“原道”、“征圣”、“宗经”等形而上学基础,因而陷入了诗意“空白”的困境。在创建新的抒情主体,抒写新的世界的过程中,汉语新诗人创建了两类不同于古典诗歌的咏物形态:一类是在词语的建筑和发明中,寻找和经营“空白”,它们在咏物诗中常以否定式或悖论式的修辞策略进行诗意言说,对词与物的关系作了各种尝试和探索;一类则努力将来自革命的、民族主义或政治乌托邦的意义和声音本体化,作为咏物的基础,形成了一套影响巨大的意象结构。
现代汉语新诗; 抒情主体; 诗意“空白”; 咏物;意象结构
一、绪论
汉语新诗一直在努力走出古典诗传统退场后诗意“空白”的困境。其重要表现之一,是现代汉语新诗写作中对如何咏物的思考。汉语古典诗中的咏物诗,多为诗人的主体写照,比如屈原的《橘颂》开启的咏物自喻传统。在古典诗中,诗人的主体形象是清晰的,咏物诗往往就是主体与物性之间的直接投射,即陈世骧谈论古典抒情传统时说的“文学切身地反映自我影象”[1]。具体表现诗人对物的抒写,对应着一套成熟的感物言志方式,比如“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2]。
由于现代汉语新诗的创建与现代中国人的主体重建几乎同时发生,新诗咏物形态的创建,也与诗人主体的重建相辅相成:新诗咏物展开诗意的限度,取决于现代诗人主体心智的成熟度,反之,咏物的诗意建设,也会促进现代中国诗人的主体性重建。
我们可以在中西诗歌比较的背景下看新诗的咏物问题。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中西现代诗歌面临的问题有相似的背景:即,古典诗的言说内容和言说形式不再无条件地有效。在西方现代诗中,这普遍表现为对神性“空白”的修辞,即如何抒写尼采所说的上帝“死”后“虚无主义的降临”[3]——这是自象征主义以来整个西方现代诗歌的重要写作主题;而在现代汉语新诗中,则表现为对失去古典诗所依赖的形而上学基础(比如,刘勰说的“原道”、 “征圣” 、“宗经”①)之后的“空白”的抒写。在古典诗歌与世界的亲密关系解体之后,现代汉语诗人如何迎向诗意“空白”的世界,重建汉语的诗性空间,成为汉语新诗切实的困境。因此,现代汉语新诗的发生,在经历了由语言变革引发的文化运动的同时,开启了创造白话汉语诗意的运动。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现代汉语新诗创建咏物形态的过程。
以研究想象力诗学著称的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曾按亚里士多德的划分模式,将想象划分为形式想象和物质想象。他认为,在诗学阐释中,后者常常被忽视,而物的形象常常是想象的直接体现。他说“诗歌形象是一种物质”[4],也就是说,诗歌形象的重心之一在于,在词语中创建物的言语形象,即诗歌的咏物形态。汉语新诗中的物,如何逐渐具备不同于古典诗歌意象的咏物形态,成就汉语新诗的物质特征,是一个值得展开讨论的话题。
下面,我们将通过重释现代汉语新诗中如蝴蝶、圆宝盒、旗帜等一些经典意象,来勾勒汉语新诗咏物形态创建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其基本特征和类型。
二、“蝴蝶”翻开空白之页
在胡适的《尝试集》中,《蝴蝶》一诗经常被研究者提及。它虽简陋却不失意味,被视为汉语新诗草创期的名作。比如,废名有个著名的论点,说胡适《蝴蝶》这首诗里“有旧诗装不下的内容”。由此,他看出新旧诗的本质区别:新诗是散文的形式,诗的内容;而旧体诗则是诗的形式,散文的内容。[5]27本文也以此诗为切入点,来分析汉语新诗咏物形态的初始特征: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作者给这首诗最后的定名为《窗上有所见口占》,据作者关于此诗的后记和日记说明,此诗先后有过《朋友》《蝴蝶》等题名。这些更替,至少表明此诗不太好命名,主题不确定。由此可知,诗中的“蝴蝶”这一关键意象的寓意,在诗人这里没有被固定下来。[6]在诗中,寓意的获得常常依靠在传统文本和新的文本之间建立互文性,即用典,但胡适没有采取这一常见手段。他是在践行自己“不用典”的诗学宣言?也许,他觉得白话新诗袭用古典文化中的蝴蝶寓意是不合适的。即使梁实秋认为,此诗内容上不脱旧诗风味[7],但这也许只是基于形式的判断。在内容上,它的确不像那些随处是典故的古典诗。即使意义较为浅白,音韵结构相对随意的汉魏乐府,也与这首诗的味道相去甚远。
众所周知,关于蝴蝶,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两个著名典故:一个是庄周梦蝶的故事。其中的蝴蝶,常被理解为灵魂自由的象征,也被理解为“相”的虚无。法国汉学家爱莲心如此解释这个典故:“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化比喻,因为它预示着《庄子》的中心思想:你必须脱去陈旧的自我的观念,然后你才能获得一个新的自我。事实上,脱去旧的自我的过程,也就是取得新的自我的过程。”[8]在这首诗里,胡适似乎也想造就一个脱去旧观念的新“蝴蝶”,却不知将“新”落实在何处。另一典故,是将“蝶恋花”的场景比喻为情爱的自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就是这个典故的一部分。
在胡适笔下,这些原来被赋予蝴蝶的寓意,都不再具有作为新诗的“新”意了,如废名所说,这首诗中“仿佛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5]26。作者没被典故诱惑,而是对所见之物进行直观性命名:只写了眼前所见的两只不知何来何往的蝴蝶。②
质言之,与现代汉语新诗歌要重“写”的一切物一样,蝴蝶在白话汉语中只剩下自己,一个等待新的隐喻归所的自己。某种意义上,蝴蝶的无所依凭的“可怜”和“孤单”,象征了白话汉语创建属于自己的诗意的一个开端,也象征了彼时中国“现实”的孤单——一个缺乏可以栖身的意义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了某种诗意的“空白”感。③
作为内在于现代汉语诗人的焦虑,这种“空白”感不断地被命名、说出。比如,到诗人林徽因笔下,这种命名幻化为石头发出的歌唱:“石头的心,石头的口在歌唱”[9],与胡适的“蝴蝶”一样,这句不太被瞩目的诗,堪称现代汉语新诗处境形象的另一种写照。在汉语文化中,歌唱的石头常常是由某一等待的女性伤心过度而变成的,比如望夫石。④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蒙田在他的散文中就梳理过,古希腊以来西方传说中的女性是如何因为伤心而变成石头的。[10]歌唱的石头,意味着一种极度伤痛而导致的死亡,也意味着一种正在酝酿的艰难新生和永恒。就汉语新诗而言,我们可以将此间的石头理解为诗歌对物的生命复活的呼唤,一块块充满了心事的石头。
由于这种孤独的处境,促使现代汉语诗人不断在词语中创建各种咏物形态,召唤新的言外之意。1937年,卞之琳在《车站》一诗里,也写到蝴蝶之死。与胡适一样,他也没有返回蝴蝶的古典寓意中:
我却像广告纸贴在车站旁。
孩子,听蜜蜂在窗内着急,
活生生钉一只蝴蝶在墙上
装点装点我这里的现实。
在卞之琳笔下,孤独的处境被写得更细微。蝴蝶被钉在墙上,作为尸体“装点”诗人的诗意“空白”感;但诗人清晰的“装点”意识,也让此诗获得一种消极美感。这种双面性,形成一种比胡适更清晰激烈的诗意寻找的姿态:意义阙如的现代汉语诗人,通过展示主体位置的微茫,尽心地编织、说出这种诗意的“空白”感。戴望舒1940年5月写的一首小诗《白蝴蝶》,也直接地透露出类似的“空白”结构:
给什么智慧给我
小小的白蝴蝶,
翻开了空白之页,
合上了空白之页?
这里的“智慧”,是不是故意对庄子智慧的呼应?对汉语读者来说,至少可以朝这方面联想。但作为现代汉语诗人的戴望舒,却避开了这种可轻易获得的意义取向,他继续指向此前已经明示的“空白”:
翻开的书页:
寂寞;
合上的书页;
寂寞。
这首诗歌收在诗集《灾难的岁月》中,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诗人作为个体在民族危机和战争处境中的诗意窘境:蝴蝶作为日常之物,它身上的古典象征意义已经不能与现代诗人的处境匹配,陆机总结的那种“颐情志于典坟”的古典诗文创作姿态(诗中的“书页”可能是相关知识典故的象征),在身处战火和逃亡中的戴望舒这里,只能带来一种深刻的寂寞和茫然。但是,诗人正是以写出这种寂寞和茫然,表明他强烈意识到蝴蝶的诗意“空白”。
三、“圆宝盒” 展开的色相
在现代汉语新诗中,有一类以器物为咏写对象的诗歌,典型地体现了诗意发明中的“空白”抒写意识,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分析视角。
为了理解汉语新诗抒写这些物的方式背后的玄机,我们可以稍微回顾古典汉语诗学的“比”、“兴”观念。据现代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推究,“兴”的本义之一为“举物环舞”,而所举之物,是用于祭祀的圣物。“兴”就是通过所见之物,与看不见的无限或神明发生关系的仪式。[11]如果我们把现代汉语新诗咏叹“器物”的言语行为,视为一种原始之“兴”的现代变奏,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汉语新诗中的咏物,在与什么样的言外之意产生共振?
我们先随意读一首关于器物的作品。比如早期在日本追随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冯乃超在1927年写的《古瓶咏》,这首诗显然受到过英国诗人济慈名作《希腊古瓮颂》的影响。关于西方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已经有汗牛充栋的研究论著。我们只须注意,汉语诗人所择取和采集的西方诗歌技艺和元素,一定是汉语新诗自身的拓展需要或缺乏的,在此诗中亦然。在西方近代科学兴起之际,浪漫主义诗人纷纷寻找新的美学资源,主张以想象力创造新的艺术神话,以抗衡科学神话对于人类存在的诗性之美的侵蚀。⑤在这样的背景下,济慈将希腊古瓮上甜蜜的牧歌和情爱画面抒写为一副永恒的神话,创建了一首西方咏物诗的典范。然而,济慈通过咏物凝聚的神圣和永恒,到冯乃超这里,却没法被改写为与所咏之物相互回响的言外之意:
金色的古瓶
盖满了尘埃
金泥半剥蚀
染上了黯淡的悲哀
……
金色的古瓶
盖满了尘埃
诗人的心隈
蔓着银屑的苍苔
诗人描写出关于古瓶的一幅幅画面,但各节的画面之间缺乏一种穿越性的凝聚力。对这位把民族情绪直接转移到诗歌中的早期左翼诗人来说,面对业已毁弃的辉煌历史和满目疮痍的当下,他还不能以咏物来创建清晰的寓意和命名机制,将历史的断裂在语言中弥合。他诗心疲倦,描写古瓶要表达的寓意不清晰,寻找寓意的姿态也是散乱的。诗人所依存的现实之难,没有成功地转换为诗歌写作的困难意识。这正是早期汉语新诗面临的共同困难。
相比之下,卞之琳1937年写的名作《圆宝盒》,却清晰而玲珑地说出言外之意的“空白”,比起胡适笔下的自然物象“蝴蝶”,卞之琳的这首咏物诗发明了新的“空白”命名机制,显示出清晰的写作意识。为方便读者,我们引全诗如下:
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
捞到了一只圆宝盒,
装的是几颗珍珠:
一颗晶莹的水银
掩有全世界的色相,
一颗金黄的灯火
笼罩有一场华宴,
一颗新鲜的雨点
含有你昨夜的叹气……
别上什么钟表店
听你的青春被蚕食,
别上什么古董铺
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
你看我的圆宝盒
跟了我的船顺流
而行了,虽然舱里人
永远在蓝天的怀里,
虽然你们的握手
是桥!是桥!可是桥
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
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
或他们也许就是
好挂在耳边的一颗
珍珠——宝石?——星?
这首诗开头,诗人没有直接描述“圆宝盒”本身的特征,却通过想象中的珍珠,从大到小地赋予了“圆宝盒”的内部世界三重内容:“全世界的色相”、“一场华宴”和“你昨夜的叹息”。它们分别对应宇宙、人间和个体,圆宝盒因此成为一个“圣物”。为什么说是“圣物”?《易大传》中对圣的解释是“广大悉备”,熊十力对此的解释是“夫广则无所不包,大则无外;悉备则大小精粗,其云无乎不在”[12],巴什拉对于圆之奥妙的描绘,可作为熊十力关于“圣”概念的阐释的补充:“浑圆的形象帮助我们汇聚到自身之中,帮助我们赋予自己最初的构造,帮助我们在内心里、通过内部空间肯定我们的存在。”[13]“圆宝盒”凝聚多层含义而不拘一格,因此具有上述“圣”的特征。这样的意义结构,给追求清晰为目的的阐释学带来了挑战。按释诗的古典法则,我们要通过字面意义来寻找“圆宝盒”的寓意,即孟子以来被反复谈论的“志”。而我们却发现,此诗的所展示的,是“圆宝盒”如何躲开各种可能的“寓意”之笼的过程。
卞之琳曾如此描绘《圆宝盒》:“这首诗,果如你所说,不是一个笨迷,没有一个死板的谜底搁在一边,目的并不要人猜。”[14]这就象戴望舒《烦忧》一诗中表达的美丽困惑:“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在卞之琳这里,“说不出”的,呼应着对已“说出”的内容的否定,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形而上学气质的“空灵”。“‘空’是空虚,‘灵’是灵活。与空相对者是实,与灵相对者是死。”[15]哲学家冯友兰如是说过。卞诗中的连续否定,谜底的“缺席”和“空灵”,就像英国画家约翰·伯格论画时所说:“真正的画触及一种缺席——没有画,我们或许察觉不到这种缺席。而那将是我们的损失。画家持续不断地寻找所在,以迎接缺席之物。他若找到某个地点,便加以装饰,祈求缺席之物的‘面孔’显现。”[16]卞之琳也不断地展示寓意的“缺席”感,以此祈求“缺席”的面孔出现。一切没有说出的,都在呼求被肯定。而肯定的方式就是不断地指出,诗歌说出的远不是诗歌想要说出的。诗歌之说,最终要呼吁那没有说出的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将“圆宝盒”视为诗歌语言抵达事物的梦想。
进一步说,这首诗里显示了现代汉语新诗三重梦想:对现代世界的得体命名(全世界的色相),对人间(人间的华宴)的命名,对个体的命名(你昨夜的叹息)。“你”是前二者的具体化,甚至可以理解为情爱话语、知音话语或与自我的对话。人都要通过理解最亲密的人或事物理解更广阔的世界,通过理解自己而理解世界。由这三层意义的并置,可以看出,诗人不愿让诗歌的私语性局限于情爱话语,如果联系现代汉语诗人的处境,这种私语性体现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孤独,甚至是知识分子“风雨鸡鸣”式的孤独。
如果只从诗意层面看,则可以更多元地理解这种孤独。省略号在此很有意味:圆宝盒中可以容纳更多“珍珠”,恰好表明了圆宝盒的真正寓意的“缺席”。它无所不包,才使对它的命名愈加困难。总之,“圆宝盒”此前对应的象征意义,甚至是此前的一切诗意形态,都被诗人一一否定了:“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古董铺/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我们可以对这四行诗作如下误读:前两行,似乎是诗人对泛滥的新诗浪漫主义爱情话语的轻微嘲讽,后两句则是对新诗因袭旧诗的警惕,质言之,“圆宝盒”作为诗歌的隐喻,它应该全然不同于以往。反之,我们也可以说,这四行提出的两种否定的过程,正是诗歌自我展示的悖论修辞:诗人在尽力否定他展示的精美,让一切说出来的美,随后即陷入不稳定之中。他试图直接展现他的“圆宝盒”:“你看我的圆宝盒/跟了我的船顺流/而行了,虽然舱里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虽然你们的握手/是桥!是桥!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圆宝盒”所要包含的“我”、“蓝天”、“你们的握手”、“桥”之间的连接,呼应了本诗开始四行之间的关系,更细致地发明主体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新命名。诗中出现了明显的典故:永远在蓝天的怀里的舱里人,让人想起古人“乘槎犯斗”等泛舟登天的典故。⑥而诗人写的“桥”,显然也源于牛郎织女鹊桥相间之“桥”。但在这里,诗人在“你们的握手”与“桥”之间,直接用谓词“是”连接,产生的更具普遍性的联想效果,冲出了“握手”的情爱话语限定。
对于卞之琳化用古典诗的能力,许多论家已经有过详述,在此不表。我想说明的是,这些代表古典诗歌崇高性的咏物特征如何与诗人的现代体验有效结合?诗人对此小心翼翼。难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最后应该给予圆宝盒什么样的定格,只能用一种情爱话语结束:一切曾经足以与“圆宝盒”匹配过的象征意义,都不足以再与之匹配,而也许只有情爱话语能够得上一种最为空前的意义感,成为圆宝盒的最后象征落脚点。但是,诗人显然对这种浅薄浪漫主义式的单一情爱话语有足够的警惕,因此他以疑问句结束全诗:“或许他们也许就是/好挂在耳边的一颗/珍珠——宝石——星?”结尾的问号,与诗开头的问号相呼应,而“星”字,也与“天河”呼应,让“圆宝盒”的暗喻指向,也偏离了情爱话语,将整首诗引入一个修辞的谜团:“圆宝盒”到底“是”什么?它可能“是”的,都已经否定,它最后“是”的,也被怀疑。
总之,整首诗就是一个悖论修辞:与其说它展开了诗人想说的“圆宝盒”,不如说,它在展开与否定的交替中,一边把发生在不同时空中的事件和变故混合于现时刻之中,一边结束了作者对附着在“圆宝盒”上的崇高性的质疑和寻找,诗歌标题告诉我们的那个“圆宝盒”没有在语言中获得一个肯定性的形象。这种诗意结构,是现代诗人早就注意到的:“就是最好的字句也要失去真意,如果它们要解释最轻妙、几乎不可言说的事物。”[17]“它们将自己觉得重要的东西包裹在神秘之中,掩藏起来只留给自己;它们将其掩藏在深处,用这种方式来指明它和保护它。”[18]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类比的角度来理解这首诗的意义指向。斯宾诺莎说:“凡是与他物有关的东西——因为自然万物没有不是相互关联的——都是可以认识的,而这些事物的客观本质之间也具有相同的关联。换言之,我们可以从它们推出别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与另外一些观念有关联。”[19]卞之琳将诸多与“圆宝盒”有关联的事物一一玲珑地摆出来,并依靠这些事物驶向诗意命名的“空白”。由这些关联振起的重重暗示,让诗歌延展出一种参差流转的意义指向。现代认知语言学者认为“类比基于世界的部分结构的相对不可辨性”[20],诗人也以一连串不可辨的类比修辞结构,簇拥着那给未被直接、肯定地具体化的“圆宝盒”。马拉美说:“把一件事物指名道出,就会夺去诗歌四分之三的享受,因为这享受是来自于逐点逐点的猜想:去暗示它,去召唤它——这就是想象的魔力。”[21]
另外,“圆”也是一个特殊的字眼,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咏物的理想。钱锺书考证过“圆”这一概念的意义源流。他认为无论在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中,还是儒道释传统中,乃至在诸多中西诗歌作品中,对“圆”都有近似的用法和理解。[22]比如,诗人瓦雷里有一首诗《圆柱颂》,与《圆宝盒》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卞之琳那一代诗人大都读过。瓦雷里这样来写圆柱的自白:“我们的黑眼睛里/有一座庙宇,那便是永恒,/我们不把上帝放在心上/而去朝拜神圣!”[23]显然,瓦雷里“圆柱”指向的,是“缺席”的“上帝”和“神圣”。但卞之琳在谈论《圆宝盒》时说出了它所指向的“空白”:“至于‘宝盒’为什么是‘圆’的,我以为圆是最完整的形相,是最基本的形相。”按卞之琳的说法,这是一种不能看“死”的“内容”:一切都是相对的,都寄于诗人的意识和诗人的“圆宝盒”[24],寄于一种新的词与物的关系之中。哲学家牟宗三在谈论佛教中“圆教”翻译成西文的困难时曾也说过“圆”在汉语语境中的独特意义:不止是圆通无碍(round),还有圆满无尽(perfect)[25]。了解“圆”在汉语中的意韵,就不得不更加赞赏《圆宝盒》的对汉语新诗的意义,它表达了出一种不依赖于革命象征体系,也不膜拜古典汉语诗意的新的汉语抒情的崇高感,这在现代汉语诗中并不多见。
在以上几层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圆宝盒》理解为对词与物的关系的再一次改写。诗歌标题中的几个元素:“圆”、“宝”、“盒”,前两个字让我们感到了诗人的汉语诗意理想,而最后一个字,则可以理解为——这用最吉祥、福乐,最饱含已经消逝的汉语之甜的字眼命名的理想,永远栖身于一个不能完全打开的语言盒子之中。里尔克说,真正的诗人的基本特征是“使可怜而疲惫的词汇焕然一新,使它们恢复处子之身,年轻而丰饶”[26]。卞之琳这首诗中的“圆宝盒”正是这样一个焕然一新的词汇。与“圆”这个字相关的意象,在最好的现代汉语新诗中不止一次出现。比如,卞之琳的《白螺壳》,袁可嘉的《空》里,也出现了这一概念,这都是现代汉语诗人处理诗意“空白”过程中,创建咏物能力的体现。
四、“旗帜”收容的远方
这种对创建咏物能力的尝试,在冯至著名的《十四行集》的最后一首中,表现为另一种激烈:
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
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
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
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
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
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
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
还有个奔向远方的心意,
都保留一些在这面旗上。
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
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
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
但愿这些诗象一面风旗
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在这首诗中,冯至也以一个与卞之琳相似的意象来开始:”椭圆的一瓶。”但与卞之琳以各种可能的比喻来“接近”“圆宝盒”,形成层层否定的推进不一样,冯至以对不同“物象”的递进式的把握,来反复撑开同一个悖论性的题旨:“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这被诗人视为27首诗的总结。同时,诗人也似乎要表明,对这些诗的命名很难,正如诗歌对事物的命名很难一样。在有些版本或选本里,会以第一行作为此诗的提名,如李商隐对《锦瑟》的命名一样。而有些版本或选本里,这首诗却是没有题名的。卞之琳以整首诗流转地“否定”自己的命名,写成了一个意义“空白”的“圆宝盒”,而冯至干脆不直接命名自己要写的内容。因为,正如他先后写出的物象“瓶”、“风旗”,是企图“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一样,全诗是在命名一些没法命名的事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这种语义分歧其实是一种悖论修辞。冯至在《十四行集》另一首诗中有一行诗也有比较浓厚的悖论色彩:“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语言哲学家认为:如果承认了命题A,就会推出命题非A,如果承认了命题非A,就会推导出命题A,就会出现悖论[27]42。比如:“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所有的话都是谎话。”[27]120卞之琳的《圆宝盒》和冯至的上述诗句也可以作如是观。这两诗令人着迷之处,正在于这种以悖论修辞推进诗意的方式:“当语言拒绝说出事物本身时,仍然不容质疑地说。”[28]对现代汉语新诗来说,物缺乏象征意义,或者意义缺乏象征物,它们往往在诗人的悖论言说中可以被焊接在一起。只是后者以更直接肯定的方式来说出悖论的处境,因此显得更有气势,在启用传统资源上更加直接和自信。
因此,在冯至的诗中,“瓶”、“风旗”两个意象都有意识地抒写具体有限的事物与浩大无限世界之间的悖论关系:后者如何呈现在前者之中?具体到诗歌写作的年代,则可以说,一个蜕变和新生中的民族,一个现代白话汉语的词语艺人,在古典传统分崩离析之后,如何以词语之躯重新把握浩大与无限?如何让个人的声音区别于集体主义神话,同时又能表达共同的困惑和希望?
许多论者已经谈论过里尔克诗歌中著名的“孤独的风中之旗”这一象征结构此诗咏物特征的影响,但为什么他受到的是这方面的影响,而不是别的方面?与此对应的是,诗人也在运用传统诗歌典故。比如,在第一行中,我们隐约看到庄子笔下“秋水”的影子,接下来的“风旗”意象,似乎也可以让熟悉古诗的中国读者想到李商隐“尽日灵风不满旗”这样的诗句。这种潜在的文本关系的构造,优化了诗人所营造的悖论修辞:被椭圆的瓶子和风旗两个物象抓住的一切意义,恰好是不明晰的,诗人对这不明晰的部分的描写,可以说是有意顾左右而言他:“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还有个奔向远方的心意”,诗句里的这些事物,可以理解为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迷茫与希望交织的象征;也可以理解为现代汉语诗歌为事物寻找寓意本身的迷惘与希望,理解为对词与物的关系的思索的呈现;更可以只理解为诗歌描写的世界画面本身。与卞之琳写《圆宝盒》一样,冯至在诗歌中所写之物,也在寻求自身的意义。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写出了一种精致的“寻找”,而这精致本身,正是现代汉诗最值得称道的新传统,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汉语新诗的诗意源泉。
“风旗”意象在其后的诗人那里继续被展开。比如1946年,同样受到里尔克影响的袁可嘉也写下了“我是站定的旌旗,收容八方的野风”[29]这样的句子。1947年,诗人穆旦也有一首名为《旗》的诗,与冯至、袁可嘉上述作品有部分的同构性。但在“寻找”的姿态上,开始出现相反的情形:“四方的风暴,由你最先感受,/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
在穆旦笔下,“旗”有了比较明晰的寓意。甚至具有一种预设的主题,支撑整首诗的诗意性。他不再像胡适、卞之琳和冯至一样,在词语的建筑过程中,渐渐呈现一种对于寓意的精致的“寻找”,而是让某个先入为主的意义,支撑诗歌的咏物形态,这就是穆旦的“新的抒情”。由此,民族的、集体的意义和声音摆在诗人们面前,占据了他们的诗心,催迫他们将这些先于诗歌的意义和声音,表现为诗歌的咏物言说。穆旦批评卞之琳的《鱼目集》,甚至认为卞的《慰劳信集》也缺乏“新的抒情”:它就是“诗歌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情感的大谐和……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他赞美艾青的诗歌,认为其诗作《吹号者》正是“新的抒情”的代表。
在穆旦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汉语新诗发生以来面临的“空白”得到了暂时的解决。因为他认为“现实生活”自身的意义,足以取代语言中的虚构、建构和寻找[30]。诗歌的使命,正在于充分地呈现它们。在这种写作意识的主导下,许多诗人的主体性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政治意识形态重叠,甚至淹没其中,进而构成了诗歌咏物的新形态。
五、结论
通过分析蝴蝶、古瓶、圆宝盒和旗帜等意象中的咏物形态,我们大致可见,在现代汉语新诗中物的诗意性形成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可以对现代汉语新诗的咏物形态类型作简单的区分。五四以来形成两类咏物形态:一类在词语的建筑和发明中,寻找和经营“空白”,它们常以否定式和悖论式的修辞方式来进行诗意言说;一类则努力将来自革命的、民族主义或政治乌托邦的意义和声音本体化,作为咏物言诗的基础,这类诗在民族危机和革命话语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抒情功能。由于前一类咏物形态1949年之后被迫中断,导致现代汉语新诗诗意追求的中断或僵化,其直接影响,便是主体建设或修复的功能的弱化。后来朦胧诗与后朦胧诗中对咏物形态的再创造,便是这一已中断的传统的复兴。
注释:
① 这三个概念,分别是刘勰《文心雕龙》开始三篇总论的题名,堪称古典文学最重要的本体论基础。
② 胡适《逼上梁山》一文中记述的此诗的写作过程可以为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③ 这种意义“空白”可以这么理解:五四运动中,经学系统作为信仰的依据被瓦解了,进入了众家平等的子学时代;白话文运动,将古典诗意栖居的语言形式瓦解了;天下帝国模式的解体,民族主义焦虑的上升等等,都造成了诗意的“空白”感。叶维廉在谈论新诗较之旧诗的新处境时归纳道:“由于传统宇宙观的破裂,现实梦魇式的肢解,与可怖的存在的荒谬感重重的敲击之下,中国现代诗人对于这种发高烧的内心争辩正是非常的困惑。”《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第253页。
④ 据说中国第一个变为石头的女性,是大禹之妻涂山氏。刘禹锡有《望夫石》诗曰:“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作孤石苦相思。”李白、王安石等许多诗人都有过关于望夫石的作品。汉魏乐府《孔雀东南飞》中也有“心如磐石”之说,虽言坚贞,但也与伤心成石不无瓜葛。
⑤ 关于想象力,济慈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只确信内心感情的神圣性和想象力的真实性——想象力把它作为美捕捉到的一定是真。”见《济慈日记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王昕若译,第27-28页;从施莱格尔兄弟为首的德国浪漫派,到柯勒律治开启的英美浪漫主义批评传统,至现代诗人如庞德、斯蒂文斯者,都强调想象力对于不同概念的综合作用。
⑥ 张华[晋]:《博物志》(卷三)说,相传天河通海,有居海渚者见每年八月海上有木筏来,因登木筏直达天河,见到牛郎织女。
[1] 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C]//陈世骧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
[2] 张潮.幽梦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30.
[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M].赵一凡,蒲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49.
[4] 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M].顾嘉琛,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2-3.
[5] 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M].陈均,编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胡适.胡适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
[7]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M]//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141.
[8] 爱莲心.向往内心转化的庄子:庄子内篇分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83.
[9] 林徽因.山中一个夏夜[M]//林徽因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8.
[10] 蒙田.论悲伤[M]//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马振聘,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4-7.
[11] 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M]//陈世骧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55.
[12] 熊十力.原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4.
[13]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67.
[14] 卞之琳.关于《鱼目集》[N].大公报·文艺,1936-05-10.
[15] 冯友兰.新知言[M].北京:三联书店,2007:12.
[16] 约翰·伯格.抵抗的群体[M].何佩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9.
[17] 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M].冯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20.
[18] 瓦雷里.文艺杂谈[M].段映红,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3.
[19] 斯宾诺沙.知性改进论[M].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60.
[20] E C 斯坦哈特.隐喻的逻辑——可能世界中的类比[M].黄华新,徐慈华,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
[21] 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M].黄念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5.
[22] 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111-114.
[23] 瓦雷里.瓦雷里诗歌全集[M].葛雷,梁栋,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82.
[24] 刘西渭.咀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91-95.
[25]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52-253.
[26] 里尔克.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M].史行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23.
[27]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2.
[28] 莫里斯·梅洛—庞蒂.间接的语言和沉默的声音[M]//符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6.
[29] 吴晓东.中国新诗总系: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52.
[30] 穆旦.穆旦诗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8-58.
HeadingfortheWorldofPoeticMissing——OntheCreationoftheModernChinesePoetryChantingForm
YANLian-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China)
Since its birth, the modern Chinese poetry has no longer metaphysical basis just likeTao,which the classical poetry has relied on , and falls into a plight of poetic missing.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new lyrical subject, and describing the new world, the new Chinese poets create two types of chanting form that different from classical poetry. One i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vention of the words, to find and operate the “blank”, in the chanting poems they often speak poeticly with negation or paradoxical rhetorical strategies , try har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things; The other is that to work hard to turn the meanings and sounds that from the revolution, nationalism or political Utopia into body, as the basis of chanting , they form a set of stracture with enormous impact.
Modern Chinese Poetry; lyrical subject; poetic missing; chanting; stracture
I207.25
A
1006-6152(2013)02-0041-08
2012-12-10
浙江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汉语新诗的象征结构演变研究”(bsh1201040)
颜炼军,男,普米族,云南大理人,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 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