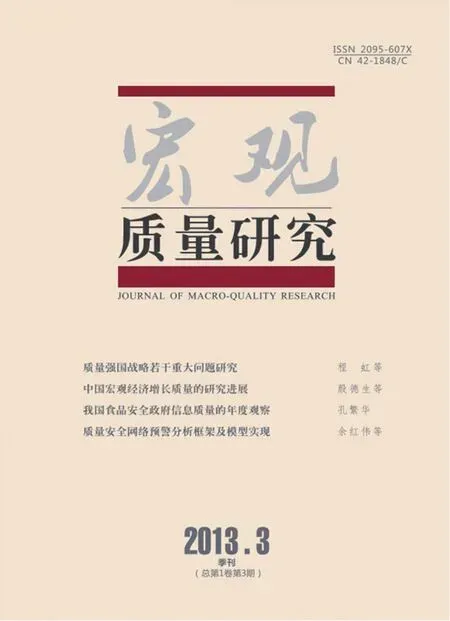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进展∗
——理论综述与政策含义
殷德生 范剑勇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进展∗
——理论综述与政策含义
殷德生 范剑勇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决定着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文章试图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述评。一方面,从文献综述中厘清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以及空间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难点与推进路径等核心问题,从文献综述中总结出一系列政策含义,讨论如何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需要何种新的增长机制,以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路径是什么,倡导经济内生增长由要素投入导向转向效率导向,依靠要素市场化、资源配置全球化和空间效率提升,走高效工业化和高效城市化道路。
宏观经济质量;经济转型;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效率导向
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力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资本增长率在1999-2007年期间达到13%,而在1979-199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约为10%(王小鲁等,200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78-1995年期间的0.028~0.038下降为1995-2005年期间的0.010~0.028(郑京海等,2008)。这种没有明显技术进步的高投资高增长是以不良资产、高污染与高能耗为代价的,政府将承担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5,2008)。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旨在依靠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自主协调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方福前(2007)、钱淑萍(2008)、周叔莲(2008)、魏杰(2009,2011)、郎丽华、周明生(2012)等将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归纳为“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特征,其面临的资源需求约束日益突出,而且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紧张。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原因总体归为三个结构性因素: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与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过去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申广斯,2009;张旭,2010;魏杰,2011;栾大鹏等,2012),并导致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李善同等,2008;朱光华,2009);过于依赖要素的投入,其产出的效率不高(王一鸣,2008,2011;葛扬,2010)。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及来源的核心指标。国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增长理论中,Helpman(2004)全面综述了这方面的文献,所形成的一致性结论是: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国内关于TFP实证研究的视角和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基本支持克鲁格曼(1999)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郭庆旺等,200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考察改革前后中国TFP的动态变化:改革之前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退步,改革之后的TFP有明显的增长(王小鲁,2000;张军等,2003);(3)强调改革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快速增长(易纲等,2003),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TFP呈下降趋势(王志刚等,2006;郑京海等,2008);(4)不是从中国总体去考察TFP的变化,而是从中国工业层次考察技术进步(涂正革等,2005;陈勇等,2007),以及省级地区层次研究TFP的变化(颜鹏飞等,2004;王志刚等, 2006;傅晓霞等,2009;刘瑞翔等,2012;匡远凤等,2012)。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中国TFP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贡献偏低。该方面的研究从省级地区层次和二或三位数的工业数据向地级城市和更细的行业层次延伸,不仅对TFP进行衡量和分解,而且考察TFP各构成部分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在衡量和分解TFP的方法上,既包括参数法又有非参数法。参数法还分为生产函数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非参数法主要指的是指数方法,例如Malmquist指数法。这两种方法都能对TFP变化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分解,但前者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后者不仅不需要设定具体函数,而且还不要求完备的价格信息。
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取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的选择。迟福林(2010,2011)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升为第二次改革的主战场,并提出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向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突出强调从生产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应当说,这三层含义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概括性,也与人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直觉吻合(Poncet,2005;杨建龙,2010)。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经济结构失衡与调整的内在体制性机制和核心问题所在,就不能对症下药。
吴敬琏(2011a;2011b)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始终不顺利的重要原因是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例如,政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大部分重要生产要素仍由行政定价并导致价格信号严重扭曲;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这些都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在上述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条件,其中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由于土地产权“并未落实到户”,农用土地转为城市商业用地时的增殖收益由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得。由此导致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高,而劳动者报酬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占比却每况愈下。魏杰(2009,2011)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
中国发展报告(2010)提出将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作为今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政策措施,并提出了具体的途径:一是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构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布局;二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均等化水平,中央政府负责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的、非市场化部分的最基本公共服务,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逐级分担公共性相对弱一些的公共服务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正是由于土地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未有起色。土地等要素市场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的价格决定机制,要素投入的价格信号混乱,这不仅使经济增长的效率(技术进步或称全要素生产率)低下,而且使原有土地相关权益拥有者的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分享增长成果的机会。
对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所面临约束条件和内外环境要复杂得多,这需要找准中国经济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所需的新的增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其基本路径就得依赖于要素市场化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高效工业化。不仅如此,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中日益重视空间效率和城市体系结构变化带来的制度红利。空间集聚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知识外溢、规模效应,城市体系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应,这些均可以大大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空间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地理集中促使空间效率提升,其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应等。以城市体系结构调整的深化改革而产生的效率提升,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配置效率提升(即结构红利或称“制度红利”),以及社会公平与环境污染减少带来的福利。
(一)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
按区域空间大小,地理集中产生的空间效率可分为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与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Fujita,Krugman&Venables,1999;Fujita&Thisse,2002)。前者指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空间集聚带来的效率,它产生于市场规模在邻近空间上累积循环效应,此即“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后者指的是城市经济学意义上单个城市规模带来的效率,此即“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新经济地理文献刻画了货币外部性产生的内在机制和理论基础,并在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差异化产品与垄断竞争市场的结构下阐明了各地区迥异的空间效率是如何形成的。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适宜应用于都市圈体系,都市圈中各城市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而产生的空间效率将促进该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总是取决于单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若该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专业化特征或以某个主导产业为主,则该城市的效率取决于其主导产业的规模大小,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地方化经济”(Marshall,1920)。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仅取决于单个城市自身的规模,而且还取决于该城市产业的多样性程度。产业种类越丰富,城市的空间效率越高,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城市化经济”(Jacob,1969)。
现有文献虽还未从空间效率上考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或者说两者之间的联系基本是割裂的,但讨论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影响的文献正在日益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一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分布与决定因素(范剑勇,2004;路江涌等,2006);二是市场规模、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志刚等,2006;黄玖立等,2008;殷德生,2010;孙晓华等,2013);三是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范剑勇,2008;范剑勇等,2010;梁琦,2009)。他们的总体结论是: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加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
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的研究目前正沿着三条扩展路径:一是随着我国近年来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制造业的区位分布、空间效率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结构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张军等,2009)。二是侧重于宏观视角的城市体系与区域经济调整政策的研究导致了对小地理范围空间效率的忽视。三是现有文献正倾向于效率目标维度,未能有效地将经济可持续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二)城市体系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
在研究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时自然就涉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杨开忠等,2008;范剑勇、邵挺,2011)。从政策选择的倾向上看,城市化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形成了“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两派。以费孝通(1984)为代表的“小城镇论”者认为,小城镇可将城乡两个市场连接起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该主张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流观点。“大城市论”者强调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认为“大城市超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中国应当走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王小鲁等,1999)。周一星(1992)对“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进行了折中,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市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市组成的,据此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进入制度层面,并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对于采取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理由是理论界讨论的规模效益或者其他经济理性的观点受到怀疑。“小城镇论”者开始放弃“就地转移论”,强调小城镇发展应适度集中,主张发展县城或以县域中心城镇为主(辜胜阻等,2000)。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叶裕民, 1999)。
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城市化道路论争出现了两种新观点:一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陈甬军等, 2009),强调经济集约、功能优化、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环境友好的统一。虽然其理论基础有待深化,但可能代表了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二是主体功能区的研究、编制与实施(肖金成,2008),将中国国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并提出中国适合经济发展的区域是位于胡焕庸线东南部分。
基于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事实,选择分散式城市体系在中国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规模经济在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及其效率、土地资源节约、环境污染治理、公共设施成本分摊上均无法发挥优势。发展特大型城市,尤其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这种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有利于提升空间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在非农用地、资源供给、单位能耗与污染治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
四、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
当前所讲的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指的是调整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对于经济结构的内涵、失衡的表现以及调整的路径,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基于所有制结构来认识,有的将经济结构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宏观经济问题的经济结构,其总是离不开GDP的来源结构。从GDP的支出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结构。从GDP的收入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体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结构,即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的结构。从GDP的生产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即各个生产主体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地区结构即各个地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是从GDP来源结构来理解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协调(魏杰,2011),这种不协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的失衡;二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失衡;三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失衡;四是地区之间的失衡,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布局不协调以及城乡二元化加剧,因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代表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方向,昭示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
目前我国经济的支出性结构最突出的失衡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的失衡。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保持一个合适比例和有效协调,当一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某一种动力时,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2001-2007年我国的GDP平均增速相比以前提高了3.6个百分点,但在这3.6个百分点中,出口贡献了63.9%(魏杰,2011)。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外需拉动型特征,但这种格局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上升,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扩大之势。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外市场份额不仅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缓呈下降趋势,而且还受到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烈争夺。除了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特征外,经济的支出性结构中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无论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还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都是靠增加大量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做法只能当做短期内的反危机措施,不能作为加快经济增长的常态战略。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的手段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需要注意的是,过分依赖于出口与过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往往是交替的,当出口下滑时,政府投资就大量增加。消费一直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2000-2007年,我国总储蓄率由35.1%上升到51.8%,上升了16.7个百分点,而1978-2000年,我国的总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5%~40%,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储蓄率高出15.3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
我国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阻碍消费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增速缓慢,这涉及经济的收入性结构。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集中表现在“两个不同步”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政府的收入增长不同步。20世纪90年代以前,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2001年以后该比例开始下降,一直降到2007年的39.7%;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14.2%和46.1%(魏杰,2011)。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不到10%;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55%左右,而中国不到42%,且呈下降趋势(魏杰,2011)。居民的财政性收入与政府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占比更小。有学者统计,我国大约有76%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大概只有1/4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民间(魏杰,2009)。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也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偏低;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占GDP比重一直在40%~43%左右徘徊,经济增长仍倚重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偏低;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创新严重缺乏;农业等基础产业的风险抵抗能力较低。产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例如,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经济结构不仅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在后危机时代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面临着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与一、二、三产业失衡等难点问题,而且还增加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经济的地区结构是GDP生产法衡量的重要体现。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入了新的调整阶段。在空间效率优化、社会公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的约束下,新时期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与路径如何选择,这是目前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昭示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我国“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范剑勇、邵挺,2011;陈良文等,2007)。新近诞生的中小城市大多数分布沿海地区(许征等,2010),多数中小城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由此导致的典型结果是制成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代价过大、经济增长粗放等一系列弊端。不仅如此,城乡收入差异或者说地区间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包括跨区域流动和区域内部流动的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上(万广华等,2005)。这实际上暗含着,只要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割消除或部分消除,地区间或城乡之间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将得到缓解。
我国经济结构四个层次的失衡,虽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体制性因素——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该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和国民收入,过深地干预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有损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魏杰,2011)。客观上说,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对于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确实有显著效果,但当经济赶超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适时改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
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政府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交替现象的形成与政府过度使用行政资源密切相关。例如,为了刺激出口,政府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涉及3000多类工业产品,不少产品退税率达到13%。政府为了配合实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人民币的三种价格——物价、利率和汇率——未能实现联动,价格扭曲导致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失衡。
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也是导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有经济的过度扩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减少了一半,但资产规模却增长了1倍多,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租金等隐形补贴。2001-2008年间,这三项补贴高达6万亿,而同期国企利润只有4.9万亿,实际亏损1.1万亿(魏杰,2011)。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阻碍了居民收入与GDP、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在增长上的“同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劳动份额逐年减少,储蓄率不断增加,投资率不断提高,产能过剩也日益严重。中国的经济事实与发达国家卡尔多经济事实之一劳动份额不变的情形不相吻合。最新经验研究指出,中国的劳动份额的变化与技术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等因素紧密相关(Young,2006;白重恩等, 2008,2009;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2008)。
产业结构的失衡首当其冲的原因可能是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要素难以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严重影响了各产业之间的市场调节机制。虽然垄断行业放开股权投资,但国有经济仍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国有企业投资中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又进一步恶化了产业结构市场调整机制。
经济的地区结构失衡,尤其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的形成同样与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对土地的征用,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间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土地与能源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了经济粗放式增长。
调整我国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的重点就在于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经济的自主协调。其实,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顶层设计,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中,首先要调整的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结构。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速缓慢导致消费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进而形成了出口、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失衡。出口和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是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和国有经济过度扩张。产业结构的地区分布以及财政分权体制造就了扁平化城市体系。
五、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难点
“结构失衡的增长”是经济赶超的必然结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合理的经济解释,张平等(2011)还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据: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动员大量资源配置到这些部门就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结构性的配置调整带来了明显的赶超增长(Jones& Romer,2009;Barro&Sala-I-Martin,1995;钱纳里等,1986)。这在中国表现为三条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工业部门。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工厂”。二是经济开放实现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入世”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成为第二大出口大国。三是城市化的空间集聚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超50%。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在经济赶超的前期和中期大幅度提高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但非均衡的赶超模式和经济规模在高增长部门的快速扩张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日益失衡。赶超带来的结构失衡导致了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扭曲。
政府干预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似乎是个常态,无论是“中国奇迹”还是“东亚奇迹”,后进国家都是通过集中资源和实施扭曲性政策达到了GDP快速增长的目的;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科尔奈,1992;青木昌彦等,1998;张平、王宏淼,2011),例如,严重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些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目前的中国又具有特殊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是边转型边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在规模已为世界第二的背景下进行,如何在经济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中成功地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目前还没有先例。
“结构协调的增长”不仅要解决新的增长机制问题,而且要解决新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结构失衡累积的矛盾随着经济规模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带来的规模报酬开始递减而越难以解决,并为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增长机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即“结构协调的增长”既离不开原来机制的路径依赖(张平、王宏淼,2011;张平等,2011),又必须赋予新的内涵。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就在于,需要找到脱胎于“结构失衡的增长”中某个增长机制并使其在“结构协调的增长”中成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断依据就是效率导向。投入驱动的增长向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变,必须排除阻碍市场机制和创新机制充分运行的制度障碍。
新的增长机制或者说新一轮规模报酬递增靠什么推动?总体来说仍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张平、王宏淼,2011),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因素要从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土地的征用,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市场;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促使地方政府间形成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沈坤荣、付文林,2006;徐现祥等,2007)。这些不仅导致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而且造成了“中小城市蓬勃发展”且又以制造业为主的扁平化城市体系。这种局面既加剧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又不利于空间效率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新的分配机制总体也是要依赖于要素市场的完善,但要素市场的完善需要政府转型,而政府转型的突破口在哪里?一般认为,在城市化率达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公共福利目标成为政府主导性的目标(张平、王宏淼,2011)。以城市化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但这需要解决好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和土地征用问题,使农民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收益。
六、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基本路径
(一)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驱动的高效工业化
在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下,政府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并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断增加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土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其结果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因此,高效工业化的驱动力首先在于要素市场化。按麦迪森(2001)的理论逻辑,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工业化才是可持续的、高效的(Helpman, 2004)。高效工业化道路不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更是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市场制度的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与资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要素驱动模式若忽视了要素市场的培育,那必将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
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封闭条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场进行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高效工业化总是以扩大经济开放为背景。开放是获取新知识、促进技术进步的有力手段。FDI和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进而促进着内生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殷德生等,2011);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加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而升级(殷德生,2011,2012)。但此种获取方式要取决于一国甚至一个行业内企业间的各种差异,尤其是技能劳动需求与供给、技术吸收能力和要素报酬差距。例如,中国若过分地依赖外资和追求新企业的引进,忽视本地企业的“干中学”,这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殷德生、黄腾飞,2010)。高效工业化还需要在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和减少环境污染中寻找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途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会影响资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资本密集型部门比例却可能诱发不利于减少污染排放的经济结构变化。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取决于效率取向的市场制度创新。目前上海自贸区就是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要素市场效率的改革,其意义在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制度体系,实现要素在全球市场的最优配置。
(二)空间效率驱动的高效城市化
城市化的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着技术创新、服务经济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城市化率和投资率呈倒U形关系,城市化率和消费率呈U形趋势;随之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经济结构将由投资拉动演变为消费拉动,这个转折点通常认为在城市化率为67%左右达到(张平、王宏淼, 2011;张平等,2011)。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刚超50%,正处于依靠城市化进程推动结构调整的黄金时期,但与经济赶超时期投入导向的城市化不同,与“结构协调的增长”相适应的是效率导向的城市化。效率导向的高效城市化倡导从扁平化城市结构向相对集中式城市结构发展,以同时实现空间效率提升、政府主导增长模式改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
范剑勇、李方文(2011)证实了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足的特征。目前我国的“大地理范围集聚明显、小地理范围集聚不足”现象导致了两对突出矛盾:中小城市过多不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和区域经济协调;中小城市过多导致资源浪费。土地稀缺和规模经济决定了中国城市体系须选择相对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相对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在非农用地、单位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拥有规模经济优势,与该判断密切相关的证据是Au&Henderson(2006),而且是解决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利益分享不公平、空间效率不高等经济隐患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将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在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追求公共福利成为政府的主导目标,为城市化提供土地的农民将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和报酬递增收益,这有利于实现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另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从内部规模经济上看,由扁平化城市体系向集中式城市体系转变,需要进一步促进大城市能级的提高,发展特大城市。从外部规模经济上看,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个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从整个规模经济上看,在城市群和特大型城市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新一轮的制度改革红利。
[1] 白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3期。
[2]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2008:《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
[3] 陈良文、杨开忠、吴蛟,2007:《中国城市体系演化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4] 陈甬军、景晋秋、陈爱民,2009:《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商务印书馆。
[5] 陈勇、李小平,2007:《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与工业经济转型》,《管理世界》第6期。
[6] 迟福林,2010:《第二次转型:处于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出版社。
[7] 迟福林,2011:《民富优先:二次转型与改革走向》,中国经济出版社。
[8] 范剑勇,2004:《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9] 范剑勇,2008:《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0]范剑勇、高人元、张雁,2010:《空间效率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选择》,《世界经济》第2期。
[11]范剑勇、邵挺,2011:《房价水平、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与城市体系》,《经济研究》第2期。
[12]范剑勇、李方文,2011:《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载于《中国区域集聚发展:回顾与展望》,陆铭等主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3]方福前,2007:《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问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1期。
[14]费孝通,1984:《小城镇再探索》,《新华日报》,5月2日第四版。
[15]傅晓霞、吴利学,2009:《中国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及其决定因素》,《世界经济》第5期。
[16]辜胜阻、李永周,2000:《实施千座小城镇工程,启动农村市场需求》,《武汉干部管理学院学报》第1期。
[17]葛扬,2010:《技术内生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视野》第4期。
[1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中国发展出版社。
[19]郭庆旺、贾俊雪,2005:《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第6期。
[20]黄玖立、黄俊立,2008:《市场规模与中国省区的产业增长》,《经济学(季刊)》第4期。
[21]科尔奈,2003:《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22]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3]匡远凤、彭代彦,2012:《中国环境生产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
[24]郎丽华、周明生,2012:《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研究》第8期。
[25]梁琦,2009:《分工、集聚与增长》,商务印书馆。
[26]李善同、候永志等,2008:《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市场一体化》,经济科学出版社。
[27]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28]刘瑞翔、安同良,2012:《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变化趋势与因素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
[29]罗长远,2008:《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世界经济》2008年第11期。
[30]路江涌、陶志刚,2006:《中国制造业区域聚集及国际比较》,《经济研究》第3期。
[31]栾大鹏、欧阳日辉,2012:《生产要素内部投入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6期。
[32]麦迪森,2001:《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33]钱淑萍,2008:《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财税对策思考》,《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第4期。
[34]钱纳里、鲁滨逊、赛尔奎因,1986:《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35]青木昌彦、金滢基、奥野-藤原正宽,1998:《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
[36]申广斯,2009:《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统计与决策》第22期。
[37]沈坤荣、付文林,2006:《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经济研究》第6期。
[38]孙晓华、郭玉娇,2013:《产业集聚提高了城市生产率吗?——城市规模视角下的门限回归分析》,《财经研究》第2期。
[39]涂正革、肖耿,2005:《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及分析》,《经济研究》第3期。
[40]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41]王小鲁、夏小林,1999:《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9期。
[42]王小鲁,2000:《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经济研究》第7期。
[43]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研究》第1期。
[44]王志刚、龚六堂、陈玉宇,2006:《地区间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1978-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45]王一鸣,2008:《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宏观经济管理》第1期。
[46]王一鸣,201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经济研究》第10期。
[47]魏杰,2009:《中国经济之变局》,中国发展出版社。
[48]魏杰,2011:《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发展出版社。
[49]吴敬琏,2011a:《发展转型成败系于改革进展》,《读书》第5期。
[50]吴敬琏,2011b:《缩小收入差距不单靠再分配》,《中国改革》第7期。
[51]肖金成,2008:《中国空间结构调整新思路》,经济科学出版社。
[52]徐现祥、王贤彬、舒元,2007:《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9期。
[53]许征、陈钊、陆铭,2010:《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地理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7期。
[54]杨建龙,2010:《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结构与趋势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
[55]颜鹏飞、王兵,2004:《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第12期。
[56]杨开忠、陈良文,2008:《中国区域城市体系演化实证研究》,《城市问题》第3期。
[57]叶裕民,1999:《有关中国城市化两个问题的探讨》,《城市开发》第7期。
[58]易纲、樊纲、李岩,2003:《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第8期。
[59]殷德生,2010:《报酬递增、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0]殷德生、黄腾飞,2010:《教育、经济增长与工薪差距》,《财经研究》第12期。
[61]殷德生、唐海燕、黄腾飞,2011:《FDI与中国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世界经济》第9期。
[62]殷德生,2011:《中国入世以来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财贸经济》第11期。
[63]殷德生,2012:《市场开放促进了产业升级吗?——理论及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
[64]张军、陈诗一、Jefferson,2009:《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经济研究》第7期。
[65]张军、施少华,2003:《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
[66]张旭,201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发展经济学考察》,《理论学刊》第3期。
[67]张平、王宏淼,2011:《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载于《中国经济研究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
[68]张平、刘霞辉、王宏淼,201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社科科学出版社。
[69]郑京海、胡鞍钢、Arne Bigsten,2008:《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一个生产率的视角》,《经济学(季刊)》第3期。
[70]周一星,1992:《论中国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管理世界》第6期。
[71]周叔莲,2008:《“十七大”为什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2期。
[72]朱光华,2009:《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南开学报(哲社版)》第1期。
[73]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人民出版社。
[74]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5:《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研究》第10期。
[75]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经济研究》第10期。
[76]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第11期。
[77]Au,Chun-Chung and J.V.,Henerson,2006,“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3, 549-576.
[78]Barro,R.J.and Sala-I-Martin,X.,1995,Economic Growth,McGraw-Hill,Inc.
[79]Fujita,M.and J.F.Thisse,2002,The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0]Fujita,M.,P.Krugman and A.J.Venables,1999,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MA:MIT Press.
[81]Helpman,E.,2004,The Mystery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2]Jacobs,J.,1969.The Economy of Cities,New York:Random House.
[83]Jones,C.I.,&P.M.Romer,2009,The New Kaldor Facts:Ideas,Institutions,Population,and Human Capital, NBER Working Paper,No.15094.
[84]Marshall,A.,1920,Principles of Economics,London:Mac Millan.
[85]Poncet,Sandra,2005,“A Fragmented China: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Disintegr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3,409-430.
[86]Young,A.T.,2006,“One of the Things We Know that Ain’t so:Is U.S.Labor’s Share Relatively Stable?”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责任编辑 汪晓清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Growth Quality: Literature Review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Yin Desheng1and Fan Jianyong2
(1.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School of Economics,Fudan University)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 main direction f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decides China’s macroeconomic growth quality.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literatures on China’s macroeconomic growth quality.On the one hand,we clarify the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growth,the direction of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and the effect of spatial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on macroeconomic growth quality.On the other hand,focusing on the key and difficult problems as well as advancing path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growth,we summarize a series of policy implications ,which include the way of changing the government-led growth model,new mechanism for“structural coordinated growth”,and the new path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We advocate that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investment-oriented to efficiency-oriented,which depending on effici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Macroeconomic Growth Quality;Economic Transformation;Government-led Growth Model,Efficiency-oriented Growth
∗殷德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电子邮箱:dsyin@finance.ecnu.edu.cn;范剑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jyfan 0393@163.com。殷德生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16)、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AZD095)、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2ZS044)以及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12SG27)的资助;范剑勇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03)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文责自负。
- 宏观质量研究的其它文章
- 最低质量标准理论研究综述∗
- 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