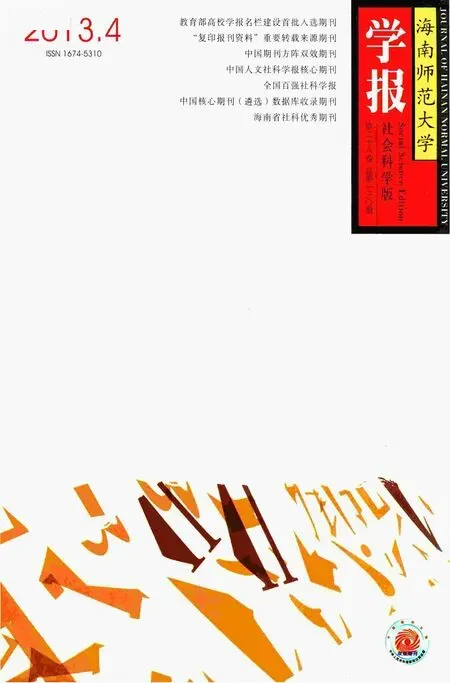《东藏记》贬损了商人吗?——关于《论〈东藏记〉的误区》的误区
杨 惠,方维保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自宗璞最新力作《西征记》发表以来,其长篇系列小说《野葫芦引》自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以后再次获得关注。重新阅读《野葫芦引》的前两部《南渡记》和《东藏记》,不由平添几分温故而知新的喜悦,理解了许多当年未曾注意的细节。然而当阅读到柴平的评论文章《论〈东藏记〉的误区》,却发现这篇文章对《东藏记》的批评有些强词夺理,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柴平的《论〈东藏记〉的误区》(下称柴文)最主要的观点是,认为《东藏记》有崇儒抑商倾向,“充斥着大量的贱商话语,呈现出明显的思想方面的缺陷。……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捍卫,使宗璞以保守主义态度对待西方文化资源……”[1]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柴文列举了几个例子,“在小说中,她让在资源委员会做经济情报的掌心雷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对在课余赚外快过舒适生活的教师尤甲仁冷嘲热讽,最为明显的是,作者在文本中极力贬低、嘲讽商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丑化歪曲商人吕香阁的形象。”[1]
小说《东藏记》果真贬损了商人吗?要弄清楚这部小说是否贬损了商人,就必须对其中三个人物命运及其最终结局进行分析,也必须追溯到《南渡记》,将两部小说看成一个前因后果的序列,才能真正完整地还原小说人物的命运。
一 关于“掌心雷”的死亡问题
《野葫芦引》系列整体风格继承《红楼梦》,①关于《南渡记》对《红楼梦》的继承吸收,可参看卞之琳:《读宗璞〈野葫芦引〉第一部〈南渡记〉》,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 期。以含蓄典雅为主,对于一件事情的交待往往“草蛇灰线”,伏笔千里,一两句话点到为止,很少大喊大叫地说明,只让读者以耐心和慧心来暗自忖度。“掌心雷”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的叙事中完成。
“掌心雷”本名仉欣雷,“掌心雷”是由其本名谐音而起的外号,从《南渡记》到《东藏记》,他露面的机会不多,但有限的几次出场都或隐或显地暗示了他对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长女峨的爱慕以及峨对他的无动于衷。仉欣雷在《南渡记》开头第一次出现时,是明仑大学经济系二年级学生,“七·七事变”前一天晚饭后,来孟家看望刚刚中学毕业的峨。在稍后的篇章里小说及时暗示了峨对父执明仑大学生物系教授萧澂的暗恋,已经预示这两人爱情的不可能。在《东藏记》里,仉欣雷大学毕业前,请峨帮助决定毕业去向,是去香港与家人团聚还是去重庆的资源委员会,而最终促使他做决定的,仅仅是因为峨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资源委员会……似乎和二姨夫有点关系”[2]138。最后一次出现则是他的意外死亡。峨隐晦地向萧瀓表示自己对他多年的暗恋,被友好而明确地拒绝后,在极度痛苦和迷乱中,遇到从重庆来的仉欣雷。他向峨求婚,峨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两人第二天去拜见峨的父母,不料为躲避迎面而来的军车滚落悬崖,峨受伤,仉欣雷身亡。
由此可见,仉欣雷确实是“突然死亡”,但绝非“莫名其妙”,从情节上来说源于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而从根本上来说,则源于他在追求一份不属于自己的感情。峨对他自始至终很冷淡,毫无爱恋可言,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对好情侣、好夫妻。仉欣雷在小说里一如峨所说,是一个比较注重现实存在的俗人、好人,缺乏超脱现实的崇高理想,但也正是这个俗人,一直在坚持追求一份不可能实现的爱情,从北平追到昆明,无论峨对他多么冷淡他却从不退缩,这恐怕是他凡俗人生中最不俗的一面。而峨则完全是另一种人,本性上她生性怪癖,沉默寡言、耽于幻想;感情上她从少女时代起一直暗恋萧瀓,对仉欣雷毫无好感。以《东藏记》第一章为例。峨突然邀请妹妹嵋陪她一起上晚上的大二公共英语课,嵋在课堂上见到了仉欣雷,而他比峨高两个年级。下课后仉欣雷对嵋解释说自己因为缺课太多需要补学分才来上课的,不管这个解释是真是假,仉欣雷从香港来到昆明,显然与峨有关,他想接近峨的追慕心理显露无遗,而这也正是峨突然请嵋陪她上课以躲避仉欣雷的原因。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仉欣雷和峨都是两个完全不相容的个体,但这两人在追求不可能属于自己的爱情上的执著和执拗,却又有几分相似。而那结局,早已注定是一场空,正如峨所求的签上的偈语“强求不可得,何必用强求!随缘且随分,自然不可谋。”[2]143他俩之所以能够订婚,对于峨是强求失败后的心灰意冷,对于仉欣雷则是阴差阳错的偶然惊喜,完全是生命轨迹刹那错位产生的相交,他们的订婚带来的必然不是幸福而是悲剧,所以小说才安排了仉欣雷突然死亡的惨剧,以了结这本不应该存在的勉强至极的婚姻。这并非是作者用佛家语故弄玄虚,而是因为他们俩都在“强求”一份不属于自己的感情,即使勉强求得,也终因违背了现代婚姻最基本的“自然”——两情相悦的爱情,终将是镜花水月,此所谓“强求不可得”。相比之下,小说中另一个同样为情所困的女孩吴家馨,也求得了和峨同样的签,最终通过仉欣雷的死亡彻底了悟强求一份感情的可怕。因此,仉欣雷的死是必然的,不通过这种方式意外死亡,也会被无爱的婚姻所窒息,绝不是“莫名其妙”。
而按照柴文的意思,宗璞之所以安排仉欣雷死亡,是因为他在资源委员会里做经济情报工作,属于商人一流,其实这是柴文对“资源委员会”望文生义的误解。
“‘资源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兴建和经营国家重要工矿企业的重要经济机构。其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1932年10月成立,……隶属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主要任务是从事军事、国际、财经、文教、工矿、交通、农林、地贸、资源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撰写各项专题报告。1934年4月,改组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主要职能已由调查研究转为国家重工业建设的经营管理机构。……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3月,改属国民政府经济部,……主要任务是创办和经营管理基本工业、重要矿业和电力事业以及主持战时工业的内迁。……它对中国资源的调查研究与开发、对中国现代工业基础的奠建,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以及抗战的胜利都作出了贡献。”[3]①关于“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始末,还可参看郑友揆著作《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1932—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可见,资源委员会前期主要是为国民政府提供经济信息的咨询机构,后期则主要是管理国家重工业的经济部门。仉欣雷本是经济系学生,毕业后进入资源委员会堪称对口就业,而其从事的经济情报工作也并非经商。而柴文却无视小说已经明确暗示的前因后果,硬将仉欣雷的死归结于作家对这个从事经济工作的人的贬低和蔑视,是不实的。
二 关于对尤甲仁的冷嘲热讽
不可否认,《东藏记》对于明仑大学教师尤甲仁的冷嘲热讽是非常明显的,但原因并不在于其“在课余赚外快过舒适生活”。我们完全可以举出反证,小说里不止一次提到明仑大学的师生由于贫困而在校外兼职,《东藏记》第一章第三节明仑大学教师李涟“说起给学生发放贷金的事。……法币贬值,物价涨得快,伙食愈来愈糟。有些学生开始找事做,看来找事的会愈来愈多。……‘最近有一个药店要找个会计,也就是记账,很好学。好几个学生争着去,叫我很难办。’”[2]30不但联大学生到处找事挣钱吃饭,联大的老师也迫于生计不得不赚外快贴补家用,如数学系教授梁明时也到联大师范学院设立的华验中学兼课,到小说第九章,曾为学生谋兼职的李涟自己也不得不“在一个暑期学校讲授文史知识,为了那点兼课费”[2]327。当提到这些人在课外兼职挣钱时作者并没有任何贬低、鄙视之语,相反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却隐含着同情和尊重,完全不存在由于“在课余赚外快”而被嘲讽的情况。因此尤甲仁的被嘲讽,决不是由于“在课余赚外快过舒适生活”。
事实上,小说每次提到尤甲仁、姚秋尔夫妻二人,确实总不免夹枪带棒、冷嘲热讽,在《野葫芦引》这样一个整体风格含蓄隽永、品评人物点到为止的小说中实为罕见。以尤甲仁夫妇第一次出场为例。先是一段肖像描写,“两人身材不高,那先生面色微黄,用旧小说的形容词可谓面如金纸,穿一件灰色大褂,很潇洒的样子。那太太面色微黑,举止优雅,穿藏青色旗袍,料子很讲究。”[2]169再形容两人说话的情形,“两三句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2]169继而写夫妻俩互相吹捧对方英文说得如何好,文章写得如何棒;最后让中文系功底最不扎实的钱明经教授以司空图《诗品》中的一段话来小小试探一番,果然尤甲仁空有超凡记忆而毫无个人创见。尤甲仁夫妻二人第一次出场即被作者从外表、语言、行为、学识等各方面着实嘲讽了一番,后面凡涉及到这夫妻二人之处,总让他们显示自己的所谓渊博、清高、公允而实则刻薄、庸俗、市侩的一面,连他们居住的地点也命名为“刻薄巷”。原因何在呢?
其实,凡是看过这部小说的人,只要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稍微有点了解,都可以看出,尤甲仁实则是在影射钱钟书,比如尤甲仁的留英经历、对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倒背如流、喜欢卖弄才学与英文、与人争论常带嘲讽等,关于这一点,早已有人指出。①详情可参见余杰:《漫画钱钟书? ——我看〈东藏记〉的暗藏机锋》,《粤海风》2002年第5 期。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时的恃才、傲岸众所周知,而冯友兰、宗璞父女与钱钟书夫妻的不和也是不争的事实,②关于冯友兰、宗璞父女和钱钟书、杨绛夫妇不和的详情,可参见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声辩》一书中“杨绛宗璞笔墨官司的来龙去脉”一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因此宗璞才以西南联大历史掌故为基础,结合后人回忆以及个人情感,在小说中凡提及尤甲仁处皆涉语成讽。《东藏记·后记》里的一段话正可以稍加解释,“在写作的过程中,曾和许多抗战时在昆明的亲友谈话,是他们热心地提供了花粉。……我也参考一些史料,当然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虽然人物的命运离不开客观环境,毕竟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我还是那句话,小说只不过是小说。”[2]337
三 关于丑化歪曲商人吕香阁的形象
事实上,小说贬低吕香阁是真,但并非像柴文所说是由于吕香阁经商。吕香阁在第一部《南渡记》里并不是个商人,但小说笔墨已经加诸不屑,而《南渡记》里出现的其他一些真正的商人则并未受到嘲讽。如小说开头,以家常而隐含深情的笔墨回忆抗战爆发前北平大学教授家庭的日常生活。
清晨,随着夏日的朝阳最先来到孟宅的,是送冰人。……送冰人用铁夹子和草绳把冰从车上搬到室外,最后抱到冰箱里。然后在已经很湿的围裙上擦着手,笑嘻嘻和柴师傅或李妈说几句闲话,跨上车扬鞭而去。接踵而来的是送牛奶的。再往下是一家名叫如意馆菜店的伙计。他们包揽了校园里大部分人家用菜。[4]15
接着看常来孟家推销小食品的“广东挑”:
广东挑的主人是地道老北京,和广东毫无关系,可能因为担上货物大都是南味食品,因而得名。这种货挑很讲究,一头是圆的,如同多层的大食盒,一格格装着各样好吃的点心。一头是方的,由一排排小玻璃匣,装着稻香村的各种小食品,……每次广东挑来了,碧初(按:孟樾的妻子)都得买这种点心。……广东挑笑嘻嘻地把东西捡出来,收了钱。[4]17-18
再看孟家常光顾的一家绸缎商:
他们又到一家熟识的绸缎店,带着瓜皮小帽的掌柜高兴地说:“孟太太,可老没见了。”……问清要求,好几个伙计把各种花色的绸缎打开,铺平在柜台上。有的搭在自己身上,……掌柜也帮着发表意见。在黯淡的灯下,各色铺展开来的绸缎发出幽雅的彩色光辉,满店堂喜气洋洋。他们沉浸在古老北平买和卖的友好艺术气氛中,几乎忘记北平已不属于他们。[4]179
以上三个例子都和做买卖有关,并没有什么讽刺和贬低之处。送冰人、送牛奶的、如意馆菜店伙计,这三个跑腿的伙计虽然算不上什么生意人,却用自己和善而坚韧的劳动体现着各自背后店家勤劳本分的生意经。“广东挑”、绸缎庄掌柜,则毫无疑问是生意人,也许对绸缎庄老板有几许轻微的遗憾,但更主要的还是对其尊重主顾、尊重自己生意的态度的赞美。且看那个做小点心生意的“广东挑”,把他的货担收拾得多么干净整齐,这一付担子,既是他维持生存的来源,也是他保持做人的自尊的体现。正是在这些平和的叙述中,饱含着作者对童年生活诗意的回忆,对普通而勤劳的生意人的赞美和尊重,他们那么和善那么自豪地将自己的生意当作事业来追求,务求尽善尽美,从而营造了老北平悠闲、适意的生活氛围。
但小说并不是不嘲讽商人,事实上在《东藏记》里,经常跑滇缅路做生意的中文系教员钱明经、昆明首富朱延清都是讽刺的对象,但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做生意。钱明经最为人诟病之处在于其没完没了的风流韵事;朱延清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以为用自己豪奢的庄园就可以买到爱情。
以上几个例子已经证明,商人并不必然成为作者嘲讽的对象,换句话说,是否成为被贬低的对象,最主要的是这个人是否有自己的人格修养和道德良心。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则可知吕香阁必然成为嘲讽和贬低对象。
吕香阁何许人也?她的父亲吕贵堂是孟樾岳父吕清非老人的本家,由于躲避债务带着女儿来到吕老人家寄食。吕香阁在《南渡记》里第一次出场,其实就暗含着作者的批评:
吕贵堂掀帘进来,后面跟着十六岁的香阁。碧初每次见她,都觉得她又长大了,更惹眼了,每次也更感到她伶俐有余浑厚不足,却不知为什么。……香阁先看碧初脸色,觉得没有阻拦之意,方从衣袋里拿出两个彩线角儿来,带着亮晃晃的长穗子,笑说:……[4]33-34
在这个亮相中,借助吕碧初的眼睛,看出这是一个长相俏丽、身形丰润、聪明外露、极善于察言观色的少女。
再看《南渡记》第四章中的一段情节。北平沦陷后,吕老人每天教几个孩子练拳。一次嵋和吕香阁练习对打,嵋比吕香阁小好几岁,个头也差一截,几个招式以后,小说这样写道:
嵋也有点累了,正要收式时,忽觉手腕发疼。定了定神见是香阁攥住她的手腕,正向她笑。
怎么会有这样的笑容!嵋很奇怪。这笑容好像有两层,上面一层是经常的讨好的赔笑,下面却露出从未见过的一种凶狠,几乎是残忍,一种想撕碎一切的残忍。拳里也没有这一招,为什么攥住人家手腕啊!
“啊!”嵋有些害怕,叫了出来。
香阁仍不撒手,反而更捏紧了,还盯着嵋的眼睛,好像说,你还有什么能耐!众人都不明白她们比什么。这时莲秀(按:吕老人晚年续娶的继室)快步走过来,抓住香阁的手臂,“嫩骨头嫩肉的,收了吧。”
“我和小姑姑闹着玩。”香阁松手,她的内层笑容骤然消失了,只剩外层,十分甜美。……
莲秀拉着嵋的手要走。香阁笑嘻嘻地说:“小姑姑别走,我跳绳给你看。”嵋站住了,向她的笑容中寻找下面一层,却找不到,只觉她唇红齿白很好看。香阁很快搬来一条窄长高板凳,拿了绳子,纵身上凳,轻盈地跳起来。……
嵋早忘了那狞笑和发红的手腕,开心地笑叫……
这时传来一阵笑语之声,绛初、玹子与峨走进正院。香阁蓦地跃下,连同绳、凳迅速地不见了。[6]119-120①引文中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引这长长的一节,是因为这一小段情节准确地传达出吕香阁的性格心理。这个情节共有几层转折,通过攥手腕、笑、跳绳、迅速消失等行为动作,一层层剥露出这个少女隐秘的内心世界。她跟随父亲从家乡躲债到北平的深宅大院,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这在她十六岁少女的心里引起的是翻江倒海的不平衡和嫉妒,这种强烈的嫉妒心又衍生出强烈的报复心。因此吕香阁心中对给与自己恩惠的吕家人毫无好感,对于嵋等在养尊处优、平等自由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怀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嫉妒和愤恨,一有机会就不动声色地下狠手报复,得逞之后又很巧妙地掩饰自己的行为,逃避责任以免受罚。她那可怕的双层笑容正是以表面的谄媚遮掩内心猛兽般的施暴欲望。
在《南渡记》的结尾,吕香阁毫无顾忌地表明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说实在的,我很恨这地方,恨北平城,包括我爹……
……
“我就愿意走,上哪儿都行。最好明天就走!”香阁轻轻地笑着。[4]245-246
“往后你就知道了。以前谁也不知道我。我爹怕我当汉奸,才这样忙着让我走。……”香阁的口气很放肆,眼光活泼泼乱转。……香阁的眼光似乎有两层,外面的像狗,里面的则像狼,温顺罩住凶狠。[4]264
这里明确表示出几点意思:一,对于吕香阁来说,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摆脱她在偌大的北平偌大的吕家所感受的严重内心压抑。二,以前展现在别人面前的她只是表面的恭顺和伶俐,在摆脱压抑后,她将充分施展自己的手腕和能耐让别人都知道她。三,再次印证吕香阁身上那种集谄媚与凶残于一体的感觉。别人在她眼里只分两种,可以利用的和不可以利用的,不管对方是谁,可以利用则温顺如狗,百般奉承,无法利用则凶狠如狼,残忍绝情。
在整个《南渡记》里,吕香阁并不是商人,可以说没有做过任何买卖,但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如狗如狼的品性已经显露无疑,而《东藏记》中吕香阁的所有行为不过是其性格的延续和展示,相比较而言,开咖啡馆做生意不过是其谋生手段之一倒并无什么不妥之处。问题在于,吕香阁即使不开咖啡馆,哪怕她从事任何一项与做生意毫无关系的职业,以这样的本性也着实让人无法赞同,这跟她从事何种职业无关。
柴文提出,“……吕香阁个人主义的幸福观具有个性解放的特征。对个人幸福强烈追求的愿望是合理的,是符合人性的。……香阁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人,有着合理的利己主义欲求,……但却被描绘成漠视国难,见利忘义,违背起码的伦理道德底线,丧失人性,沦为资本的人格化或金钱的人格化,这是《东藏记》思想上所存在的巨大局限。”[1]
柴文认为吕香阁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个人主义精神。这里柴文其实没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个人主义精神,滥用了“个人主义”这个概念。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基于个人主义,这是有其特定内涵和外延的,它并非损人利己和享乐主义的代名词。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一书指出,真正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应该包括个人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等概念,而这些概念里面同时也包含着一个底线,就是每个人在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个性发展的同时,都应该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5]对照这个概念,我们会发现吕香阁身上体现的绝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
首先吕香阁不懂得个人尊严,不尊重自己。仅举一小例为证。一天晚上,澹台玹、峨、嵋、凌雪妍和吕香阁五人在吕家大院里玩带有神秘性质的蜡烛游戏,以各自认领的蜡烛燃烧的时间长短来预示命运的好坏,凌雪妍的白色蜡烛最先熄灭,吕香阁的黑色蜡烛燃烧时间最长。吕香阁赶紧说:“这全是闹着玩,只该我的先灭。全颠倒了,可见不足为凭。”[4]156五人中,除吕香阁外都是从小养尊处优的小姐,但她们并未由于蜡烛的早灭而迁怒于她,只是感到命运的神秘和不可预测,吕香阁却自觉自愿地自我贬低,毫无个人尊严和自主精神可言,有的只是一个心机沉重的少女在地位高于自己的人面前的谄媚之态。
其次,吕香阁完全不懂得尊重他人,他人在她眼里只是垫脚石和攀爬的阶梯。俗话说“盗亦有道”,也即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自己基本的行业标准和道德底线,商业行为也不例外,做人更是如此。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战争年代,仍然存在某些普世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原则,而不是上帝已死为所欲为。而吕香阁的问题恰恰在于不顾一切谋求更好生活的野心,行为处事百无禁忌,只要对自己有利,明知会损害与她毫无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应该奉守的自我尊重和尊重他人的精神底线,恰恰在吕香阁身上是缺失的。
以柴文极力赞同的吕香阁对待澹台玹的美国男友保罗的态度为例。
忽然有一个想法,可以把发展自己和破坏别人结合起来。夜深人静,吕香阁坐在床边,她的两结合计划已经完成。首先是向保罗借钱,她要描述自己的梦想,那就是开一家舞厅,如果保罗肯借钱,澹台玹必然很不高兴,这是第一步。还有第二步,第三步,还要仔细规划。她很快进入梦乡,而且睡得很好。[2]248
玹子走过去,看见男女二人靠得很近在低声说话,正是保罗和吕香阁。香阁见玹子来,更把头靠在保罗肩上。……保罗忽然警觉,抽身站起,……这时吕香阁也走过来搭讪,一口一个玹子小姐。说今天用的是保山咖啡,别看是土产,很不错的。[2]249
在吕香阁对待澹台玹和保罗的关系上,如果她对保罗情有独钟,反倒说得过去,但事实上吕香阁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接近保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想盖过玹子的风头发泄自己当年在吕家感受的压抑。即使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吕香阁的心思,也不过理解为一个女子在乱世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不得不锁定保罗为结婚对象而恶意拆散他和澹台玹,但理解不等于认同,不等于赞美。
如果说吕香阁的上述行为还让人有一点点理解的话,那么吕香阁对待凌雪妍的行为则让人无法原谅。吕香阁在李宇明和凌雪妍的带领下一路逃离北平,途中对诸多艰难、不便多有抱怨和后悔,这本情有可原,任何人都有趋利避害、贪图享受的本能欲望,何况是在那样一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战乱年代?但吕香阁在昆明站稳脚跟后,对别人散播凌雪妍和李宇明的谣言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说商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时不得不打击竞争对手,而很显然凌雪妍和李宇明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可能成为她的生意对手,那么吕香阁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制造这个莫须有的桃色新闻呢?除了自己的道德缺陷和内心的不干净外,恐怕很难有其他解释。
吕香阁这个形象其实是有着丰富的心理学基础和文学的饱满性的。她的父亲吕贵堂因妻子病死而欠了许多外债,不得已带着女儿到北平投奔吕老人,在吕家的深宅大院里做一个客居者。由于吕贵堂知书达理又忠厚能干,因此颇得吕老人赏识。但吕贵堂在吕家的地位很特殊,虽然是吕老人的本家,但实际却是来寄食的;虽然帮着料理家务,却不是名正言顺的管家和佣人;虽然人到中年,但按照中国家族制度来说辈分很低,和吕家的外孙们同辈。种种尴尬之处使吕贵堂在吕家的地位非常奇怪,以至于不好称呼,家中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直呼其名,包括吕老人最小的外孙6 岁的小娃在内。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讲究称呼、名分的国家,一个成人被别人直呼其名显然带有某种不言自明的轻视。父亲的这种地位在女儿心里必然会引起某种不平以及自卑。
而与吕家孙辈的几个孩子相比,吕香阁自身条件并不差,但却由于出身环境的不同而处于天壤之别的状况,一边是娇生惯养、轻松自由的少爷小姐,一边却需仰人鼻息、寄人篱下,正处于最敏感年龄的吕香阁必然感触颇多,羡慕、嫉妒、自卑、愤恨……如果吕香阁是一个没有什么才能因而认命的少女倒也罢了,但她偏偏是一个颇有能耐希望出人头地的姑娘,这就使她心机颇深,处处察言观色,压抑自己的本性、讨好奉承以求得较好的生存环境。但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而又处在长期的自我压抑中,必然会造成心理失衡,一定会变相寻找发泄的途径,因此一旦有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她必然要放纵自己的能力和欲望,以实现自己早年被压抑的愿望。而这种变态心理则在一个由于战乱而失范的社会里被放大和充分实现,而不必受到正常社会的道德压力。因此吕香阁在小说第二部《东藏记》里,日益显露出自己原来一直隐藏和压抑的本性,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敢于挑战任何对手,行为处事更是百无禁忌。
总之,无论是《南渡记》还是《东藏记》,赞扬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是真,但并未因为崇儒而抑商,对于遵守最基本的商业道德的商人,小说是尊重的,柴文所列举的几个被贬低的例子是不成立的,尤其在吕香阁这个人物身上,作者贬低吕香阁和她是否经商完全无关。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在熟悉和尊重文本的基础上发挥个人见解,而不能抱着某种先在的理念或成见来生拉硬套,张冠李戴,否则既容易造成对人物理解的偏差,也失去了文学批评的基本价值和意义。
[1]柴平.《论东藏记》的误区[J].当代文坛,2004(3).
[2]宗璞.东藏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许嘉璐.中华史画卷·现代卷[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149.
[4]宗璞.南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M].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