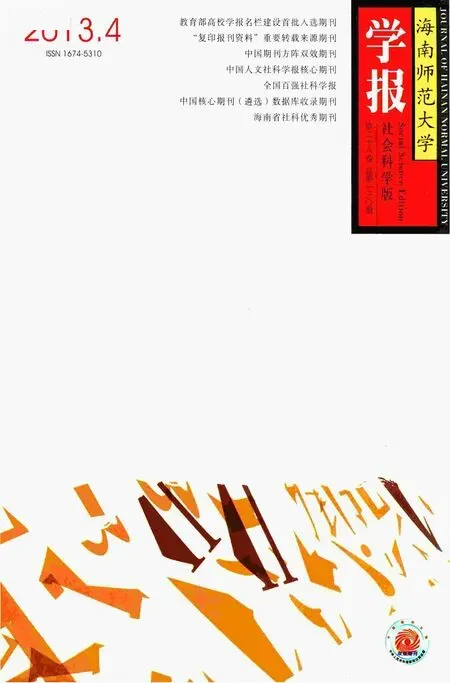从“集体记忆”中突围:“后革命”视域下的“文革”书写
冯 雷
(北方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144)
假如说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是现代性的追求的话,那么革命其实也是一种追求现代性的方式。然而在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产业工人阶级的迅速萎缩,革命似乎成了一个历史的玩笑。在现代化轨道之内,伴随着发展民族经济成为新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理想和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明日黄花。当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逐渐取代革命的丰功伟绩而成为政权合法性更有力的佐证时,“后革命”的历史反思和文学表达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革命,固然体现为炮火连天、坼天陷地的军事斗争,但是革命的影响却并不会随着军事斗争的偃旗息鼓而烟消云散,其发酵与挥发是一个更为内在和长久的过程。具体到中国来讲,“革命”便成为一个不断“扩容”的词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被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标志,由此,中国大陆基本告别了烽火硝烟的军事战争年代而逐步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9 页。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又给中国上紧了阶级斗争的发条,直到1971年林彪“9·13”事件的发生,才促使晚年毛泽东“文革”政治理想逐渐瓦解。[1]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把时间下限再稍稍后延,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短暂而又漫长的“在徘徊中前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极“左”路线,“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②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5 页。这本来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判断,但是随着后来的“反右”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展开,这一正确判断却被否定了。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对这一判断重新予以确认。“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因而从1978年开始,革命才真正成为历史。[3]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则把中国革命延长到了1980年代中期。[4]1985年,他把自己对中国革命系统观察、思考全部付诸书稿,当然这不是全部的原因,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不如说是延续了他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在他眼中,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一段在西方影响下、漫长而充满颠簸的“现代化”的过程,所以他才把回望历史的眼光一直上溯到1800年,所以具有丰富言说性的“文革”才是“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所以中国革命也并不因为“文革”的结束而结束。事实上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整肃说明政治禁忌依然极其敏感。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又一次刷新了人们对于历史和革命的认识。在汪晖看来,1989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的界标,它不仅标志着暴力革命时代的终结,而且预示着国家属性的微妙改变,“两个世界变成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5]中国由此真正进入“后革命”时代。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无疑大大强化了赤色“革命”时代的终结感。中国语境下,革命话语的让渡是如此的一波三折,则“后革命”的到来和诉求又怎能不分外“暧昧”?
因此,对于中国革命来讲,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形态的革命已经终结,可是革命的理想和记忆却并未终结,并且还于有形和无形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革命的影响和作用泅渡穿过逐渐成为历史记忆的“文革”和正在进行中的“改革”直达现实生活的岸边,于是乎“文革”便成为中国语境下“后革命”不应忽略的一个部分。
一 理想主义的浮桥
对于“文化大革命”,“新时期文学”采取了与主流政治相合作的态度。文学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共享了高层政治对于“文革”的历史解释——主流政治对于“文革”的时间界定不仅成为文学史分期的又一重要坐标,而且在立场、态度上,文学和政治一样,也把“文革”视为是历史的倒退,对“文革”的揭批、控诉以及所谓的“反思”也成为“新时期文学”最初的情感主调。时至今日,“文革”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特殊的、重大的题材领域,如许子东所说“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与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与影响,这是一个很少中国(特指大陆,下同)当代作家能够忽视和回避的题目”,[6]1-2几乎所有“文革”之后的重要作家都曾贡献过他们各自对于“文革”的回忆和思考,当然,这些表态和反思必然是顺应主流政治的。于是,“文革”的历史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一段非常特殊的“一体化”的集体记忆,“文革”总是意味着政治阴谋、经济崩溃、文化颓败以及人性的深渊,这些关键词同许诺光明、美好“未来”的革命背道而驰。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在“新时期文学”的“模板”上,“文革”同“革命”是必须严格区分开的,“文革”是对革命理想的盗窃和歪曲,是“五四”以来种种人文精神的跌落,总之,至少在文学领域里,“文革”的“债”不能记在“革命”的“账”上,相反,革命理想是要继续弘扬的——在80年代,宏大者如“四项基本原则”和被喻为“革命”的种种改革,精微者如教育中小学生每天在“革命”的名义下“保护视力”,进入90年代,当市场化浪潮袭来之时,革命理想又同商业运作、大众文化结合,随“主旋律”作品之风潜入千家万户丰富的夜生活之中。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文革”题材的创作或者说文学对于“文革”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许多作品主动将“文革”和“革命”对接起来。例如红极一时的《亮剑》(都梁,2000)、《历史的天空》(徐贵祥,2000)、《英雄无语》(项小米,1999)等“老兵新传”,“革命”时期的挥斥方遒和“文革”期间的耿直不屈共同谱写了“老兵”们的英雄传奇,而且正由于作品的前半部分即“革命”年代里“老兵”们生龙活虎、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的映衬,“老兵”们随后在“文革”岁月中的凄苦遭遇便显现出为理想而殉难的品质。随着李云龙们晚年将星闪耀、修成正果的“大团圆”结局,“老兵”们被“正典化”,革命理想、革命情怀穿越了革命和“文革”两个时期,经受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考验,最终重新得到弘扬。“文革”期间,赵刚在批判大会上慷慨陈词:
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想过将来要当官,我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7]
尽管“文革”依旧是作为历史的错误部分而受到批判,但“文革”和“革命”却由于共同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发生了深刻的联系。“文革”和“革命”之间原本清晰的界线变得模糊而暧昧了,这是当初“新时期文学”里所不曾有过的。同样,在《旧址》(1993)、《圣天门口》(2005)、《山河入梦》(2007)等“历史追问和质询”中,也纷纷把“文革”和“革命”合在一起作为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而这种结合相比较于“老兵新传”又往往体现出某种自觉的思考和探索。对于李锐而言,《旧址》也好,《银城故事》(2002)也罢,都是围绕探求“文革”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而展开的。①李锐在一篇访谈中讲到:“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成为这些苦难追问的中心。我用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反复地追问和表达……而我的银城系列,还是这样的追问,但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展开的。”参见李锐、钟红明:《〈银城故事〉访谈——代后记》,《银城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 页。而《圣天门口》我想除了体现出刘醒龙的抱负之外,还体现出他相当的耐心,他以七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来描述和思考革命理想、革命理论的是是非非,这种思考集中体现在傅郎西这个人物上,从早年的热衷于暴动和杀戮,到晚年幡然醒悟,否定暴力但不否定革命。这样,“文革”和“革命”之间的联系就不仅仅只是故事时间上的对接,而是体现为更为深入、更为紧密的内在逻辑的演变,于是“文革”和“革命”二者浑然一体,就此而言,在“文革”与“革命”的整合方面,或者说在对“新时期文学”“断裂”式的认识框架的破除方面,《圣天门口》是我所读过的诸多小说当中做得最好的。在这些作品里,“文革”和“革命”之所以能够被贯通,其中最重要密钥便是以激进的“革命理想”为浮桥,不露痕迹地跨越“经验”和“教训”之间的天堑。在“老兵新传”里,革命理想在“文革”时期“落难”,“革命”成为一份“被背叛的遗嘱”。而在刘醒龙、李锐那里,“文革”则是导源于“革命”这一现代性工程内部的缺陷、漏洞,是这些缺陷、漏洞不断升级、扩大而又迟迟没有得到有效修正的历史必然结果。事实上,党的官僚化和知识分子的贵族化是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最为担心的问题,②参见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 页。因此在革命阵营内部要整风学习“继续革命”,而对于知识分子则必须进行史无前例的思想改造和文化革命。所以“文革”的爆发便不能不说是出于高层政治的特殊考虑,是“革命内部的革命”,也不见得就是历史的无厘头闹剧。至于说“文革”在其中后期濒于失控,则自然是背弃了高层政治和革命理想的初衷。换个角度来看,“文革”很明显承袭、发挥了“革命”的负面效应,李泽厚、刘再复把这些负面效应具体化为“迷信意识形态”和“迷信斗争经验”,[8]而“文革”在话语宣传方式和社会组织、动员方式上也同“革命”如出一辙,这样一来,“文革”和“革命”便无法截然分开,“新时期文学”的基本认识框架便宣告失效。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文革”可以而且也应当被作为“革命”的一部分,重新进行反思,但是反思“革命”很明显同反思“文革”不是一回事,于是谈及“后革命”时又该如何吞咽“文革”这块思想和文学的飞地呢?
二 “集体记忆”的代价
事实上,“新时期”以来,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始,当代作家便开始不断地叙说“文革”、回忆“文革”、思考“文革”,并且在现代性观念的怂恿之下,他们的写作通常也被视为是不断进步、不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的。相比较于威严的政治文件,个人化的文学作品更具亲和力也更具感染力,“新时期”以来的“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的创造过程”[6]3。但是如前所述,从一开始,“新时期文学”就毫不犹疑地接受了高层政治对“文革”的解释,因而文学想象催生的“集体记忆”莫不如说是在政治意识要求下形成的一种自我抚慰:“‘文革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历史记载、政治研究、法律审判及新闻报道的某种功能,而且这些‘故事’的写作与流通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政治、法律、传媒乃至民众心理的微妙制约。”“这种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与其说‘记忆’了历史中的文革,不如说更能体现记忆者群体在文革后想以‘忘却’来‘治疗’文革心创,想以‘叙述’来‘逃避’文革影响的特殊心理状态。”[6]3今天看来,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几乎全部都是“愤怒”和“控诉”的文学,这些“愤怒”和“控诉”的矛头当然是指向“文革”的,但“文革”从何而来?起码从作品中来看,作者们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文革”是因为“四人帮”、林彪反革命集团。这样,在文学参与形成的“集体记忆”之中,“文革”这个历史的毒瘤便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是因为一些人为的原因而导致的,“文革”“被记忆”为一个“人性恶”的深渊,或者说人们往往自动地从“人性恶”的角度、从“个人阴谋”的角度去清算“文革”。裴晓云、刘麦克(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1982)理想与生命的终结,钱文(王蒙:“季节系列”)的失落和彷徨,高爱军、夏红梅(阎连科:《坚硬如水》,2001)的迷狂和惊悸等等,这些“文革”记忆所共同宣泄的其实都是“文革”对个体心灵和个人命运的戕害,毫无疑问,这样的“文革”“集体记忆”当然是真实的,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文革”“集体记忆”更加“正确”——“它们不仅从对幸存者们的有用性这个意义上说是正确的,而且从社会接受性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正确的。”[9]也就是说,“文革”“集体记忆”的“真实”是以“忘却”许多追问和质疑为代价的,而那些被“忘却”的部分又往往被划定为“不正确”、“不合适”,从而长久地搁置在一个背光的世界里。换句话说,“新时期”以来的“文革”“集体记忆”都是在就事论事式地讨论“文革”,就“文革”而论“文革”,而对历史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能进行更多的思考和追问。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是被限定在一种单一的认识和阐释框架之内进行的,这一框架被赋予了权威、客观、科学的重重魅影,因而锁闭了其它认识和阐释的可能空间,希望藉此来维系对历史的阐释方式及其有效性。但历史从来都不是断裂式的,而是动态联系着的,顺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追问,顺理成章地便可发问道:没有“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没有革命化的“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又何来“文革”文学?但恰恰是在这里,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止步不前,这使得“文革”成了一件“无头”公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禁觉得尽管距离“文革”结束已经过去快40年了,可是对“文革”的反思力度却有必要重新估量,反思的角度和向度也还有待重新寻找和调整。在“后革命”的召唤之下,费尽心机地去讨论和解读那些反映“文革”的小说实属徒劳,它们那原地转圈的方式离所谓的“彻底”反思实在相距太过遥远。
并且在我看来,当前这种“集体记忆”的羸弱和不彻底或许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今天,在“文革”过去快40年之后,“新左派”会傲然崛起,他们当中不乏其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为“文革”翻案、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辩护。当然,他们的论辩方式也很独特,他们往往是把“文革”和“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进行对接,从“革命”形势发展的角度来梳理“文革”的必然和必要,于是“文革”便自然成为“革命”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这种“对接”同前面讨论到的文学作品里的对接可谓殊途同归。很明显,这种“对接”同“新时期”以来的历史模版是相抵触的,同“文革”的“集体记忆”也是不相容的。因而,这种“对接”难道不应当视为是对旧有的社会“集体记忆”的一次突围吗?由此又使我想到“季节系列”和《坚硬如水》等“文革”题材的小说里,大量对“文革”话语和口号的借用。这其中的讽刺、鞭挞之意不言而喻,只是鞭子是打在“文革”的屁股上,而真正受罪的又该是谁呢?
三 “文革”书写的“后革命”追认
另一方面,近年来“文革”题材的作品本身也发生了许多饶有趣味的变化。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青涩而短暂的青春年华无疑是最为美好和宝贵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当中受害最深的是裴晓云、钱文、王二(王小波:《黄金时代》等)、高爱军、夏红梅等这样的“青年人”,他们的理想被撕碎,他们的青春被搁浅,他们的生命被荒废。而在当前“文革”题材的作品里,主人公往往比这些“青年人”更加年轻,简直就是一群孩子,比如《生逢1966》(胡廷楣,2005)里的瑞平和蓓蓓(两人都不满19岁①陈瑞平“要到今年冬天才到19 岁”,蓓蓓“还要小一点,要到明年过年才是19 岁”。参见胡廷楣:《生逢1966》,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 页。),《启蒙时代》(王安忆,2007)里的南昌(约十六七岁②南昌“在相对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参见王安忆:《启蒙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 页。),《兄弟》(余华,2008)里的李光头和宋钢(李光头14 岁,宋刚15 岁[10]),《沉默之门》(宁肯,2004)里的李慢(13 岁,小学六年级[11]),《英格力士》(王刚,2004)里的刘爱、李垃圾(小学五年级[12]4),《扎根》(韩东,2003)里的小陶(约八九岁③“小陶生于三年困难时期”,而故事发生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参见韩东:《扎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第3 页。),甚至于在《大浴女》(铁凝,2000)和《蒙昧》(柯云路,2000)里,主人公尹小跳、尹小帆和茅弟在登场之初竟还是童蒙未启的少儿。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文革”的反思逐渐从偏重于政治层面逐渐滑向偏重于心理层面,从与主流政治共享若干重要历史前提和框架的阶段滑向历史开掘、反思的个人化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沉痛、凝重相比,当前新一批“文革”题材的作品的内在气质和情绪则表现得相当平静甚至是轻松。假如说在《英格力士》里,刘爱把“Long Live Chairman Mao”记作“狼立屋前门毛”[12]24只是王刚偶一为之、小说虽然局部不失戏谑而总体仍然严肃的话,那么在《漫游革命时代》(2007)里,“我”把英语的“毛主席万岁”记作“狼礼服前门猫”[13]112则想必近乎于林白“文革”经历的真实状态,在林白的《致一九七五》(2007)和《漫游革命时代》两部长篇小说里,“文革”不再意味着血腥和恐怖,插队、下乡也不再等同于劳动和绝望,如小说题目所示:“漫游”,这其中透露着从容、轻松、自由和欢快——“我早已厌倦家庭和父母,想着早些到那个叫做‘广阔天地’的地方去”,[13]103实际上这也正是作品呈现出来的情感基调。与之相类似的是,在《扎根》、《沉默之门》等小说里,作者不再以渲染“苦难”、“悲痛”为能事,相反表现出相当的柔缓、平静的韵味。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血色浪漫》(2004)以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2006)里,“文革”则几乎完全等同于狂欢,作为“黑五类”之列的、受到冲击的革命干部的子女钟跃民并不像在“新时期文学”里那样郁郁寡欢、惶惶不可终日,而是和郑桐、袁军等年轻人一起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这同80年代初期“文革”题材、“知青”题材的作品形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所谓批判、反思之后,“文革”时期的话语符号居然在文化市场上出现“回潮”和“复兴”:革命老歌的复制和热销(例如1993年的《“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①包括《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亚克西》、《八月桂花遍地开》、《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战士歌唱东方红》、《情深谊长》、《颂歌献给毛主席》、《祖国颂》、《日夜想念毛主席》、《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我爱北京天安门》、《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及《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蝶恋花 答李淑一》、《受苦人拿起枪闹革命》、《红灯颂》、《众手浇开幸福花》、《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万泉河水清又清》、《想念毛主席》、《满怀深情望北京》、《红梅赞》、《毛主席派人来》、《大红枣送亲人》、《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北京有个金太阳》共30 首歌曲。),“样板戏”、“红色经典”的改编和热议,取代了如来、观音而摇曳在汽车驾驶室后视镜上的革命伟人照片,以及大量粗制滥造的、印有毛泽东、雷锋以及切·格瓦拉头像的绿色军用帆布书包,真可以说“红太阳热”、“毛泽东热”、“红色经典热”、“红色旅游热”、“文革文物热”是一浪接着一浪。当然这背后的文化寓意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是激动的怀旧,有的是商业利益的表达,有的则纯粹是政治波普。现实生活中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的对峙也殊为有趣,老干部、老教授们为“文革”的反思和研究而摇旗呐喊,文坛每有新作出版便欣然命笔评说一二,现实生活的不平和不满则大大激发了弥漫在中年群体中的“文革”怀旧情绪,对于更为年轻的一代来说,“文革”是“听说过没见过”(崔健的歌词)的“新长征上的摇滚”——“‘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②这是《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张艺谋后拟定的新闻稿的题目,并非张艺谋的原话,题目与张艺谋的原意略有不同,但出入不大。张艺谋的原话是:“你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改变,我们中国人几乎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了。我们的80后90 后已经把‘文革’看做历史了,如此长的一个十年浩劫,中国民族都挺过来了,那场政治运动触及到人人的灵魂啊,我们都可以走出来。”参见夏辰、张英、俞峥:《“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这究竟该说是老干部、老教授们刻舟求剑、落伍得有些可爱,还是文艺达人、潮人洞明世事,超前得近乎玩世不恭呢?是商业文化对民族梦魇的可怕洗脑,还是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的有意“催眠”呢?但不管怎么说,与“革命历史”题材的“后革命”改写几乎同步,“文革”题材的作品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形,这种“同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当代的文化意识把“文革”追认作了“革命”的一部分,从而溢出了“集体记忆”之外呢?如果我们承认“文革”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应当把“文革”放置在“革命”思潮之中来予以反思的话,那么显然“后革命”也理当包括对“后文革”的整合,只是钟跃民他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又当如何填充进“后革命”的格局当中呢?如何才能克服“文革”的改写之于“后革命”的那种方枘圆凿的尴尬呢?
[1]祝东力.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转折[J].批判与再造(台湾),2005(16):17.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C]//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
[3]任剑涛.后革命与公共文化的兴起——《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前言[J].开放时代,2007(2).
[4]〔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M].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5]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M]//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2.
[6]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 篇文革小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0.
[7]都梁.亮剑[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395.
[8]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84-102.
[9]〔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 [M]//〔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6.
[10]余华.兄弟(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2,1.
[11]宁肯.沉默之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27.
[12]王刚.英格力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3]林白.漫游革命时代[J].西部华语文学,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