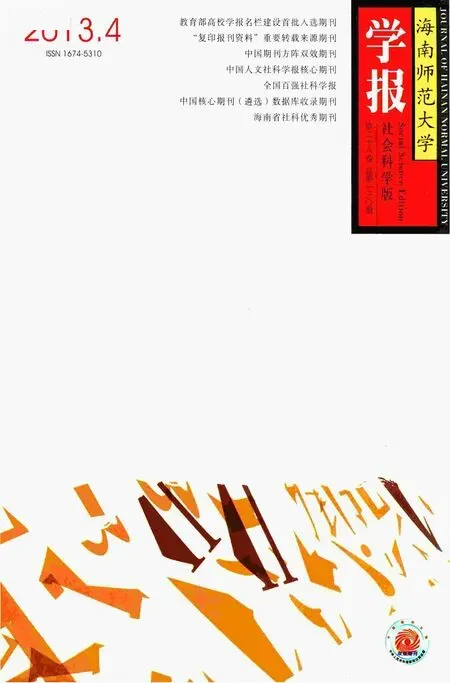现代作家笔名现象探究
殷 翔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笔名这个名词源于西方的“pen name”,中国的近代国门被西方国家打开,报纸、杂志等新式媒体迅速发展,大量的文学刊物也在此时涌现,作家们经常署用笔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许多作家的本名不为人知,笔名却名声在外。顺便言之,同为文名,现代作家的笔名有别于古代的文人字号,古代的文人字号主要是文人自我标榜的符号,它具有固定性,现代作家的笔名更主要作家们掩饰真实身份的符号,它具有多变性,作家们笔名的数量之多,变换之频繁,都是前所未有的。
从数量上看,笔名最多的10 位现代作家,第一是鲁迅,①“鲁迅”本是周树人的笔名,但这笔名已经成为他的通用名,故在列举作家时皆用通用名,下文皆如此。笔名213 个;第二是巴人,笔名132 个;第三是茅盾,笔名121 个;第四是周作人,笔名94 个;第五是夏衍,笔名75 个;第六是郑振铎,笔名71 个;第七是瞿秋白,笔名69 个;第八是王统照,笔名61个;第九是唐弢,笔名50 个,第十是沈从文,笔名47个。②以上统计参考徐迺翔、钦鸿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以下统计数据皆参考此书。以写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213 位现代作家为例。其中只拥有1 个笔名或以本名为笔名的作家共10 位,占4%;拥有2 到10 个笔名的作家共123 位,占59%;拥有11 到20 个笔名的作家共47 位,占22%;拥有21 到30 个笔名的作家共15位,占7%;拥有30 个以上笔名的作家共18 位,占8%。可见,笔名的使用是现代作家文学活动中的普遍现象。
一
笔名的大量使用,是新的时代使然,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姓氏作为一种世袭品,是家族系统的标志,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名一旦被先人取下,也不能随意变更。而“五四”时期,宗法制度受到强烈冲击,姓名不再被看得那么神圣,有的人故意使用假名,还有更激进者主张废除姓氏,冯文炳干脆以笔名“废名”来宣示。“丁玲”这个笔名也是废姓得来的,她原名蒋冰之,1921年丁玲来到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书,一度废姓用“冰之”名,后来“废姓引起很多麻烦,只好随便加了一个姓”,这个姓就是笔画比较简单的“丁”。1925年丁玲又萌发了当电影明星的念头,于是改名“丁玲”,她说:“‘丁玲’毫无意思,只是同几个朋友闭着眼睛在字典上各找到一个字作名字,‘玲’字是我瞎摸到的。”[1]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府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报纸法》、《管理新闻营业条例》。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当局也出台了《出版法》、《新闻检查标准》。这些法律条例对文化出版物实行严格的检查,作家们为了躲避文网,不得不变换笔名发表文章。1934年1月21日鲁迅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了杂文《批评家的批评家》,使用的笔名是“倪朔尔”,这个笔名看起来有些古怪,后来有人解释,“这个笔名是将英语Lusin(鲁迅)的各字母依次倒写,就成了Nisul(倪朔尔)。”[2]巴金1934年4月在《文学季刊》第1 卷2、3 期发表小说《龙眼花开的时候——一九二五年南国的春天》(即《电》),使用笔名“欧阳镜蓉”,1934年4月《文学季刊》一卷二期发表散文《倘使龙眼花再开时》使用笔名“竟容”。在《〈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中巴金对这两个笔名做过详细说明。长篇小说《电》写成后交给上海《文学》发表,刊物已将前两章排好,但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第一批清样后,禁止发表。“我便又把小说带到北平,决定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它。”“《电》在《文学季刊》上发表的时候分作了上下两篇。题目改为《龙眼花开的时候》,另外加了一个小题目——一九二五年南国的春天。作者的姓名变成了欧阳镜蓉。”“我当时要使读者相信欧阳镜蓉是一个生长在闽、粤一带的人,《龙眼花开的时候》是费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在九龙写成的一部小说,我甚至用了竟容这个名字写了一篇题作《倘使龙眼花再开时》的散文,叙述我写这部小说的经过。”[3]
刊物的编辑也经常变换笔名写稿。1930年10月至1932年4月,老舍主持《齐大月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当时稿源严重不足,老舍便频换挈予、挈青、舍予、舒舍予等笔名,自己动手凑稿子。编辑预约的写稿者也如法炮制,巴人从1924年到1956年共使用了132 个笔名,其中在1937年就使用笔名72 个,使用这72 个笔名所写的文章全部都是发在《立报·言林》上面。巴人说“在抗战爆发前一年,我无以自活,《立报·言林》的编辑谢六逸同我相约,每月写短评二十五则,致送酬金三十元,但不必署名,由编者自填。因恐引起猎狗之嗥嗥而不利于我。”[4]
二
更换笔名是为了掩盖作者的真实身份,大多数笔名的取用却并非随意,经过作者的成熟思考后取的笔名,里面往往包含着命名者丰富的个人寄托。
胡适原名嗣穈,后改名胡适,他的许多笔名是由他的字“适之”演化而来,如“适庵”、“适广”、“胡适之”。晚清时期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对当时的读书人有很深的影响。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写道:“有一天早晨,我请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两字。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5]
鲁迅曾有过一个笔名“宴之敖者”,首见于1924年9月21日作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故事新编》里面《铸剑》中的主人公也叫“宴之敖者”。许广平说:“宴之敖三字很奇特,查先生年谱,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载:‘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迻入。’民国十二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可见他是把八道湾屋买来修缮好,同他的兄弟迻入,后来才‘迁居’了的,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实。究竟为什么‘迁居’呢?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笔名表达了对那位弟媳的不满。[6]
巴金年青的时候信奉无政府主义,曾留学法国追慕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有人认为“巴金”这个笔名是从他所崇敬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事实并非如此有意。巴金在《谈〈灭亡〉》中说:“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笔名中的那个‘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起的,那个时候我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说我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名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7]
胡适、鲁迅、巴金的笔名里面分别包含着对新的思想的追求、对兄弟感情失和的纪念、对友人不幸的缅怀和信仰寄托,这些情感是内指的。还有的笔名包含情感是外指的,这些外指的情感包含了对自我个性的张扬,对政治时局的态度,笔名将其突显出来,比如郭沫若和萧军的笔名。
“爱牟”和“麦克昂”是郭沫若的笔名,“爱牟”是英语“I’m”的音译,1924年郭沫若在《致成仿吾书》中首次使用这个笔名。1926年9月创造社出版的小说散文集《橄榄》,其中的《炼狱》、《十字架》、《行路难》、《未央》等篇也都以“爱牟”为作品主人公的名字,《橄榄》相当于郭沫若自传性小说、散文集。“麦克昂”这个笔名首见于文艺论文《英雄树》,发表于1928年1月《创作月刊》第一卷第八期。郭沫若说“‘麦克’就是英文maker 的音译,‘昂’者我也,所以麦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于笔名中凸现。[8]
萧军原名刘鸿霖,他的笔名有“酡颜三郎”、“萧军”等。“酡颜三郎”这个笔名看起来象是日本人的名字,可以起到遮人耳目的作用,实际上却有其内在含义。“酡颜”是酒后脸色发红的意思,那正是他青春年少、红颜赤颊的健壮体魄的一种恰当比喻。“三郎”则来源于他和两个好友结拜,按年龄长幼他排行第三。“萧军”这个笔名是他在青岛时期与鲁迅通信时起的,取“萧”为姓,是因为他喜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老英雄萧恩,又因为他是辽宁省人,古时辽人多姓萧;取“军”作名,一则因为自己原本行伍出身,一个字可把他早年的经历概括无遗,二则因为当时正处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蒋介石调动白军围剿红军之际,他对此十分气愤,为了表达自己对工农红军的感情,就把红军一词一分为二,作了萧红和他的笔名。萧红和萧军的笔名相加,即是“小小红军”之意。[9]这可谓笔名政治的显例。
三
笔名的使用又是和作品及作家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与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联系起来分析。从文学内部研究的角度看,把笔名视为文本阐释的引线,可以利用它对文本进行进一步的阐释。从文学外部研究的角度看,把笔名视为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的一个联接点,可以借此研究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条件,认识这些条件有助于理解作家的文学活动。
若把作品的正文视为正文本,就可把环绕在正文本以外的引语、题辞、注释、笔名等视为作品的副文本,副文本既是文本的构成因素,又是正文本的阐释因素。①“副文本”(peritext)的概念源自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的《广义文本之导论》(《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是相对“正文本”而言的概念。从这个角度研究笔名对文本的阐释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作家使用新笔名发表新作品,笔名和作品之间往往具有互文性,可以“茅盾”、“逃墨馆主”这两个笔名为例。
茅盾原名沈德鸿,“茅盾”这个笔名首见于1927年9月《小说月报》上的小说《幻灭》。茅盾本来取笔名“矛盾”,后来经过《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的修改,笔名变成了“茅盾”,但加了“草”字头并不能掩盖其“矛盾”意蕴。茅盾说:“为什么我取‘矛盾’二字为笔名?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结合茅盾小说的文本,他用“茅盾”这个笔名发表的三部小说(即《蚀》三部曲)确实反映了他说的各种矛盾,《动摇》中的劣绅胡国光与县党部的权力斗争,反映着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特派员史俊与特派员李克处理店员风波和农民暴动的不同做法,方罗兰的动摇与软弱,反映出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静女士感叹“一方面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方面却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烦闷”,方太太自叹“实在这世界变得太快,太复杂,太矛盾,我真真地迷失在那里头了!”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茅盾1927年夏在庐山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陷入了苦闷,这也是茅盾在生活上、思想中的矛盾。所以“矛盾”可视为解读这个三部曲的关键词。
再看“逃墨馆主”这个笔名,这是《子夜》1932年1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的署名,当时小说的题名为《夕阳》。“逃墨”二字出自《孟子·尽心下》:“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茅盾在自传中称:“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夕阳》取自前人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喻蒋政权虽然战胜了汪、冯、阎和桂、张,表面上是全盛时代,但实际上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是‘近黄昏’了。”[10]结合茅盾对《子夜》的写作意图的说法,他说这部小说同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当时的论战者,大致提出了这样三个论点:一、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是革命派。二、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这是托派。三、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夹缝中取得生存与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子夜》通过吴荪甫一伙终于买办化,强烈地驳斥了后二派的谬论。”[11]这表明茅盾是倾向于第一派的,即革命派,印证了他对“逃墨馆主”这个笔名的解释,茅盾早就有“赤化”的倾向。
若将笔名视为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的一个联接点,作为一种传播策略,它的兴起、高涨和衰退与新文学的发展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使用笔名的多是新文学作家,因为新文学在发轫期不见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话语,即旧文学话语,在这种情况下要争夺文学话语权,新文学作家不得不署用假名发表文章,比如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戏”。钱玄同在《新青年》第4 卷第3 号上以“王敬轩”的笔名发表反对新文学变革的文章,刘半农等一批新文学倡导者群起而攻之,一些不明就里的旧派文人站在“王敬轩”的立场上帮助“王敬轩”说话,而这恰恰是新文学倡导者设下的陷阱。通过与旧文学的论争,新文学渐渐确立了其合法地位。
越来越多的新文学作家使用笔名发表作品,当作家用某一笔名发表的作品成为其代表作时,这个笔名往往会取代作家的真名成为他的通用名,并且成为他的象征资本。①象征资本,就是不管属性怎么样(无论哪种资本,有形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这种属性被社会行动者所感知,他们能感受它,确认它使之有效。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5 页。鲁迅用“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之后,好评如潮,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就从未换过笔名;巴金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时署用笔名“巴金”,这个笔名就一直保留下来;“老舍”这个笔名是舒庆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署用的笔名,这个笔名也成了他的主用名。笔名往往凝聚着作家的创作风格、作品特色,一个作家的笔名被广大读者认可,也就意味着这个作家所代表的文学倾向、审美趣味被认可。随着新文学作家的笔名成为招牌式的通用名,笔名的作用已渐渐从对新文学作家真实身份的遮蔽转向了对新文学作家“作家”身份的彰显。
40年代,笔名浪潮开始衰退。从使用笔名最多的几个作家来看,茅盾在20年代更换笔名20 个,30年代更换笔名16 个,40年代以后更换笔名19 个;巴人在20年代更换笔名8 个,30年代更换笔名120个,40年代以后更换笔名7 个;郭沫若在20年代更换笔名10 个,30年代更换笔名6 个,40年代以后更换笔名6 个;巴金在20年代更换笔名19 个,30年代更换笔名12 个,40年代以后几乎没有更换笔名,由此可见,“30年代末期以后,笔名使用的普泛化程度降低,笔名对文学发展的实质性影响锐减。中国现代文学的质地也发生了微妙的调整,如果说此前的新潮文学、白话文学与传统文学比,充斥着挑战者的姿态,那么此后,新文学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新宠,那些‘以假乱真’、‘混水摸鱼’的匿名发表作品策略都不必再用,新文学统治地位的取得与新文学家真名意识的膨胀相互协调、互相印证。”[12]
四
作为一种历史沉淀物,披沙拣金,现代作家笔名仍然有挖掘的价值。通过笔名的考证可以确认文章作者的真实身份,对于文学史料的整理有很大帮助。通过发掘作家新的笔名,又可以藉此找到作家的佚文。无论是史料的整理还是佚文的发现,它们都可以充实、甚至改变作家在文学史上的论述。
1928年8月《创造月刊》2 卷1 期发表了一篇文艺批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作者署名“杜荃”。文章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Fascist”等。此文发表多年一直无人知晓“杜荃”是谁,直到1979年有学者提出大量论据,论证“杜荃”即是郭沫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3]联系到郭沫若某些笔名的含义,“杜荃”这一笔名的含义可试解为:杜,是郭沫若的母姓,郭沫若为纪念母亲曾以母姓取过“杜衎”、“杜顽庶”、“杜衍”的笔名;荃,一种香草名,亦名“荪”,屈原《离骚》有“荃不察余之衷情兮”之句。作为一篇创造社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代表性文章,“杜荃”这个笔名的发掘,对于廓清“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详情,以及研究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都有重要意义。
研究文章的署名可以确认文章的作者,发掘出作者的新笔名,又可以从新笔名下手,发现作家的佚文,佚文的发现可以充实对作家的研究。例如,《周作人笔名“牧童”及佚文两篇》一文,②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6 期,作者刘涛。通过阅读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6月4日、5日《明珠》副刊,发现一篇散文《苍蝇》,作者署名“牧童”,而《苍蝇》是周作人早期散文的名篇,最先发表于《晨报副镌》1924年7月13日,署名“朴念仁”,后又刊登于《小说月报》第15 卷12 号“文章选录”栏,署名“周作人”。确认了“牧童”即是周作人,通过对“牧童”这一笔名的考察,研究者又发现了周作人用这个笔名发表的《抽烟与思想》、《都市的热》这两篇佚文。《“五四”女作家苏雪林笔名考辨》一文,①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 期,作者王翠艳。通过对《益世报·女子周刊》上发表的新文学作品的笔名进行考辨,发掘出苏雪林的“伽”、“病鹤”这两个笔名,明确了《女子周刊》的主编兼主笔“伽”即苏雪林。借助《女子周刊》的文章,又可以发掘苏雪林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价值趋向,从而为探索以她为代表的过渡时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复杂人格获得第一手的可靠史料。就这一意义而言,苏雪林以“伽”为笔名写下的文章,不仅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苏雪林近80年的创作生涯中具有引人注目的开端地位,在苏雪林本人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史上亦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目前对作家笔名的研究多侧重在笔名的收集与考证,或对某个有特殊意义的笔名进行阐释。对现代作家笔名的研究,还存在着拓展的空间。笔名虽小,但是它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笔名是文本的一部分,它不是空洞无物的能指,而是作者所处时代、自身经验和身份的多棱镜。转动这面镜子,我们看到的是文本正文暗示过但又无法企及的无数其他文本。”[14]对在创作的不同阶段使用笔名较多的作家,研究他们的笔名,发掘新的史料,对作家的研究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1]丁玲.丁玲文集:第10 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100.
[2]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192.
[3]巴金.巴金选集:第4 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455.
[4]王任叔.巴人杂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21.
[5]胡适.四十自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47.
[6]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2 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46.
[7]巴金.巴金选集:第10 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1.
[8]郭沫若.郭沫若文集:第8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6-287.
[9]纪维周.萧军笔名的由来[J].世纪,2005(4).
[1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5.
[11]茅盾.茅盾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60.
[12]袁国兴.隐身与遮蔽:“笔名”对发生期中国现代文学质地的影响[J].文学评论,2009(3).
[13]单演义,鲁歌.与鲁迅论战的“杜荃”是不是郭沫若[J].西北大学学报,1979(10).
[14]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