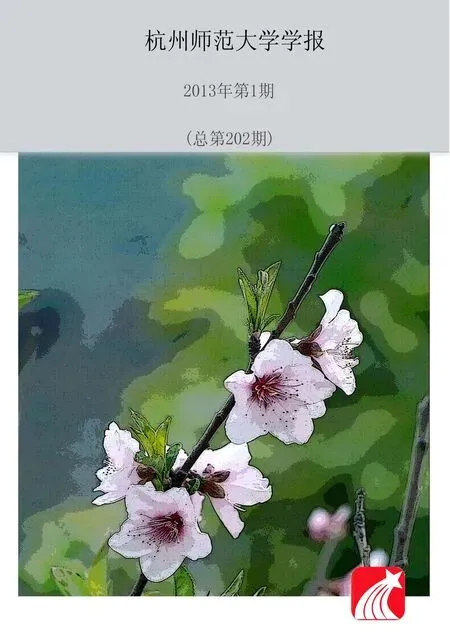恐怖伦理学
[美]雅克·莱兹拉著,王 钦译
(纽约大学 比较文学系,美国 纽约 10003)
恐怖伦理学
[美]雅克·莱兹拉著,王 钦译
(纽约大学 比较文学系,美国 纽约 10003)
“恐怖”作为伦理学基础预设了共同体边界的确定和普遍性主张的适用范围的不确定性。在考察索福克勒斯和塞涅卡对于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塞涅卡的《俄狄浦斯王》将索福克勒斯设置的僵局从政治本体论领域转化到审美领域,并在审美的层面上处理它们。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城邦的持存前提是政治的丧失——被转化为塞涅卡的喜剧。由此,“恐怖伦理学”的命题导向政治概念的缺陷性问题和主权问题。
恐怖;伦理学;主权;俄狄浦斯王
让我们把故事设定在1982年。哲学家列文(Michael Levin)提出一个假设:一座城市的存在岌岌可危,而它的存亡取决于我们的决断。列文说的是一座具体的城市,但它代表任何城市。他著名的寓言令人感到恐怖,但这却是他所意在达到的启发经验,或者更好地说是公民经验——如果我们真的感到恐怖,那我们就会行动起来保卫这座城市。他所讲述的故事涉及伦理判断和政治利益的关系,并且将全球化与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放置在一个大都市想象的形式之中。列文写道:
设想一个恐怖分子在曼哈顿安置了一枚核炸弹,它将于7月4日正午爆炸,除非……(这里列举了一连串常见的要求,例如金钱、释放同伙等。)然后,设想他在灾难降临的那天上午10点被捕,但是他宁死不屈,不愿透露炸弹安放的位置。我们该怎么做?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等候他的律师、进行进一步审讯——数百万人将会死去。如果解救这些生命的唯一办法在于施加极其残暴的折磨在这个恐怖分子身上,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么做?我认为没有理由。无论如何,我请你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个问题。
严刑逼供恐怖分子违宪吗?很可能。但数百万人的性命当然要远远胜过合宪性问题。严刑逼供的手段野蛮吗?大规模杀伤性袭击远远比这野蛮。事实上,为尊重某个藐视自己罪责的人而让数百万无辜者白白送死,这是道德懦弱的表现,也是政治上不愿意有损自己清白的表现。如果你抓住了恐怖分子,如果你知道数百万人因为你不愿使用电刑而死去,你还能睡好觉吗?*Michael Levin, “The Case for Torture”, Newsweek, June 7,1982.这篇文章被收入很多文集,网上可见http://www.coc.cc.ca.us/departments/philosophy/levin.html。也见Linda H. Peterson和John C. Brereton编的The Norton Reader: An Anthology of Expository Pros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03),694-696。
与之相反的论辩从未占过上风,至少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美国媒体或政治辞令中没有,“9·11”事件以后就更没有了。甚至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和关塔那摩监狱受到曝光的囚犯待遇和“强化审讯”等种种丑闻,都没有对上述论辩产生冲击——无论是在法理上、法律上,还是文化上。在学界内部,列文提出的争议场景的影响力也丝毫不弱。这篇文章在各类写作课或修辞课的课程大纲上出现,与其说证明了它论证的自洽,不如说证明了它在论题、意象和技巧方面的出色,以及与令人难过的时事之间的切合。*虽然从原则上讲,“恐怖”威胁或行为的真实例子要比假设性的场景更能阐明对于酷刑的功利主义式运用,但真实例子有很多实际的和概念的约束。首先,臭名昭著的一点是,由于严刑逼供而来的信息常常不准确,能够证明酷刑对于调查或法理程序起帮助作用的实际例子少得可怜。其次,拿酷刑在真实情况下“奏效”——阻止某起恐怖行动——作为例证,马上就遇到我们或可称为“道听途说”的麻烦。因为没有任何政府或组织希望被人看到运用严刑逼供的手段,政府或组织就很难以第一人称断言,在阻止某起具体的恐怖袭击时,他们确曾运用过这种手段。相反,人们可以说自己曾听到某个政府或组织曾利用过从酷刑中得到的信息——比如,德肖维奇(Alan Dershowitz)坚称,菲律宾政府曾于1995年利用严刑逼供套得的信息以“挫败暗杀教皇和使11架商务客机坠落太平洋的计划”(Alan M. Dershowitz, Why Terrorism Works: Understanding the Threat,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137)。人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或美国政府曾利用过我们听来的菲律宾通过酷刑获得的信息,以挫败某项恐怖计划。”反过来,菲律宾政府可以诉诸某种相同的“道听途说”:“为了挫败某项恐怖计划,我们菲律宾政府将我们听到的信息——据说是某个政治组织利用酷刑得来的——传达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或美国政府。”为酷刑负责的总是他者,而任何以第一人称说出类似“我因为原因X或Y而动用了酷刑,为的是达到效果A或B,取得信息L或M”的话,从表面上看都是自我挫败的:承认对他人施以酷刑的主体,由于这一事实本身,就没有资格对于已经做出的酷刑给出任何理由。真实例子(如果确实存在的话)还有进一步的逻辑约束和实际约束。人们可以这样分析严刑逼供的“真实例子”:比如这样一个陈述——“这个信息是通过明令禁止的审讯手段收集来的,作用是阻止某项袭击或犯罪行为”——结合了两类陈述。一方面,对于事态的描述做出了事实论断或指涉性论断。“在此我们拥有或曾经掌握着某个信息”是个可以被证实(更可能的是被证伪)的陈述,而“某个恐怖行动并未发生在这个或那个时刻、这一天、这个地点”看上去也是个事实陈述,某种意义上看上去是真的和可证实的(尽管我们首先要对什么是这里的“事实性”或“真”进行相当狭隘的理解)。另一方面,有一些陈述的基础是,将貌似事实性的陈述以关键的、虚词性的(syncategorematic)形式组合起来。比如这样一个论断——“某个恐怖行动没有发生在某天,因为我们掌握了某个信息”,这个假设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成立,但它并不在任何条件下都成立,而且它从来不是必然成立的。我们总是可以设想其他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某个行动(包括恐怖行动)不会或不曾在某天发生——从意外事故、内部故障到世界末日。关于酷刑的文献多得让人束手无策,最近的文献列表可见Sanford Levinson编的Torture: A Colle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基于“定时炸弹”场景的功利主义论述相当刻板,并且,如电视剧《24小时》所表明的那样,“更多人的更大数量的善超过任何特殊利益,也超过某些普遍利益(例如体现于保存法律与‘合宪性’之中的抽象社会利益)”——这一论题具有不可否认的商品特征(commercial cachet)。反对列文场景的最有效方式是从实际性的反对出发(例如,论证严刑逼供的手段并不奏效,因为它并不产生所需要的效果,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或者论证说,严刑逼供的手段会纵容他人用同样的方式对待美国士兵;或者论证此类折磨有损美国的国际声誉,等等)。义务论、价值伦理、宗教道德——当想象这座城市危在旦夕之时,一切反对酷刑和国家恐怖的伦理学论辩都倒塌了。城市的围墙保护我们不受敌人的袭击,抵挡恐惧,形成我们彼此的交际圈,界定了一系列实践、习惯和语言,正是它们规定了我们的身份。在城市的围墙内,我们都是人文主义者;权利得到平等保护,政治自主性的标准得到确定。当我们允许那些实践逾越城墙,并运用于那些并不接受这座城市的语言和习俗的(域外的)人们身上时,我们就被扣上“道德懦弱”的帽子。
我们继续在这一点上停留片刻。更仔细地解读列文的立场,我们会发现它取决于一种要么是不自洽的、要么是不切实际的价值论述。首先,在列文的描述中,之所以严刑逼供被允许,是出于其“求真”的作用,但这一作用或许无法与其他次级的、更次级的作用分开,而这些其他作用则无法因同样原因被允许(因此也就需要与首要目标进行权衡,假设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举两个例子:产生“真相”(如果确实如此的话)的折磨行为也必定产生对这些手段的自返性证成(reflexive justification)。如果我们成功拯救了这座城市,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得到了证成;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我们至少不必有“道德懦弱”的愧疚,即便我们对其他事情感到愧疚:我们的英雄主义属于悲剧英雄一类。下述原则——严刑逼供因其奏效而可被允许——并没有因此被反驳;恰恰相反: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审错了恐怖分子(可能是其他人知道炸弹安放在哪里),也可能是我们没有对那个知道真相的人施加足够的酷刑。这第二种自我正当化的、英雄主义式的作用,并不作为折磨行为的目标而在道德上被允许,但它无法与第一种作用区分开。而且,折磨行为也具有人们或许可以称为词序上的(lexical)次级的后果:如果我可以允许自己运用电刑,那么我就不再是在此之前的那个我了(例如,我或许由这一姿态而获得了某种宪法之外的英雄主义),而我所拯救的城市如今被笼罩在一圈域外的、法理之外的围墙内,这些逾越的围墙不同于之前那些界定并守护这座城市的围墙。正如不存在一种单一而谨慎的折磨行为——相反,存在的是行为的“复数性”,包括各种姿态、决断、不同势力运用的各种工具、在时空上的延伸,等等——因而也就不存在折磨行为的简单结果(例如,吐露真相也是一种报复行为)。
第二,考虑到严刑逼供下的陈述行为,上面这种行为的杂多性,以及它跨越空间、行为者、时间的分化和渗透,同样成立。忏悔,或者是有关地点、计划、姓名的坦白,在证实条件满足以前,将不会算数。坦白与事实相符吗?要是所陈述的信息是真的却不完整,那怎么办?换句话说,可能炸弹确实在X位置,可我还没有告诉你如何拆除它(恐怖分子都聪明得可怕)。例如:告诉我炸弹安放在哪里;炸弹在X位置,比如说在法航售票窗口,但这一陈述即便证明为真,也不足以阻止炸弹爆炸。还需要进一步的答案,以及更进一步的其他问题。(如何拆除炸弹?)从法学角度出发则又预设了另一类问题和答案,由种种问题而确认这个人确实是我们需要套其口供的恐怖分子(而不仅仅是个漫步于城市的游客)。一些问题滋生出其他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问题。这里的困难既是概念上的,也是实际上的:在开始提出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设想非常多的情况,不存在单一的问题足以应对列文所设想的场景。问题本身也是杂多的。
认为存在一个单一的、主导性的问题,这个幻想也与时序幻想密不可分。思考一个古代的故事:这次场景是在忒拜群山间,两条道路在城市附近交叉,那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悬而未决的犯罪,以及一起私下的、被人遗忘的犯罪(抛弃一个孩子),这两起犯罪仍然在困扰这座城市。牧人说出了那个当初把孩子交给他的人的名字,由此瘟疫消失了,或者不如说,他同时命名了这个瘟疫并通过命名而终结了瘟疫。像索福克勒斯的寓言那样,列文的寓言具有神话的视野:当恐怖分子因酷刑带来的痛苦而说话的时候,威胁消失了。事实上,我们意识到威胁已经消失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的话是真的。或者是因为,答案已经提前知道了(正如在列文的例子里,大家都知道日期是“注定的”。就像“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而他的信息着实会帮助拯救这座城市等等事实那样,俄狄浦斯的出身也预先就被诸神、斯芬克斯、先知提瑞西阿斯[Teiresias]、俄狄浦斯、观众们知道了)。我们会说:“当然啦,我们始终都知道炸弹装置就在那里”,并且现在炸弹不在那里了,或者已经失灵了。如果没有这种神话式的意识结果,折磨行为就无法在产生真理和拯救城市的层面上展开——这种行为是我利用信息时所产生的间接后果(虽然我或许是有意为之)。相反,如果没有上述意识结果,产生的就会是这样一种言语,其真假有待在最后一刻揭晓: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学家或许会称之为“未来偶然事件(future contingent)”。(这类事件是在真理上保持中立或有待确定的陈述,无法适用亚里士多德的排中律原则——即要求命题必须或为真或为假。最著名的例子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一场海战会在明天爆发”。如亚里士多德的例子那样,“安放在曼哈顿的炸弹将在‘7月4日中午’爆炸”尚不为真或为假:它仅仅会变成真的或假的陈述。)在未决的时期,介乎陈述和证实之间、行为及其结果之间的时期,我的判断同样是中立的、悬而未决的、悬置的。说到底,如果不是把一种行为、一个决定、一种事态与其预期的或推断的结果相联系,或与某些确实是内在的、公认的、清晰的、构成共同体纽带的标准和准则相联系,我(或者我所在的共同体)又将如何进行评判呢?*我强调算计或推测的一面,以阐明这一政治共同体观念与韦伯(继滕尼斯之后)所谓的“结合性社会关系(Vergesellschaftung)”相关,在这个群体中“社会行为的导向依赖于理性驱使的利益调整,或受到类似推动而达成的一致,无论理性判断的基础是绝对价值还是暂时的理由”。见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1968; r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40-41。
人们无法同时依照结果主义和真理上中立的偶然性来证成某个行为(或一组行为:严刑逼供);人们无法假定哪些行为后果将从属于伦理判断、而哪些仅仅是偶然事故;或者不如说,人们可以这么假定,但仅仅能够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这么做。举个文学的例子或许有帮助:考虑另一个故事。这次是《炼狱篇》,维吉尔正指导朝圣者但丁如何理解出现在他眼前的折磨和惩罚场景:
我的眼睛正专心致志地望着,
要看极愿意看到的新鲜事物,
但掉过去观望他时并不迟缓。
读者,我不愿意你因为听到了
上帝如何命定罪人偿清债务,
就吓得抛弃了你的善良意图。
且不要注意那折磨的形式;
要想一想那随着来的,想一想
这痛苦最多也不会超过末日审判。*Dante Alighieri, Purgatorio X, ll. 103-111, trans. W. S. Merwi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2000),99;行数根据原文略有调整。(译者按:引文翻译根据朱维基译但丁《神曲:炼狱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80页。)
这里的场景引人走神,以至于诗人但丁转而(站在旅程终点的高度而回溯性地)指导他的读者如何理解他在维吉尔帮助下所目睹的折磨。他告诉读者:想一想那随着来的,想一想“末日审判”。专注于折磨的种种形式,便犯下了滥施同情或“道德懦弱”的过错。只有从结果或事件(event,对于“succession[随之而来]”一词的程度很强的佳译)的角度来看,从奥林匹亚的位置来看(这个位置是保留给那些人的:他们不仅知道时日和行为有其结果,并且知道行为的赏罚;他们拯救了城邦或灵魂),人们才能真正做出判断。但丁用了两遍动词以示强调:不是目见或想象,而是思想,il pensier,帮助我们从我们看到或想象的折磨中找到用以证成这些折磨行为的结果。结果主义思想能够防止一个例子变成反面教训,也能防止(比如)从他人的受苦场景中感到太多的兴趣、快乐或满足,也能防止我们的所见或所想从附属位置反过来压倒一切“善良意图”,像美杜莎那样麻痹我们的判断并摄住朝圣者。列文的寓言既要求读者具备关于事件的神话视角,也将这个视角作为城市赖以建立的基础,以及判定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基础。公民的判断被放在末日审判的角度来思考,从属于主权的完整性。主权思想将我们仅仅看见和想象的事物排除在城墙之外。这座城市是一种末世论。是否存在另一种方式来想象恐怖、判断和城市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开始故事。仍然是古代的场景,古老的悲剧:女性、枯萎、瘟疫;它们的原因不得而知。这座城市,城邦(polis),支撑它的制度和共同体实践,使这些制度和实践得以可能的牢固的城墙,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一切都处在危难中。两个故事交错于这个古代场景中:城市的受难故事及其统治者的起源故事。在这两个故事交会的地方,主权者正向仆人说话;这个仆人(他起初保持沉默——出于什么呢,克制?礼仪?忠诚?)被迫开口说话:出于暴力(violently)。对于总是在旁的公民歌队而言,这一场景有着索福克勒斯或塞涅卡的现代读者所不熟悉的形式。例如:我们作为这些古代悲剧的现代读者或观众,相信出现于歌队面前的故事与出现于我们面前的故事应相互区分,因为一者涉及到公共事务,而另一者涉及私人事务。并且我们相信,将主权(既有镇定自若[self-possession]的意思,即能够自主决定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也有政治主权的意思)置于一个职务或一个个体身上,或是将主权分配到各个团体身上,其背后的道德基础取决于一项区分:城市的利益与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的利益。我们或许要再次询问,对于以城市为名实施的行为而言,判断其是否允许的基础,是否可能是世俗的、非末世论的?最后,我们相信,即便我们承认如果仆人不说出那个故事,城邦就不能继续持存;进一步,即便我们承认为了达到持存的目的,仆人(或恐怖分子)按照列文的话说可以“被施以最为严酷的折磨”——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会下结论说,此后这个城邦将不再是它之前那个样子了,当它以暴力的方式获得那个将会使它得救的故事时,它的种种自我理解也就不复存在了——例如,它将不再是一个“合宪”的社会,它的价值将不再具有普遍性或得到普遍应用。
当这个古老的故事开始的时候,这四种反对都不相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尚未采取其现代的、差异性的、相互关联的、对立的形式,而且它们之间的区别也不具有规范性价值。仆人的故事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属于这个城邦,而它在公共事务中的位置则是暴力的结果——当代的眼光可能会觉得这种暴力根本无效,甚至是自我挫败的;巨大的、低效的、精微的世俗化装置在那时还没有立足点。*关于奴隶的“对体性”历史,见Page DuBois, Slaves and Other Objec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在索福克勒斯那里、甚或在塞涅卡那里,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世俗立场,借此某个角色、歌队的某个成员,或事实上是某个观众能够:第一,询问这个城邦在牧人说出故事后、在探得这个故事所需的暴力被实施后,还能否继续持存;第二,判断集体利益是否确保了个体的牺牲(仆人或主权者)。没有一个单独的概念——比如“城邦”、“个体”,或其关联,“公民权”——能够脱离那场威胁着这个城邦及其居民的瘟疫,不存在这样一个中立而无涉的概念,借此人们可以判断是否(或要求)某种行为应当被实施,由谁实施,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实施,然后描述并制定规则以“按流程实施”。不存在任何稳固的立场,借以做出哪怕是最简单的伦理判断或政治判断——也不存在借以任何评判它们关系的立场。不存在任何一个这样的位置,由此出发可以确定,决定接受城邦法律的行为,发生在法律存在之前还是之后;或试图确认这一行为究竟是不是一项决定: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阐述的关于国家的理论将会探讨这个空缺。*对于伦理言语和政治言语之间的“缝隙”(尤其涉及列维纳斯的著作)的细致论述,可见Simon Critchley’s “Five Problems in Levinas’s View of Politics and the Sketch of a Solution to Them”, Political Theory 32,no.2(2004):172-185。
因此,这就是我想提到的古代场景。这个场景是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公共的或政治的故事与私人故事交汇的场景之一,也绝不是最具有暴力性的一个。或者,不如说它的暴力性不同于提瑞西阿斯盛怒下的质询,也不同于俄狄浦斯与克瑞翁的对峙,也不同于以下两种极端的、却是幕后的具体叙述: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双眼,这个姿势将一个故事永远与另一个故事缝合起来,他瞎了的眼窝标志着两个点,城邦的故事,主权者的故事,以及每个公民对它们的了解,都在那里汇集到一起;盲目的点,十字路口,绝境。城邦的利益、城邦的健康、城邦的持存:这些因素在戏剧开始时就显然处在关键地位(俄狄浦斯对乞援人和歌队说:“你们每人只为自己悲哀,不为旁人;我的悲痛却同时是为城邦,为自己,也为你们。”11.60ff),但在这高潮性的一幕中却不是如此。俄狄浦斯并未以政治理由询问仆人,这里存在着另一种逻辑:
报信人:喂,告诉我,还记得那时候你给了我一个婴儿,叫我当自己的儿子养着吗?
牧人:你是什么意思?干吗问这句话?
报信人:好朋友,这就是他,那时候是个婴儿。
牧人:该死的家伙!还不快住嘴!
俄狄浦斯:啊,老头儿,不要骂他,你说这话倒是更该挨骂!
牧人:好主上啊,我有什么错呢?
俄狄浦斯:因为你不回答他问你的关于那个孩子的事。
牧人:他什么都不晓得,却要多嘴,简直是白搭。
俄狄浦斯:你不痛痛快快回答,要挨了打哭才回答!
牧人:看在天神面上,不要拷打一个老头子。
俄狄浦斯:(向侍从)快来人,立刻把他的手反绑起来!
牧人:可怜呀,为什么呢?*Sophocles, OedipusRex, ed. R. D. Rawe, rev.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70-71。对这几行的阐释历史,见Jean Bollack, L’Oediperoi de Sophocle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1990),v.3,753:“因为‘把手反绑起来’并不是开始一系列审问性酷刑的姿势,apostrepsei几乎总是被译成‘连起来(bind)’……至于‘扭’,译者们依赖的是《奥德赛》中有关墨兰托(Melanthio)的惩罚的描述……因此,威胁是被明确指出、但未被执行的。”(dustēnosantitou)
关于上述诗行存在一些编辑上的细微分歧。牧人的呼告——dustēnos,“可怜的,灾难性的,悲惨的”——普遍被读作自指,虽然有些编者指出这一形容词也可能用于俄狄浦斯:这个词在仆人和主权者之间滑动,对两者都有意义。关于俄狄浦斯的“快来人,立刻把他的手反绑起来!”一句也存在分歧: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威胁(把牧人的手绑起来,准备其他未明言的酷刑),也可以理解为牧人的苦难已经由此开始了(被扳住双手就是牧人所受折磨的一部分)。
由此,这一对话产生了两种舞台布置:一种认为仅仅对于苦难的惧怕就足以使牧人说出故事,而另一种则将角色的受苦展现出来:第一种理解符合这出戏自始至终对于暴力场景的处理,即将其置于想象性的、幕后的领域中(谋杀拉伊俄斯[Laius]、伊俄卡斯忒[Jocasta]的自杀、俄狄浦斯刺瞎双眼);第二种理解则威胁要将暴力场景搬上舞台。塞涅卡的版本青睐于第二种理解。他笔下的俄狄浦斯质问福波斯(Phorbas)——负责照看忒拜城皇家羊群的牧人:
俄狄浦斯:(旁白)为何还到远处寻找?如今命运已近了。(向福波斯)完完整整告诉我,那个婴儿是谁?
福波斯:我的忠诚禁止我这么做。(Prohibetfides.)
俄狄浦斯:你们谁,拿火来!火焰马上会烧尽忠诚。(Hucaliquisignem!Flammaiamexcutietfidem.)
福波斯:真理是靠这种血腥手段寻得的吗?我恳求您原谅我。(Pertamcruentasveraquaerenturvias?)
俄狄浦斯:如果你认为我残酷无情,你马上可以找到报复手段:告诉我真相!(Siferusvideortibi/Etimpotens,paratavindictainmanuest:/Dicvera.)[1]
无论是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命令(“说出故事”或“把他的手反绑起来!”),还是塞涅卡的(“告诉我真相!”),都不是基于城邦利益与公民利益的严格区分。两个版本的《俄狄浦斯王》在这一点上都不可能自洽地在主权者表达的欲望(作为儿子、丈夫、有谋杀嫌疑者、被背叛者;作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作为盲目追随他人安排的命运的人)与城邦利益之间做出区分。尽管种种区分在这出戏将两者进行比较的领域内具有决定意义(确定家族或世代的区分;区别陌生人和亲属,奴隶和公民,主权者和臣民,或现在与过去;确定表面上看是自由的行为是否确实是自由的,抑或其实遵循了某个更古老的逻辑),但在政治判断甚或伦理判断的领域内,这些区分都既是根本的,也是不可能做出的。*不可能做出区分——更好地说是毫无意义。比如,维特根斯坦在其“伦理学讲演”结尾说(Ludwig Wittgenstein, “A Lecture on Ethic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4(1965):3-12):“现在当这种异议出现时,我便立刻清楚地看到,不仅我能想到的一切描述都不能描述我所谓的绝对价值,而且我反对任何人从一开始就根据其重大意义而提出的一切意味深长的描述。这就是说我现在明白了,这些荒谬的表达并非没有意义,而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表达,但它们的荒谬性却正是其本质。因为我对它们要做的一切就是去超越这个世界,即超越意味深长的语言之外。我整个的倾向和我相信所有试图撰写或谈论伦理学或宗教的人的倾向,都碰到了语言的边界,像这样在我们囚笼的墙壁上碰撞是完全地、绝对地没有希望的。伦理学渊源于希望谈论某种关于生活之终极意义、绝对善、绝对价值的欲望,就这点来看它不能成为科学。伦理学谈论的事情,在任何意义上都对我们的知识无所补益。但它是人类思想中一种倾向的纪实,对此,我个人不得不对它深表敬重,而且,说什么我也不会对它妄加奚落。”(译者按:中译根据万俊人译文,见《维特根斯坦的伦理学演讲》,载于《哲学译丛》1987年第4期,略有改动。)对于那些普遍稳固的区分的虚假必然性质(这些区分带有维特根斯坦这里所谓“绝对价值”的性质),我在这里特别想到的是实用主义论辩,如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说,实用主义论辩正确地坚持认为,“从‘某种区分无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这一事实,无法得出‘无论如何它都不成立’”。(Hilary Putnam, Ethics Without Ont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118)事实上,将某些概念区分进行(人们或许可以说)“本体论化”(ontologization)是一项特别弱的哲学技巧,但尽管如此,索福克勒斯和塞涅卡的戏剧关注的确是此类区分。这两出剧被算作悲剧(事实上,从黑格尔到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论述中,它们定义了文学文类和哲学写作的一种亚文类),恰恰出于其稳定的文化、政治甚或神学重要性(gravity),这两出剧为各种必然(出于同样重要的原因)终归失败的区分赋予了上述重要性。
顺着这两部戏所划出的弧线,一种形式的伦理—政治逻辑消退而另一种随之上升(似乎是一种补偿)。到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剧末(作为这出戏的结果),“属于城邦”的涵义、公民的涵义、主权者的涵义、歌队成员或观众的涵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统治者的故事和城邦故事的不同面向的责任已分摊到公民中间,因而公民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定义、重新塑造、中介(mediated)和转化。正如俄狄浦斯和克瑞翁的家庭关系一样。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一系列要求结尾,这些要求涉及不同层次并基于各种不同的规范性框架。其中两个要求特别引人注目。歌队向观众(包括忒拜城民众和这出戏的观众)表明俄狄浦斯已经刺瞎双眼,令人想起主权者的好运(ēntuchais,明确而反讽地指向俄狄浦斯在l.1080处宣称他自己是“幸运女神之子”paidatēstukhē s)曾一度激起热切的模仿乃至嫉妒,然后从俄狄浦斯的陨落中得出了对于忒拜居民的著名训诫:在死之前不要就任何必死者的幸福或不幸做出判断(ll.1524-1530)。值得注意的是忒拜城的“居民(enoikos)”和“公民(politēs)”之间的区别。“居民”在索福克勒斯这里并不常见,事实上所指也更广泛;索福克勒斯剧中唯一另外一处使用这个词的地方出现在《菲洛克忒忒斯》中,指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动物:尼米亚猛狮(hoi poteNemeasenoikon);柏拉图在《克力同》(113c)中用这个词描述亚特兰蒂斯的原住民伊夫纳(Evenor)。歌队加于观众身上的要求,将观众(包括忒拜人)转变成仅仅是空间的占据者。他们是居住者而非公民;他们的生命是动物或原住民的赤裸生命;城邦如今被理解为一个由野兽栖息的空间。更确切地说:一个动物园。当俄狄浦斯请求克瑞翁保护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请求克瑞翁让他向她们祝福,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基础只有亲属关系;他的要求并不是基于任何社会的、伦理的或政治的标准。在索福克勒斯那里,牧人故事令人痛苦地揭示了真相,预示着城邦政治生活的终结——政治生活如今不可避免地分裂为仅仅旨在居住的利益和家庭的贵族式要求。忒拜城随着俄狄浦斯的放逐而恢复了健康,驱散了斯芬克斯和瘟疫的恐惧,但也失去了恰恰使得这座城邦成为政治空间的东西:主权者的创伤、他对命运的敏感、纯粹的偶然性、遍及整个城邦的主权者自身的弱点。正如伊俄卡斯忒称自己与俄狄浦斯的关系是“不名誉的双重纽带”:将受伤的主权者以牺牲的方式逐出城邦,拯救了城邦,同时也判了城邦的罪,并隐约开启了想象替代性方案的可能,即主权的缺陷性、分裂和偶然性并不被驱逐,而是被城邦所接纳并分摊到全体民众:被人们记住、重复、反复推敲。
塞涅卡对于城邦中(为了城邦)说出真相的“真相”(“truth” of truth telling)所做的简要观察,首先就令人瞩目地将索福克勒斯含糊其辞的事情摆上了舞台。塞涅卡的真相看起来位于一段残酷经历的终点。它与忠诚冲突。而实情(true story)在表面上所采取的残酷、实情为了拯救城邦而采纳的折磨手段,使得真相变成了一种报复工具:说出真相实际上就是以牙还牙,用苦难抵消苦难。[2]塞涅卡有关在折磨之下说出真相的“真相”所做的上述观察(也是关于真相的运用和结构所做的观察),并不彼此从属,也不从属于某个“说出真相”的规范性观念,不管它是道德的还是认识论的;它们甚至不是彼此相关的观察。这幕场景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上述无序的观察与塞涅卡在俄狄浦斯旁白中勾勒的领域之间的对比:“为何还到远处寻找?如今命运已近了。(Quid quaeris ultra? Fata iamacceduntprope.)”故事的真相在于它命中注定要去的地方;当实情呈现出来的时候,无论如何它都会被人们辨认出(如果不是已经被知晓了的话)。因而这就是为什么福波斯讲述的故事会立即被理解,并被认为是真的:牧人的故事重复了俄狄浦斯以某种方式已经知道了的故事,他已经在向自己讲述这个故事,他已经对此感到害怕。简言之,在塞涅卡的城邦中,以及对这个城邦而言,说出真相的真相与其重复和辨认密切相关。(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塞涅卡的城邦中,真相总是一个神话,一个被不断回忆和重复的公认的故事。)
其次,在塞涅卡的《俄狄浦斯王》中,“说出真相”的真相同样与角色的内在性(在非常初期的意义上的“内在性”)相关。俄狄浦斯预先便体验了自己的故事和城邦的故事,而塞涅卡对这个故事的重复,展现出一种性格特征(统治者在折磨自己;他是城邦的污染物;折磨福波斯是将心理状态外显化的方式)、一种内在性的表征(舞台上演出的故事由此可以以对应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观众对于如下的戏剧性反讽了然于胸——即酷刑的威胁或体验在其中既再现了统治者所感受到的(以及不断加诸自身的)痛苦,也为他将体验到的酷刑埋下伏笔——那他们就会以同样方式理解,自身为何会意识到此前戏剧中出现的种种重复,但效果(affect)则截然相反:即理解到存在这样一种记忆,戏剧可能与之对应也可能不与之对应,但戏剧暗示着这种记忆并从中获取其身份认同(identity)——一种来自主权者创伤景象的集体认同。
第三,与之相关的是俄狄浦斯与歌队之间的关系。索福克勒斯的歌队代表城邦,直接向国王唱出城邦的利益,并作为公民集体而直接与国王对话,但塞涅卡的歌队则不是这样。塞涅卡的歌队作为道德性普遍原则的来源,代表着一种不安的、迟来的、或许可以说是遗留的习俗,在戏剧历史上它不久就将被抛弃。随着戏剧空间逐步被理解为心理空间的象征,歌队的作用就被性格设置和传统所吸收。
最后,同样在性格这一点上,塞涅卡的俄狄浦斯表现出极度的牺牲式的(sacrificial)自哀、极大地突出了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的一个特征。塞涅卡的俄狄浦斯向观众如是说:
所有你们这些心智孱弱、重病缠身、几与行尸走肉无异的人们,看哪,我被驱逐而离开这里:抬起你们的头来,我走之后你们会迎来明澈的天空。起死回生的气息将吹拂到那些垂死于病榻上的人们身上。去吧,去帮助那些被遗弃的人:我会将这片大地上致死的疾病都带在自己身上。野蛮的命运、狂暴的疾病、破坏性的瘟疫和遍地的苦难,都跟我走吧,跟我走吧:我欢迎你们做我的向导。[1](PP.110-111)
我们在此看不到任何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结尾处具有的模棱两可:驱逐是回报和治愈;受伤的主权者的离开给城邦带来健康和繁荣,使之延续。
简言之,塞涅卡的《俄狄浦斯王》将索福克勒斯设置的僵局从政治本体论领域转化到审美领域,并在审美的层面上处理它们。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城邦的持存前提是政治的丧失——被转化为塞涅卡的喜剧。这种策略仅仅是部分地成功了,但在类似列文所论述的城市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末世论所仰仗的正是上述策略。
对我们而言,问题不在于“回到索福克勒斯”(不管这意味着什么),而是在关于城市利益(以及这些利益所需要的伦理秩序)的种种当代表征背后,寻找另一种古老的立场——一种非末世论、非英雄主义、非牺牲的,确切地说是政治性的立场——由此出发,确定在面对城市时伦理判断所处的位置。是否可能得出某些标准,用以判断某种行为或情境是否与城市的准则相符,并且这一判断无需诉诸某种规范性理念,或用审美来代替政治性问题,或诉诸某个概念、某种幻想(例如,有关此类城市或共同体或许会是什么样子、或许需要什么条件的理念、概念或幻想)?从内摄的(introjected)缺陷性主权这一极具寓言性的意象中能得出什么?
[1]Seneca.Oedipus[M]. John G. Fitc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Page DuBois.TortureandTruth[M]. New York: Routledge,1991.
TerribleEthics
Jacques Lezra, tr. WANG Qin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10003, USA)
As the basis of an ethics, ‘terror’ presupposes the indeterminacy of the bord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its universals. By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a same story narrated by Sophocles and Seneca, we can find that Seneca’sOedipus, in short, translates the impasses that Sophocles devises from the domain of political ontology to that of aesthetics and addresses them at that level. Sophoclean tragedy, the loss of the political that is entailed in the city’s survival, is converted to Senecan comedy. Thus, the thesis of ‘terrible ethics’ leads us to the problem of ‘defective concepts’ and, ultimately, sovereignty.
terror; ethics; sovereignty; oedipus
2012-12-01
雅克·莱兹拉(Jacques Lezra),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主要从事政治哲学、莎士比亚、批判理论等研究;王钦(1986-),男,上海市人,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政治哲学、批判理论等研究。
B82-02
A
1674-2338(2013)01-0035-08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