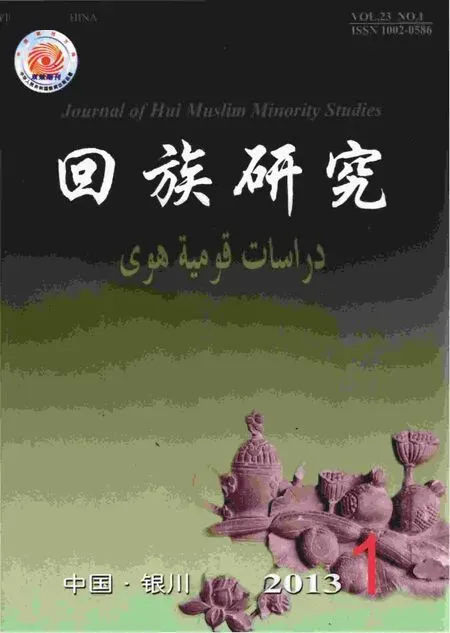从“小锦”说到边疆教育上的文字问题
白寿彝
“小锦”是在受过宗教教育的中国回教徒中间通行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底历史,至少要有四五百年。但这个名子底原来,毫无可考。这个名子底意思也很不清楚。有人说,“小锦”应该写作“效经”,意思说它是仿效经典文字的一种东西。有人说,“小锦”应该写作“小儿经”,意思说它是给小儿阅读的一种东西。又有人说,“小锦”应该写作“小讲”,因为这种文字最初是为作经典讲注用的。这三种说法大概都是由于揣测,并不足信;好在我们现在也不是考究这种文字底历史,对于这一点可以置而不论。
“小锦”最重要的特色,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中国话。在中国回教寺院教育所常用的十四种基本教典中,差不多每一种教典都附有这种文字。有的是在经典原文底左右空白上(即书页底边缘上)写着,有的是在一个单字底附近写着,有的是在一段原文完结后写着。头两种写法,以解释字句者为多;第三种写法则是解释全段原文底意思的。用第三种写法的,一段文字写得很长,除了大体上写的是中国话外,还夹杂着许多阿拉伯话和波斯话。凡学习这类经典而不识中国方块字的回教徒,平常都是用这种文写信,记账和记事。依不明白这种情形的人之素日的看法,往往以为回教徒没有甚么著作,识字的人太少,其实回教徒何尝没有著作,识字的人又何尝少,不过用中国方块字著作和认识中国方块字的人太少罢了。
近来友人庞士谦阿衡常常和我谈到这种文字,使我觉得这种文字不只在中国拼音字史上应该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目前回民教育底广大推行上,更是一种很要紧很应该充分利用的一种教育工具。我的最重要的理由和办法,约有两项。
第一,依照我们所见到的不甚完备的统计材料作最低额的推测,全国底回教礼拜寺至少要在一万座以上。如果每三个年头,每一座礼拜寺只教育了二十个学生,则在最近三十年中所训练出来的,能应用这种文字的人,至少也要有二百多万。在这二百多万人中,有的年事已长,有的奔走衣食,依一般的情形说来,另外有机会学习中国方块字者恐怕很少。现在我们如果用这种文字办一种报或杂志,按着一定的时期,免费分送各地礼拜寺代发,则这二百多万的庞大群众都可以得到救济知识荒的机会,可以使他们慢慢地提高他们的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国家情绪。二百多万人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三十年的训练不是经过很短的一个时期。我们眼看着这样已有的广厚的成绩而不知利用,作进一步的展开,我们更要利用甚么呢?
第二,在我们的边疆上,西北如陕西甘肃,西南如云南,都是回教徒聚居最多的地方(新疆土著的回教徒另有他们的语言文字,故不列在里面)。而这些地方,因爱新觉罗氏政策底播弄,正是回教徒与非回教徒关系最欠圆满的地方。这些地方底回教徒视中国方块字为“汉字”(这和一般人心目中所谓汉字,意义是不大一样的),视读汉字书为汉化底开端,为离经判教的行为。历来西北及西南学校教育所以得不到当地回教徒底拥护,实以学校拿方块字为讲授的唯一工具,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我们如果不斤斤于文字统一的假体面,而采取避名就实的过渡办法,除设立以方块字授课的普通学校外,还应该广设短期的回民小学,初级班底课程完全以“小锦”讲授,必要时还可以加上一点正式的阿拉伯文,高级班可以慢慢地加上用“小锦”注音的方块字。“小锦”虽也应该说是一种中国文字,但因为用的是阿拉伯字母,在一般的回教同胞看来,总是一种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的文字。这种文字上的改变,大可为边疆上回教同胞之视听所系;用这种文字办的边疆教育,不只可以减少许多阻力,还可以取得许多爱护。我们觉得,文字是假的,文字所表示的意义是真的。边疆上的同胞暂时不懂得所谓“国文”,用不着发愁;我们没有法子让他们和国家精诚团结,才真正可愁呢。
在这两项中,第一项的办法较为容易,只要有一笔固定的款子和少数的人才,经过一个短的研究时期就可以举办。第二项,因为需要整个的规划,师资底训练,和教材底编制,则需要较长的时期来筹备。自然,这两项都非私人之力所及,是需要政府来提倡的。
关于第二项,我觉得不只对陕甘云南等处的回教同胞如此,对于新疆,蒙古,西藏等处同胞和苗,爨,摆夷等族同胞也需要有类似的办法;如果想对于他们办一种教育,也须用他们通用的正式文字。他各有各自的历史,各有各自的语言。中国方块字不惟和他们的历史没有深厚的关系,而且和他们的语言毫不相干。用方块字在他们中间来推行教育,简直是空中楼阁,比让陕甘等地的回教同胞读“汉字书”更艰难,更无效。而且中国方块字是一种独立的单音字,和蒙文、藏文、维吾尔文、摆夷文之用字母组成者,在学习的难易上大有差别。方块字在这一点上,也是一个推行的大障碍。为真正的教育计,我们是无舍易就难之理由的。
我常感到,在内地的一般人往往以所谓“汉人文化”等于全盘的中国文化。“汉人文化”也许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一部分,但中国文化底内涵决不仅限于“汉人文化”。我希望,我们以事实来纠正这种观念,希望公私教育当局能在各种特殊教育中给予国内各种特殊文字以适宜的地位。更希望由各种特殊文字应用上之发达,而作国内各种特殊文化之发扬,由个别的发扬走到相互的吸收和集合,以造成真正的统一的中国新文化。
——原载《申报》“星期论坛”,民国26年(1937年)五月二十三日。另见《语文》,民国26年(1937年)第1 卷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