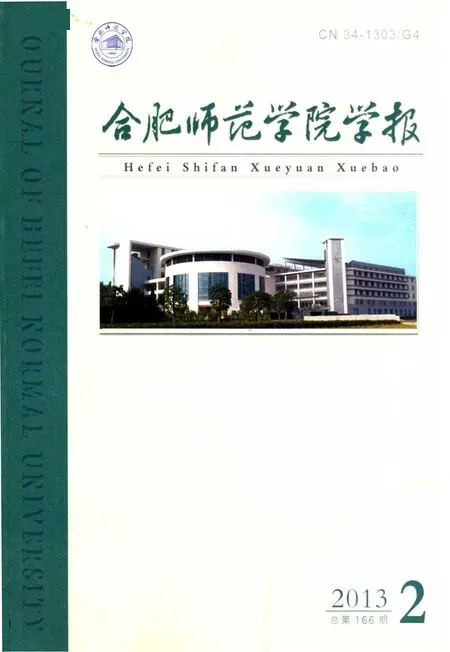试析政治对南宋词嬗变之影响
卫宏伟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241003)
南宋词与北宋词之不同,在宋以后历代词话中,已有论及。如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1]10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2]62词从北宋发展到南宋而有所变化,大致来说,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是燕乐发展演变,以及到南宋乐谱失传,或词乐被用于南戏而新词乐得不到有效补充造成词与乐之渐趋分离;其次,受时代条件之影响,“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再次,词体自身发展以及诗、文发展对词之影响。就影响北宋到南宋词之嬗变来看,政治为首要因素。
一、题材风格与功能之变
北宋初期词,承袭唐五代,题材上多拘于花前月下、闺阁宴帏、离亭别席,风格多侧艳清丽、缠绵婉转,在功能上主要用于娱宾遣兴、歌咏太平、叙别感时。虽经苏轼于被贬黄州之后在题材、功能上皆大为开拓,而毕竟未成风气,又北宋时人论中,颇有微议。欧阳修在《西湖念语》中所言“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3]153-154,正可见北宋词之主要功用,而《采桑子》组词亦可窥其题材。与北宋词相比,南宋词在题材与功能上均有了极大的开拓与变化,这首先与南宋建立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
历史上的南宋时期指从公元1126年“靖康之役”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南宋词指在此期间及南宋灭亡不久词人之词作。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金兵分两路南下,一路攻取太原,一路攻取燕京,然后合攻北宋都城东京。太原守军逃亡,燕京守将降金,金兵长驱直下进取东京。宋徽宗惊慌失措,先下罪己诏召各地驻军“勤王”,之后又退位。太子赵恒即位,定次年年号为靖康,是为宋钦宗。钦宗软弱,早有投降之意,又因用人不当,贻误战机,东京终于在靖康闰十一月为金兵攻破,钦宗出城赴金营投降。次年四月,金兵抢掠之后,挟徽、钦二帝及诸皇室北上。同年五月,赵构于应天称帝南渡,是为宋高宗。迫于金兵追击,赵构于江浙一带到处奔跑,直至绍兴八年(1138年)方定都临安。
词人随宋皇室纷纷南渡,故南宋词人之创作始于这种颠沛流离的时代背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词之题材风格与功能之变化为时势所趋。
首先,南宋初期词,在题材风格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身经乱离后的浅吟低唱,第二类是面临危难时的高声疾呼。前一类词人由于身份、处境、性格、词体观念诸因素的影响,表现乱离较为内隐;而后一类词人则发展了苏轼所开辟的题材风格,以他们的创作最终确立了此类词体风格在词史上的地位。这两类词都具有政治意识的强化,区别只在隐与显。如前者举李清照《添字采桑子》词为例:“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馀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此词为感时伤世之作,写流亡时心态。“芭蕉”在词中有愁苦之意,李煜词“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陈廷焯评为“情词凄婉”[4]32。上阕芭蕉阴满中庭之景,为下阕之言情奠定了凄婉之基调。词人于战乱中流落建康,而建康又临金兵之侵,故伤乱怀危之绪时时缠结心头。三更时分,午夜梦回,想起故国家园物事皆非,惟闻雨打芭蕉之声,点点滴滴,伴着词人的愁情。李清照为尊体词人,讲究词别于诗,即便如此,由政治形势造成的伤时危乱之情在其词中也得已反映,只是与后一类相比,较为内隐而已。故此类风格为化悲痛为凄婉。后一类词人包括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等。这些词人的词作,大量涉及政治题材,而且风格激昂悲壮,表现政治较为明显。如李纲《念奴娇》词:“追想当日巡行,勒兵十万骑,横临边朔。亲总貔貅谈笑看,黠虏心惊胆落。寄语单于,两君相见,何苦逃沙漠。英风如在,卓然千古高著。”此词借咏汉武帝北巡事喻抗金复国志。貔貅为猛兽,借指勇猛之军。冀南宋皇帝率勇猛之军北上抗金,敌军虽狡黠但必心惊胆慄,逃于沙漠。虽经千古,仍须继承发扬汉武这种英雄之风。这就较为明确地表明了词人冀时代多出英雄,以酬抗金复国之志的心情。
词之功用,于南宋的发展主要有二:一是反复申说抗战复国之志,以引起时人关注;二是重在抒写个人行藏。申诉抗战复国,于南宋初期开始,到中后期皆有此一类。如李光《水调歌头》写“兵气暗吴楚,江汉久凄凉。当年俊杰安在,酌酒酹严光。南顾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荡,矫首讯穹苍”,陈述“兵气暗吴楚,江汉久凄凉”之危难形势,呼吁俊杰安在,救国之急迫,岳飞词“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决心,陆游“胡未灭,鬃先秋”的感叹,皆属此种。甚至到后期,陈亮词如《贺新郎》中所写“父老长安今馀几,后死无仇可雪”、“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亦属此种。北宋词主要用以写闲情艳事、离情别绪、酬赠感怀,虽苏门词人于被贬之后,以词抒写怀抱,寄寓感慨,但还未大肆在词中抒写个人行藏。自“靖康之役”后,南渡词人以他们的创作实际,一面呼吁救国,一面于词中抒写个人行止出处。如周敦儒《彩桑子·彭浪面》记述词人乘舟流落江西,“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之后词人又经江西流落岭南,又在《雨中花·岭南作》中写道:“胡尘卷地,南走炎荒,曳裾强学应刘”。辛弃疾则有意识地于词中叙写个人行止,其《鹧鸪天·不寐》写:“随巧拙,任浮沉。人无同处面如心。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
二、言情方式之变及其影响于词风
宋词的言情方式经历了从陈情到寄情,到直抒其情与比兴寄托的发展变化,而此发展过程有赖于政治之影响。所谓陈情,即即景言情,因北宋初期词多写闲情、艳情、离情,经乐工歌妓之口唱于离席欢宴之前。故词中所言之情多为即事即景而发,情景和谐交融。寄情是将个人之难言之情寄寓词中,这在北宋已出现,主要受政治影响。如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作于其元丰五年被贬黄州之时。《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引鲖阳居士语曰:“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此与《考槃》诗相似。”[5]95张惠言、谭献也持此说。[5]96鲖阳居士所言,一一指实,不免牵强,然而苏轼此词具有政治上失意之寓,尚属中肯之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皆作于被贬黄州之时,而秦观于绍圣三年贬徙郴州所作《踏莎行》(雾失楼台)亦有政治上迷茫失落之寄寓,于此或亦可见政治对词风变革之影响。词中之比兴寄托,承继了《离骚》之艺术手法,有四种比体,一为以古比今之咏史,二为以仙比俗之游仙,三为以男女比君臣之艳情,四为以物比人之咏物。贺铸词中已见此,如陈廷焯言及贺铸《芳心苦》词说:“骚情雅意,哀怨无端,读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泪堕。”[3]17
比兴寄托于词中之大量运用,蔚然成观,则在南宋。南宋政治对词之抒情方式影响的主要因素有二:一为金兵侵凌之外患,二为朝廷内部主和与主战两派之矛盾。前者影响于词之抒情方式为直抒其情,多表现为辞愤义激、志气慷慨。而从后者来看,南宋政局,长期以来主和派把持朝政,主战派人士或被贬迁,调离要职,或长期闲居,无以重用。他们一面对朝廷屈和于金有怨,一面对主和派对他们的排挤打击有恨。而这“怨”“恨”之情不便直言,故借助于比兴寄托。
对于直抒其情,可结合前面政治对于南宋词题材风格及功能之影响来看,在此为避赘述,仅举张孝祥《六州歌头》一例。“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羽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此词上阕写中原国土遭异族侵占,曾经的“弦歌地”变为牛羊奔跑的牧场。下阕直抒其情,中原遗民渴望南师北伐,夺回故地,而久望不见南师,使人义愤填膺。正是陆游诗“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之意。朝廷主战与主和派的矛盾对于南宋词比兴寄托之影响,现举张元干词《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试析之。“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主张向金投降,金使来宋令高宗跪受诏书。意即秦桧所谓“和议”实为使宋为金之属国。胡铨上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头,高宗、秦桧大怒,斥胡铨“妄言上书,语言凶悖,仍多散付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罢胡铨官,贬为昭州编管,改监广州盐仓,又改签书威武军判官。五年后将胡铨除名于新州。张元干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七月写此词为胡铨送行。而时人为胡铨送行多获罪,如王庭珪因作诗为胡送行被判充军罪。在如此背景作词言情,自然借以比兴寄托。“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寓指中原沦陷。而造成中原沦陷的原因,接着三句作了说明。“天意从来高难问”,托指宋高宗及主和派奉行投降政策难以理解。“况人情、老易悲难诉”之“人情”指恢复之志,托指南渡诸公之恢复之志已随时光流驶而消沉。“更南浦,送君去”之“君”指胡邦衡,亦指如胡邦衡一样坚持正义怀恢复大志的仁人志士,此句借送别比贬谪,朝中正义之士皆被远谪。
由政治而造成言情方式幽微隐约的比兴寄托,必然对词风有一定影响。兹着重述辛派词人中摧刚为柔之风格,至于尊体派词人接受政治影响而词风之变化拟置于后文述及。南宋朝廷中主和派所奉行的投降妥协政策,影响到词人的言情方式,从而词风也随之发生变化。对于辛派词人,其主要影响便是摧刚为柔,化慷慨为悲凉。这在辛弃疾词中最具代表性,不过,需说明的是这只是其中一类词风,并非辛派词人全部词作风格皆如此。如其《摸鱼儿》“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此词写作背景为:“淳熙己亥(1179年),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此词于上阕开始便将无限感慨、幽愤融于传统的惜春之中,春去匆匆,落红无数,这些花还能禁得起几场风雨?是典型的摧刚为柔之风。陈廷焯评曰:“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3]24-25后阕以男女之情比君臣关系,是前面所言离骚之以男女比君臣之比兴寄托。借用汉武帝之陈皇后被幽禁于长门宫,陈皇后以千金请司马相如为其作《长门赋》,然武帝终不为所动。以陈皇后之情言己报国之志,而朝廷于之态度如武帝之于陈皇后,是为“怨”。后面又以飞燕、玉环喻佞臣,言佞臣虽谄媚惑君而终归尘土,是为“恨”。这样,朝廷中之政局皆以男女之情托寄。上如武帝,不闻忠臣之心;忠臣如陈后,含冤而不辨;佞臣如玉环、飞燕,媚惑君心而君不察。此言之意如《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词人所表“怨”“恨”之情本应为辞愤意激,但借比兴寄托出,从而摧刚为柔,最后又言愁倚危栏看斜阳,化慷慨为悲凉。再如《小重山》“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将无限感慨以婉转之言出之,亦是摧刚为柔。
三、情景关系之变及尊体派词人受政治影响
北宋词承袭唐五代词创作之风,多即景言情,而南宋词多为有所言而作,故巧见安排,因情叙景。周济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6]8究其原因,一面与南宋词渐与音乐脱离及词自身发展有关,但政治因素影响亦是此种情景关系变化之由。辛弃疾《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词:“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盘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此词作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主和派史致道任建康知府,辛弃疾为通判。此时词人已南归七载,沉沦下僚,不得重用,朝廷之妥协政策有增无减。词人与主和派史致道政见自然不合,虽登赏心亭观望,却不见诸葛亮所谓“虎踞龙盘”之景。在作词之前,就受一种愁郁之情感所驱使,这正是南宋词在情景关系上区别于北宋词见景生情的根源。故词人首先写道“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万斛”,此实则先有“闲愁万斛”后“来吊古”。在这种感情基调下,自然所见之景不是“虎踞龙盘”,而是“兴亡满目”了。后面所写之景都是因情安排,柳外之斜阳,水边之归鸟,陇上之乔木,西去之孤帆,笛声传过之霜竹。所取景物为情所限,感情基调不同者,所取景物自然不同。试与北宋宋祁《玉楼春》相比,《玉楼春》下阕所写“浮生长恨欢娱少”之情是由上阕词人于东城风光好中划棹而游见绿杨烟外、红杏枝头之景而生。周济所言至稼轩、白石而变,实为稼轩、白石较典型而已。
前面言及辛派词人由政治影响词之抒情方式从而影响到词风,尊体派词人也接受了政治影响而词风有所变化。所谓尊体派词人,指认为词别于诗,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风格诸方面不同于诗,在南宋以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为代表。同样,他们受政治影响,抒情方式亦采用比兴寄托,然与其对词体的推尊作用于创作,则显幽微隐约、烟水迷离之致,有时指意不免晦涩。《人间词话》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处其间耶?”[7]210王国维从境界之角度,认为南宋词“隔”。尊体派词人虽受政治影响而用比兴寄托,但不像辛派词人表情达意较为明显,决不流于叫嚣。从意境来看,有雾里看花之感。从风格来看,则具烟水迷离之致。现举张炎词《绮罗香·红叶》为例:“万里飞霜,千林落木,寒艳不招春妒。枫冷吴江,独客又吟愁句。正船舣、流水孤村,似花绕、斜阳归路。甚荒沟、一片凄凉,载情不去载愁去。”以“万里飞霜”喻新朝,以“千林落木”喻故国,以红叶喻遗民,与前所举辛弃疾词以男女之情喻政治相比,可谓不着痕迹,词旨隐晦,哀感无端。如陈廷焯所言:“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3]190
如果说南宋前期及中期词是“乱世之音哀以怨”,则末期及南宋灭亡后一段时间可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而尊体派词人于南宋末期词作风格则是受政治影响后所形成的。
四、词体观念之发展与词之诗化
北宋时,词人于词之认识,普遍认为词有别于诗。陈师道较早陈述了这种观念,他在评论苏轼词时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8]309“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8]311又说:“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后李清照《词论》中词体观念与之极为相似,论苏轼等人词为“句读不葺之诗尔”[9]267,论及词别是一家时说“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9]267。北宋人对于词体普遍认为,词于题材多涉风月艳情、离情别绪、闲愁遣兴,协律、可歌,境界幽深,语言婉丽。虽苏轼于贬谪之后,词风渐变,胡寅所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10]58,然此类词在苏词中亦属少数。直到“靖康之役”,大量词人随高宗南渡后,大量词人在词中叙写亡国之恨、复国之志,辞愤义激、气势慷慨,词坛上之主体词风尚为一转。随着这些词人的创作,这类词作已蔚成大观,最终为人所认肯。此时,苏轼所倡的“自是一家”才普遍为人所接受,由尊体到兼体。之后,南宋词坛上前者主流为辛派词人,而后者主流渐发展为所谓“骚雅派”词人。
词之诗化与词体观念之发展,可谓同步。词诗化之实践,于北宋影响较大者主要为苏轼,虽然李清照于《词论》中将晏殊、欧阳修之词也评为“句读不葺之诗”,然而此二人之词与苏词差别明显,更见唐五代词之印迹。北宋文人于贬谪之后,患于党争,谨于诗中言志,渐于词中寄难言之志。不过,终归词之诗化蔚成风气且为人所普遍接受亦是南渡之后,诗化之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发展了词的言志功能,而且在传统于表现艳情的词中言志,如刘熙载在评前引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及张孝祥《六州歌头》时说:“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11]3709;其二,出于言志之需,将诗中所用比兴寄托手法大量用于词中;其三,词之语言趋于雅化,用典增多。尤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为典型,不仅在词中大量用典,还用“离骚体”,用经用史,以散文句式作词。如辛弃疾《水龙吟》(听兮清佩琼瑶些)仿楚辞《招魂》通词将韵脚前移,以“些”字为形式上的韵脚,刘过《沁园春·寄稼轩承旨》全词用散文句式,又用铺叙,使上下阕紧密衔接。
南宋词,一方面,在北宋词中已孕变因之上继续发展,使这一变化成为一个时代词之风格;另一方面,萌生北宋词未有之特征。而南宋政治是影响这些发展变化不可忽视之因素。
[1](清)朱彝尊,汪森.词综·发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唐圭璋.全宋词[M].孔凡礼,补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南唐)李煜.李煜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G].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6](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清)王国维.人间词话[M].徐调孚,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8](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第三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11]唐圭璋.词话丛编·词概[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