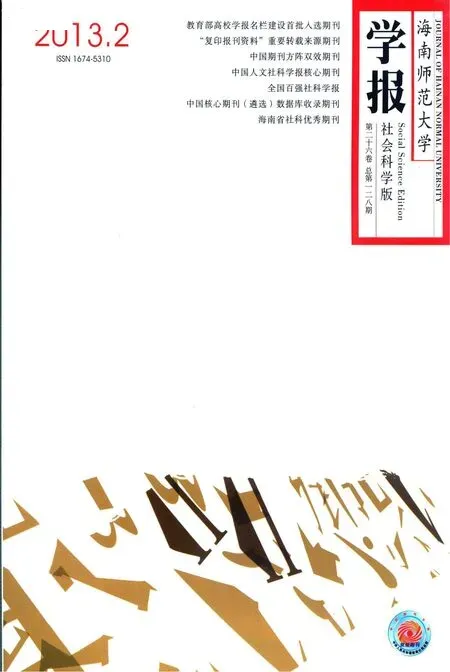民间鬼神信仰与贾平凹的“魅性”审美
刘 宁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5)
鬼神信仰是一个民族的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人们死后世界的理解。它表明人的灵魂不灭,体现着人们对生命的尊重,而这正是文学的本质所在。“只要稍将人文学的文字涉猎一下,便可相信许多仪式与信仰底核心都是人生底生理时期,特别是转变时期,如受孕、怀妊、生产、春机发动、结婚、死亡等时期。”[1]21死亡是生命的最后一个环节,具有巨大的转机,因此,设法寻求不死或者永生,永远都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最为热烈的追求之一。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羽化成仙固然充满诱惑,但却是人人不可企及的结果,因此只好寄希望于死后的想象世界。商州地处秦头楚尾,敬鬼神、好淫祀,因而,沉浸在秦汉大地民俗风情之中的贾平凹始终对鬼神葆有一种敬畏、神秘感,不论其文本的丧葬礼俗的描写,还是驱鬼、敬神、祭祀场面的勾勒,都流露出其对民间鬼神文化的亲和感,这自然孕育了作家魔幻思维和诡异文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魅性”审美意趣。而这种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文学的书写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左传》曰:“人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2]魂魄指的是人生时之心知。至于魂魄与鬼魂有何差别?人死为鬼的观念究竟起源何时?已不可考,但是人死之后与魂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却是不可否认的。魂魄字皆从鬼,王充《论衡·论死》道:“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①转引自钱穆:《灵魂与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正因为此,民间才有繁琐的埋葬形魄的丧葬之礼和虔诚的登高招魂之俗。商州地处秦楚交界地,弥漫着浓郁的鬼神信仰,形成了一整套丧葬礼俗和一系列祭祀、巫术仪式,可在贾平凹文本中窥见上述内容。
(一)报庙、入殓停柩
“报庙”指的是将刚刚过世的人去世的消息报告给阎王爷的一种行为。《龙卷风》、《远山野情》等作品里都有儿子把即将死去的父母的日常用物送至城隍庙去的情节,这实为一种“交感巫术”。民间普遍认为,人的日常生活用物上附着了人的灵魂,将老人的生活用品,如一根拐杖、一件衣衫抱到土地庙,这等于是将其灵魂交付到阴间。因为土地庙、城隍庙或者五道庙通常是通往冥界的入口,所以人死之后,灵魂必然是先到上述地方报到。接着是对死者遗体进行清洗装扮,在入殓之际,于棺中放置柏朵、灰包。《龙卷风》、《西北口》中都详细地记述了这些民俗。放灰包大概是为了防止尸体腐化时血水外流,置柏朵则可能是缘于另一种精怪信仰。《风俗通义》云:“方相氏葬日入圹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长令方象立于侧,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3]428
(二)写铭旌、踏穴、浮丘
尽管商州地处边缘,但是秦汉时“商山四皓”隐居于此,所以民间语言和风俗受四皓影响,也颇具典雅之风。最能体现商州文化气息的是“谁家有人过世了,已经没有了在石碑上刻墓志铭的豪华,但红绸子上却要以金粉书写铭文,”[4]“铭旌”相当于今之悼词,是歌功颂德的四六骈文,用泥金胶写于红绸之上。虽然商周之际,铭文是镌刻在青铜器上的,但是在后世,铭文则多书写在帛绢或雕刻在墓碑上,并为历代士人所重视。贾氏的许多文本都描述了商州撰写“铭旌”之俗,从“商州系列”作品始至散文《我是农民》、小说《秦腔》中都在夸耀这一故乡丧俗之古雅。“铭旌”写好之后,一切安排妥当,下葬之前,则先要选好墓址。选墓址讲究深藏,所谓“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使人不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足以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树之哉”。①转引自钱穆:《灵魂与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在此意义上,“踏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美穴地》是一篇以“踏穴”为叙述背景而演绎的情爱故事,生动地再现了民间勘地舆时讲究阴阳五行相携的信仰。它反映了地理方位与人世之间的超自然联系,为了使祖先灵魂得到永久的安息,或者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了墓地风水会对死者的家人和后代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人们必须重视死者葬地风水地形。《葬经》云:“有垄中峙法:葬其止,王侯崛起;形如燕巢法:葬其凹,胙土分茅……形如植冠,永昌且欢;形如投筭百事昏乱;形如乱衣,妒女淫妻……。”[5]“踏穴”、建墓之后,是择日举行安葬。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生的各种事物都与时辰有关,所以死之日与葬之日必须相配相济,而当一时寻找不到合适的日子安葬时则宁愿等一段时间,暂时将棺木安放在某处,待忌日之后方能入土,这在商州称作“浮丘”。“浮丘”不算正式埋葬,《浮躁》、《晚雨》等诸多文本中都有关于此民俗的描摹,可见,对阴阳五行相携的信仰,在商州还是非常浓郁的。
(三)公鸡引魂、唱孝歌
人死之后魂魄相分,游魂不定,所以在将灵柩送往墓地之际,需要有引亡魂之物。《商州》里的珍子和刘成死后运回家乡时棺材上绑缚一只白公鸡,《高兴》中五福死后刘高兴也是为其买了只白公鸡引魂。这一习俗大概缘于汉时,《风俗通义》云:“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辩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3]432可见,公鸡是祭祀之物,民间以其引亡魂。唱孝歌是下湖人的风俗,人死之后,人们围着棺材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唱孝歌。《白夜》、《怀念狼》以及散文《说死》等作品里都提及了这种丧俗:“为人在世有什么好?说声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亲戚朋友知道了,亡人已到奈何桥。阴间不跟阳间桥一样,七寸的宽来万丈高,大风吹得摇摇摆,小风吹得摆摆摇。”[6]在这一习俗中隐约可见庄子“鼓盆而歌”的影子,此俗大概源自楚国。据史载,清时朝廷曾大规模地将下湖人迁移至商州,随着下湖人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湖北的花鼓戏,而且也将许多楚国丧俗引入。清同治五年湖北《长阳县志》的记载可以验证:“丧次擂大鼓唱曲,或一唱众和,或问答古今皆稗官演义语,谓之打丧鼓、唱丧歌。”[7]唱孝歌丧俗融入了楚人擅长的生死与天地想象,超越了生死大限而直抵宇宙起源的混沌之根。
(四)祭祀、敬神、驱鬼
“葬礼的最后,代表死者的灵牌与其他祖先的牌位放在一起,至此,死者已完全被认为安息在灵魂世界里,在世的亲戚和子孙要不时去祭奠他,这种供奉又叫祭礼。”[8]从头七到七七,每七日举行一次祭祀,从一周年到三周年死者忌日也要举行盛大的悼念活动,尤其是以三周年最为隆重,《高老庄》即描述了这种家族祭祀的状况。而一旦亡魂被安置在灵魂世界里,则上升为家族的保护神。所谓“神”,说文里解释为从“示”从“申”,“示”标示祭祀,“申”为闪电,都隐含着神秘莫测的意味。在中国民间信仰里,成神有凭借羽化而登仙的,而绝大多数则是依靠死后方才成神。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或是生前具有神异功能,或是曾经造福乡里,另一方面是缘于死者死后带给人们福祉。《商州再录》里《金洞》篇中的小儿和《死了才走运的老头》一文里的老头或因死后造福民众,或因生前有功于当地,死后都被视为神人,香火不断。
一言以蔽之,上述不论是在家族私祭中的保护神,还是在公众场合下公祭里的地方神,都是善鬼成神的,代表着民间生者对亡魂崇拜的信仰。然而,如果某人死于非命,冤魂就会结聚不散,为恶乡里。为此,需要民众举行公祭予以安抚,《白夜》里反复描写的《请巫禳灾》、《灵界》、《目连救母》戏等都属于此类祭祀鬼戏。但是并不是所有亡魂都能获得超生,还有很多罪孽深重的鬼魂或在人世继续作恶,或侵入活人之体,使其丧失本性抑或生病,面对这种情形,就必须实行巫术进行驱除。如果说巫术的基本原理是人通过实施法术,来主动控制或要挟神明鬼怪,那么“鬼神可杀”或驱除则可以被视为巫术的进一步发展。驱除恶鬼意味着鬼神的存在是有限的,它们的能力或许比人大,但是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法术控制它们。“通说”是贾平凹文本中描述的活人被鬼魂侵入身体,言行不能自控的一种情形。“通说”者往往和依附在身的鬼魂生前的言行基本保持一致,驱除的办法是“用簸箕覆盖其头,然后用桃木枝抽打”。鬼为阴,桃木属阳,所以有驱鬼的功能。《黄帝书》云:“上古时有神荼、郁律,二人性能度鬼。度索山上有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者,缚以苇索,执以饲虎。”[3]306另外,还有一种驱鬼的民俗活动,《古堡》里称其为“红场子”,即轰赶鬼魂和霉气。新房子盖好之后,闹房的众人皆赤上身,胸前背后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头缠红布,手舞足蹈并鸣放鞭炮以达到驱鬼的目的。汉时“四灵”是作为吉祥和方位的象征,有驱邪的功能,红布代表阳气,有镇阴驱邪的作用。此外,水、镜子也是贾氏文本描写中常见的驱鬼法器。水为清洁之物,阴阳师做法事时常口含清水,喷洒在认为有妖魔附着的物体上。镜子能驱魔,“《抱朴子·登陟》说: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心,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9]所以《太白山记》里反复出现镜子意象,《远山野情》里阴阳师禳治的办法之一也是使用镜子。
就贾氏文本丧葬礼俗的梳理来析,从最初的报庙、入殓停柩,历经写铭旌、踏穴、浮丘,到引魂、唱孝歌、下葬、祭祀,敬神、驱鬼,可见民间鬼神信仰之浓烈。在很大程度上,对鬼神的畏惧与崇拜,驱除与敬仰折射出民间百姓对死后世界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也反映了他们为追求一己和家庭之幸福的放诞而热烈的想象。
二
自古以来,人们一面在棺木上或墓室里绘上神人仙境的图画,竭力想象着极乐世界的仙云缭绕、芳草遍生,另一面却又运用各种手段试图驱散想象中地府的阴森、恐怖,这不仅反映了人们面对死亡时的矛盾心理,而且也说明了鬼神世界纯属想象的产物,而就想象而言,这正是文学的生发之处。萨特讲,艺术是艺术家的一种新的创造,其特征是非现实的和想象性的。如《庄子》之文,“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①见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据世界文库《晚清文抄》本,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文艺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想象的瑰丽、奇异是文学最富有魅力之所在,尤其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疯子、情人和诗人,全都是想象的奴隶:疯子眼中尽是鬼魂,多得连无边的地狱都难以容纳;情人也是一样地疯,竟能在埃及人的黑脸上看到海伦的美;诗人的眼睛在微妙的热情中一转,就能从天上看到地上,从地上看到天上;想象能使闻所未闻的东西,具有形式,诗人的莲花妙笔赋予它们以形态。”[10]
贾平凹的文学想象怪异新奇,可分两类。一类是创造的想象(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他能将云中的鸟与水中的鱼联想在一起,能让木板里隐藏人形,杀人时砍下的不是人头,而是人的垢甲壳等等,这些想象通常运用两种手法构成:第一种是嫁接、移植。指将不同物体相互连接在一起,像《白夜》里将夜郎和马面连缀,《土门》里给成义嫁接一只女人手。《废都》中的牛哲学家,《古堡》中麝所拥有的人之思考,《秦腔》里人长瘤子后,想象着把树上的树瘤割掉后人就可以痊愈。上述想象中有的是将人的思想移植给动物,有的是宣扬人与植物之间存在着感应。前者具有极强的寓言性,后者包含着交感巫术。第二种是变形、变异。这是一种对知觉的重新组合,大凡神魔、志怪小说都擅长使用这种手法,贾氏小说运用颇多。《怀念狼》中的人狼互变,《高老庄》里的人变猪,《太白山记》里有意将想象中的虚像转化为实像。《土门》里梅梅长出的尾骨,《秦腔》中白雪的女儿生下来没有屁眼等均属于此类,这些想象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事物,能在直观中将其表现出来,并具有产生新对象的能力,有魔幻的意味,是想象中富有创造性的一种。另一类是幻想(phantasy)。按照西方的文艺理论,这是一种使本身不出场的东西出场的想象力。所谓本身不出场的东西是指知觉中、感性直观中从未出现过或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东西。然而,“不管幻想这种想象与现实世界如何抵触,但无论如何,幻想为我们开拓了视野,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更大、更多的可能性。”[11]贾氏的《病相报告》、《太白山记》里沟通了人间、冥国、天堂三界,《烟》中有“思接千载”的幻觉,《太白山记》中写到,老村长与村支书活着的时候有路线之争,于是,想象中二人死后成鬼各自坐在自己的坟头上吵架,并且“吵得庄严而有趣”。贾平凹的想象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联想,因为联想和回忆是将过去曾经感知的事物重新在头脑中再现出来,这是一种最常见,也最普通的想象。贾氏的文学想象不只是起联想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具有建构性,他的想象创造出了新文学形象,并在想象中自我思绪真正飞扬起来。当然,思绪的飞扬也是有条件的,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贾平凹写作时也有怪癖,喜欢关门关窗,窗帘也要拉得严严实实,如果是一个地下的洞穴那就更好。刘勰讲:“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12]写作时精神的虚静状态是艺术创造的前提,可能贾氏写作时需要一种阴郁鬼气氛围方能进入情境。提及鬼,还需要涉猎巫以及觋概念,这三个词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巫是指专门从事降神驱鬼的人,最初指女性,觋指的是男人,可是到了后来男子也可称巫,并成为专用。“觋”从“巫”,从“见”,“见”与“咸”相通,“咸”是束棺材之绳,因此,巫是抬棺材的男人,与死亡、鬼神有一定联系。不言而喻,鬼神是想象之物,巫师是具有沟通鬼神人特异功能的人,所以在人神感应、幽明互通的巫术活动中,“‘巫’或‘魔’,似乎在任何人心里都激起某种潜在的意念,激起希望看奇迹的憧憧之怀,以及相信人类本有神秘力的可能等等下意识的信仰。”[1]52于是,不难理解在氤氲鬼气中,万神归位,贾平凹被某种神力驱使,思绪也由此物而联想到彼物,由不在场想象着在场,由人间飞驰幽都,由人类推及动物,想象中作家的思维打破时空,超越有限。所谓“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13]贾氏的想象终是一种鬼神魔幻思维,同时也是一种矛盾思维。《高兴》中锁骨菩萨曾以妓的身份普度众生,圣洁与淫荡并存,《土门》里成义双手的一阴一阳,《白夜》以昼与夜命名、《秦腔》中的白雪与夏风不仅命名对立而且生活中貌合神离,《高兴》里的刘高兴与韦达的互为镜像,《废都》中的庄之蝶与周敏的二位一体,贾平凹的想象之中思维总是处于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状态,这种矛盾的思维模式既反映了社会现实、事物的复杂多样性,也蕴涵着作家生命体验的深刻多重性,从而使其文本充满张力和神异,正是这种神异造就了贾平凹的魅性审美意趣。
三
“魅”一词语见于马克思·韦伯的论著,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理性的发展而提出来的。在韦氏看来,现在社会“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14]“除魅”表明宗教世界观的瓦解,科学文化的繁荣与普及,人们不必再像相信某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一切行为、事物求助于神灵和魔法,科学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话语,就是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的研究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它的研究的工具,便是剧本。然而,“历史不是一元的线性发展,历史进步行为与人文文化尤其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文精神传统常常表现为一种逆向的复调解构。”[15]鲁迅先生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沈从文也试图以神性拯救人们日渐式微的生命,尤其是对一个有探索、追寻意识的人而言,当精神性的超越意识被唤醒之后,寻求灵魂的归依——信仰宗教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通过对民间丧葬礼俗的描写带来了“魅性”审美的复活,在探寻人类的精神世界、追寻生命意义上无疑是最具有文学性的。“沿着文化发展的一切道路散布的遗迹,正是那些能够辨认其题铭的人的路标。”[16]贾平凹的文学也因融进传统民间文化而获得了“魅性”审美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怪诞诡异
尽管在中国怪诞并非艺术审美的正宗,但是“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如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7]贾平凹的作品里既有现实事物的变形、变异,也存在全凭想象而诞生的鬼魅精怪形象。天马行空的奇思怪想,扭曲变形的渲染夸张,极尽人世的艰难繁复,生命的曲折异化,这是个体历尽人间沧桑、遍尝种种生活苦难之后的变异心态的折射,更是传统的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陌生化、被篡改的荒寒、残破的隐喻。尤其是他的许多作品都喜欢以死亡、鬼魂煞尾,《秦腔》中“一种死亡的氛围在小说的结尾处弥漫,在传统民间文化的末日弥漫,如吼如哭的秦腔作为哀歌也恰如其分”。[18]《高兴》最后五福作为一个孤魂野鬼在城市的夜空飘荡,《白夜》在《精卫填海》的鬼戏里让冤死的鬼魂游离。在这弥漫着死亡、骚乱、丑陋、冷漠的气息里,怪的意象揭示了人类异化处境的尴尬,带血的头颅撞击的是理性世界的大门。不言而喻,贾平凹的作品充盈怪诞诡异。怪诞是“把各种大相径庭的成分串连在一起,没有清楚的形式,组织和结构对称完全听其自然的大杂烩”。[19]诡异指的是变化多端、异军突起。然而,当文学表现出怪诞时,其上凝结的是作家对丑恶现实和虚伪文明人的否定性体验,它昭示着我们去积极肯定生命的价值,肯定文学艺术对人的灵性、情思的守护。中国艺术一般以清逸为最高境界,追求放逸,贾平凹选择了鬼神意象,也就放弃了清逸,然而,“艺术的眼睛在人类遭受科技飞速发展和心理机制急遽紊乱之中,深情冷眼地睁着,它不仅在广漠不毛的荒原吹响一哨绿笛,也以惨烈的面容直面人自身的丑陋。”[20]
(二)幽深晦涩
这一层审美意蕴是由怪诞诡异引申而来的,由于倾心于鬼魅精怪的想象,神巫魔幻氛围的营造,想象中思维的矛盾,贾平凹的文本也就拥有了幽深晦涩之味。幽深者,似一泓池水难见其清明也;晦涩者,如手抚一片麻布难以有光滑顺畅感也。众所周知,《庄子》文善于描写至人、真人、神人境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四海之外。”[7]在庄子的方外思维之下,想象在天地人之间飞扬,而贾平凹的鬼神想象、矛盾思维也就使其思绪在人间与冥界徘徊。郭熙讲:“山有三远。自山上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①转引自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此虽是论画,但却与文学审美意趣有关。“秦关望楚路,霸岸想江潭。”商州水道以汉江为主道,顺流而下可至湖北荆襄,陆路以商於古道可至豫、荆之地。自古荆、楚之地巫风颇盛,因此,贾平凹之文也就沾染上了诡异、神秘之气。这是从地域文化角度论及贾氏作品。如果我们将其放置在上个世纪寻根文学思潮背景之下考虑,就会发现其“魅性”审美趣味还缘于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在那场响应“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和国内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皈依与反思之中,贾平凹领悟到他的那些“地域文化”与传统的秦汉文化之间的相通,因此他迅速从当代文坛上脱颖而出,出奇制胜。一直以来贾平凹拥有浪漫情怀,然而,与同时期作家相比,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浪漫在于由从沈从文、孙犁那里继承来的清逸,而转向了汉文化艺术的神秘。历史上,虽然汉王朝在礼法、制度等方面基本上延承秦制,但是就文学艺术而言,汉文化由于融入楚文化因子,所以其中更多弥漫着将“生者、死者、仙人、鬼魅、历史人物、现世图景和神话幻想同时并陈,原始图腾、儒家教义和谶纬迷信共置一处”[21]的气息,而这正是贾氏苦苦求之的。从《卧虎说》流露出的对汉文化的艳羡,到文学贵在“雄中有韵,秀中有骨”理论的倡导,“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22]这是贾平凹对汉文化最深切的体味。然而,可能是由于他个人艺术修养所限,其审美终究还是匮乏了一层玄奥、恣肆的意蕴。
但是,贾平凹的“魅性”审美却使我们看到了人的灵魂中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在鬼神信仰中体验的是一种思想飞扬的自由想象,在巫术描摹中感悟的是一种情感宣泄的舒畅,其中包含了对庸常生命的超越,充盈着精神创造的愉悦,儒家讲“子不语怪力乱神”,贾平凹醉心于鬼神世界的描摹使其脱离了正统的文化体系,可是,在奇思怪想之中彰显的却是对生命的尊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天地万物,追求思想的放飞,这对于务实的中国人而言,贾氏文本无疑激活了人们日益僵化的思维、滋润了人们逐渐枯萎的审美情感,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事项,揭示了民众真实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状态。毋庸置疑,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内涵。
[1]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2] 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1.
[3] 吴树平校释,〔汉〕应邵.风俗通义校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4]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6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36.
[5] 郭璞.葬经[M]//娄子匡.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专号3堪舆篇.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7:9-10.
[6]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7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271.
[7] 杨义.庄子还原[J].文学评论,2009(2).
[8]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 许地山.道教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36-137.
[10] 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3:241.
[11] 张世英.论想象[J].江西社会科学,2004(2).
[12]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53.
[13] 袁于令.西游记题辞[C]//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丛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8.
[14] 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9.
[15] 孔范今.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J].文学评论,2003(4).
[16] 〔英〕爱德华·伯纳特·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
[1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5.
[18] 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创业史》到《秦腔》的贾平凹[J].当代作家评论,2006(3).
[19] 凯泽尔.美人和怪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M].曾忠禄,钟翔荔,译.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14.
[20] 荣格.荣格文集(卷九)[M]//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75-176.
[21] 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80.
[22]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