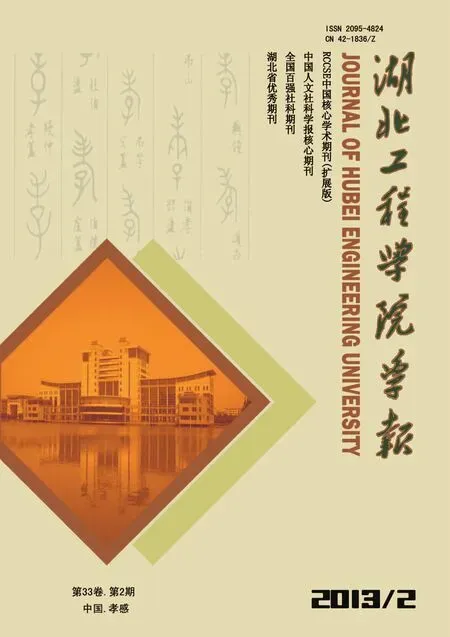基督教视域中的《白卫军》人物形象分析
罗 妍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时间大约有20年,其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作家踏入文坛至1927年,后期从1928年至1940年。其中《白卫军》(1922-1924)集中体现了作家的宗教思想,宣扬基督教信仰和基督之爱的宗教精神,塑造了在受难中的信仰者形象和基督式的英雄形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一、永恒的家园与基督精神的守护者形象
《白卫军》开篇就引用《启示录》中“于是死人们都按各自做过的事情和书中所写的内容受审”[1]1一句,这使全书蒙上一层神秘主义色彩和启示录情绪,也点明了小说的主旨:人需要在战争与苦难中接受信仰的考验。作家通过几组人物的对比来表现这一主旨,即弃城逃跑的黑特曼统治阶层、生活在社会中上层的图尔宾一家与社会底层的瓦西里夫妇。对于深陷战争危机的市民阶层而言,对物质的焦虑与需求使他们呈现动物般的生存状态;而 “彼特留拉”暴徒——来自旷野的野兽般丑陋而顽强的乌克兰农民代表原始的生命力,他们不断从旷野入侵城市,践踏城市精致而孱弱的文明。 图尔宾一家是城市守护者的代表。尼克尔卡·图尔宾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有以履行军人职责为原则的荣誉观和责任感,这种天真的、视荣誉为生命的理想主义使他迫切地投入荒诞的战争,他渴望将生命奉献给受难的同胞,这也是一种基督教式的爱的激情与受难的激情。阿列克谢·图尔宾是布尔加科夫自传色彩浓厚的“讽刺性同貌人”,作家以讽刺和怜悯的口吻塑造了这个人物,他的价值观和对基督教的理解都有些狭隘,经历生死考验之后他逐渐成熟起来。与天使般的尼克尔卡相比,阿列克谢则阴郁、理性得多,他认识到在黑特曼弃城逃跑后参军是种向死而战的行为,腐败的统治者根本不值得效忠。他并不是个全知全善的人物,而是站在保皇党立场上抱着狭隘的偏见憎恶乌克兰民族分裂势力和布尔什维克,其立场没有正义性,在现实层面上是个失败者。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坚守独立的、个人的道德抉择,通过勇敢的行动履行人生的职责,仍然不失为受难却不丧失信念的英雄人物。在《白卫军》改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中,作家把阿列克谢与纳-图尔斯合并为一个人物,这正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人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与图尔宾一家形成鲜明对立的是机会主义者塔尔贝格,他是黑特曼政权的代表人物,在危难中抛弃妻子、见风使舵。黑特曼统治下的城市失落了“新耶路撒冷”的精神气质,变得像巴比伦一样充满了庸俗市侩气息,统治者与市民阶层一边趁危机尚未降临奢侈享受,一边敛财为弃城逃跑准备后路。城市失去了它的永恒性,成了各种势力轮番掌控捞取利益的堕落之城。逃跑的塔尔贝格和弃城的黑特曼政权是世俗性玷污神圣的永恒性的象征,而图尔宾一家则是神圣的、永恒的家园与城市的守护者。“灯罩是神圣的。永远,永远也不要从灯上摘下灯罩!永远也不要鼠窜般地没有明确目标地逃避危险。在灯罩旁边打瞌睡吧,读书吧——让暴风雪去吼叫,——等着吧,让人家来找你。”[1]25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城市是神圣、永恒的家园的象征,这表现在它的居民——誓死保卫城市的图尔宾式的人物身上,也表现在它的自然风光、历史遗迹甚至现代化气息之中。作家以诗意的笔触描写城市,把它上升到了基督教精神家园的高度,这从小说中多次提到的弗拉基米尔的雕塑可以看出来。电器化时代的到来昭示了人类力量的强大,但并未撼动上帝的神圣看护,弗拉基米尔的雕塑手持白色电十字架,仍然给迷失的小船指引方向。布尔加科夫的笔下的城市凝缩了自然与历史、上帝与人世,从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跨度上都可谓是一幅神圣之城的历史画卷。基辅是俄国基督教的早期堡垒,古老的文化中心,在俄国历史上以“俄国大地上的耶路撒冷”、“俄罗斯城市之母”而著称,于1853年树立的弗拉基米尔纪念碑代表俄国在988年定东正教为国教并接受洗礼。《白卫军》中描写的那座城市是以基辅为历史原型,同时也是宇宙的象征:它是文化的先驱与文化生活的一种浓缩。莫斯科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后,大量资产者逃往基辅,这些外来者彻底扰乱了城市的文化氛围,把城市扫荡一番后弃城逃亡西欧;代表神秘自然力量的“彼特留拉”也将继续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生活在城市一隅的图尔宾一家跟其他基辅市民和外来者一样,深陷这个狂风暴雪般的历史社会变革中,盲目而坚定地抗争着。盲目是因为作为普通市民,他们缺少全局的政治视野,作为生命个体,脆弱的肉身不堪炮火侵袭。作家以人物片面的、不确定的视角来观看战争,没有确切的信息,只有不可靠的预兆和判断,人们因为盲目而恐慌、丧生,这种手法最大程度地传达了人在战争时代的存在感,同时也对统治者的不负责任进行道德批判。“拉丁语的turbo-turbinis意指‘玩物’及‘旋风、飓风、风暴’。图尔宾一家是历史环境的玩物,但是凭他们本身的资格来讲也是积极力量。”[2]100
从以上分析可见,图尔宾一家是城市的守护者,更是基督教精神的捍卫者,他们在这种摧毁文化的战争中的抗争与受难正是对信仰的考验,从中体现出人性的高度,他们在战争中成为精神贵族与信仰的骑士。
二、白卫军英雄人物的牺牲、受难与永生
小说中的基督式人物纳-图尔斯上校,是一名战败军人,在黑特曼政权逃跑后自发组织白卫军保卫城市,“用布尔加科夫的话说,他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抽象的人物’,代表着‘我想象中理想的俄国军官的思想观念’”[2]99。纳-图尔斯上校有着 “纯净,深沉无底,从内部发亮”、“使人心中暖和的蔚蓝色”目光,他的声音是“清爽的、像城市森林中的小溪一样透明”。作家的这些赞美性的文字表明他是一个道德上十分纯净的人物。纳-图尔斯以惊人的行动力组织义勇兵团,有着作为一名军人极高的职业素质。这个忧郁而沉默寡言的人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对士兵的关爱,他怀着这样的战争道德观:保卫城市者同样需要得到保护,没有皮帽和毡靴等必备的物资而让士兵去冒死打仗是不道德的,是对士兵生命的不负责任和不尊重。但纳-图尔斯这样一名理智与道德兼备的军人却遭遇腐败的官僚体制,只能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他的胆识与正气让外强中干的官僚胆寒。
荒诞的是,已经弃城逃离的黑特曼政权的司令部竟然还在向前线军人下达作战命令,让不知内情的保卫者去遭受无意义的屠杀。双方交战的地点在“一个完全死掉一样的十字路口”[1]157,这是十字架的隐喻,意味着死亡和受难。年轻的尼克尔卡成了牺牲品,还在幻想着战死的荣誉,被英雄主义冲昏头脑一心要赴死。可是,纳-图尔斯上校死得并不像尼克尔卡幻想的那样悲壮,反而是滑稽可笑的:“他一只脚跳了一跳,另一只脚挥舞一下,像在跳华尔兹舞,又像在舞会上一样露出一个不合时宜的笑容。”[1]173纳-图尔斯上校给他的遗言是“您不要充英雄了”。尼克尔卡经历了母亲的去世和图尔斯的牺牲,但对死亡仍然懵懂无知,也不懂得生命的意义。在此,作家对廉价的英雄主义荣誉观作了辛辣的讽刺,他用滑稽的场景取代悲壮,告诉读者:任何牺牲都是不得已的,如果把牺牲的价值无限抬高成引人追逐的虚幻理想,就成了魔鬼的诱惑,模糊了生命的真正尊严与意义。纳-图尔斯是个理想的人物,但作家花的篇幅并不多,而且主要通过外部描写如外貌、简短的对白、较晚的出场时间等,不像描写阿列克谢那样表现人物的情感、思想、情绪、梦境等。纳-图尔斯是个“被看者”,像基督一样受难、牺牲,以死亡保护、启示他人;死后寻找他的尸体成了尼克尔卡的主要任务,最终获得珍贵的生命领悟;他的死亡给母亲和妹妹带来了悲痛,得到她们的爱与哀悼,让人联想到基督受难后圣母玛利亚以及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悲痛。他还在阿列克谢的天堂之梦中出现,是小说中唯一经历了人世、地狱(储存尸体的地窖)、天堂三重世界的人物。
寻找纳-图尔斯遗体的情节是对《圣经》的仿写。“陈尸所的那段情节在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中只有一个类似的情节,即《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约书亚被钉十字架。”[2]96《圣经》中记载: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及格罗罢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也就是说,见证耶稣受难的有三位女性,她们的名字都是马利亚;而三天后,前往坟墓看耶稣遗体的女性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纳-图尔斯上校的母亲的名字也是“马利亚”,在上校死后三天,尼克尔卡前往陈尸所领取遗体的情节与《圣经》暗合。陈尸位于地窖中, 正是一个现代的“沉落地狱”,这既是一个古希腊罗马神话原型,也有基督教“圣母玛利亚沉落入地狱”的意味。就如《大师与玛格丽特》“撒旦的盛大舞会”一章,身份各异的死者、魔鬼、女巫和腐尸汇聚一堂,《白卫军》也有类似的地狱场景:“他抓住一具女尸的一只脚,滑溜溜的女尸咚的一声滑到了地板上。尼克尔卡觉得她非常美,像一个女巫,并且是黏糊糊的。她的眼睛张着,直盯着菲奥多尔看。”[1]293“尼克尔卡直接看看纳-图尔斯的眼睛,张大的、玻璃般的眼睛没有会意的反应。”[1]294在尼克尔卡眼中,死者似乎也是有生命的,因为根据基督教观念,人不会只死一次,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死者终将复活。地狱也不过是末日审判前关押罪人的临时空间,圣母沉入地狱怜悯受惩罚的罪人,向上帝祈求宽恕,死者在炼狱赎罪之后就能上天堂。死去的英雄纳-图尔斯在死后三天得以离开陈尸所,在上帝的殿堂里安息。上校的葬礼是温馨的,甚至是愉快的,因为死者为自己能够安息感到高兴。作者在此确认了基督教的永生观念。尼克尔卡完成了纳-图尔斯的葬礼,履行了人生中比起逞英雄地送死更有意义的事,因而解了生与死的意义,也体现了对于牺牲、受难者给予爱的回馈的基督教精神。
三、圣母原型:庇护家园的永恒女性形象
《白卫军》中的女性形象也与俄罗斯文学的“永恒的女性”宗教文化传统相关,她们是家庭的守护者,是圣母精神的化身。根据《圣经》的记载,在 “主叫拉撒路复活”一章中有一个重要的女性——死者姐姐马利亚,“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3],有感于马利亚的悲痛,耶稣行奇迹让死者复活。与《圣经》神话一致,《白卫军》同样让濒死的阿列克谢的姐妹叶莲娜的哀痛和哭泣感动了基督,这体现了小说的重要观念——家园与亲情,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能够感动上帝降下奇迹。《圣经》中“马利亚往看坟墓”一章中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三天,抹大拉的马利亚前往坟墓亲眼见证了耶稣的复活。《圣经》中与“复活”相关的场景都有女性的存在,她们是母亲、姐妹和受难者(有罪的女人如抹大拉的马利亚)。姐妹叶莲娜正是在为兄弟的濒死哀哭时看到了基督的幻象,紧接着就是阿列克谢奇迹般的康复。也就是说,小说中阿列克谢“复活”的情节是对《圣经》“复活”场景的仿写。更引人注意的是,叶莲娜并没有直接向基督祈祷,而是求助于圣母玛利亚,以圣母为中介求上帝显容基督行奇迹。圣母玛利亚曾在十字架旁目睹了基督的受难与死亡,拉撒路的姐姐马利亚也经历了兄弟的死亡,而叶莲娜也正面临兄弟的死亡,这是一个以女性情感体验的共通感为纽带的关系,叶莲娜觉得圣母最能体会她的痛苦,她一直强调圣母与基督的家庭关系,多次称圣母为庇护者。叶莲娜本人也正是图尔宾一家的庇护者,是圣母般的永恒女性的形象。
四、获得救赎的堕落者形象
《白卫军》中有一个略显突兀的人物:梅毒患者鲁萨科夫。他在小说的第九章和最后一章出现过。在第九章中,鲁萨科夫作为白军装甲营指挥官米哈伊尔的“对比人物”出现,米哈伊尔过着令人羡慕的“健全”生活,似乎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模范人物。而事实上,他却是个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丧失了基本的良知和责任感,是一个空有一副好皮囊却对他人、社会无益的“多余人”。鲁萨科夫是米哈伊尔文学社交圈的一个不受欢迎的成员,他称米哈伊尔是“城市里所有人中最强的”、“如此漂亮,似乎有点太健康了”,而自己则像这个城市一样“正在烂下去”。梅毒患者与城市一起被这些所谓的“强者”和“健全者”抛弃,自生自灭。鲁萨科夫是有罪的弱者,他曾狂妄地写诗讽刺基督教理想,患上了虚无主义的时代病,相信人可以像米哈伊尔那样凭借自己的健康、才智获得幸福,但当他染上梅毒后,才醒悟并求助于上帝的怜悯,明白基督教对于弱者的爱与拯救是不可或缺的崇高道德与精神慰藉。健康与否是个偶然事件,但人的幸福不能建筑于偶然性之上,机会主义者由于随波逐流追求短暂的物质、个人满足,其精神世界是空虚不定的,人的幸福只能以永恒的信仰为根基,爱与良知同样如此。“疾病和痛苦在他看来是不重要的,非本质的。他没有感觉到害怕,而是感到了一种明智的顺从和敬仰之情。”[1]319身体的疾病让他认识到精神的病态才是真正的顽疾,才是需要医治与救赎的。最后,他彻底否定了米哈伊尔这种“反基督者的先驱”,找回了信仰,在神父的劝导下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念,在基督教精神指引下寻求“复活”。
[参 考 文 献]
[1] 布尔加科夫文集:第3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2] 莱斯利·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3] 新旧约全书[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