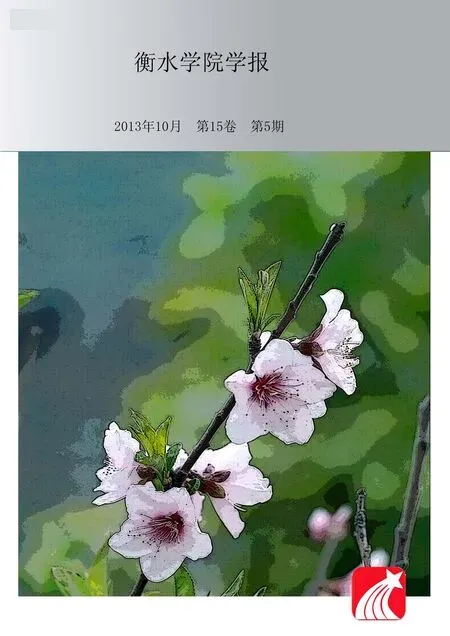董仲舒人性论探微
聂 萌
董仲舒人性论探微
聂 萌
(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2)
董仲舒的人性论有其内在的理论结构,他的人性论是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渗透到社会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他的“性三品”“性情说”等人性论思想无疑在儒学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人性论不单单是一种思想,更是在汉代大一统背景下为政治而服务的理论工具,是儒家思想重新被重视成为正统思想的主要理论原因。
董仲舒;天人感应;“性三品”说;人性论;儒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他对《公羊春秋》颇有研究,是当时的今文经学大师,曾任两个诸侯王的国相,退休以后,依旧深受汉武帝的尊敬,他的人性论是其教育观、政治观的理论基础,在儒家人性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旧为人们所研究着。在张实龙所著的《董仲舒学说内在理论探析》中,作者强调学者应用“假设的同情”的罗素式态度去看待一个思想家,看待历史上的董仲舒。接下来笔者将以求实的态度来分析董仲舒的人性论。
一、董仲舒人性论的本体论根基
研究董仲舒人性论必须应看到其人性论背后的天人感应思想,正如高春菊所说“天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天道是人道的终极根据”,董仲舒的人性论的提出是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天”是人性论的本体根基,是人性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终极价值根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将天和人联系起来的同时,也把天和君主联系起来,把君主和中民联系起来,更让其人性论有了可信服的依据。天人感应思想是董仲舒人性论能为君主以及当时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的思想前提。
“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董仲舒认为天人相副,天是人的根据,所以可见人性也是以天为根据的。“是正名号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暝。情亦性也。谓性已善,奈其情何?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尤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董子认为身的名称是从天取法而来的,上天同时有阴阳二气施放,身也同时有贪婪、仁爱的本性。天人相副,天有阴阳,人有性情,“乍全乍伤,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进一步指出人类应减损自己的欲望而停止自己的追求来回应上天。这也是董仲舒教育观的理论基础。
除了天人相副推导出身有性情之外,天人感应思想中还强调天赋予君主实施德政来弥补人性的质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既然天任用德教,作为天派遣的王更应任用德教,对百姓施行教化,使民向善,弥补人性的质朴。“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董子在《深察名号》中一直强调人性是由天赋予的,但那不是善,只是有善质而已,为了达到善需要王的教化。
董仲舒利用汉代较为流行的阴阳思想来阐释其天人感应思想,并以此形成其人性论。人有性情,性有贪仁,是天人感应的结果,可以说人性的根源在于天道。同时君主受到天的召唤来实施教化使民向善。天与人性通过天人感应的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有阴阳”到“性情观”的过渡,这不仅能体现出董仲舒学说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还可以看成董仲舒秉承《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路径,将天、人用人性理论完美地贯穿在一起,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良苦用心。
二、董仲舒人性论的重点内容
(一) 性情观——董仲舒人性论中的哲理基调
董仲舒的性情观是董仲舒人性论中最基础部分,“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非度制不节”。(《举贤良对策一》)他认为性是有生以来上天就赋予的既有的本质,情是人后天所拥有的欲望。这跟《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董仲舒将性看作是人天生就有的东西,与生俱来的,而情是人们后天所有的欲望,性情这俩字在董仲舒那里是分开的,内涵是不同的,性是质朴的,需要教化向善,情是欲望,所以要节欲,限制欲望,性非同于情。这跟现代所了解的性情有所不同,简单说来,董子是从普遍的人性论上所说,而如今的性情更倾向于个体。
王永祥将董仲舒的性情感表述为:待教而善的人性论。曾振宇将其表述为“天赋善恶论”,也有人将其表述为:性善情恶论。不论进行怎样的表述,学者在研究董仲舒的性情论时首先应必须要清楚董仲舒的“性”有广义狭义之分,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地提出了这点,“董仲舒用‘性’字,有时取广义,有时取狭义。就狭义上,性与情分开而且相对;就广义说,性包括情”。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认为董仲舒的性情论是矛盾的。
“是正名号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暝。情亦性也。谓性已善,奈其情何?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尤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周晓露针对这个找出阴气-情-恶质,阳气-性-善质的对应关系,认为性只有善质了。可见她认为出现了矛盾,随后她又解释道由于董仲舒要建构其“性未善”的观点,所以董仲舒说“情亦性也”。周晓露显然没有认识到“性”的广狭义之分,性广义看是天性或者质朴的性,里面有善端而不是善,狭义的性就是善了,身有性情的性应当狭义讲,故对应善。顾玉林根据“情亦性也”和“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这两句话得出董仲舒似乎陷入了性情二元论。笔者认为顾玉林也没有认识性的广狭义之分,在董仲舒的人性论中广义的性包括性和情,所以董仲舒的人性论不是性情二元论,而是性情一元论。
至于“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许多人的解释不同。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中的理解是董仲舒认为善是主导的方面,情欲是从属的方面。而余治平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相关的问题:“性与情都为天地所生,是生存世界里不可回避的‘天令之然’。”在本质论和发生学的意义上,性与情甚至就没有任何的区分,“性就是情,情就是性,性与情一同始起,一同周始,也一样重要,一样产生作用”。董仲舒说了性与情不同,在这里又说“情亦性也”,这是一种矛盾吗?不是,正如刚才所说,性有广义狭义之分,性作广义讲,性包括着情和狭义的性,情也就是性。“情是恶的,但又在人的质(广义的性)中”。这些说得都有道理,不过可以这样理解,董仲舒的人性里面包含着善端,情通过后天的教化可以向有着善端的性靠拢,最后达成的就是圣人之善了,也就是“情亦性”了,或者可以这么说本性和情感互相一致深入到善,这时我们就分不清情性了。它们一起为善作努力,只不过一个完善善端,一个节制欲望,谁都否定不了两者的紧密联系。
(二)“性三品”——董子人性论的核心学说
荀悦的“天命人事的上中下三品”,王充的“人性善中恶三个等级”,韩愈的“上者善;中者可导而上善或下恶;下者恶”的明确的性三品说,这些都有性三品的影子,不过正如王永祥所说“董仲舒乃是提出性三品说的先驱或鼻祖”。
大多数学者认为董仲舒的性三品是独特人性思想,持肯定态度,认为性三品正是董仲舒社会教化的理论根据。比如曹影曾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是对先秦和秦汉的人性理论、人性现实甚至于是治国实践的总结和概括。”不过也有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分析了董子的人性论的不足之处,黄开国从逻辑角度上认为董子的性三品说是明显的逻辑矛盾,并提到:“只有在认识到儒家人性论发展的三种基本形态,才能懂得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处于儒家人性论从性同一说向性品级说发展的逻辑转折点,而明白董仲舒人性论的混淆。”“在研究哲学家时,必须以把握到某一思想理论的发展逻辑为前提。”周晓露也说过:“董仲舒的人性观并非全部值得肯定,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并从3个方面阐释了董仲舒人性观的不足。对于董仲舒人性理论,从最早研究的相关论著到现在的一些论著,我们其实能看到分析评价人性论时的态度从绝对肯定分析、绝对否定分析再到辨证分析的阶段历程,也能看到从进步、退步的阶级分析到科学求实的态度的转变,这是值得肯定的,毕竟学者们在分析哲学家思想时理性的一面越来越突出。
董仲舒认为人性分3种: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在他的著作中他主要论述了中民之性,值得强调的是有些学者不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是性三品,而是其他,比如陈云森认为是质朴的一品论,陈德安认为是四品论,不过总的来说主流思想是三品论。
“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在性三品中,我们该如何理解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呢?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专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经过分析在他之前的关于董仲舒性三品的思想,其中尤其阐释了以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性三品说的思想观念,最后得出“董仲舒所谓圣人之性仅指少数圣人,并非包括一切封建统治者(皇帝)。斗筲之性仅指极少数严重危害社会的大恶人,并非指劳动人民。所谓中民之性即指绝大多数人的本性,包括上自一般皇帝,下到平民百姓乃至奴隶在内”。在笔者阅读相关董子的论文、书籍、资料时发现有的人把“斗筲之民”定义为“封建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劳动之民”,如顾玉林《董仲舒“性三品”的人性论及神学化的思想倾向》;还有的人将斗筲之民看成“教而不能善”的人,比如曹影所作的《性三品:董仲舒社会教化的理论根据》。
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中把斗筲之性看成下愚之性,认为“斗筲之性又叫下愚之性,是经过教育也不可能转化为善的性,圣人之性不需要教育,是先验的善的性”。不过他的论述较为简单。
廖其发在《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中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斗筲之民是天生就没有接受教育的潜能的人,没有善质,外界的教育不能对其起作用。
王永祥在《董仲舒评传》中涉及到相关问题,提到:“‘斗筲之性’,当然在本质上也不属于人性,而只能是鸟兽之性。鸟兽之性自然亦无善质,只能是绝对的恶质,有王教亦不能使之为善。”在他看来,董子的圣人、斗筲都不是人。
商聚德《试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中相对详细地提到了相关的东西。他认为圣人既然是纯善的象征和化身,那么斗筲之人便是纯恶的象征和化身,他们的本性只能设定为先天的恶,是不可救药、不可教化的,因此被排除在“待教而善”的讨论之外。
笔者认为既然董仲舒的人性论其实在为政治统治张本,那么将圣人理解为不教而善的人(即不需要教化的人),将斗筲之民理解为教而不善的人(即不值得教化的人)较符合董子人性论意愿。相对于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与教而不善的斗筲之性而言,董仲舒认为中民之性是需要教化的,“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缫以绾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於教训而后能为善”。(《春秋繁露·实性》)董仲舒讲中民之性讲得较多,他认为中民的本性就像茧和卵,蚕茧经过抽丝就可以成为丝,鸟卵经过孵化才成为小鸟,人性经过教化才会成善。这为教育理论提供了人性论基础,同时也反映出儒家一直以来直面现实的外王精神。
三、董仲舒人性论与其他思想家人性论比较
先秦的孔子、孟子或者荀子这几位思想家所阐述的人性观都具有代表性,又因为董仲舒与他们同属儒家学派,所以学者对董仲舒的人性论进行评价时总是将其与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性论进行比较,董仲舒为了力证自己人性论的可靠性,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就把自己的人性论和孟子的人性论作了比较,董仲舒用“深察名号”的方式提到反对孟子性善论。
首先,他说:“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于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用性比作禾,将善比作米,虽然米出于禾中,但是米又不同于禾,通过比喻得出结论,善是由天性经过教化而来,但是天性并不是善,而只是有善端而已。孟子主张所有的人本性全可与善想对等这一观念是错误的,强调人性不是善,只是善端而已。这在很多著作中将性与善的关系看成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以此为着眼点进行将董子待教而善的人性论与孟子性本善论作比较。
其次,董仲舒认为:“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於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善。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孟子所谓的善是爱父母,相比禽兽善良就是善,而董仲舒的善即圣人的善,两者对何谓善的标准不同,相比之下,董仲舒的善即圣人之善层次更高些,更难达到些,正因如此人性的完善需要教化,需要向圣人看齐。
除了董仲舒自己之外,历来的董学人性研究著作也针对董仲舒和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比较。在1995年王永祥著的《董仲舒评传》中,作者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分析和评价,总的认为:“董仲舒综合孟、荀,从总体上来说,毫无疑问,比孟、荀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某些方面,却表现了某种后退。”在《儒家思想导论》中,马秋丽、张德苏也认为董子的人性论是孔子、荀子和孟子的融合。顾玉林在分析了先秦诸家人性论后认为董仲舒兼综“善”“恶”,是一种神学人性论。但在曹影的《“性三品”:董仲舒社会教化的理论根据》中,曹影创新性地提出“董仲舒的‘性三品’是直接吸收了韩非的思想,是再次对治国之道的总结”。
董仲舒的人性论到底是借鉴了先秦哪位思想家的理论的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笔者认为这还需要各位学者今后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董仲舒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构在政治大一统体系下的人性论。在今天这个学问纷呈的年代,我们不能用进步或者反动的字眼来简单总结董仲舒的人性论,答案不是研究的重点,重点应是回到当时提出理论的时代背景下用不同的思路和角度将董仲舒的人性论与先秦思想家的人性论进行比较的过程。比如黄开国就在《析董仲舒人性论的名性以中》中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是处于儒家人性论从性同一说向性品级说发展的逻辑转折点,应看到董仲舒人性论的混淆”。其站在把握儒家人性论发展逻辑的高度来研究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说是个特色。
四、评价
董仲舒作为儒家发展到汉朝阶段时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对儒家正统地位的重新确立有积极影响。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为其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可以说人性论而政治则是董仲舒思想的现实归宿,也正因为这一点,儒家思想才摆脱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境地,这也是董仲舒会被称为“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的原因。按照尼采的历史观:“真正的历史是应服务于生活的。”我们应从董仲舒的人性论去寻找对我们现在生活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注重人性的善,发掘人们内心的良知良能等,这才是历史的意义而非历史的滥用。
[1] 张实龙.董仲舒学说内在理路探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前言1-2.
[2] 高春菊.近十年董仲舒研究述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25-130.
[3]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曾振宇.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J].史学月刊,2002(3):16-23.
[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28.
[6] 周晓露.试论董仲舒的人性观[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220-222.
[7] 顾玉林.董仲舒“性三品”的人性论及神学化的思想倾向[J].唐山学院学报,2006(4):20-23.
[8]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9] 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4.
[10]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三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4.
[11] 曹影.性三品:董仲舒社会教化的理论根据[J].社会科学战线,2008(8):36-39.
[12] 黄开国.析董仲舒人性论的名性以中[J].社会科学战线,2011(6):34-38.
[13]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4] 廖其发.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2):62-68.
[15] 商聚德.试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J].中国哲学史,1998(2):81-88.
[16] 马秋丽,张德苏.儒家思想导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181-182.
Dong Zhongshu’s Theory on Human Nature
NIE Me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Shaanxi 710122, China)
Dong Zhongshu’s theory on human nature, which has its internal theoretical structure,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telepath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has been applied in social,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aspects. His theory on human nature such as “three grades of human nature” and “theory on temperament” undoubtedly occupies a certain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It is not only a kind of thought but also a theoretical tool to serve politic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ification of Han Dynasties, and that is why Confucian thoughts were thought highly of again as the main theory of orthodoxy.
Dong Zhongshu; “telepath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three grades of human nature”; the theory on human nature; Confucianism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10.3969/j.issn.1673-2065.2013.05.005
B234.5
A
1673-2065(2013)05-0023-04
2013-06-07
聂 萌(1992-),女,河北晋州人,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