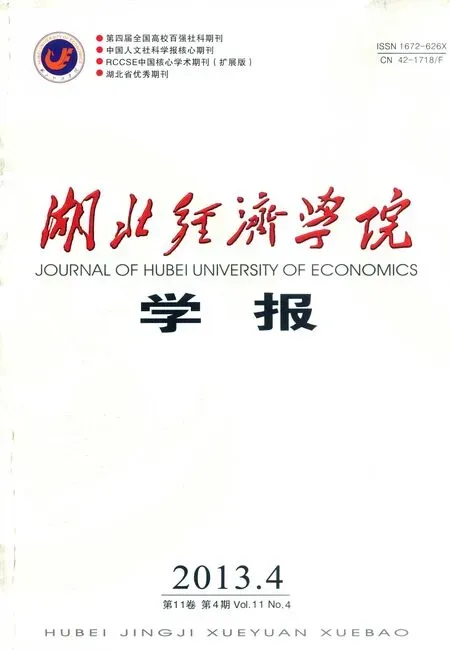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及破解
刘晓玲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经济教研部,湖南湘潭411100)
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及破解
刘晓玲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经济教研部,湖南湘潭411100)
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存在着行政性分权、“权力搅买卖”、预算约束软化和价格扭曲等四大体制性障碍。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锚定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取向,通过回归公共财政、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巩固产权制度和建设有限高效政府等措施,破解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双轨制;体制性障碍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这意味着我国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中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我国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总的来说,改革是以市场取向为特征的。[2]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就明确了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今年已经是这一概念提出的第21个年头了。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内仍存在很多计划经济的遗迹。这是因为,在改革之初,我们不能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只能在肯定传统体制合理性的前提下,做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进行局部的改进。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的关键就是在保持计划经济基本框架不受触动的同时,引进市场经济的因素作为补充。这样,就使得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是一个完善的体制,而是一种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双重存在的体制,也就是计划轨和市场轨并存的价格和资源配置体系。正是双轨制中的旧“体制性障碍”阻碍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改革的深化。本文拟通过对体制性障碍的分析找出破解之道。
一、制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体制性障碍
(一)行政性分权造成了市场割据
行政性分权主要由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下放财权和经济管理权限,特别是财政分权导致的。1994年,我国实行财税制改革,以分税制取代了此前的财政承包制。虽然之后进行了多次微调,但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仍然没有改变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
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中,支出责任大多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的,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承担了许多全国性的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包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现在流行一个顺口溜:“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勉勉强强,地方财政拆东墙补西墙,县级财政哭爹喊娘。”它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县、乡两级财政困难是事实。由于重要公共产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又没有相应的收入来源,转移支付也不足以弥补财政缺口,因此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级政府不得不致力于产值的高增长。因为各级政府的收入与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值直接挂钩,所以导致财政体系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下的特征,即大量财政资源被用于竞争性部门。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部门自然形成了对GDP的崇拜。各级地方政府变成了经济的首脑,于是各级政府官员的主要政绩就简化成了经济增长率。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动用配制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绩。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一方面“跑步(部)前(钱)进”等非常规行为再度兴盛,“傍央企”也成为各地政府做大财富蛋糕的重要做法;另一方面广泛地采用地区封锁、税费歧视、变相补贴等办法保护本地企业免受外地企业的竞争。沉重的支出责任与不充分的收入来源的结合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之外,还造成了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差异,加剧了地区间贫富分化现象。
(二)“权力搅买卖”加剧了寻租腐败
双重体制并存扩大了“权力搅买卖”和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实行双轨制使得同一经济中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套规则,造成了同一种商品有计划价和市场价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的价差在经济学中叫做“租”。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人运用走关系、行贿等手段接近权力,从而获得计划价和市场价之间的价差(租金)。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大量从事倒买倒卖活动的“倒爷”。这些“倒爷”往往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成为身价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富翁。“倒爷”们并不是倒买倒卖实物,而是倒买倒卖有权取得低价资源的官方文件:从调拨物资的“批件”、能够取得官价外汇的“进口配额”,到从国有银行取得低息贷款的信贷指标,都是他们倒买倒卖的对象。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绝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这只是铲除了寻租活动的一小块领地,仍然没有动摇它的制度基础,即权力对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和控制。由于土地、资金、汇率等生产要素价格远远没有市场化,于是,寻租活动的重点在新的领地蔓延:一个是土地,另一个是贷款。我国农村的土地是属于集体所有,城市的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于是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以很低的价格把大量的农用土地转移到城市中来。还有就是现行的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的,各级政府在信贷的发放上其实有很大的权力。政府掌握了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在资源配置中就仍然扮演主导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双轨制并存造成了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制度环境,于是党政部门的有些官员就利用职权从事“设租”、“造租”活动。一方面,这些官员创造新的“双轨制”,设立更多的市场准入、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另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家拉拢贿赂贪官污吏谋取私利。换句话说,只要这种寻租的基础广泛存在,寻租腐败行为就不可避免。
更为严重的是,寻租的巨大收益刺激了更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如此一来,容易形成“寻租—设租—更大规模寻租”的恶性循环。这些市场扭曲创造了大量的租金。根据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这种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额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差距加大和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预算约束软化酿成了货币超发
预算软约束描述的是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国家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无法对国有企业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作出辨别,就只能承担起企业所有的亏损,从而出现“预算软约束”。对国企而言,提高企业收入和员工福利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兢兢业业地提高生产效率,另一种是向国家要补贴。显然,向国家索要保护补贴是更加方便而且成本较低的办法,所以就会出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不断增加的情形,即预算约束软化的趋势越来越强。
当政府财力吃紧时,如果通过增发货币来支付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就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如果通过各种手段抑制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以此来平衡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生产率缺口,就会导致经济衰退。同时,地方政府还面临投资风险的软约束。地方政府官员总是优先选择那些有利于政绩最大化的经济发展策略,如通过干预国有银行迫使其向本地企业大量发放贷款,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则外化给中央政府。其结果是助长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而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又导致生产过剩。
总之,预算软约束的体制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抑制了经济的活力,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隐患和风险。[3]
(四)价格扭曲巩固了粗放式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资源和指定资源投入方向的能力。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原材料价格以及工人工资等都被人为压低,这就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得以延续。以汇率为例,长期以来,我国选择将出口和外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外贸战略上配合出口导向战略。这一战略的重要特征即以人为压低要素成本和人民币汇率为基础拉动出口。
从微观经济方面来看,在人民币低估的政策庇护下,出口企业由于没有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充分压力,往往表现出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动力不足。这进一步鼓励了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削弱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而出口以外的部门则很可能长期维持在欠发达的层次上。
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出口导向战略和投资驱动增长模式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中国经济内部结构失衡的表现之一是拥有庞大的国内储蓄和固定资产投资。储蓄率过高直接表现为银行体系资金过剩,这又引起货币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行业产能过剩,而国内市场又无法消化,结果就是出口快速增长。因此,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很容易形成投资和出口相互依赖的恶性循环。从更深层面上看,出口高于进口的快速增长使得我国顺差不断扩大,造成了巨额贸易盈余。虽然自2008年8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意愿结汇制,意味着外贸企业和商业银行有权不向央行售汇,可以自留、自用外汇,或者售汇给自己的客户和存款户。但是实际上,无数出口企业挣来的美元结汇给了商业银行,而后者还是把绝大部分外汇卖给了央行,因为央行购汇的出价最高。在人民币稳定汇率目标的硬约束下,央行不得不动用基础货币大手购汇:一方面,中国物质形态的产品过剩转变为价值形态的外汇储备过剩;另一方面,央行不得不吐出大量基础货币用于购汇,对内就转成越来越多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货币超发可能形成三种局面:一是房地产、证券、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膨胀,形成“资产泡沫”;二是一般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即“通货膨胀”;三是两者兼而有之。无论是哪种情况,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都会进退两难,如果处置失当甚至会使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从实际效果来看,“价格扭曲”鼓励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支持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弱化了培养内需的动力,也削弱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
二、破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性障碍的对策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手段。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意图不仅要突破传统的经济体制,还要冲破其他各种旧的僵化体制,直面破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体制性障碍。
(一)回归公共财政
一是调整和优化政府的支出结构。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其核心意思是按公共产品的性质属于全国还是地方来重新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只有地方财政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得到解决,地方政府才能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二是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重要手段。如果解决了基层政府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不匹配的问题,一些地区的地方财政仍然入不敷出,就应当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弥补。
公共财政不可能彻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最基本的支出应该相对平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矫正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机制
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土地、劳动力、技术等,与之对应的价格即利率和汇率、地价和地租、工资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绝大多数商品和工业生产资料已经实现了计划和市场并轨,最终完成了向市场形成价格机制的转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价格改革向要素市场推进的条件已经成熟,在生产要素配置上也应实行单一的市场价格制度。
一是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双轨制,尚未完成从双轨到市场的并轨,政府仍旧严格控制着资金的价格和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育和成熟,要逐步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实行人民银行调控下的市场利率体制,使利率能够灵活浮动,真实反映货币市场和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同时,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使人民币汇率能够真实反映国内外汇供求状况以及国际货币变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目标。
二是改变级差地租的分配模式。在“农转非”过程中,适当扩大政府征地所得对农村和农民的补偿,逐步拿出更多资金返还给农村以保护耕地和整治土地,从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中固定一部分资金用来保护耕地和开垦新耕地,并将其作为硬约束。提高征地所得的返农比例意味着增加征地的成本,这有利于为大规模利用市场机制、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有限的转让制度、充分发挥级差地租规律创造条件。[4]
三是完善工资形成机制。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工资形成机制也要相应转换,要更多地由市场调节,使工资能够反映劳动力生产率和供求状况的变化。[5]要素禀赋结构是不断升级和变化的,因此要素价格也是随之改变的。如果某种要素相对丰富,它的价格就会相对较低;相反,如果某种要素相对稀缺,它的价格就会相对较高;如果某种要素的积累速度快于其他要素并从相对稀缺转为相对丰富,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从相对较高变成相对较低。我国资本的快速积累逐渐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同时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转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生产方式也会逐步从劳动力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这个过程中反映在要素价格上就体现为收入分配逐步向劳动力倾斜,工资不断上升。[6]此外,信息价格、技术价格等也要真正放开,要在市场竞争中形成。
总之,要把生产要素定价权还给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应由它们本身的稀缺度而非由行政官员决定。只有矫正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才能消除寻租腐败行为的制度环境,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让各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最终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
(三)巩固产权制度基础
财产制度是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全社会的财产都属于国家所有。这种公共占有的情况无须也无法对产权属于何人作出界定。改革开放后如果产权界定仍然不明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因为市场关系即不同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换关系,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改革原有的产权关系,对产权作出明确的界定。
一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自1978年以来一直是每年的改革重点。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一般都采取公司制的形式,看起来好像是产权明晰,但是由于国企的领导人既是经营者同时也是所有者的全权代表,真正的所有者并不在位,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也无从建立。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国资委作为国企的股东,必须严格监督和约束国企经营者。如果企业经营不好,可以对其经营者进行必要的惩罚;如果企业仍然没有改善,可以让其他企业收购之,甚至让其破产。
二是落实农民的土地产权。长期以来,正是因为农村土地产权不落实,农民缺乏对保护耕地和改良土地的热情。更大的问题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土地屡屡被随意滥占、乱卖,农民往往无法从土地转让中获得应有的补偿。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只有妥善解决了农村土地产权问题,才能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
(四)建设有限、高效政府
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要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为“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企业、商会和其他社群组织。
一是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这是避免政府“越位”问题的核心。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权力和职能有限的政府,这与计划经济中的全能大政府显然不同。在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失灵且政府干预确实有效这一例外,其他任何情况下都要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直接干预市场和企业的微观决策的权力。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发挥基础性作用。
二是履行政府应有职能,建设高效政府。政府把自己不该管的事交出去并不等于政府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能,实行“无为而治”或者无所事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需要政府低成本地履行以下几方面的职责:通过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公平;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酌情使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加以弥补。我们各级政府只有开明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才可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3-11-08.
[2]陈佳贵,刘树成,等.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J].经济研究,2008,(10):4-15.
[3]葛新权,杨颖梅.我国经济转轨期软预算约束与通货膨胀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3):17-18.
[4]周其仁.重视成都经验探索城乡统筹——在成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N].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07-03(5).
[5]马凯.积极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J].价格理论与实践,1994,(1):17-18
[6]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3-236.
(责任编辑:许桃芳)
System Obstacles and Policy Advices on Deepening Our Economic Reform
LIU Xiao-ling
(Economic Department,Communist Party's School of XiangTan,Xiangtan Hunan,411100,China)
In our country,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economic reform,there are four major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the government intervening in market",budget constraints soften and price distortions.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we should anchor the goal of market reform orientation.While through the regression of public finance,correction factors price distortions,consolidating the property right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limited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we can solv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of our economic reform and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system reform;double-track pricing system;institutional obstacles
F121
A
1672-626X(2013)04-0011-05
10.3969/j.issn.1672-626x.2013.04.002
2013-05-22
刘晓玲(1981-),女,湖南湘潭人,中共湘潭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