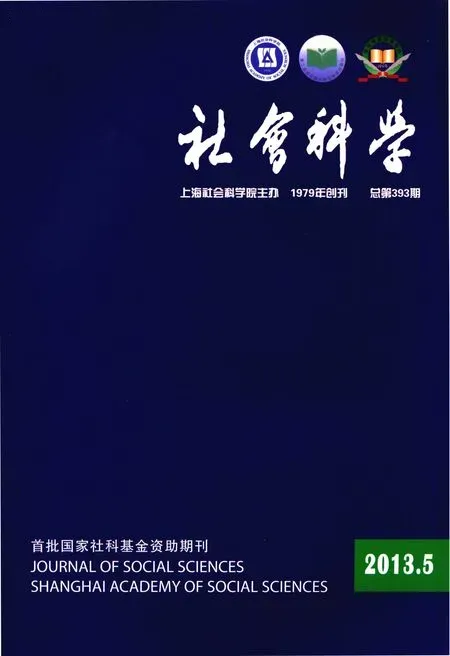比较政治研究议题的设定:从何处来
朱德米 沈洪波
从20世纪50年代比较政治学出现、繁荣到今天的持续稳定,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具有身份标志的二级学科已经存在六十多年了。它与政治理论、政治方法论、美国政治、国际关系等并列成为美国大学政治科学系的标准的二级学科设置。研究生的培养和教授职位都清晰定位为比较政治学。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方向,乃至比较政治学的定义本身,还存在一些富于争议的命题。是不是在美国以外的政治研究都属于比较政治范畴?还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称之为“比较政治”?比较政治属于方法论还是本体论?比较政治是否会因其在政治学领域的“无处不在”而使学科发展走向一种“虚无主义”?比较政治是否有明确的学科研究对象?它的研究议题的设定具有什么规律性?本文将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1983年至2007年间比较政治研究议题的演变进行分析和归纳,并结合最新出版的《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和回答。
一、比较政治:方法论还是本体论
分析比较政治研究议题的设定,需要对比较政治的本质进行界定。在方法论与本体论之间,涉及到对比较政治的认知与定位。一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此存在着持有不同立场的两方。
一方面,从方法论者的角度来看,以霍尔特和特纳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比较是研究和分析的方法,但不是实质性的研究领域”。在他们看来,“严格地说,在同一社会中,进行文化比较和行为比较在本质上没有差别”①Holt and Turner(eds.),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Research.New York:Free Press.1970.pp.5-6.。由此,关于比较政治学的4个主要理论框架——系统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发达与不发达理论、阶级理论之间就没有本质的划分界线了。在方法论者看来,比较政治只是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是人类认识未知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比较政治的独特性来自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其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规定了自身的特殊性,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沿着这样的思路,政治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都可以成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当比较政治“无处不在”的时候,也就无从探寻它的学科规律性了。
另一位方法论者的代表人物查尔斯,在他的《目前我们都是比较主义者——国别研究学者为什么必须以及如何采用比较政治方法》一文中,强调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对于国别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对目前的政治学者来说,国别研究者的出路在于转向比较研究的综合与转化,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必定要在国别研究中被采纳。无论美国政治、欧洲政治还是中国政治,离开比较政治,单一的国别研究将呈现碎片化,而比较研究能够使国别研究增加深度与精确度。在比较研究与国别研究的内在关系上,他强调,虽然“国别研究可以从比较研究的经验和理论中受益”,“比较研究能够拓展国别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但比较政治只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在国别研究发展的道路上,是可能进一步拓展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空间的”②Charles Lees,We Are All Comparativists Now-Why and How Single-country Scholarship Must Adapt and Incorporate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roach,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6,Volume 39,November 9,pp.1097,pp.1105.。可见,从学科界定上看,他更加倾向于国别研究。
方法论者认为,比较政治应该作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而存在,如果将其作为本体论来看,它将成为无所不包的比较政治“帝国主义”,自然陷入比较政治“虚无主义”的误区。比较政治方法在世界政治和国别研究中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它也为国别研究开辟了方法多元化的路径。
另一方面,从本体论者的角度来看,方法论者的强力论证不能改变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20世纪,比较政治已然发展成为了政治学的一个特殊分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领域的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比较政治的发展脉络与它的学科特点。至今,给比较政治下一个定义仿佛仍然很难,但比较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它与所属的一级学科具备相近的理论基础;它具备三个主要的学科要素 (比较方法、民族国家和经验科学);形成了基本的研究框架,具有了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从学科基本架构来看,美国政治学主要由政治理论、美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方法论等来构成,比较政治赫然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二级学科出现并受到广泛重视。
比较政治作为研究本体的出现,并非偶然。在理论上,它历经了从行为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再到一般性理论的更迭;在现实中,它经历了战后经济复苏到经济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再到全球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发展。它作为研究本体的出现,是一种实然与必然现象。按照米勒的观点,“经济学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渗入无疑增强了比较政治的影响力并为其研究拓展了新的大道”③Gary Miller J.,The Impact of Economics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1997,no.3:1173-204.。按照布朗迪的观点,当人们意识到世界政治的“全球整体框架不能够为政治学科中探索人类的本质提供支撑基础”的时候,相形之下,“比较主义虽然被认为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和静态不变两个方面的缺陷,但它至少能够让人们观察到真实的世界正在发展的事物”④Jean Blondel,Then and Now:Comparative Politics,Politics Studies,1999,XLVII:158.。如是观点肯定不能完全解释比较政治作为一个学科本体的出现,但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比较政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学的一个特殊的分支兴盛发展起来。当下,对于比较政治的本体论者们来说,更为迫切需要证明的,应该是:庞杂的比较政治是否有学科明确的研究对象?作为独立的学科,这个研究对象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区别及研究规律体现在哪些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文献的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比较政治研究议题的演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与比较政治相关的研究议题相继涌现。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研究议题、研究理论不断丰富,也在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本文将通过对3篇比较政治研究的统计分析文献——李·西格曼与乔治于1983年发表的《现代比较政治:总体考量与评估》①Lee Sigelman & George H.Gadbois Jr.,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Politics:An Inventory and Assessment.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83,16,October,pp.275-305.,艾德里安在1999年发表的《比较政治学:自1980年代的总体考量与评估》②Adrian Prentice Hull,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An Inventory and Assessment Since the 1980's,Political Science March 1999,pp.117-125.,赫拉多尔·蒙克与理查德·斯奈德在2007年发表的《讨论比较政治的方向:基于主流杂志的分析》③Gerardo L.Munck& Richard Snyder,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7,Volume 40 Number1,January.pp.5-31.——的研究与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与比较,探索比较政治研究议题的变化及变化的规律。
1983年,李·西格曼与乔治在《比较政治研究》杂志发表的《现代比较政治:总体考量与评估》是基于1968年—1981年的比较政治研究的统计分析文献。文中,将这些年间发表在《比较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分类 (按照理论架构、经验和地区政治)与量化统计。这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学的第一份评估文献,为后来的比较政治研究的考量与评估奠定了基础。
1999年,艾德里安在西格曼与乔治的研究基础上,在《政治学》杂志发表了《比较政治学:自1980年代的总体考量与评估》,基于1982年—1997年在《比较政治》、 《比较政治研究》、《世界政治》发表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以是否涉及以下三个研究框架之一:理性选择、文化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为标准,并借助SPSS等软件资源来分析已经获取的资料。显然,他的统计分析在西格曼与乔治的分析基础上增强了科学性。
2007年,赫拉多尔·蒙克与理查德·斯奈德在《比较政治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讨论比较政治的方向:基于主流杂志的分析》的文章,基于美国的3个主要杂志《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和《世界政治》1989年—2007年的文章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分析了比较政治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联结、理论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的缺陷、未来的发展方向。力图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充分地结合起来,以解释比较政治是怎样的一门学问。
以上3篇文章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研究统计分析的代表性文献。为了对比较政治的研究议题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对上述3篇文献中的部分统计数据进行了整理,分别选取了1983、1999和2007年的研究议题进行排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比较、分析:
1983年,比较政治的分析议题 (substantive focus)主要有28个和其他类:包括发展、政党、政策、投票与选举、稳定/不稳定、研究方法、精英、意识形态、非选举参与、次国家政治、援助—效益、民族—多元主义、一般政治行为、社会化、行政、国家整合、军队、立法、利益团体、执行、国际、外部影响、宗教、信息—沟通、分离主义、殖民主义、法院、宪法和其他类。
到了1999年,比较政治的研究议题 (substantive focus)已经有32个和其他类:包括发展、政策、政党、国家—社会关系、投票与选举、民主、民族—多元主义、利益团体、稳定/不稳定、国际、信息—沟通、非选举参与、精英、社会化、外部影响、性别、军队、研究方法、立法、环境、执行、意识形态、行政、法院、国家整合、宗教、次国家政治、援助—效益、政治行为、殖民主义、分离主义、宪法和其他类。
将1983年与1999年的研究议题进行比较,主要的变化在于:(1)1999年的比较政治研究多出了4个议题:国家—社会关系、民主、性别、环境;(2)两个年度相比较,前10个议题发生了变化:1983年的前10个议题为发展、政党、政策、投票与选举、稳定/不稳定、研究方法、精英、意识形态、非选举参与、次国家政治;到了1999年,前10个议题变化为:发展、政策、政党、国家—社会关系、投票与选举、民族—多元主义、利益团体、稳定/不稳定、国际。
到2007年,比较政治的分析议题 (substantive scope)已经包括25个主题和其他类,由5个主要论题组成,分别是:(1)政治秩序:包括国家构建与国家崩溃、战争、环境、民族主义、内战与暴力、民族与民族暴力;(2)政体:包括政体多样性、民主化与民主崩溃;(3)社会行为体:包括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 (含社会资本、社会抗议)、利益团体 (含企业和劳工组织)、公民态度与政治文化、宗教、庇护主义;(4)民主与国家制度:选举、投票与选举制度,政党、民主制度 (行政、立法)、联邦主义与分权化、司法、官僚、军队与警察、政策制定;(5)经济与跨国家进程:经济政策与改革 (含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多样性)、经济发展、全球化、跨国家整合及进程。
2007年研究议题的排序为:(1)按照研究主要论题的排序为:民主与国家制度、经济与跨国进程、社会行动者、政体、政治秩序;(2)按照研究具体论题排序 (前10位)为:经济政策与改革、民主化与民主崩溃、政党、利益团体、公民态度与政治文化、政体的多样性、选举、投票与选举制度,政策制定、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民主制度。
比较2007年与1999年研究议题,主要变化包括:(1)出现了全球化、社会运动、民主化与民主崩溃等新议题;(2)研究议题排序上出现了变化 (见上),经济议题地位飙升,公民态度与政治文化、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民主制度取代民族—多元主义、稳定/不稳定、国际问题,进入主要议题之中。
以上比较分析结果,与近三十年来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200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查尔斯·波克斯 (Carles Boix)和苏珊C.斯托克斯 (Susan C.Stokes)主编的《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该手册是对国际范围内比较政治学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和归纳的“百科全书”。他们开宗明义指出:“为什么权威主义国家要民主化?如何解释民族—国家的外形、变化的动力和意识形态?在什么样条件下爆发内战和革命?为什么在当代民主体制下政党是政治代表的渠道?为什么有的政党运作政策项目,有的政党却关注人际关系?公民能否通过选举和司法机构来使政府负责任?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是比较政治学所要回答的。”①Carles Boix,Susan C.Stoke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根据这个判断,比较政治学应当有着明确的研究议题,因此具有本体论的特征。《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共分为7个议题:理论与方法,国家、国家形成以及政治同意,政体及其转型,政治不稳定、政治冲突,民众政治动员,政治需求的应对,比较视野中的治理。手册按照两个原则来编写:一是学科的理论进步与创新,二是体现出比较方法。其言下之意是比较政治首先应有研究的核心议题,这样在政治科学“家园”里才有存在的必要。研究议题的相对稳定有助于学科的创新和进步,同时也避免了比较政治学沦落为“为方法而存在”。接下来的问题是比较政治议题的设定:从何处来?
三、本体论比较政治:在政治与科学之间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本文试得出的结论是:比较政治作为本体论,它有着长期关注的议题,表现为现实政策发展的需要,体现着政治学追寻人类美好生活与科学精神相统一的使命。比较政治研究议题从以美国以及发达国家以外的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为对象逐步演变为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再到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放到同一框架下比较。比较政治学正在实现其目标。
1.比较政治有着长期关注的研究议题,具有持续性,为本体论
比较政治研究议题的变化与比较政治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比较政治的发展历经了两次革命:行为主义革命和科学主义的革命。比较起来,行为主义革命侧重于比较政治行为的社会性,而科学主义革命更侧重于用经济学等理论来植入科学的方法①Gerardo L.Munck & Richard Snyder,What Has Comparative Politics Accomplished?APSA-CP.Newsletter of APSA Organized Sec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2004,15(2),pp.26-31.。本文中分析的3篇文献恰好是对两次革命前后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统计与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关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比较政治已经有了诸如发展、政党、政策、投票与选举、稳定/不稳定、民族主义、宗教、国家—社会、经济改革,等等数十个可持续的研究命题,对这些命题的长期关注,使比较政治的发展成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比较政治学也随之作为学科本体取得了广泛的发展。
通过对3篇文献的分析,我们也看到,比较政治的研究议题在不断增多。在政治学一级学科领域范围内,比较政治仿佛已经“无处不在”,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在笔者看来,比较政治的“无处不在”首先源于比较政治方法的普遍应用。政治学的很多概念只有在比较和对比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并得到恰当的使用。还因为,比较政治学似乎没有特定的研究内容,它时常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出特定的兼容性。并且,比较政治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或者至少应当是独立的政治体系,所以现代的比较政治学时常被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但是,以民族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把国家和政府作为考察对象。在比较政治议题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我们看到,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国家总体框架与情境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单位,无论群体、组织还是个人,都已纳入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之内。但这些不能是比较政治作为方法论存在的原因。
从研究本体的角度来看,比较政治的本体研究已经具备相对稳定的研究内容,并且研究有可持续性,不同政体、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实践都为比较预留了空间,政治学研究内容的比较早已超越了方法论本身。所谓方法论者,是用来探求一种认识事物的普遍方法。这种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是原则性的,是可操控的、有趋向性的理念。而所谓本体论者,是对事物的本质的追求。比较方法只是比较政治的核心要素,而不是比较政治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理性选择与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使比较政治作为本体科学发展更快。这说明,是世界政治的发展需要比较政治的方法来进行科学解释,比较政治并非作为方法论而表现为具有趋向性的分析政治事物的工具。需要强调的是,至今比较政治学仍然在不断努力探索的,“并不是比较政治对所有未涉及问题的解释能力,而是将人类传统与对其至关重要的科学精神的相互统一”②Gerardo L.Munck & Richard Snyder,The Past and Present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Passion,Craft,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forthcoming.。这是推动比较政治作为一个学科本体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因此,比较政治不会因为其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而走向学科发展的“虚无主义”的误区。
2.新出现的议题或热点来源于多个国家的“共生事件”的影响,有着现实的政策需求
从上述文献分析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比较政治新出现的议题和学界关注的热点,主要来源于多个民族国家的“共生事件”。全球化、社会运动、民主化与民主崩溃等新议题的出现,经济问题地位飙升,主要体现了时代政治的发展变化和其对民族国家影响较为剧烈的部分,也说明了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亟待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释和思考。
那么,是因为新议题的出现需要选择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还是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政治学固有的“理性选择”框架?
的确有这样的观点,政治学自亚里斯多德开始就是比较政治的科学,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政治学的一切领域。对这一问题,笔者试图以经济议题为例加以阐释。前文提到,2007年与1999年、1983年的研究议题相比较,比较政治中经济议题的数量与地位凸显出来。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就已经提出,宏观经济的问题要建立在微观的基础之上,他们倡导从国家经济发展与变化中去理解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行者。但是,他们都没有使政治经济学形成一种独立的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比较政治经济学还只限于大量的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调查,没有将经济理论、政治现象与比较研究直接地结合起来。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伴随全球化经济和合作竞争的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各国都在努力适时调整经济政策以适应快速的经济发展变化。这时,政治经济学家们认识到,“经济政策是属于政治的,因为它影响社会的财富与收入分配。因此,理解政策需要理解在大多数社会利益中的权力分配。经济政策是属于政治的,还因为它影响了一定的制度背景下选举出来的政治家所作的决策”①Alt J.& Crystal A.,Political Econom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33.。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工具与理论结合起来了,如何用经济学的手段来理解政治现象的问题受到了重视,比较政治经济学家们开始探寻政治现象的经济原因,探索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经济对政体的影响。
比较政治中经济议题的拓展,也使规范化模型、博弈理论和经济方法从其固有的经济领域移植到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来②Margaret Levi,The Economic Tur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 N.6/7,August/September 2000,pp.835.。由此,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家必须学习经济的理论与政治学的方法,以至最终人们会发现,比较政治经济学使诸如贸易保护、货币政策等问题不再有明确的政治与经济界限。可见,比较政治不断变化和增加的议题,可以理解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方法的盛行,但在本质上是由于这些新出现的议题或学界关注的热点,来源于多个民族国家的“共生事件”,具有可比较性。民族国家要在对外比较中进一步完善其国内外政策,是属于国家政权、政体、政策发展的现实需求的部分。
长期来看,关系到国家行为体的规范化运作问题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会一直存在。通过比较民族国家在过去与现时政策上的变化及影响,进而探索更加规范的政策,会一直是比较政治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这些问题的研究恰好符合比较政治的三个要素:比较方法、民族国家、经验科学,它以国别政治比较与政策探索为开端,推动着全球范围内的公众讨论和公共政策的不断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治理理论的出现,拓展了比较政治研究的范畴,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同一框架下进行比较研究。诚如《牛津政治学手册》所指出:治理理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领域。
3.比较政治议题的拓展,在政治与科学之间
一直以来,比较政治面临的一个较大的争议,是它的西方中心主义。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比较政治学者较为集中地在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与方法、比较政治的理论产生和经验分析方法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证,仿佛已经形成了比较政治研究的“美国经验”。他们的理论、方法、经验似乎也已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全球标准”。而事实上,比较政治并非源于美国。一直以来,美国比较政治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所占有的比例也并不占多数。从本文中提到的3篇文献对比较政治研究学术论文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已经考察的比较政治研究的文献中,1982年—1997年间,西欧政治占36.3%,东欧政治占10.3%,北美政治占7.7%,拉美政治占18.0%,亚太政治占15.7%③Adrian Prentice Hull,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An Inventory and Assessment Since the 1980's,Political Science March 1999,pp.120.。1989年—2004年间,西欧政治占41%,东欧政治占10.8%,北美政治占17%,拉美政治占27.2%,东亚政治占20%④Gerardo L.Munck & Richard Snyder,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ume 40 Number1,January 2007,pp.10.。我国学者经过研究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之后,发现中西政治发展并不具有完全“可比性”,在比较政治盛行的当下,仿佛中国的国别政治研究被削弱了,而比较政治的框架一时又难以建立与完善。那么,我们如何面对比较政治作为一门西方经验科学的现实存在?
首先,关于学科标准的认识。需要明确的是,比较政治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科学。它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经验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或经验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通过描述、解释和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具有科学性。但是,假使认为比较政治即将成为政治学在全球范围的科学,那也不意味着,比较政治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全球共同目标与任务。比较政治的发展过程已经说明了,比较政治不会有全球标准。
其次,关于学科的理论探索。比较政治理论一直在争议之中,到目前还没有这个领域的权威理论。因此人们一直所做的都是试图讨论如何面对这一现状、如何回答这一现状。也或者,正是比较政治多元理论的竞争避免了任何理论在这一领域中的独大地位①Lichbach,Mark Irving,I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ll of Social Science?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p.152.。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一些人仍在坚定地捍卫行为主义理念的时候,而另一些人则试图从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的交叉领域来探寻研究的空间。通过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到理性选择理论的产生,再到一般性理论,比较政治理论越来越强调在规范科学与经验科学间的平衡,不断增强与扩大比较政治适用的范围。
再次,关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对于中西政治发展并不具有完全“可比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因此而放弃国别政治比较,将民族国家政治的研究孤立于世界政治的研究体系之外。这需要国别研究者弄清本国的政治研究规范与更普遍的规则 (或者说欧美规则)之间的差异。这种总体研究也属于比较研究,它帮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知事物。同时,需要更加灵活地认识与运用比较政治学方法。“比较方法要求研究者不仅仅单一地去利用理论和经验规则,其直接目标是使所研究的问题更为清晰。往往在个案选择上的精心设计会与国别研究更具相关性,且跨学科研究同一事物会让比较政治的学者有更深、更宽的视野。”②Gerring J.,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4,98,pp353.这是否也在启发我们,比较政治学提倡对同一类型事物的跨学科比较,当对同一类型的事物进行国家间比较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试图对其个案进行更精心的设计,而后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或者如此去做,会成为这一类问题的研究出路之一。
4.正在涌现的比较政治研究议题
全球化的推进、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积累,都使今天的比较政治学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从而作出比上一代学者更好的研究成果。时代的大命题刺激着比较政治研究者作出更为宏大的研究。近几年来,社会科学界关注的时代大命题是,在当今,人类社会为什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富国与穷国难道是“命中注定”的吗?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时刻都在刺激着学者的思考。从历史中寻找解释的因素,从比较中发现共同的规律,成为比较政治研究正在涌现的研究议题。2009年—2012年,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比较政治研究经典的3本专著问世,开始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2009年,道格拉斯·C.诺斯 (Douglass C.North)等人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有纪录历史的概念框架》提出,从“社会秩序”(social order)角度来解释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持续繁荣和长治久安。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出现了3种类型的社会秩序:(1)觅食秩序 (foraging order),狩猎时代形成的秩序;(2)限制准入型秩序 (limited access order)或自然状态 (the natural state),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社会处于这种类型的社会秩序;(3)开放型秩序 (open access order),当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富裕发达国家处于这种秩序。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后面两种类型的秩序如何形成,以及为什么有的社会从限制准入型秩序向开放型秩序转变能够成功,为什么有的则失败。他们从暴力、组织、制度和信仰4个概念来理解历史。在限制准入型秩序里,社会人际关系处于主导地位,社会呈现出等级制,中央高度集权,少数人享有结社和统治特权,经济易受各类危机冲击。开放型秩序的特征是政治和经济高度发展,民众普遍享有结社权,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高度分权、社会关系以非人格化为主,法治、自由、产权保护、公平和正义①Douglass C.North,John Joseph Wallis,Barry R.Weingast,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 A Concept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12.。
2011年,著名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的《政治秩序的起源》问世。他从比较的眼光来分析良好政治秩序的形成。他指出:没有比较,无法知道特定的实践和行为对特定社会适用还是对多数适用。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可能把当今世界上类似地理、气候、技术、宗教或冲突的因果关系搞清楚②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pp.18.。良好政治秩序的形成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通过对全球国家的比较,他发现了三类制度安排非常重要:强有力的国家、法治以及负责任的政府。
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 (Daron Acemoglu)和政治学家詹姆士·A.罗宾逊 (James A.Robinson)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的问题,考察了“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来源”③Daron Acemoglu,James A.Robinson,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New York:Crown Business.2012.。他们认为制度是造成国家繁荣和贫穷的最关键因素。制度分为:汲取型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和包容性制度 (Inclusive institutions)。汲取型经济制度的特征是,缺乏法律和秩序,产权得不到保护,垄断导致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运行以及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汲取型政治制度的特征是,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法治、政治家缺乏约束与制衡等。与此相对立的制度类型是包容性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特征是政治制度允许更多的参与、多元主义、法治、权力的约束与制衡等。根据这个分类,可以形成四种组合关系:汲取型经济制度和汲取型政治制度、汲取型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汲取型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在人类经济史上,这四类组合关系都出现过,从而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繁荣或贫穷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汲取型经济制度和汲取型政治制度的组合构成了恶性循环,其结果是贫穷。而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组合构成了良性循环,其结果是繁荣。其他两类组合则构成了短暂的繁荣,不能实现国家的持续繁荣和长治久安。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探讨时代的大命题,寻找一个富裕、持续繁荣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运用了长时段的历史资料、全球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许他们代表了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庞杂、理论繁多的时代里,对比较政治研究议题的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