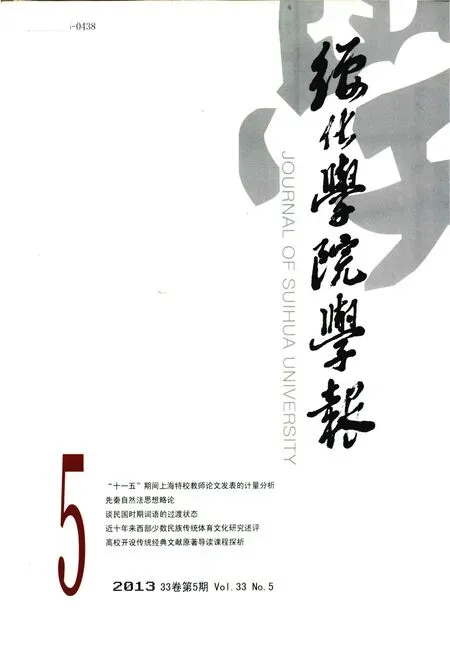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野下文学作品译者身份的探讨
何洪娟
(福建江夏学院人文系 福建福州 350108)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探讨中,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度没有得到正确认识。他们曾被认为是“一仆二主”[1]的仆人,是服务于原作者和译作读者的。还被称作是“速记员”[2]、“打字员”[2],最多也只是一个“匠人,也许只比木匠或油漆工强些”[2]。这些偏颇的看法反映了人们对翻译活动的不甚了解。近几年,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译者不再被认作是对原作者亦步亦趋的模仿者,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接受美学翻译理论就是这些研究发展的成果之一,从这一理论的角度分析,对译者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这种主体能动作用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研究的启迪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诞生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文学批评理论,姚斯和伊瑟尔是这一批评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文本是一个由多层次结构构成的意向性客体,其中包含了许多空白点和未定点。这些空白点和未定点是文本的召唤结构,具有激发性和诱导性。在读者阅读过程中,这种召唤结构会激励读者充分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对文本的未定点和空白点进行确定和填补,由此形成自己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因此,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的本意,它是一种开放性,不断更新的结构,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得到充实和完成的。或者说,文本的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是读者对文本进行积极解读和阐释的结果。接受美学突破了传统文论只专注于作者和作品研究的局限性,将注意力转向以往被忽视的读者与阅读接受的问题,强调了读者在文本意义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参与作用。
接受美学这一理论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传统的艺术翻译理论把忠实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尽力忠实于原文,避免在译文中展示译者自己个性化的语言和行文风格。这实际是忽视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主体能动性。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则将翻译过程程式化、简单化,认为翻译就是两种语言、两种文本之间的一种机械对等转化。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原文成了翻译研究的基础,不仅译者变成了原作者的附庸和仆从,他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受到压制,而且译文读者对译文的能动接受也完全被忽略。将接受美学这一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可以使翻译研究从这种文本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文本的阅读与接受是一种阐释活动,文本意义的产生是读者对文本进行阅读与挖掘的结果。因此,文本的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双重的阅读过程,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原文文本的意义在译者阅读、翻译过程中得到丰富、增补并实现。而译文文本意义的最终生成则依赖于译文读者对译文文本的解读与接受,或者说一部译本的最终完成是通过译本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来实现的。因此,翻译的过程也就不仅仅只是从原作到译者,再到译文的一种机械而单向的转化模式,翻译的过程应该是一种互动沟通的过程,原作者、译者、读者、原文和译文都是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者。接受美学和翻译研究的结合,凸显出译者和译文读者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能动作用。
二、接受美学视野下译者在文学作品翻译活动中的多重身份
(一)译者的读者身份
译者在文学作品翻译活动中的主体能动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多种身份。首先,译者是原文的读者。但是,他不同于一般的读者,普通的读者阅读一部作品时,可以一目十行,跳过自己不感兴趣的章节,也可以不求甚解,不必为某个字词的涵义反复思量斟酌。但是,译者对原文的阅读必须完整而透彻。他要整体把握原文的艺术风格,情趣意旨,体悟揣摩原文隐含的言外之意。译者对原作整体而深入的探索是必须的。因为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每一个阅读文本都充满了空白点和未定点,这些空白点和未定点隐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对它们进行丰富和填充。译者如果没有读懂读透原文,他的这种丰富和填充就可能出现偏差,从而曲解和误读原文,并导致误译和错译的出现。例如:就曾有译者把《西游记》中的一个人物“赤脚大仙”译为red-leggedimmortal(红腿的不朽之神)[3]。他显然没有理解“赤脚”中的“赤”是裸露的意思,而不是指红颜色。所以,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原作深入而细致的研读是确保译文质量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正因如此,傅雷才说,翻译要“事先熟读原作,不厌其祥,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法门。”
(二)译者的研究者身份
1.对原作者及原语文化的研究
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不仅应该是原文孜孜不倦的读者,同时,他还应该是一名研究者。因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原文是一个包含了众多空白点和未定点的文本,任何译者,不管他有多么深厚的译语功底,如果他对原语文化、原作者及其作品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他在阅读过程中就无法对原文中全部的空白点和未定点作出合理而具体的想象。或者说,他对原文中一些微妙的言外之意无法作出合乎情理的理解和阐释。因为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创作,都是建立在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考察和体验之上,是作家自身生活阅历的提炼和升华。所以,要深刻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使自己的译作契合原作的精神风貌,译者不仅要了解原作的创作背景,还要对原作者的生平、经历、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总体的创作风格都进行详尽系统的研究,甚至要阅读关于原作者的传记。正如第十三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一等奖获得者王祥兵在获奖后所感叹的,文本的背景知识比文本本身更重要。
同时,由于文学作品的内容涵盖面广,常常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译者要深刻透彻地理解原文文本,就必须具备广博的原语文化积累,尽量掌握原语丰富的历史、地理、社会风尚习俗等方面的知识,否则,他在翻译过程中会遭遇理解障碍。例如:小说尤利西斯中有这样一句话:“But a lovely mummer! …Kinch,the mummer of them all”,其中的mummer在金版译本中译为“假面哑剧演员”。金如此译法是因为在英国和爱尔兰有一种传统的戏剧式娱乐活动,参与者都戴假面具,这种娱乐活动称为“mummery”。译者如果不了解这一娱乐风尚,就很难确定mummer在原文中的意思。因为mummer在字典中的释义是“哑剧演员”。又如:John can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3].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在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由于天主教徒反对政府,新教徒为了表示对政府的支持,拒绝在每周星期五、即斋日吃鱼,因为根据教规规定,天主教徒在这一天只能吃鱼。因此,“eatno fish”的引申义为“忠诚”。而“play the game”中的“game”有比赛的意思,为了比赛的公平,参赛者都必须遵守比赛规则,因此,“play the game”的引申义为“守规矩”。译者要了解英国的宗教斗争史,才能对这个句子作出正确的翻译。
2.对译文读者的研究
为确保译文的质量,译者不仅要对与原文相关的资料作详尽的研究,同时,还应该对译文的受众,即译文的潜在读者进行研究。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文本的意义是文本与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实现的。因此,译文在被译文读者阅读之前,它的意义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译文意义的最终生成依赖于译文读者对译文的解读与阐释。因此,译文读者是翻译过程最终环节的接受主体,译文必须能被他们欣赏与接受,并激发他们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类似于原文读者的感受和联想,翻译的过程才算最终完成。所以,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对译文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知识范围、思想情感等方面,都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使读者接受并欣赏自己的译文。
当然,这种研究,应该是针对主要的潜在读者群的一种群体性的研究。单个的读者,他们的阅历、性情、喜好各异,对译文的接受能力、理解与欣赏程度也会有差异,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共同受制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体的文化视野与文明水准,因此,他们在语言习惯、文化传统、知识范围、思想感情等这些方面,都会表现出某种群体的倾向性,即某种共性。译者可以依据这种群体的共性,来制定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使译文能顺利地被接受与欣赏。
(三)译者的创作者身份
1.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和阐释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
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是原作特殊的读者,他不仅要读懂和读透原作,还要对原作进行阐释。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和阐释,体现了文学翻译再创作的特点。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文学作品的文本充满了未定点和空白点,这些空白点和未定点使得文学作品的意义具有模糊性、多义性等特点,例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一句独白:To be,or no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这句独白字面意思简单,但内蕴却复杂而深刻。国内外众多的莎剧研究者都对它的真正意义作出不同的阐发,有的认为这句独白是哈姆雷特对生死的一种哲理性的思考,有的则认为这是他对自杀利弊的一种权衡。从莎剧研究者们的各执一词可以看出,译者由于各自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文学作品中的一些空白点和未定点,即作品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很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和阐释。也就是说,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带有一定主观性,并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个人的生活经验、知识背景和审美情趣等主观因素融入其中,因此,这种活动和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再创作。
2.译者对原作精神风貌的传达体现了译者的创作性
译者对原作精神风貌准确传神的传递也体现了他的创作性。在翻译的表达阶段,译者既要尽量准确、忠实地在译文中传达出原文的精神内涵,又要考虑译文读者对译文的阅读感受,因此,这一阶段的翻译实践,要求译者充分考虑两种文化以及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以灵活的方式处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样,他才能译出高质量的作品。例如:霍克斯对对《红楼梦》第二十回描写史湘云“咬舌字”的一段文字的翻译,就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在原文的描写中,史湘云因为“咬舌子”,本该叫宝玉“二哥哥”,却叫成了“爱哥哥”。如何处理这个“爱”字,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在译文中将“爱”字翻成“love”,不仅失去史湘云“咬舌子”的效果,而且会让译文读者莫名其妙,无法理解史湘云为何将宝玉叫成了“爱哥哥”。于是霍克斯在翻译时放弃“爱”字,改用与此字无关的英语本身咬舌音:
原文:湘云走来,笑到:“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不容易来了,也不理我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又该你闹‘爱’三了。”[4]
译文:Xian-yun reproved them smilingly for abandoning her: “Couthin Bao, Couthin Lin, you can thee each other every day. It’th not often I get a chanthe to come here; yet now I have come, you both ignore me.!”Dai-yu burst out laughing:“Lisping doesn’t seem to make you any less talkative ! Listen to you :“Couthin!”“Couthin!”Presently, when you’replaying Racing Go, you’ll be all “thicktheth”and“theventh”![5]
经过霍克斯的调整,原作的精神风貌以新的语言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史湘云“咬舌子”的毛病,她娇憨活泼的形象,黛玉敏捷却不依不饶的个性,以及对话所蕴含的轻松幽默的情趣,都生动地在译文中得以再现。可见,译者要准确传神地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内涵,就不能只拘泥于语言层面机械的对等转换,他要考虑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并进行相应的语言层面的调整,这样产生的译文,充分体现了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再创作能力。
译者始终是文学作品翻译活动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参与者,他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扮演了多种身份,他既是读者、研究者、又是创作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这些身份是一个相互交融的统一体。在翻译的不同阶段,译者必须兼顾这些身份的作用,才能创作出高质量的译作。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53.
[2]俞佳乐.翻译的社会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79.
[3]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2,113.
[4]曹雪芹.红楼梦[M].湖南:岳麓书社,2007:134.
[5]Cao Xueqin,David Hawkes 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0: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