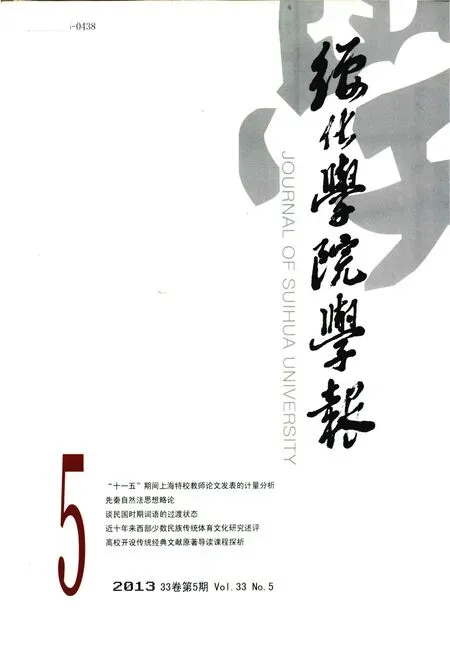先秦“自然法”思想略论——以老子和孔子为例
陈炜强
(北京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1)
人类社会的活动始终围绕着“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和“实际上应该怎样生活”这两个主题而逐项展开。“人应该怎样生活”所隐喻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然性、自然属性,应然性说的是人之为的理想生活;“实际上应该怎样生活”所要深虑的是人之外的一切客观存在条件(其中自然地理环境对其后的一系列条件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它负有前导责任。)实然性讲的是现实制约,而正是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客观环境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文明、风俗习惯、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但是,实然性和应然性又不冲突,人之为人的理想生活只是在不同的现实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了。也就是说,生活、理念是共通的,差异者,方式、概念表述而已。
“自然法”这个概念及其理念就是一例。自然乃自然而然,并非人为之物,且人也是自然之一种,一切自然有其规律和法则,这是中西共通的理念。“自然法”理念在古代中国的“轴心时代”必定也早已有之。孔子和老子的“自然法”思想就是两个典型代表。
一、孔子“天道”之“自然法”思想
那么,作为万物之据的天道是如何运行的呢?《易大传·乾卦》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天寿之属也。”这在强调自然而然之属性。何谓“正”?《管子·法法》云:“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总括起来,天道就是依据万物本来的“性命”在起作用,要使得物各付物,让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自身而存在,而不是干涉和阻碍。正所谓:“率性谓之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庸》)
对于天道之特性,孔子说:“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对此的进一步解释是,“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中庸》)
这是在指出天道的广泛性、恒久性、基础性等特征,而在天道运行时又有“不见”、“不动”、“不息”、“不测”、“不贰”等等特征(《中庸》)。
二、老子“道”之“自然法”思想
老子的“自然法”思想是建立在以道为核心的自然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他的道就是西方的“自然法”观念。
首先,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根本,这与儒家对道的认识是相通的。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人之秩序的运行都是受到道的支配与决定,道是支配和决定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法则。这里的“法”是效法,遵从的意思,“自然”就是万物自然而然的本性。“道法自然”说明的是道支配与决定的方式,即听任万物自由按照其本来的性质发展,没有任何人为或者强迫的成分。在这里,老子并不是说道来源于自然或把“自然”当作一切事物的起点和归宿,而只是说道的运行方式就是自然而然的方式因此,这和儒家的天则、天道观是相一致的,孔子曰:“率性谓之道”,性就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规律。
其次,老子之道的性质。一是道的本源性,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老子说,“可以为天地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四章》)他形象地比喻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六章》)总之,正是这无所不生、无所不有的道,化生和主宰着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二是至上性,至高无上,至大无宗,是万物之主、万物之奥(《老子·六十二章》);三是永恒性,“道乃久”(《老子·十六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二十五章》);四是普遍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七十三章》),即道的网络广大无边,无所不生;五是公正无私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老子·十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不足。”(《老子·七十七章》);六是道运行的客观性,“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它是在“惟惶惟惚”中运行的,“其中有精”、“其中有信”、“其中有象”,即产生了“精”、“信”、“象”。(《老子·二十一章》)
最后,道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状态。有和无是两种基本存在形式,“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当道以“无”表现时,它是“一”、“始”,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当将“道”以“有”之“物”来论时“,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二十五章》),这是说道这个物的本源性,而且是一种“混成”的状态,形象言之“,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二十一章》)老子进一步解释到,它是无形、无色、无形的,即“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餛(音:角),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於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老子·十四章》)总之,“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惟道,善贷且成。”(《老子·四十一章》)这是一种纯粹的宇宙观,大象、大方、大器、大音都是一种意象。宇宙没有边际,万物之生成无法看到它的全过程,宇宙在无声之中运行,宇宙的混成是无形无状的。而道在这个空间中演化生成万物。
三、孔子之“自然法”和礼法的关系
孔子认为自然界及人世间万物都受天道、天则的支配,因此,作为参通天地人、天下归往的圣人必须按照、遵循、效仿自然法则来制定人定法。具体言之,圣人在认知、体悟了自然现象和定则、规律后,就摹仿、效法之,一切器物制度礼俗就被制定出来了。孔子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象生而后有物”(《易传·系辞上》),这说明“象”、“形”都是天道变化之表现,而后有实体之物。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简略地表述为天道、模仿(象)和器物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又集中体现在其对《周易》的阐释中,《易·系辞传》曰:“易也者,象也。”胡适先生就认为孔圣人领悟到了《周易》的真谛,即易也,象也,辞也。[1]
那么,何谓“象”?儒家之变法派管子释曰:“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管子·七法》)简言之,其动词乃模仿、效仿之谓也;名词则包括两种意思:一是自然现象;二是意象。由现象生意象,由此意象推演出他种意象。天地万物之变化无穷,都由简易变繁颐;一切器物制度礼俗都由象演化而来,人类文明史乃诸法象实现为制度文明的历史。而诸意象变动、作用时(卦象)有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现出来(思后面之引语,胡适此辩欠妥,辞以载之,爻以象之更当。),使人动作有仪法标准,使人明知厉害,不敢为非。此《易大传·系辞》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仿效)”。
古代的“礼”便是“道”显现为“象”后经人制定为“物”,即这一具体的人定法。它是道或者说自然法的具体化、实在化、现实化。《礼记·乐记》曰:“礼也者,理之不可者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礼与天地同节。”《仲尼燕居》曰:“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运》曰:“礼也者,义之实也。”这里的“理”、“天地之序”、“天地之节”、“义”都是“道”之“象”。《礼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情。”《礼记·乐记》曰:“厘节民心,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通异,明是非也。”《礼器》曰:“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利,顺于鬼神,合于人心,以理万物者,根本天地之自然法,而制订于具体的,为一切行为之标准,以使人民践履之者也。”
孔子的“自然法”观念更关注人类本性、人道。因此,可以称之为自为法或理性法。孔子从人性、人道出发探究起源,子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天降也,非地出也。”(《中庸》)可见,礼仪皆本于人性,本于人情的。荀子继承和丰富了孔子的思想,他说:“凡礼仪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荀子·性恶》)荀子在这里强调礼仪是由圣人自觉地通过“化性”而制定出来的,不是自然而然由“性”自发演化而来。那么,何谓“化”?《管子·七法》回答的很详细:“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何谓“性”?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谓之性”。(《荀子·正名》)《中庸》曰:“天命谓之性。”这两句话都是在讲人之所以为动物之自然性,人之为动物应遵从的自然法则。但是圣人的礼仪是“化性”,就是要在遵从人之自然法则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人之为人的社会法则。
《礼运》曰:“夫礼之初,始于饮食。”即是“化性起伪”最好的说明。饮食当然是人要生存最基本的、本能的需要,而礼就是在这最初、最基本的需要中产生出来。为了群自我的生存、和谐,天人之间的和谐,圣人必须在饮食过程中“化性”而起“礼”。比如,出于敬畏自然,遵从自然法则之故,把天或神看作活人,举行仪式并给以食物等等,这就产生了祭礼。再比如,在群自我的聚会和宴会等饮食生活中讲究对长者和宾客的尊敬,乡饮酒礼由此产生。
四、老子之“自然法”与礼法关系
“道”、“象”、“物”三者之间关系的阐释,老子和孔子的观点是一致的。老子认为,道在“惟惚惟惶”中成“象”,在“惚兮惶兮”中有“物”,在“窈兮冥兮”中有“精”且“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即在“惟惚惟惶”中先生“象”,再在“惚兮惶兮”中成“物”,而最后在“窈系冥兮”中彰显出种种物质之“信”与“精”。《说文》释曰:“精,择也。”、“信,诚也。”
具体在天道与人道,即“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上。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处无为之世,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即人类最高的德行,就是真正地按“道”行事。总之,人定法要服从“道”。老子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仁义、道德、礼仪、圣智都是违背天道的,主张实行顺应天道的“无为而治”。具体言之,一是要“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反对法令的“多”、“滋”,反对严刑峻法,反对重税剥削,反对滥用刑杀;二是“绝圣,绝仁,绝智”(《老子·十九章》)。因为仁、德、礼、圣智、巧利这些都是违反人性自然的,人的本性就是质朴无私,希望过恬静安适的生活,反对人为的干预。由于老子绝对的崇信自然,推行遵循自然的无为之道,故而有排斥人定法之嫌。在这个日益社会化的世界,最终只能走入“小国寡民”的理想王国之中。
这种有关自然规律、法则的理念,在西方是“自然法”概念,只是逐渐地西方将其“自然法”注入了太多地人之理性。而在古代中国,则表述为“天道”、“天意”、“则”、“道”等诸如此类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差异性表现出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即西方的“自然法”是“理性的普遍设定”,而吾族之“天道”则秉持着“智的直觉”,是“性智的圆觉神悟”。中西在“自然法”这一共通理念上思维方式、表达话语的不同绝对是客观生活环境所致。俞荣根认为,“儒家法思想不是自然法,道家、墨家的法思想同样不能归结为自然法。”[2]这种结论完全是强行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人,而且是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梁治平先生则认为,考据中国古代文献,并无“自然法”一说。[3]这更是无稽之谈,古代中国人怎么可能有“自然法”这样的概念表述。况且这个概念是不仅是现代的、西方的,更是现代中国人翻译过来的。其实,自近代以降,在移植西法中翻译就存在很大问题,如英文 Natural law 最早不是译为“自然法”,而是“天然律例”、“天律之法”、“天然之理”。因此,中西古今概念表述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并不能否定人类共通的理念,也包括“自然法”理念。
老子和孔子代表着传统中国“自然法”思想、理念的两种不同方向,孔子崇信“自然法”而思用之以指导人定法,老子绝对的崇尚自然,从而拒绝一切违背自然的人定法,甚至有排斥后者之嫌。在这样一个日益社会化、理性化的世界,老子的这种理念不可能实现,在传统中国“自然法”和礼法之间的互动就是指孔子思想的实践。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46.
[3]梁治平.法辨[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