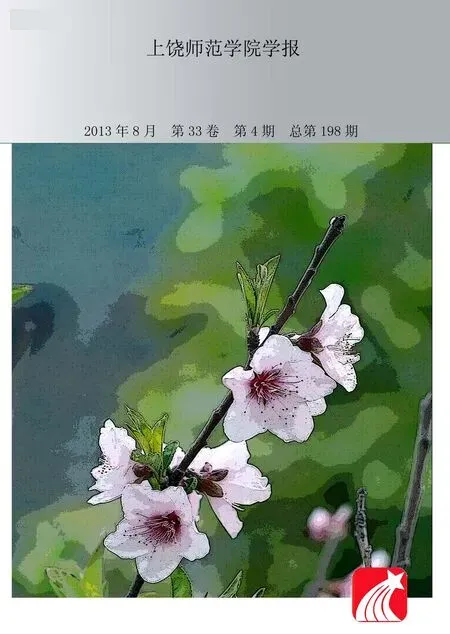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民问题
(上饶广播电视大学,江西上饶334000)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可以得知:“五四”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农民是没有地位的,即便是出现过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作者没有塑造出能完全反映农民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的人物形象,作品中虽然刻画了农民出身的宋江等系列人物,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原始的宗法意识形态的藩篱。至于其他作品中歪曲,甚至丑化农民形象的比比皆是。
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改变了这一局面,农民开始在作品中常作为主人公和正面人物被加以刻画,其中最突出的是鲁迅的作品。他在这时期创作了《故乡》、《明天》、《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反映中国旧式农村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农民形象。这类小说以其思想内容的深刻性,表现形式的新颖独特性为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更为唤醒民众去改造愚昧、麻木的国民性进而去推翻罪恶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一、鲁迅对农民问题的态度
综观鲁迅的小说可以看出他对农民的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是鲁迅对农民态度的基本出发点;“怒其不争”是鲁迅对农民态度的基本归宿[1]。
鲁迅对农民的“哀”,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对黑暗罪恶社会统治下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对农民自身的麻木、愚昧、精神迟钝的哀怜。
《故乡》中的闰土就是作者笔下的一个人物典型。少年的闰土,给人们以美好的记忆,“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那时的闰土天真、活泼、聪明勇敢、机智能干、充满生命的活力。与“我”亲密无间,教我捕鸟,亲密地叫“我”“迅哥儿”。而当“我”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见到的闰土则是:“先前的紫色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向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见到“我”却是“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虽然“我”仍然按照过去的关系叫他“闰土哥”而他却毕恭毕敬的叫“我”一声“老爷”而且要儿子水生“给老爷磕头”,当“我”母亲让闰土仍按旧时称呼“我”“迅哥儿”时,闰土却说:“那时是孩子,不懂事……”把过去的天真无邪说成是不懂事,而现在所谓的懂事是指什么呢?无非是懂得些封建礼教的恶习。多么可悲呀!闰土“都苦得他像个木偶人了。”任他挑选一些带不走的东西时,他除了挑几件应用的家具和草木灰以外,还特别选了一付香炉和烛台,他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神灵的庇护上。而这些反映出闰土这一贫困农民身上存在严重的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和宿命论思想。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农民在“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的折磨和封建观念的侵蚀下承受的深重灾难和人格的伤害。作者通过闰土前后外貌、行动等方面的对比,以强烈的反差给人们以心灵的震撼,同时也流露出他对闰土这样的贫苦农民的深切的同情,深情地希望他们走出一条新的路,希望他们的后辈有“新的生活”。
鲁迅对农民这种精神状态的揭示,更突出地表现在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鞭挞上。
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一个偏僻的农村未庄。他无家无室,贫无立锥之地,只能靠打短工为生。他割麦、舂米、撑船都会做,别人雇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他是一个很能劳动但极端贫困的流浪雇农。
阿Q在物质方面一无所有,但值得一提的,也是他唯一的东西,那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阿Q真是穷得不能再穷了,可是他自己却不肯正视,不想承认,死要面子。和别人争吵起来,他会“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用并不存在的过去,来骄傲于人。甚至到他被抓、被杀时,也没有清醒,认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有时不免要被抓进抓出,要被杀头的。法官叫他在死刑判决书上画押,画个圆圈,这是死到临头了,可他还不在乎,还一心一意地要把圆圈画得圆,争个面子。与这种不正视现实的特点相联系的,就是妄自尊大。别人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偏偏看不起别人,自己来抬高自己,作精神上的对抗。当他与别人打架打输了时,他心里暗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当他挨打了之后还被迫说是“人打畜生。”但阿Q却说:“人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阿Q的这种异常的行为和思想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呀!阿Q的行为和思想越反常就越显出作者对阿Q这一农民身上弱点批判的深刻性。
由于阿Q恋爱的悲剧使他失去了谋生的饭碗,他就怪与他同样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同阶层的小D,认为没有小D,他就没有竞争的对手。甚至见到小D动手便打。再看看阿Q对待革命的态度吧!他认为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抢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不快打嘴巴……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由此可见,农民阿Q认为革命就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成为新的剥削者。阿Q这种愚昧麻木的精神面貌是十分可笑的,从情感上说,作者已从“哀”转到了“怒”。
二、鲁迅关注农民问题的缘由
鲁迅对农民问题的深刻剖析不是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而是深深地扎根于当时的历史和现实的沃土之中的。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鲁迅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与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掌握国家政权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从而使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因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以及不敢去发动广大农民去参与,最终以资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顽固的封建势力依然统治着整个中国。
觉醒的人们都为辛亥革命的到来而欢呼,都为当时革命风云人物而呐喊。鲁迅本人也曾卷入了辛亥革命的漩涡之中。而那些土豪、劣绅、官僚政客们在革命到来时对革命激烈地反对,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甚至对进步力量进行疯狂的遏杀。但一旦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些人便摇身一变,转而去拥护革命,那些“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的,一路的呵!’”于是革命党人便对他们“不咎既往”“咸与维新”了,最后竟同流合污。鲁迅亲眼目睹了这一现象的具体实例:在他家乡绍兴,他认识的革命党人王金发刚进城时,还算革命的,可是不久,就被绅士们和那些投机钻营的“革命党”所包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自己忘其所以,结果是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杀害他战友秋瑾、徐锡麟的刽子手章介眉等被无罪释放,有的竟成为“座上宾”,要求革命并为革命作贡献的人们却成了“阶下囚”。
面对这些惨不忍睹的事实,鲁迅立即从热血沸腾的冲动中冷静了下来,他开始对革命前途感到茫然,苦闷……。但他没有悲观,泄气,他苦苦地思索着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层的社会原因,很快他那敏锐的目光开始搜索社会变革的各种力量,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视的社会的一角,鲁迅目光锁定在“农民”这一社会最底层的群体身上,他通过深刻分析农民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农民具有的反抗压迫的优良传统,从而认识到: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没有农民参加并充当主力军,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鲁迅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祖上家气兴旺,但到他的祖父周介甫时,家庭突变。周介甫因科举作弊案,被关进杭州监狱。家人为买通官僚,设法营救,只好变卖田产,致使家境日衰。作为长孙的鲁迅也因家境不得不辍学在家。后来鲁迅父亲染病,在这样祸不单行的日子里,鲁迅为给父亲治病常奔波于当铺与药铺之间。在这期间,他曾遇到势利眼的鄙视和亲戚的白眼,甚至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体验到世态的炎凉。“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上,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正因如此,鲁迅体验到了生活底层的农民的悲惨与辛酸,与农民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同时,鲁迅的外祖母家在农村,他常借助探亲的机会,从小就交结了许多农村孩子,与他们一起在乡间玩耍,并与闰土等孩子成为挚友。这些生活经历,为鲁迅将来对农民的认识打下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鲁迅早期是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进化论思想是他主导思想,他相信“将来一定超过现在”。他这种认识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是相符合的,当时,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因此,鲁迅还不明确中国革命应当由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尤其是对工人阶级力量没有深刻的认识;他还没有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那时的鲁迅对农民阶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不仅看到了农民身上存在缺点,也发现了农民具有的优秀品德,意识到农民群体的伟大力量,察觉到没有农民参加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鲁迅关注农民问题的目的
我们认为鲁迅关注农民问题的根本目的是引起人们对国民性的关注,进而去改造落后的国民性。
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为了以文为武器,唤醒沉睡的大众。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在他所处的时代,要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就必须面对现实,就必须敢于揭露国民身上的弱点,通过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以引起人们对国民性的关注。[2](P117)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对国民性的改造是以暴露农民身上的弱点为切入口的,从而推及其他群体直至全体国民。鲁迅笔下的阿Q这一农民身上几乎具有所有国民性的弱点,他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封建落后,自欺欺人。其中以“精神胜利法”最为典型。作者对阿Q这一形象的批判是十分尖锐,不留情面的。试想:如不敢揭示疮疤,像阿Q那样习惯忌光忌亮,“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那么中国人民就要继续做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的奴隶,而且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面对当时“漆黑一团”的社会状况,鲁迅认为:“围在高墙里面”的普通百姓,“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3]他希望“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大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农民身上的弱点,不论进行多么深刻的针砭,都是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怀着满腔的热情。他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反对者。他在解剖农民时,也是在解剖自己。
实际上,鲁迅对待农民问题始终是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看到他们身上的弱点,也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
《故乡》中作者在塑造闰土这一人物形象时,对其麻木愚昧的一面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其优秀品德从心底肯定。虽然,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墙壁了,但闰土还是忠于友情的,把仅有的一点稀罕物青豆带来了。说:“冬天没有什么东西,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这样淡淡的几笔就把闰土身上的纯朴、诚挚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我”让闰土选其所要的东西时,他只拣了几样很一般的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付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外加上一堆草木灰。”从中可以看出他多么平实,对别人没有什么奢求。这与小市民阶层的杨二嫂等相比明显不同,杨二嫂一见面就来拉关系,然后就要东西,“‘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又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吧”顺手便将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可见闰土是多么纯朴、善良、高尚。
再看祥林嫂、单四嫂等劳动妇女,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能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祥林嫂辛勤劳作一生,直至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单四嫂也是如此,“她的勤劳在鲁镇是没有人能比的,在深夜鲁镇亮着灯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应酬者聚集地咸亨酒店,另一家便是单四嫂,昼夜纺线。”而这些都是作者在创作时极力肯定的。
综上所述:鲁迅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空前的。他不仅为中国文学画廊中塑造了一系列像阿Q、闰土那样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而且他首次把农民问题与整个社会变革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力图通过对农民身上弱点的揭露,以引起人们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从而去改造整个国民性,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3] 沈从文.学鲁迅[J].知识与生活,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