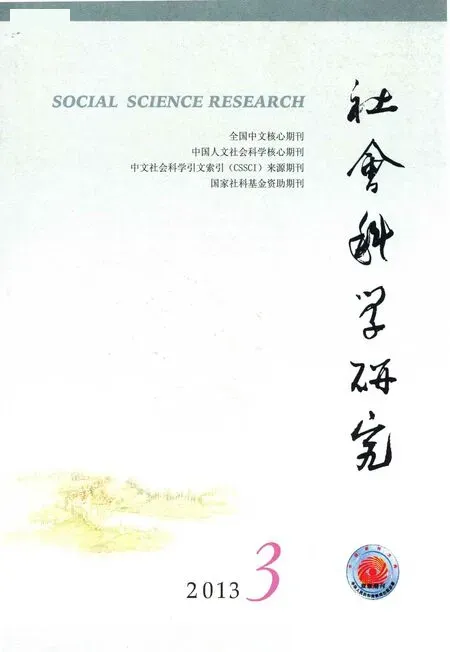定量研究的反思与重构——以语言学为例
李德鹏
一、引言
定量研究是目前学术界非常流行的研究方法,已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认为目前学术界对定量研究理论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定量研究的作用被夸大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提出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朱佩娴也曾说过:“在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时,就需‘三思’而后行。一思是否有必要进行定量研究?二思是否具备条件和能力进行定量研究?三思如何进行科学的定量研究?”〔1〕朱佩娴的文章发表于很有影响力的《人民日报》,但是依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实在令人遗憾。本文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引起学术界更多研究者的关注。我们将从定量研究的概念、哲学基础、作用和方法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并以笔者熟悉的研究领域――语言学为例对定量研究进行反思和重构。
二、定量研究的概念
什么是“定量研究”?很多学者都给出自己的定义,如苏新春认为:“计量研究,又叫定量研究,通过对语料进行数的反映,以达到认识语言规律和特点的目的。”〔2〕赵家祥等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对事物进行数量分析,称作定量研究。”〔3〕唐钰明认为:“所谓定量方法,就是将处于随机状态的某种语言现象给予一定的数量统计,然后通过频率、频度、频度链等量化形式来揭示这类随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规律性。”〔4〕《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定量分析是分析化学上测定某物质所含各种成分数量多少的方法。”〔5〕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定量研究”、“定量方法”、“定量分析”的内涵基本一致,都是指对事物进行数量分析。以语言学为例,确定《现代汉语词典》中义项的数量〔6〕、现代汉语中单音词占多数还是双音词占多数、教材编写中高频词和低频词的界定等等,都需要运用到定量研究的方法。
学术界一般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个概念对举。赵家祥等认为:“在科学研究中,确定事物及其运动状态的性质,称作定性研究。”〔7〕《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定性分析是分析化学上测定某种物质含有哪些成分的方法。”〔8〕以语言学为例,所有概念确立都需要定性研究的方法,如声母、语素、形声字、成语、拟人等概念。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苏新春认为:“在语言研究的历史中,曾出现过经验与哲理、归纳派与演绎派的对立,这就是人们在谈论语言研究时通常会说到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对立。其实,进一步探索会发现二者并不是对立存在的,而是共同在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不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互为支持与印证。计量研究又是定性研究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9〕赵家祥等认为:“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10〕朱佩娴认为: “从逻辑上说,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11〕我们同意朱佩娴和赵家祥等学者的观点: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关系如下:
定性1(前提)→定量→定性2(结论)
前提和结论都是定性研究,从前提到定量到结论,是单向性的关系,不是互为支持与印证的双向性关系。
第一阶段,前提到定量。也就是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以语言学为例,如果要判定一个句子有多少语素,必须先要知道什么是语素,这是基础。
第二阶段,定量到结论。也就是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结果,以语言学为例,黄伯荣、廖序东曾说过:“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占优势。”〔12〕这个论断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定性,这个结论和前提不同,它是通过定量分析得出来的定性。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定性研究不仅是定量研究的基础,还是定量研究的结果。朱佩娴认为:“一般而言,定性研究收集到的‘属性’信息,能回答‘有无’或‘是否’的问题;而定量研究收集到的‘数量’信息,能回答‘多少’或‘大小’的问题。”〔13〕朱佩娴所说的定性研究就是我们所说的前提,而她所说的定量研究收集到的“数量”信息能回答“多少”或“大小”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论。
两个定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前提和结论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从二者的区别上来看,前提是主观的,结论是客观的。前提不需要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结论是要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才能获得。以“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占优势”〔14〕为例,这个结论是客观的,但是这个结论有个前提,就是先定性什么是双音词,什么是单音词。这些定义是主观的,这是二者之间的区别。二者之间又有联系,结论是在前提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如果承认了前提,定量统计过程也正确,就必须承认结论。
从二者的联系上来看,结论是在前提基础上定量分析的结果。如“语素是最小的意义结合体”〔15〕,通过定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他是好人”这个句子里有4个语素这个结论。
三、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
唐钰明说:“任何事物的质都表现为一定的量,量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因此,透过量来把握质,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科学途径。”〔16〕苏新春说:“计量研究认为,事物的质与量有着密切的关系,质存在于量之中,量反映质。”〔17〕唐钰明和苏新春都点出了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质量互变规律。笔者认为,质量互变规律不能作为整个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而且目前哲学界所说的质量互变规律值得商榷。
赵家祥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认为:“量变和质变是辩证统一的。第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第二,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第三,质变体现和巩固量变的成果,并为新的量变开拓道路。量变是指事物量的规定性的变化,即事物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量变一般是不显著的、逐渐的、连续性的变化。质变是指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变化,即事物由一种质态到另一种质态的飞跃。它是突破了事物的度的变化。质变一般是明显的、突发的、非连续性的。”〔18〕但是他们所说的“质变”和“质”是矛盾的两个概念。关于什么是质?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质。质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这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19〕也就是说,事物不同,质不同,两种事物有两种质,那么“质变”就应该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一种事物变成另一种事物。但是他们又认为质变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到另一种质态的飞跃,也就是说质变是一种事物内部的变化,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其论述是前后矛盾的。事实上,一种事物不可能变成另一种事物,例如羊不能变成鱼,桌子不能变成杯子,质变只能是一种事物内部不同状态的变化。赵家祥等所举的质变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事物的量在度的范围内变化,事物不会发生质变,量变超出度的范围,事物就会发生质变。例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温度就是0℃至100℃。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水保持液态,如果温度的变化突破度的两个关节点 (0℃或100℃),水就会变成冰或水蒸气了”〔20〕。他们所说的质变就是H2O这种物质的固态、液态和气态变化,根本没有变成其他物质。所以,我们认为“质”的定义应该修正为“质是事物内部一种质态区别于其他质态的内在规定性”。
我们以“最后一根稻草压死骆驼”为例,首先,不是稻草的量变导致骆驼发生质变,量变和质变的对象必须是同一的,是稻草的量变引起骆驼发生量变,骆驼的量变导致骆驼的质变。我们一般把骆驼的生到死看作是质变,这个质变是同一事物质态的变化,不是骆驼变成了其他动物,另外,这个质变的临界点也是主观设定的,人们往往把感觉不到骆驼呼吸定义为死亡。
以语言学为例,拙文曾经论述过,“‘了’表示从无到有的实现过程。如邢福义认为‘百把斤的猪了,哪能随便卖出去’能说,而‘猪了,哪能随便卖出去’不能说,原因是‘百把斤的猪’是由‘不到百把斤的猪’变来的,有推移性,因此能说成‘百把斤的猪了’;‘猪’不是由别的什么东西变成的,没有推移性,因此不能说成‘猪了’。邢先生所说的推移性,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实现过程,‘百把斤的猪了’能说,就是因为有一个‘不到百把斤的猪’到‘百把斤的猪’的实现过程;而‘猪了’不能说,就是因为不存在一个从‘不是猪’到‘猪’的实现过程,除非是在神话故事中。”〔21〕这个问题也可以从量变质变的角度进行分析,“了”可以用在表示质变的词语后面,但这个质变只是事物的一种质态变成另一种质态,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所以可以说“百把斤的猪了,哪能随便卖出去”,而不能说“猪了,哪能随便卖出去”。
“质量互变规律”的说法给人的感觉是: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引起量变,互为动因,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这个规律还是叫“量变质变规律”更妥切。
前面已经论述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关系分为两类:一种为定性研究是定量的基础,另一种为定性研究是定量的结果。“量变质变规律”只涉及定性2,和定性1无关,“量变质变规律”中的“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和定性2是定量的结果是统一的;“量变质变规律”中的“质变体现和巩固量变的成果,并为新的量变开拓道路”,这个质变也是定性2,是前一个阶段性质变的结果,又是下一个阶段性质变的起点。所以说,“量变质变规律”不能作为所有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只为“量变到定性2”提供理论支持,和“定性1到量变”无关。
四、定量研究的作用
朱佩娴认为:“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统计方法的迅速发展,定量研究方法得到迅速推广,获得了公认的学术地位,‘用数据说话’已成为学术界的时尚。应该说,定量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对于深化研究是大有裨益的。”〔22〕以语言学为例,郭锡良指出:“如果不作定量分析,就很难把握住汉语诸要素在各历史时期的性质及其数量界限。我们的断代描写和历时研究也必然要陷在朦胧模糊的印象之中。从随意引证到定量分析,是古汉语研究为走向科学化而迈出的重要一步。”〔23〕唐钰明认为:“定量方法对研究共时的语言现象意义重大,对研究历时的语言现象也同样重要。我们若能在频率、频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某种历时现象的频度链,那么对揭示这种现象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层次就有重大的意义。”〔24〕苏新春认为:“几千年来汉语词汇的研究传统,都是以具体词语的词义为主要对象,以考释为主要目的,以研究者的主观感悟为主要手段。到现代,虽然重视了对词汇整体的理论属性的探讨,逐渐摆脱了专注于具体词义的考释性研究的旧格局,但在研究手段上却一直没有大的改变,靠的仍是研究者个人的语感,或个人所熟悉的那一部分语料。因此,定量研究方法的引进与推广,在当代词汇研究中有着重要的革新意义。”〔25〕
我们也同意定量分析在科学研究中有很大作用,不过,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合运用定量研究。就语言学而言,专书研究中可以运用,如何乐士的《左传》 《史记》研究、张双棣的《吕氏春秋》研究、毛远明的《左传》研究等。在词汇专题研究中采用这一方法的也相当多。如“词汇的双音化”、“构词法”、“词性类别词”、“语义类别词”等,都是研究相当集中的领域。〔26〕
在汉语双音词的判定中,很多学者把频率作为词和短语之间的划界标准。程湘清说过:“赵元任先生在谈到如何区别词和词组的问题时,曾指出见次频率是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的确,在实际口语中,词的出现频率一般要高于词组,因此在坚持上述三个标准的同时,也可以参考一下词语的出现频率。”〔27〕丁喜霞认为:“人们对于新出现的事物或现象,一般都需要一个逐渐认可和接受的过程,对于出现次数较少或者只是偶见一次的事物或现象,往往会视之为‘异类’,对于词的性质的认定也存在这种现象。鉴于此,我们可以考虑把使用频率作为认定词的一个次要的辅助条件。”〔28〕杨吉春认为:“临时组合的和几千年以来就经常组合在一起使用的反义词组应该是有区别的。”〔29〕笔者认为,按照我们上面的论述,双音词属于前提,是不能通过定量分析得出来的,就双音词而言,定量分析只能得出类似某专书含有多少个双音词这样的结论。短语的使用频率再高也不会变成词,原因是短语和词是两种事物,而量变研究只适用于同一事物的阶段性质变。
朱佩娴认为:“当一项研究只需回答‘有无’或‘是否’问题时,就没有必要消耗人力、物力、财力,非要追逐定量研究这一时尚。特别是一些定量研究在大费周折之后回答的却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而且,如果连‘有无’或‘是否’的问题都没搞清楚,又怎么能回答好‘多少’或‘大小’的问题?但现在一些研究者对定性研究不甚在意,对定量研究却情有独钟,无论什么研究课题一上来就想先贴上个‘定量研究’的标签,以显示‘实证’、‘权威’,却对‘有无’或‘是否’这一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清楚,实际上辛辛苦苦研究的有可能是一个伪命题。”〔30〕朱佩娴所说的定性定量研究和我们上面论述的定性定量研究不太一样,我们同意她所说的“有无”和“是否”的问题是不需要通过定量研究方法来解决的,也就是“前提”与定量研究无关,只有在“前提”基础上的“结论”才需要运用定量研究。美国学者劳伦斯·纽曼说过:“最好的研究常是结合两大研究类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特点的作品。”〔31〕但笔者认为,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需要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以语言学为例,如语素、词、短语、反义词、成语、比喻、拟人等所有基本概念都不需要定量研究,只有语素的多少、反义词的多少等问题才需要运用定量研究。目前很多学术期刊特别热衷于定量分析的文章,似乎一有数字统计,文章的科学价值就提高了,定量研究的作用被夸大了,这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
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原序》中曾说过:“当我作归纳的研究工夫时,常守着一个规则:‘例不十,不立法’。”〔32〕王力认为:“所谓区别一般和特殊,那是辩证法的原理之一。在这里,我们指的是黎锦熙先生所谓‘例不十,不立法’。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就是‘例外不十,法不破’。我们寻觅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不免要遭遇一些例外。但如果只有个别的例外,绝对不能破坏一般的规律。古人之所以不相信‘孤证’,就是这个道理。例外或孤证当然也有它的原因,但是那往往是一种偶然的外因,例如传抄之误。”〔33〕我们认为黎锦熙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例不十,不立法”的意思是说,不到十个例子,不设一条语法规则,尽可能从更多例子中寻找共性,语法规则当然不能一个例子设一个了,这是一种枚举归纳推理,“列举的数量越多,考察的范围越广,枚举归纳推理结论的可靠程度就越高”〔34〕。而王力先生“例外不十,法不破”的观点值得商榷,“例外”只要有一个,“法”就破,这也属于枚举归纳推理,“由于枚举归纳推理的结论是否可靠,关键在于有没有发现反例,因此在尽可能地列举事例后,注意考察一下有无反例是极为必要的。如果有一个反例,就不能推出一般结论”〔35〕。
定量分析还有一个作用是防止犯“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例如,在论述某个事情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举极个别的例子,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大学生回乡养猪种菜成为千万富翁的新闻,似乎每个大学生都能以这样的方式就业、成就一番事业,其实这样的例子不具有普遍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科学的,这时候就需要定量分析来发挥作用,用百分比等数据来说话。
五、定量研究的方法
朱佩娴认为:“强调定量研究需‘三思’,并不是要否定定量研究。事实上,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既要作出‘有无’或‘是否’的判断,又要作出‘多少’或‘大小’的分析,这就需要研究者能恰到好处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起来。”〔36〕我们同意这个观点,定量研究要注意方法。
首先,定性研究是基础。所有的定量研究要有一定的前提,以语言学为例,所有的专书词汇研究,必须搞清楚什么是词,否则结论是不科学的。目前学术界的很多词汇定量研究忽视了这个问题,笔者不揣鄙陋,曾提出了汉语双音词判定的语法意义标准,对现代汉语双音节介词的范围进行了重新计量。〔37〕
其次,公开定量分析过程。要得出科学的结论,前提正确很重要,其次是定量分析过程要正确。以语言学为例,假定双音词的概念是明确的,由于数字统计出错,会导致结论不一。词的判定是语法学界公认的百年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搞清楚了才可以定量研究,这就要求所有的专书研究应该详细展现所有词汇的定量分析过程,有待以后的研究者在新的双音词判定标准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数据修正。所以说,无论前提是确定还是不确定,都是公布定量分析过程。定量分析是自然科学的常用方法,即使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也要遵循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性实验的规律。研究过程只有方便并经得起其他研究者的验证,才是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而目前的专书研究,大都是给出最后的统计数字,部分地列举一些例子,根本无法进行重复性实验,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统计分析必须公布统计标准和统计过程,否则统计结论不科学,这也是目前很多部门的统计数据不能令人信服的原因。
六、结语
通过对定量研究的反思与重构,我们发现学术界有一股很不好的风气,习惯跟风,其根本原因在于对问题缺少深入的研究,对待科学的问题缺少科学的研究态度,这种倾向应该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1〕〔11〕〔13〕〔22〕〔30〕〔31〕〔36〕朱佩娴.“定量研究”需三思〔N〕.人民日报,2011-09-15.
〔2〕〔6〕〔9〕〔17〕〔25〕〔26〕苏新春.词汇计量及实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7,11,9-11,7,9,16.
〔3〕〔7〕〔10〕〔18〕〔19〕〔20〕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9,159-160,157-158,159.
〔4〕〔16〕〔24〕唐钰明.定量方法与古文字资料的词汇语法研究〔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4).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2〕〔14〕〔15〕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7,216.
〔21〕李德鹏.“介词+了”及相关现象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1,(2).
〔23〕郭锡良.1985年的古汉语研究〔J〕.中国语文天地,1986,(3).
〔27〕程湘清.试论上古汉语双音词和双音词组的区分标准〔J〕.东岳论丛,1991,(4).
〔28〕丁喜霞.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87.
〔29〕杨吉春.汉语反义复词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33.
〔32〕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3〕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23.
〔34〕〔35〕南开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逻辑学基础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57.
〔37〕李德鹏.现代汉语双音节介词成词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