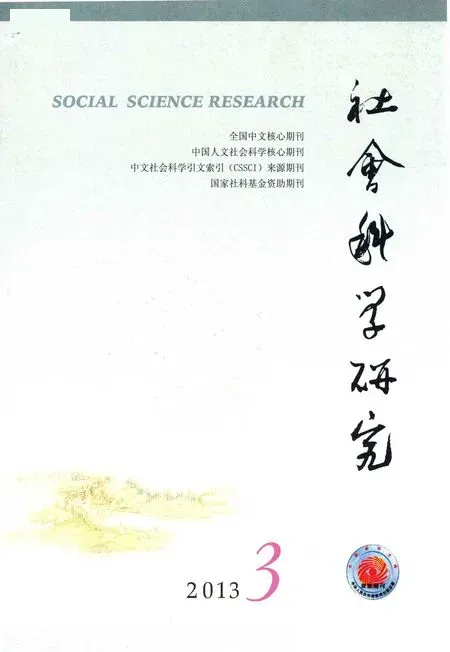迪达勒斯蜡质羽翼的飞地——后现代思想中宗教的复兴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启示
史 静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詹姆斯·乔伊斯对自己成年之前生活的回忆和思想的总结,也是他艺术家的宣言书,预示了更伟大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的诞生。不过,只承认没有《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就没有《尤利西斯》是不公平的,它本身就是一本已然成熟的现代艺术的杰作。
虽然因为乔伊斯的作品数量本来就不多,所以只要谈起他总少不了顺带提到这本书,但是它依然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了,特别是在中国。从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段话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界很出名,我们在大量关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在强调现代后现代艺术的独立性,反对单纯的作家论式的研究,不强调传统作家艺术家的个人感情和主体性在作品中的统治权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艺术家在完成自己的作品之后,就和作品无关了,冷淡地躲在旁边“修剪着自己的指甲”。通过这个比喻,我们似乎确认了解构主义对作者死亡的宣判,那个对作品具有绝对权威的作者似乎就此失去了自己统治作品这个小宇宙的无限的权力。特别是语言学转向给文论带来新风向之后,以无主体的文本观念更使得这个形象的比喻像是出自福柯或者德里达之手。
中国文论界接触到这个妙语起于王岳川和尚水编的一本影响很大的文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中W.V.斯潘诺斯的一篇文章《后现代文学及其境遇》。在此文末尾,斯潘诺斯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观念。作者在此把斯蒂芬·迪达勒斯的观点与新批评派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这是传统的作者具有绝对权威的“极点”:作者在迪达勒斯眼里是:“隐匿的和不可思议的显示全貌的神”。他分析道:“艺术家不明言小宇宙,他本人从世人的瞩目中隐退。他从无比消极的距离之中,从一种理性的肯定之中,漠不关心地修剪他的指甲。”〔1〕这句话出自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韦勒克、杰姆逊新批评并无直接关系,而乔伊斯笔下的这位青年艺术家反对的正是作者的个性和权威。这里很可能是一处误解或者误译,实际上斯潘诺斯此文的论点并不是完全赞同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观,作者虽然也和读者一样被羁绊在时间之中,但斯潘诺斯同意德里达的观点,即使在作者与读者之外还有“以理性的中心的表现逻辑的一种特权”〔2〕,完全没有理性的文本之自由游戏是不存在的。
在小说中斯蒂芬·迪达勒斯谈论他稚嫩的美学理想的时候,说道: “美学的神秘,和物质的创造的神秘性一样,是逐渐形成的。一个艺术家,和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永远停留在他的艺术作品之内或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他已使自己升华而失去了存在,毫不在意,在一旁修剪着自己的指甲。”〔3〕即使是我们把迪达勒斯的说法与后现代的作家观相等同,说他的这个想法强调“非人格化”,但它与解构作家的权威、反对文学的历史研究以及重视文本本身的游戏倾向并没有什么关系。在小说中斯蒂芬受到的反而是托马斯·阿奎那美学思想传统的影响。而阿奎那是不可能反对作者在文本中的权威声音的。这个满脑子塞满自己“根本不相信的宗教”〔4〕的贝尔维迪尔学院的青年大学生的对艺术和美的看法是为了从国家、民族、宗教和家庭中逃脱出来,开辟新的生活道路,而从书中凑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时候别人的思想对他来说就像随买随换的灯盏,他自己的脑袋则像是“装在柳条筐里的一筐水”。〔5〕相对于各种他未摆脱的传统思想,还不明确的艺术则是必须无条件拥抱的理想,在他看来艺术是一个与这些思想的束缚截然不同的新天地,是他怀抱中的“一种还未曾来到这世上的爱”〔6〕的象征。他把艺术分为三种:抒情的、史诗的和戏剧的。这第三种戏剧的艺术就是摆脱情感中心、人格中心的艺术,把自我升华到一种新的境界中去的艺术。这种艺术的美产生于一种新的“神秘性”,这和阿奎那美是完整、和谐和光辉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阿奎那看来“美的最高特性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照来的光,是那物质不过是它的阴影的理念,是只不过作为它的表象的物质后面的真实”〔7〕。这与其说谈的是艺术和美学,倒不如说谈的是对一种崭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向往。这时候,那个修指甲的现代艺术家还没有真正诞生,因为他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创作生涯。很多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对这个艺术家与文本中心观念的联想也并不符合乔伊斯的原意。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迪达勒斯对天主教、耶稣会的感情是复杂的,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对他的思想影响。他身上的问题也是乔伊斯身上的问题。他出生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在童年一直在耶稣会创办的克朗戈斯-伍德中学上学,后来他上的贝尔维迪尔学院也是宗教性很强的大学。和小迪达勒斯一样,宗教思想曾经强烈地震撼过乔伊斯。迪达勒斯甚至一度有可能加入到天主教耶稣会去当教士。乔伊斯与宗教的关系如此密切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学革命时期所无法想象的,没有天主教在乔伊斯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也就不会有他后来强烈的宗教反叛,和文学先锋实验的激进创新。之所以在乔伊斯那一代文学家那里文学理想的地位如此崇高神圣,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文学的天地当成了宗教世俗化以后的一个代用品,而且为了抵抗强大的宗教的力量,这个代用品被无限放大了。我们注意到了“没有上帝之后,什么都可以做”这样一条似乎揭开了现代、后现代美学革新面纱的思想断裂的起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悠久的基督教传统就不在这些文学家身上起作用了。事实上,上帝的缺席,也意味着上帝信仰传统在空缺中更强烈的在场。
在小说中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的朋友克兰利劝他不必认真对待基督教,为了自己的母亲可以假装参加圣餐,崇拜上帝,他回答说: “比那个 (指被上帝打入地狱——引者注)更使我害怕的是,如果我对某一种象征给予虚假的崇拜就可能在我的灵魂中发生那种化学作用,因为在那个象征后面已经聚集着二十个世纪的权威和崇拜了。”“二十个世纪的权威和崇拜”是不可能顷刻间消失于无迹的,它重重压在迪达勒斯身上,让他不能作假,必须认真对待。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对他是一种怎样沉重的思想解放。“我说过我已经失掉了信念,斯蒂芬回答说,但我并不是说,我失掉了对自己的尊敬。如果一个人放弃掉一种合乎逻辑的,合情合理的荒唐信念,却去抓住一个不合逻辑的和不合情理的荒唐信念,那算得是一种什么思想上的解放呢?”〔8〕为了建立起一个更合逻辑、更合情理的新信念,很多西方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同样的,这就提示我们研究文学艺术与思想的同时,对待他们身后“二十世纪的权威和崇拜”的传统的时候要更重视那些不断复活的“幽灵”及其意义。
不过,当我们重新讨论了乔伊斯这个妙语在二十世纪初特定背景下的起源,我们也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它就与后现代美学思想完全无关。从那个站在艺术品和文学作品旁边修剪指甲的艺术家所处的特殊处境来说,它们又是相似的。后现代美学正好就是乔伊斯那一代人的思想从宗教走向世俗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实际上,斯潘诺斯说后现代主义反对的是西方传统权威的声音,不是“以理性的中心的表现逻辑的一种特权”;可是这后一种特权恰恰也是属于西方传统的,甚至更为神秘,它在德里达那里既反对理性的霸权,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中心。否则,作品文本就会完全没有逻辑性,更谈不上什么文本的游戏可言了。那么,这个既反对权威的文本阐释,又使得文本可以理解的东西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一个缺席又同时在场的逻格斯的上帝吗?后现代思想发展到现在,中国人也一路跟踪到现在,我们终于发现它根本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思想根源,它要逃离的宗教的幽灵最终还是重新纠缠了上来。
这一点我们从晚期的德里达、福柯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更别说哈罗德·布鲁姆、利奥塔、特里·伊格尔顿、斯拉沃热·齐泽克、阿兰·巴迪乌、让·卢克·南希、雅克·朗西埃、阿甘本等等思想家了。从左翼思想传统上来说,最早本雅明和布洛赫就已经与宗教纠缠在了一起。他写作《拱廊街计划》时就被马克思主义和犹太神秘主义夹在中间,这不光可以从他的写作碎片里体现出来,也清晰地体现在他与左边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朋友和右边的犹太神秘主义研究者格肖姆·肖勒姆的大量通信之中。在《神学-政治学残篇》等片断中我们可以发现乌托邦与弥赛亚的思想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哈罗德·布鲁姆则在因为《解构主义与批评》一书而被划到解构主义团体之后就一直感到不满,不久就陷进对犹太神秘宗教卡巴拉 (kabala)的研究之中,后来更对美国的摩门教入了迷。到九十年代后期则向后现代思想宣战,写出了挑战性的作品《西方正典》,直接回到了保守主义文化的大本营之中。特里·伊格尔顿本来就出生于天主教家庭,青年时期属于天主教左派的团体Slant,在早期的作品《新左派的教会》〔9〕和《作为语言的身体:新左派神学概论》〔10〕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一直只重视他《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引论》和《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但早在他的名著《意识形态导论》〔11〕中,他就批判性地解析了左翼思想的核心之一的意识形态观念,与左翼的潮流进行了明显的区隔。之后他的作品《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 (有中译本)〔12〕和 《异见者的肖像》〔13〕中的宗教叙事的回归再正常不过。他的新书是西方左派出的一套激进领袖的新传记中的一本《耶稣基督:福音书》〔14〕,直接把耶稣的形象和格瓦拉等革命者等同了起来。澳大利亚的学者Roland Boer这样评论说,伊格尔顿的宗教转向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只是回复到了他早期罗马天主教左翼思想的覆辙之中,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唯物主义的世俗神学观念。在这种意义上他心目中结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成为临时的美学策略。审美的批判性在这里变成了对宗教神性色彩浓厚的作为“震惊的瞬间”的革命的空幻期待,和对组织社会意识和社会力量的实用主义想象。
这种对美学的政治想象同样体现在斯拉沃热·齐泽克、朱迪·巴特勒、欧内斯托·拉克劳、阿兰·巴迪乌等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里。无论他们以前的理论资源是拉康、德里达、阿尔都塞还是福柯,在近期他们都转向西方宗教思想寻求探索的可能性。齐泽克在《论信仰》〔15〕、《易碎的绝对性——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16〕等大量著作和文章中都在宣扬基督教的保守主义与他眼中“列宁主义”的相似性,即调和对革命历史的弥赛亚的信仰和改良的社会进步运动的可能性的信念。同样兴起的还有左翼思想中的圣保罗主义。台湾学者朱元鸿在《保罗复兴:当代基进政治的新圣像?》〔17〕中注意到陶卜斯《保罗的政治神学》〔18〕,巴迪乌《圣保罗:普适主义的奠基》〔19〕,阿甘本 《余留的时间:罗马书评论》〔20〕三本研究圣保罗和《罗马书》的著作在英语世界的相继出版,并对它们所张扬的普适主义理念和弥赛亚思想进行了总结和评论。朱元鸿的敏锐起源于2005年4月14日到16日美国西拉库斯大学举办的以此关于圣保罗精神复兴的国际研讨会,名为“哲学家之间的使徒保罗:主体性、普世性与事件”,旨在讨论圣保罗与普世主义的关系问题,巴迪乌、齐泽克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圣经》中本来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碰到异相,幡然悔悟,成为早期基督教从犹太族传教到向外邦人传教的奠基人。这种建立新信仰、确立新身份和联合新人群的做法一时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新的理论想象的对象。这是面对逃脱象牙塔内的理论困境,重新寻找自我认同的努力,一种新的“激进思想”,并与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激进”一词台湾学界似乎译为“基进”,其实很是贴切,它不是一种社会革命的思想,而更倾向于对左翼基本思想的换血般的变革与演进。《保罗复兴》一文把这种思潮命之为“一场保罗的正典运动”。朱元鸿的讨论似乎不够全面,苏哲安在台湾《文化研究》杂志《“复兴”还是“复辟”?论当前欧陆理论的限度与突破—— 〈保罗复兴〉一文引起的省思》文章中进行了评论,并且同样批判了这种解读古典文本所带来的对新主体、新人民的呼唤和建构,并指之为“西方偏见”和“帝国语言”,并且补充说至少还有利奥塔、内格尔、南希、瓦蒂莫、利科等大量资料。这次在台湾学术界的讨论和批判是深入和深刻的,但同样除了表达了对西方思想界返回文化根源并以此不断加强其自我主体身份的义愤之外,似乎并没有有力的回应。朱、苏两位学者都对这次热潮表示怀疑其实并不奇怪,在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性”的解释里,早就不把它看作一种合乎理性逻辑和日常经验的理论构造,而当成一种不构成主体性的矛盾的主体倾向,只在组织社会力量进行边缘性的、零散的、无中心的社会运动 (同性恋群体、女权主义、少数族裔?)临时性地出现。这次“保罗的正典运动”,可以说是又一次“例证式”的宗教性非理性方式的尝试。客观上讲,它激发了后现代左派关于未来可能性的想象,维系了经过严重政治挫折以后的对革命和进步的信仰,同样也启发了后来的思想探索者。它的复杂的问题意识根植于西方理论的内部,这也就难怪让其他文化中的研究者莫名惊诧了。
其实,陶卜斯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学者,并不是属于“左翼”,这次基督教理论复兴也不光是体现在左翼理论思想界,即使是说左翼的基督教神学倾向也要追溯到黑格尔之后的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去。这方面对后现代思想的指责也是源远流长,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可以从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一书中《科学、政治和灵知主义》以及《灵知社会主义》两文中找到详尽的论述,他把左派思想直接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联系在了一起。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不是它是不是一种“复辟”,而是它的历史和当下的相关性到底在哪里?左派的基督教叙事与右派的“新帝国”叙事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回应?简单的批判只能重新返回到另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之中,不是附和后现代左派的基督教叙事,就是又落入右翼的理论魔障。甚至,我们应该认识到简单的思想左右之分,都是来自西方的宗教分化之后的理论资源。德鲁里在《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21〕中,把现在市面上左右叙事都同归到了后现代的政治之中,他们都高张相对主义的大旗,一个有强烈的教条主义倾向 (指左翼的后现代思想家),一个则走向宗派主义的深渊 (指右翼的施特劳斯主义者)。表面上形同水火,实际上暗通沟壑。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里奥·施特劳斯及其弟子的思想虽然带上了重新阐释古希腊罗马传统的面纱,但同样是以“后宗教”复兴的面目出现的,左右两者都已经西学东渐,成为当下中国学界的热门。对于学习了十多年后现代思想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迪达勒斯在希腊神话中是伊卡罗斯的父亲,他们父子两人发明了一种蜡质的翅膀,并且安装在自己身体的两侧要借他们飞上天空。不幸的是,在半空中,蜡质翅膀被太阳的光芒熔化,最后堕入大海之中。如果我们把迪达勒斯父子脚下的大地和旁边的大海看作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传统的话,那么蜡质的羽翼就是他们后现代的翅膀,在复杂的现实的阳光灼烤之下,理论的翅膀终于还是失去了效力。他们还是回到了自己的陆地和海洋的家园。在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末尾,迪达勒斯就要告别自己的母亲走上反叛的不归之路了。他的母亲对此做了预言,他“还会再回头相信上帝的,因为我的思想总也不得安宁”,“那意思是说,我从罪孽的后门离开教堂,却又要从悔罪的天窗再进入教堂了。不可能悔罪。我这样明确地对她说……”〔22〕虽然西方的迪达勒斯们不可能悔罪,但他们确实又从天窗回到教堂了,以一种仍然西方主义的方式。
从西方思想界基督教复兴的反面启示方面来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后现代思想中宗教的复兴正告诉我们:无论它怎样强调解构中心、打碎逻格斯和重估一切价值,它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西方的思想。第三世界在欧洲中心主义传统那里找不到自我,同样的,在没有中心的、零散化的后现代传统之中也是找不到自我的位置的。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个“自我”被解构和抛弃,它的“空位”就更会像西方的死亡的上帝那样成为一片强烈存在的场地,而且是更容易被西方的思想入侵和占领的“空位”。不能自我言说的“自我”,失去“自我”言说可能性的“自我”其境况比起从天窗回来的迪达勒斯们更为可悲。这个“空位”只能成为西方新思潮的更为空旷无碍的跑马场。后现代思想终于返回到了它的宗教起源之中,那么我们的“自我”难道需要再被这种世俗的西方宗教重新述说吗?我们可以知道的只是:被西方世俗宗教思想述说的第三世界将更让我们感到陌生。纵观现在中国市场上不断高涨的一波又一波重读西方经典的浪潮,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境。我们面对的是否将会必然是一种双重的“空位”的尴尬与失落呢?
〔1〕〔2〕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48,250.
〔3〕〔4〕〔5〕〔6〕〔7〕〔8〕〔22〕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M〕.黄雨石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246,278,211,293,243,283,290.
〔9〕Terry Eagleton,The New Left Church,London:Sheed and Ward,1966.
〔10〕Terry Eagleton,The Body as Language:Outline of a‘New Left’Theology,London:Sheed and Ward,1970.
〔11〕Terry Eagleton,Ideology:An Introduction,London:Verso,1991.
〔12〕Terry Eagleton,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Oxford:Blackwells,2003.
〔13〕Terry Eagleton,Figures of Dissent:Critical Essays on Fish,Spivak,Zizek and Others,London:Verso,2003.
〔14〕Terry Eagleton,Jesus Christ:The Gospels,London:Verso,2007.
〔15〕On Belief,London:Routledge,2001.
〔16〕斯拉沃热·齐泽克.易碎的绝对性——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7〕朱元鸿.保罗复兴:当代基进政治的新圣像?〔J〕.台北:文化研究,2006,(3).
〔18〕Jacob Taubes,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Paul,translated by Dona Hollande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9〕Alain Badiou,Saint Paul: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translated by Ray Brassie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0〕Girogio Agamben,The Time that Remains: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translated by Patricia Dile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1〕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M〕.赵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22〕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画像〔M〕.黄雨石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