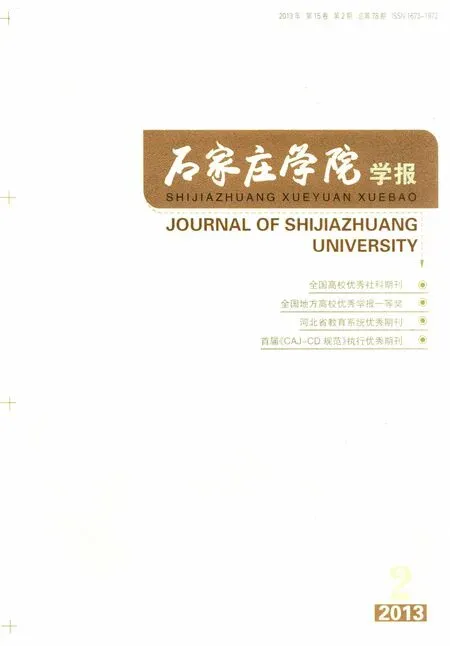秦汉律简“同居”考论
贾丽英
(石家庄学院 历史文化系,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同居,是古代家庭法中一个专门术语,早在清末就已进入律学家的研究视野。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专有《同居考》一节,汇集了汉唐明各代与同居有关的若干法令条文。[1]1325-132920世纪70年代睡虎地秦简出土,又引发学界就秦汉律中“同居”一词的深入探索。那么“同居”与“户”之间是否可以划等号?“同居”包括哪些人?至今认识不一。①唐刚卯认为秦汉时期的同居为“同户籍”(参见唐刚卯《封建法律中同居法适用范围的扩大》,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86页);日本学者冨谷至认为,“所谓缘坐对象的同居,可以解释为户籍上登记的家族”(参见冨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晔译《秦汉刑罚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彭年认为同居包括父母妻子而不包括奴婢(参见彭年《秦汉同居考辩》,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第104-110页);张世超则认为奴婢属于同居(参见张世超《秦简中“同居”与有关法律》,载《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第88-92页);台湾杜正胜认为“同居皆指同户的同母兄弟而言,没有包括他们的子女”(参见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载《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阎爱民认为同居与同产一样“是汉人常用的,以母亲为中心的亲属称谓,而用于律令上的概念,都兼指同母的兄弟”(参见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等等。现今随着三国吴简以及部分里耶秦简的公布,使我们对秦汉三国的户籍原貌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张家山汉简律文中“同居数”这一新概念的出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同居”提供了可能。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利用新出简牍材料,就秦汉同居的涵义、范围,以及同居的法律效力等讲行讨论。
一、同居及范围
(一)何谓同居
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同居”最早出现在秦律中。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可(何)谓“同居”? 户为“同居”。 (简 22)[2]98
可(何)谓“室人”? 可(何)谓“同居”? “同居”,独户母之谓殹(也)。·“室人”者,一室,尽当坐罪人之谓殹(也)。 (简 201)[2]141
简22“户为‘同居’”,即登记在同一户籍上的人称为“同居”。但对简201“独户母”的解释,学界所持观点不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认为是一户中同母的人,国内学者多沿此成说。日本学者佐竹靖彦释“母”为“毋”,通“贯”,“独户母”即“一个户贯”。 冨谷至进一步认为“户贯”即“户关”,也就是门闩的意思。“独户母”就是拥有同一个门闩的居住房屋。而最初的户籍登记以同一住所为基础,因此,“独户母”应指登记在同一户籍上的人。[3]154-156
不过,同籍为同居并不排除没有登记在同一户籍上,但现实生活中同财共居者不为同居。因为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是就某些具体法律提问中的术语进行解释,而不是对某一术语的全面解释。所以,我们推断睡地秦律关于“同居”的释义,并非秦律的完整意义。“同居”一词涵盖的范围可能更广。
而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张家山汉简中除了出现“同居”一词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词“同居数”。《二年律令·置后律》提到死事置后的顺序:
诸死事当置后,毋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毋大父(简370)以大母与同居数者。(简371)[4]59
同产子代户,必同居数。(简380)[4]60
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毋子,其夫;夫(简386)毋子,其夫而代为户。夫同产及子有与同居数者,令毋贸卖田宅及入赘。其出为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户。(简387)[4]61
同居数,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为“同一名籍”,甚是。 因“数”即“名数”,《汉书·万石君传》:“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唐颜师古注:“名数,若今户籍。”[5]卷四十六
“同居数”这一术语的出现,说明“同居”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是同居数,一是同居不同数。比如汉末赵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6]卷二十三。从已公布的三国吴户籍简看,与友人合籍的情况没有见到。笔者推测此三家户籍是分离的,但现实生活中同居通财。类似的情况还有依托型家庭。比如梁鸿“依大家皋伯通”,伯通“舍之于家”[7]卷八十三。当时梁鸿很贫困,推测梁皋两家应同居通财,否则梁鸿不可能“潜闭著书”[7]卷八十三。后梁鸿病死,伯通主持丧葬,“葬毕,妻子归扶风”[7]卷八十三。 《隶释·梁相孔耽神祠碑》载孔耽有兄弟三人,耽是最长者。兄弟三人早年应分异。后文有云“小弟升高,游荒畜积,道富财贫,君引共居四十余年”[8]59。我们不知道孔耽与小弟以后是否合籍,但汉制八月案户籍,所以至少在一个时期之内,他们应该处于“同居不同数”的状态。而“同居不同数”在唐代律令中称作“同居别籍”。《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同居相为隐”释“同居”:“谓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9]卷六
当然,“同居”一词还不仅仅是生活实态上的同财共居,如果在行政上没有分异,即使没有居住在一起,也仍被称为“同居”。我们称之为“别居同籍”。《二年律令·户律》就提到:
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简337)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简338),及道外取其子财(简339)。[4]55
这是家庭不和睦导致的同籍异居。也有因在外为官,与乡村本家自然分居而造成的。如文帝时的廷尉张释之:
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10]卷一百二①近世华北农村惯行社会调查也显示:若未分家,不论是否一起居住,均称为同居。惯Ⅰ296页下段:“因为房子显得狭小而在另外的地方建一个新家,将家族的一部分人转移到那边的时候,这叫做分家吗?=不叫分家。”“叫做分居吗?=不叫做。”“那叫做什么呢?=叫做‘同居隔宅居住’。”转引自[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汉末陈留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议”[7]卷六十下。 “三世”应为父辈、蔡邕辈、子女辈。事实上,尽管这几辈人可能登记在一个名籍之上,但蔡邕的叔父蔡质、蔡邕常年在各地为官,早已成自然分居状态。
笔者推测,或许“别居同籍”不仅存在于官宦之家,随着孝悌观念的深入,“与母别居”[7]卷十八成为不孝罪名,部分人会沽名钓誉,面合而实分。因为户籍上的分异是公开的,而家庭内部的异财则可以做得更隐蔽。当时的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11]393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这种现象。
据上,同居的涵义有两层:一是同居数,一是同居不同数。同居数即登记在同一户籍上,既包括“同居同籍”②2010年甘肃张掖临泽出土的《田产争讼爰书》简册,提到“庶叔三人共同居同籍”(简6298)要(参见贾小军《临泽出土〈田产争讼爰书〉释读及相关问题》,载《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66-71页)。可见“同居数”的概念至西晋已没有了。,又包括“别居同籍”。同居不同数,指没有登记在一个户籍上,但现实生活中却“共居”或“共居业”。
(二)同居范围
从法律意义上,秦汉社会生活中“同居”者都是什么人呢?《辞源》“同居”条:“汉代称大家族中没有分住的兄弟及兄弟之子为同居。”[12]257这条解释的来源是《汉书·惠帝纪》中颜师古的注。原文是:“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颜师古注曰:“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兄弟若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财也。”[5]卷二如果将此解释放入原文,应该是“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兄弟若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
但是如果把这个注放入另外一个例子,就出现了问题。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提到:
吏坐官以负赏(偿),未而死,及有罪以收,抉出其分。其已分而死,及恒作官府以负责(债),牧将公畜生而杀、亡之,未赏(偿)及居之未(简84)备而死,皆出之,毋责妻、同居。金布(简 85)[2]40吏坐官事而负欠,若已死,都可免除,不必责令妻及同居者赔偿。我们将上述颜注中“同居”一词的注释放在此处,就成了“毋责妻以及兄弟若兄弟子等见与同居业者”。那么“父母、子女”又哪里去了?
由此看出,《汉书·惠帝纪》中的颜注并不是对秦汉社会什么叫“同居”的解释,它只是对文本当中出现的“同居”进行就事论事的注释。《辞源》将注释当做解释,无疑是以偏概全。《汉书·惠帝纪》中“父母妻子与同居”是因为“父母妻子”亲近恩重,特单独列出,以示强调。《秦律十八种》简 84、85中“妻、同居”,也因夫妻一体,“妻”的责任大于他人,故列于前。这些人在法律意义上的身份都应该属于“同居”。下面据文献和秦汉简、吴简的材料对“同居”的范围作具体分析。
首先,妻子儿女。一个人最小的亲属圈子应该是妻子儿女,社会学上把这样的家庭称为核心家庭。不论什么时代,由己身与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都是同财共籍的基本单位。秦汉社会也是如此,勿需赘举。事实上,不仅常居状态下如此,即使在外官吏、士卒、服劳役者,甚至减死罪犯,也都妻、子自随[7]卷二,或妻、子在官[13]299。
其次,父母同产。同产,即现在所谓的兄弟姐妹。父母同产既可以同居,也可以不同居。秦简《法律答问》:
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为盗主,且不为?同居者为盗主,不同居不为盗主。(简21)[2]98
既有同居者,也有不同居者。到了汉初,从《二年律令》所反映的父子同产的居住情况就更加清晰了:
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 (简 337)[4]55也就是说祖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等各种近亲亲属关系的同居,不论是分异还是归户,都是法律所允许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可能与成年的兄弟核心家庭在一起生活之外,吴简中发现了与姐姐共同生活的例子3例,其中寡姊2例,推想应该是婆家无人依靠而回娘家生活。不仅是寡居的姐妹,如果是没有人照应的外甥、外孙、外女孙也常会回到“外家”,即母亲的娘家来依托生活。吴简中就有外甥1例,外孙3例,外女孙2例。[14]187-196此类情形在文献材料中也能见到,如朱祐“少孤,归外家复阳刘氏”[7]卷二十二,范升“代郡人也。 少孤,依外家居”[7]卷三十六,等等。
第三,伯叔堂兄弟。汉代典籍中记载兄弟同居共财的不少,但是记载三世共财或三世同居的例子并不是很多,据许倬云先生统计,大约只有4例。[15]384-403但从已公布的吴简看,三世同居共财的家庭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多。比如从吴简中收集到与伯叔父(也称从父、从小父、季父)共户籍的有22例,从兄26例,从弟11例,从兄子2例,等等。有的还提到“侄小妻(简1929)”[16]756,显然是与成年的侄子共户籍。
除了伯叔侄堂兄弟等男性宗亲,在吴简的户籍简中,我们还发现了有4例姑、2例姑子女的记录,其中4例姑中有2例为寡。这种情形似应与寡姐妹的情况相似。
第四,妻系、赘婿及其他远亲。秦汉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从夫居是婚姻生活的主要形态,户内同居的多为父系亲属。但是,现实社会生活千姿百态,而非整齐划一。比如从吴简的统计中我们发现有妻的尊亲属6例,如妻父、妻母、小妻母;妻的同辈或卑亲属,如妻弟10例,妻从兄、妻从弟各1例,外侄子3例,外从男弟1例,[14]187-196等等。
当然,妻系的亲属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庭实态的动态发展,也有渐变为母系亲属的可能。比如我们从吴简中就见到1例这样的户籍简:
亮舅何铁年卌筭一 铁妻大女姑年卅九筭一(吴简贰4655)[16]812
除了从夫居、从女居,秦汉社会还有一种从妻居的风俗,也就是赘婿。从贾谊“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5]卷四十八,以及文帝时诏令禁锢贾人、赘婿等不得为吏,武帝时发天下七科谪[5]卷六等可窥见秦汉赘婿之俗。吴简中也发现明确记载为“婿”的简3枚。
遇到特殊情形,其他远亲也有同居的可能。文献史料中这样的例子常能见到。如汉宣帝年幼时曾归祖母史良娣之家,被祖母的母亲贞君所养。[5]卷九十七上还有曹全“收养季祖母”[17]473,侯瑾“少孤贫,依宗人居”[7]卷八十下,周党“少孤,为宗人所养”[7]卷八十三,等等,都是服属较远之宗亲。吴简中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专族孙仕伍佰(?)年五岁 专中妻大女纯年五十已死(简贰1952)[16]757
第五,奴婢等非亲属。奴婢是否属于同居,一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早年唐刚卯先生曾根据惠帝诏书“父母妻子与同居”一语,“推测汉代‘同居’有所专指,即是包括亲属以外的奴婢、客等”[18]76。但唐先生的结论曾被学界所批驳。彭年先生撰文 《秦汉“同居”考辨》认为奴婢不为同居,“问题的关键在于奴婢是否与主人同籍,即奴婢在主人家中是否有户籍。考察秦汉时期奴婢的实际状况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答案是否定的”[19]107。
不过,随着新材料的出土,这个问题可以作进一步研究了。首先是奴婢的户籍问题。2003年公布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发现了多支奴婢的户籍简。奴婢如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被附于户人简的后面,诸如:
温户下奴李年十四(吴简壹8892)
温户下婢钱年七十□(吴简壹8894)[20]1078
也有不少与户主的其他家庭成员同一支简登记的情形。比如:
孙子男□年六岁 孙户下奴土长六尺 (吴简壹 4141)[20]980
赤妻大女□年六十 赤户下奴银长五尺(吴简贰 2035)[16]759
次弟公乘材(?)年七岁 次户下奴吉长六尺(吴简贰 2217)[16]762
还有记家庭成员总数的简,也将家人与奴一起登记:
右见师佐廿一人兄弟妻子及奴七十八人合九十九人(吴简壹6708)[20]1032
事实上,不仅吴简如此,早在西汉早期奴婢就与主人登记在同一户籍上。江陵高台18号墓出土了甲、乙、丙、丁4块木椟。其中乙本身就是一个向地下官府上报名数的“户口簿”:
新安户人大女燕关内侯寡大奴甲大奴乙大婢妨
家优不算不徭[21]
此种文例与吴简中的“口食人名簿”非常相似。先记“户人”,再记其他家庭成员,最后再对家庭口食、算赋和徭役情况进行汇总。只不过,很多学者更加关注于告地书中奴婢与车马并列的情形,而忽视了此木椟的“户口簿”性质。
比西汉文帝时期的这一户口簿更早的还有里耶秦简,其登记方式也是将奴婢编入主人家户籍。以比较完整的 K27、K30/45 为例:
第一栏: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第二栏:妻曰嗛第三栏:子小上造□第四栏:子小女子驼第五栏:臣曰聚
伍长[22]203
第一栏:南阳户人不更彭奄弟不更说第二栏:母曰错妾曰□
第三栏:子小造状[22]205
当然,奴婢是主人的财产,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秦汉奴婢是“物”的概念还没有固化,在国家法中具有“人”的性质,但他们毕竟不同于家中亲属。他们与主人之间不具备相互扶养、经济偿负的双向义务。同时,“奴婢”与“民”之间在某些同居连坐中被免责。比如劫人罪,“诸予劫人者钱财,及为人劫者,同居(简 72)智(知)弗告吏,皆与劫人者同罪(简 73)”[4]19,但是“诸当坐劫人以论者,其前有罪隶臣妾以上,及奴婢,毋坐为民;为民者亦勿坐(简70)”[4]18。奴婢被单独免责,一方面说明 “奴婢”的同居法律效力与“民”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同居必包涵奴婢,若非,就没有必要把奴婢特殊免责。
除了奴婢,秦汉社会还有一种特殊依附身份的人,与主人登记在一个户籍上。里耶秦简牍K4简有“隶大女子华”与主人一家登记在一块木牍上,排在户主之妻后面。“隶”显然不同于奴婢或臣妾,不是买的。里耶秦简牍中还有一条较为完整的记录:
南里小女子苗,丗五年徙为阳里户人大女婴隶。 (简 8-863+8-1540)”[23]238
此“隶”是徙来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第4例中的女子符“自占书名数,为大夫明隶”[4]94,也非买来,而是自己申报的。显然这些“隶”都与主人家“同居同籍”。
汉末三国吴简中还发现与奴地位相近的一类人,其户籍也可能附于主的户籍之下。这就是“客”。
□休食客五役年廿五刑左足 □客□年十六(吴简壹 7754)[19]1055
弟仕伍黑年七岁 衣食客成年十五刑右足(吴简贰 1842)[16]755
文献中“客皆注家籍”[24]卷二十四最早见于隋,从吴简来看,可能这种情形在汉末三国时就出现了。
除了登记在同一户籍上的人,即“同居数”者,还有未登记在同一户籍,或暂时没有登记在同一户籍,现实生活中却共居、通财的人,即“同居不同数”的非亲属关系者。比如上文提到的各类依养、依托型家庭。在简牍材料中,此类人等或称为“寄者”。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子、卯、午、酉不可入寄者及臣妾,必代居室(简 127背)。[2]225
二、同居法律效力
秦汉家庭法中,同居关系一经法律确认,便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因为不能与现代部门法的法律效力相对应,我们仅从权利、义务以及同居相犯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同居权利
1.继承权
家庭法中的继承权包括两大项,一个是身份继承,一个是财产继承。财产继承一般意义上是诸子平均析产。而身份继承往往以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性别、同居等为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同居不仅使某些身份继承获得优先,同时也是特定身份继承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
首先是死事置后。《二年律令·置后律》:
诸死事当置后,毋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毋大父(简370)以大母与同居数者。(简317)[4]59这里大父、大母即祖父母,如果是以大母为后,必须是“同居数”。如果是同产相互为后,那么也是以同居者为优先。《二年律令·置后律》:
同产相为后,先以同居,毋同居乃以不同居,皆先以长者。(简378)[4]60
其次是代户。代户即户主继承。这一身份继承与是否同居的关系更加密切。比如说:
同产子代户,必同居数。(简380)[4]60“同居数”是侄子能够代户的必要条件。寡为户后,在《二年律令》中没有见到条件的限制。但是到了西汉晚期,也有了法律规范。成帝时期尹湾6号汉墓木牍(6反)有这样的文字:
臣请寡代户者得以同居
毋次以不同居长者代(以上为第五栏)[25]118寡,既寡夫或寡妇。寡夫、寡妇代户,也应该是同居优先。夫妻不同居,在多妻制的汉代社会也是一种常见的婚姻现象。比如齐王刘肥的母亲为刘邦“外妇”[10]卷五十二。 汉律中称居住在外面的“妻”为“为户若别居不同数者”[4]32。估计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寡代户”产生了诸多法律纠纷,才有了“臣”关于“寡代户”同居者优先的上请之辞。
绝户之家,奴婢也可以代户。《二年律令·置后律》:
死毋后而有奴婢者,免奴婢以为庶人,以□庶人律□之□其主田宅及余财。奴婢多,代户者毋过一人,先用劳久、有(简382)□□子若主所言吏者。(简383)[4]61
显然,奴婢代户适用的也是家庭同居法。
2.减免赋役权
高级官吏之同居,可以减免赋役。这条材料见《汉书·惠帝纪》:
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5]卷二
六百石以上的现任官吏,以及那些曾佩将军都尉印及二千石印的故吏,其父母妻子以及同居共业之人,除了交纳军赋之外,其他所有赋、役均免。无疑,这是对高级官吏的优惠政策,是为了重其禄、安其心。
平民的同居,法律也有特殊规定。这主要体现在国家的徭戍律中。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
戍律曰: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简39)[2]89
戍,是指行戍服兵役。如果一家有两人同时行戍,肯定会影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不过,此戍律当为无战事时适用,若战事起,恐怕父子兄弟同时服役的情形不可避免。
(二)同居义务
与现代法不同的是古代法更加强调社会控制,因此就同居关系而言,在家庭法中所见到的同居的义务要远远多于同居的权利。
1.相互扶养
同居的家庭成员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尤其是对老人的赡养和未成年人的抚养。因此有老人、病人、未成年人的家庭,法律不允许他们分户异居。《二年律令·户律》:
寡夫、寡妇毋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癃)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毋(简342)异其子;今毋它子,欲令归户入养,许之。(简343)[4]55
这是对“子”“同居”的强制性规定,同时也是对寡夫、寡妇、幼者、老者、病者所提供的法律保护。
如果儿孙与尊亲属同居而赡养不周,则要被赶出家门,见上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简337和338。
实际上,同居之间相互扶养的义务,不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它也是一种民间自发的互助行为。如上文提到的宣帝、侯瑾、周党、曹全等,或依托外亲、族人,或收养同族孤寡。而吴简中也有不少寡姑、寡嫂、寡弟媳等的户口记录等,都是对同居之间相互扶养义务的一个印证。
2.监督与连坐
古代法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集体责任。[26]562也就是亲属、同居、近邻都负有相互监督的责任。犯有重大罪行的人,其亲属、同居、近邻等都要受到集体性惩罚,古代法称之为连坐或缘坐。
而古代法的这一特征,越是在社会发展早期越明显。 众所周知,商鞅变法之时,著名的“告奸”[10]卷六十八令就已出台,让编户在同一什、伍的百姓相互监督并告发,若监督不力,则相连坐。《二年律令·户律》也这样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简305)[4]51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秦汉家庭法中专门强调同居法律责任的有以下几种。
首先,盗铸钱。盗铸钱是严重危害社会金融秩序的行为,是国家法律打击的重点。“民坐盗铸钱被刑”[5]卷七十二的记载屡见于两汉史。而盗铸钱需要“器具”[4]36,还要“买铜、炭”[4]35,不是一人能够秘密做得了的事情。在法理上同居、伍人、里人有能力监督这种犯罪行为。因此,汉初的《钱律》将这些人的连带责任纳入了律文:
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简 210)[4]35
王莽时期一度“盗铸钱者不可禁”,为了严厉打击盗铸钱,规定“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5]卷九十九中。而同居的连坐责任不会轻于没为奴婢。
其次,劫人、谋劫人。
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简68)[4]18
因为犯罪性质严重,不知情的妻子儿女要连坐为“城旦舂”,如果知情不告,同居者则要处以“磔”。《二年律令·盗律》:
诸予劫人者钱财,及为人劫者,同居 (简72)智(知)弗告吏,皆与劫人者同罪。劫人者去未盈一日。能自颇捕,若偏(徧)告吏,皆除。(简73)[4]19
再次,盗窃。盗窃似乎是上古社会很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秦律和汉律中有专门的《盗律》,用于日常占卜的日书也有《盗者》《盗》等篇章,对盗者的状貌、性别、方位等进行推测。从法理上讲,盗窃罪也是容易被周围的人所察知的,因此秦汉律中盗窃罪也涉及到了同居连坐:
律曰:“与盗同法”,有(又)曰:“与同罪”,此二物同居、典、伍当坐之。(简20)
诸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简22)[2]98
从简20来看,不仅盗窃罪同居要连坐,只要律文中出现了“与盗同法”,都是要连坐同居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事实上,同居连坐的犯罪行为要比我们已知的多。
当然,上述几种犯罪都是可能“居处相察,出入相司”的行为,如果犯罪行为不能被同居、亲属等监督,同居则不需连坐。如秦律中就有一条诬人之罪同居不坐:
甲诬乙通一钱黥城旦罪,问甲同居、典、老当论不当?不当。(简183)[2]1373.经济偿负
同居以同财为特征,因此同居的家庭成员不管在居住实态上是否住在一起,经济利益都是一致的。如果同居家庭成员有在外服役、为吏者,家庭有为其支付正常生活费用的义务。比如睡虎地4号秦墓中的两件木牍,就是在外服役的人向家人索要钱、衣物的家信。一件是黑夫写的:
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中母毋恙也?前日黑夫与惊别,今复会矣。黑夫寄益就书曰:遗黑夫钱,毋操夏衣来。今书节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襌君巾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钱来,黑夫自以布此。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书到皆为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闻王得苟得?
(以上为正面)[27]83
另一件木牍下断残缺,是惊写的,大意也是向家中索要钱、布。兹不赘引。从两件木牍的内容看,黑夫和惊都参加了“淮阳”之战,这期间他们都向家中要钱和衣物。显然,黑夫和惊与衷、母属于同居共财的家庭,他们在战争中获得的军功爵及其相应奖励要归于家庭,同时他们在外面的费用也由同居家庭来负担。
也有同居兄长负责在京为吏的弟弟日常生活用度的。如上文提到张释之,以訾为郎,但10年没有升迁。张释之“欲自免归”,说:“久宦减仲之产,不遂。”[10]卷一百二因为汉代以訾选为郎者,不仅有一定的资财限制,还要自备鞍马、服装、兵器,以及出资供郎署文书财用。“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 ”[5]卷六十六由此可见张释之兄长对于弟弟经济上的支持力度。
既然是同财,不仅平时生活用度由同居家庭承担,遇到经济问题,诸如债务,同居家庭成员的连带责任也不可避免。比如居延汉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就记载了寇恩直接用儿子钦为粟君捕鱼的劳役来抵自己债务的事情,“以钦作(简16)贾谷十三石八斗五升,直觻得钱五万五千四”[28]476。
事实上,秦汉社会同居共财家人的债务担保责任,在契约中就有直接体现。居延汉简中有这样的债务契约:
这份契约的前半部残断,后半部大意是讲在九月份时卖出粮食,双方钱物交割完毕。如果有死亡,其债务由家中现有人承担。
类似的债务契约在居延和敦煌汉简中屡见:
五凤四年六月庚子朔戊□
即使契约中没有写明同居家人的债务担保责任,当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或下落不明时,债权人(方)也会直接找同居家属承负。已公布的里耶秦简中就有12枚追讨戍卒债务的木牍,在叙述完戍卒的负债情况后,紧接着都提到对其家人进行追讨“已訾其家,[家]贫不能入”[22]185-191。 可见,同居家人的债务担保不仅是法律文书的规定,可能已经是社会的约定俗成。
(三)同居相犯
相侵身犯,是指侵害生命、身体以及名誉等的犯罪。同居的相侵身犯比照亲属相侵身犯,刑罚的原则是尊长侵犯卑幼较凡人减轻,卑幼侵犯尊长较凡人加重。同居不是相侵身犯判刑的要件。如秦简《法律答问》有这样一例:
士五(伍)甲毋(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简71)[2]110
此例的判决为“弃市”,与杀害普通人一样量刑。奴婢并非亲属,因同居关系纳入家庭法,与主人的相侵身犯律比卑幼:
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简34)
父母殴笞子孙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简 39)[4]14
不过,同居以同财为特征,因此“同居”在相侵财犯中是定罪量刑的一个要件。同样数额的盗窃行为同居者判刑轻或无罪,非同居者判刑重。上引秦简:
可(何)谓“家罪”?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父已死,或告,勿听,是胃(谓)“家罪”。(简 108)[2]119
参照简106,即父子同居的情况下,子杀伤及盗窃了父亲的奴婢、畜产,父已死,如果有人上告,官府不予受理。
奴婢的盗窃行为,判定为“盗主”与否,也是以“同居”为前提。秦简《法律答问》:
·人奴妾盗其主之父(简20)母,为盗主,且不
为?同居者为盗主,不同居不为盗主。(简21)[2]98
奴婢盗窃主人父母的东西,作为盗主还是不作为盗主?主人的父母与主人同居,就作为盗主;不同居,就不是盗主。而盗主的处罚,在已公布的秦律中没有见到。不过,在家庭法中奴婢的地位同于卑幼,其处罚定比一般窃盗为轻。
三、同居与分异
“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这在后世法律中属于“十恶不赦”之一的“不孝”罪。[9]卷一但秦汉社会因“别籍异财”而获罪的情况却非常少见。正因为分异的普遍性,杜正胜先生把中国古代的家庭分为汉型家庭和唐型家庭,并认为“汉型家庭结构以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甚者‘生分’,老人虽有子孙却无人照顾,自己过家庭生活”[29]45。事实果真如此吗?户籍的别离、财产的分离、居住地的变动是不是就意味着分异出来的“家”与原来的“家”的关系的断绝?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有一份《告子》爰书,是父亲告子不孝的法律文书:
告子 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己(简50)往执。令史己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毋(无)它坐罪。 ”(简 51)[2]156
由“同里士伍”可以判断甲与丙这对父子没有登记在同一户籍,而且很有可能也没有住在一起。因为后文有“不孝甲所”这句话。《封诊式》中还有一份《迁子》爰书,是已分家的父亲告子不孝,要求官府“谒杀”或“鋈足”。官府最终按照父亲的意愿“令鋈丙足”,并“迁蜀边县”[2]155。由此,子女对父母的孝亲责任并没有因分异而受到影响。另外睡地秦简中“免老老人以为不孝”[2]117、张家山汉简中的“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4]13的相关律文,也应该是既适用于同居,也适用于分异。
所以在盛行“生分”的秦汉社会并非老人无人照顾,自己生活。“孝”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不管同居也罢、分异也罢,子女的孝亲责任始终不变。
反过来,父母对子女的疼爱也不会因为儿子分异或女儿出嫁而终止。当儿女生活贫困时,父母也往往会以己财救济子女。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扬州胥浦M101女棺中出土了一份《先令券书》,提到墓主老太太有6个同母异父的子女。其中“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姓,遂居外”[30]1900,显然,这个成年的儿子公文已自立门户,与母亲分异。两个女儿君、弱君也已经出嫁。但是,女儿们“贫毋产业”,老太太就把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给弱君,波田一处分给君。后来公文伤人触犯了刑律,也“贫无产业”,于是,老太太又将给女儿们的田收回,“分予公文”[30]1901。未成年也好,成年也好;分家也好,同居也好,父母对于子女的爱也是永恒的。
还有其他的亲属身份犯,比如:
殴兄、姊及亲父母之同产,耐为隶臣妾。其奊訽詈之,赎黥。(简41)
殴父偏妻父母、男子同产之妻、泰父母之同产,及夫父母同产、夫之同产,若殴妻之父母,皆赎耐。其奊訽詈之,罚金(简42)四两。(简43)[4]14
……
不管是牧杀、殴骂、殴笞,还是擅杀,都以亲属身份来量刑。尊长犯卑幼,并同减凡人论,卑幼犯尊长,则并同加凡人论。而秦汉时期的“族”中,“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4]7也是以亲属身份为要件,而非同居。比如汉末的伏皇后案,后及“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7]卷十下。如果以同居的概念来看,除了伏皇后与二子为同居外,其他如兄弟、宗族、母亲显然都各自别户异居。但是从法的视角上,不管是否同居,只要血脉相连,就逃不过“族”的惩罚。
[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3][日]冨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洪适.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2]辞源(合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3]谢桂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4]贾丽英.秦汉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
[15]许倬云.汉代家庭的大小[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6]长沙市文物研究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7]高文.汉碑集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18]唐刚卯.封建法律中同居法适用范围的扩大[J].中国史研究,1989,(4):75-86.
[19]彭年.秦汉“同居”考辨[J].社会科学研究,1990,(6):104-110.
[20]长沙市文物研究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21]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高台18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3,(8):12-21.
[2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M].长沙:岳麓书社,2007.
[23]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4]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5]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6][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7]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9]黄宽重,刘增贵.家族与社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30]初师宾.中国简牍集成:第十九册[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秦汉时期“伏日”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