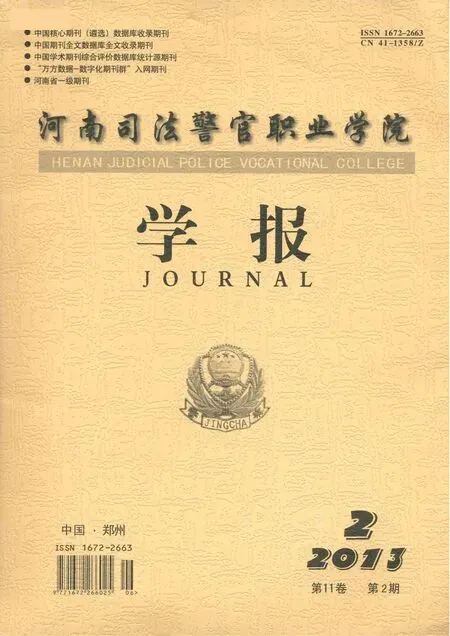肉刑在两宋时期的思想论争与制度表达
李 伟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266590)
肉刑是中国古代刑罚史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构成奴隶制五刑的主体。西汉文帝时,虽然颁诏废除了肉刑,但实际上肉刑却一直形未全灭而神犹存,在制度上还曾一度死灰复燃,而有关肉刑存废的论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更是连绵不绝,几乎历朝历代都出现过与此有关的争论。
从已有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在肉刑存废之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涉及人物最多的一次论争发生在汉末魏晋时期,这场长达三百多年的大讨论,为封建制五刑在隋唐时期的确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1〕笔者同意这一看法。但目前所见,学者们普遍对于隋唐以后的肉刑论争及制度表达着墨不足,多是一笔带过而语焉不详。实际上,在封建五刑确立之后,有关肉刑的论争仍不鲜见。从封建社会后半期来看,肉刑应否恢复之争在两宋时期再度出现,并且具有一定的论争规模和影响,在肉刑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阶段。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思想与制度缘由,应该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北宋神宗朝的恢复肉刑之争
在两宋时期,关于肉刑存废的较大争论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宋神宗时期,第二次是南宋时朱熹和陈亮的肉刑存废之争。与肉刑之争同时存在的,是刺配之法在两宋时期的大量施行,这种制度上的表达,是两宋时期肉刑之争的现实背景。
针对当时死刑增多的司法形势,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时任删定编敕官的曾布上《肉刑议》,主张恢复肉刑。在这篇呈送给皇帝的上书中,曾布认为:“先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然而有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非得已也。”在他看来,不管统治者的本心如何仁德,肉刑都是不得不实行的。究其原因,在于如若仅凭赎刑,难以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因此“先王”要设立墨、劓、剕、宫、大辟等刑罚,这样才可以显示轻重之别,以使得罪责能够相适应。而对于汉文帝废肉刑和后世以流刑替代肉刑的做法,曾布持反对态度:“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后世因之以为律。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墨、劓、剕、宫,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有违先王的本意,而且不能体现轻重差别。从这个理论基础出发,出于对宋朝当时刑罚体系的判断,他提出流刑和折杖法已经不能体现出刑罚的威慑作用:“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2〕随着时代的变迁,百姓的安土重迁观念已经逐渐淡化,当时的流刑犯到流放地一年后即可听其附籍,已经远远达不到流刑初设时的惩罚目的;而折杖法刑罚太轻,导致犯法之人日益增多,最终犯死罪的人数自然会增加,这样最终的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欲轻而反重”。而如果实行肉刑,就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一些情节较轻的死刑犯实行肉刑而达到减少死刑人数的效果,同时发挥出刑罚所应该具有的威慑作用。
从曾布的观点可以看出,北宋时旧有的刑罚体系业已不能达到惩治犯罪的目的,重新设置刑罚等差是其主张恢复肉刑的主要依据。对于曾布的这种观点,时居宰相之位的王安石、冯京二人发生分歧。王安石对于曾布的主张总体上持有一种肯定态度,“理诚如此,即行亦无害,但务斟酌”。他还以军士逃亡为例进行了说明:“如禁军逃走未曾构结为非,又非在征战处,诸合斩者,刖足可矣。”逃亡的军士依律是要被处以斩刑的,但是如果不是处在战时状态,并且在其逃亡后没有为非作歹的情况下,可以将斩刑减等而为刖足之刑,从而保全其性命。冯京不同意王安石的观点,认为这样会破坏现有的军法,有可能制造新的混乱,并且一代明君唐太宗亦弃肉刑而不用,复肉刑之举实不可行。其实,作为皇帝的宋神宗,其态度是倾向于恢复肉刑的,如他所言:“如盗贼可用肉刑更无疑,斩趾亦是近世法。”〔3〕但是,毕竟肉刑已经从形式上废除,虽然恢复论者亦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根据,但要想真正恢复,则不得不有所顾忌,因此这次讨论的结果——至少在制度形式层面而言——便是没有结论,“迄不果行”〔4〕。
针对这场争论,理学先驱张载的观点与曾布、王安石是基本一致的。他认为:“肉刑犹可用于死刑。今之大辟之罪且如伤旧主者死,军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刖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观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轻视其死,使之刖足,亦必惧矣。此亦仁术。”〔5〕在张载看来,恢复肉刑,既可以使罪犯得以活命,宣示皇帝的仁义之心,又能够警示他人,起到一定的犯罪预防作用,可谓一举两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皇帝仁术的一种体现。
苏轼则对恢复肉刑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认为肉刑有违以仁义为本的治国之道。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他为此甚至不惜犯颜直谏:“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6〕苏轼认为,恢复肉刑的举措,乃“以力胜之”,而这样的措施是不能长久的,可能会导致天下大乱的后果,因此肉刑断不可复。
在神宗朝有关肉刑应当恢复与否的来往交锋之中,持恢复论者与反对恢复论者各执一词,似乎各有道理。这一方面可以看到当时的司法情形变化,同时也能观察出执政理念、道德观念以及历史惯性施加于具体司法制度上的影响。虽然最终没有一个能够为各方都接受的结论性共识,亦未出现新的制度性规定,但是,通过争论,双方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其政治态度、法律观念得以更加清晰地展现在历史面前,这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实际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南宋时朱熹与陈亮的肉刑存废之争
南宋时理学勃兴,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极力主张恢复肉刑。他提出:“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过于重者,则又有不当死而死,如强暴赃满之类者,苟采陈群之议,一以宫剕之辟当之,则虽残其支体,而实全其躯命,且绝其为乱之本,而后无以肆焉。岂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适当世之宜哉!”〔7〕在朱熹看来,恢复肉刑的理由有三:第一,徒流之法过宽,不足以惩治罪大恶极者,不能有效制止人们犯罪;二是肉刑废除之后,在死刑和生刑之间缺乏过渡的中间刑罚,使得定罪量刑轻重失当,有不当死而死者,死刑过多造成了比肉刑更加严重的后果,违背了圣贤先王制刑的本意和宽严适中的刑法原则;三是认为如恢复肉刑,既可以断绝了犯罪之人重新犯同类型罪的可能,又能够增加刑罚的威慑力量,以反面示例很好地教育威慑他人,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基于上述原因,朱熹认为恢复肉刑非但不残酷,而且是一种“仁爱”之术,“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8〕。
对于朱熹恢复肉刑的主张,陈亮进行了明确的反驳:“法家者流,以仁恕为本;惟学道之君子始惓惓于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他认为,肉刑制度与仁恕之道的价值观是相抵触的,不应当成为道统文人的主张。“圣人之恐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者,今既尽废而不可复举矣。独惓惓于圣人之恐其或用者。纵使可用,无乃颠倒其序乎!使民有耻,则今法足矣;民不赖生,虽日用肉刑,犹为无法也。”〔9〕针对朱熹所认为的不用肉刑就不能制止犯罪的主张,陈亮批驳说圣人制刑就是为了消除争夺戕杀之患,现在怎么能够抛弃圣人留下的好传统呢?在陈亮看来,肉刑只能残民肢体,而不能起到有效预防犯罪的作用,道学家们口口声声讲仁义道德,在实际中却要依靠残酷的肉刑来维持封建的统治,这样正证明了道学家的“天理”不能确立。
与北宋神宗朝有关肉刑的争论相比,朱熹和陈亮与此有关的争论在诸多思想史著作中被提及较多。朱、陈二人皆为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所代表的理学派和浙东事功学派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有关肉刑存废的争论中,亦可以管窥其政治法律思想。在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理论旨归的朱熹看来,司法应当以严为本,增加刑罚的威慑力量。而倡导功利思想的陈亮,则主张法令贵在宽简,所谓“持法深者无善治”、“法愈详而弊愈极”〔10〕,只有法律宽简、实施轻刑,才可以达到善治。
三、两宋时期肉刑的事实存在——刺配之法的大量施行
与肉刑恢复之争相呼应的是,宋朝时大量肉刑实施的事实存在,这是宋朝肉刑恢复之争的现实依据。有宋一代,在制度上规定了刺配之法,并且在实际中大量使用,远远超过历代王朝。宋代的“刺配之法”,可以说是古时黥刑在宋时之发展,其虽不在法定“五刑”之内,却是非常完整和系统,可谓历代黥刑之集大成者。
在宋代,对罪犯而言,黥刑往往不是单一使用,而是与其他刑种结合使用。对获罪者杖脊、刺面、配役三刑兼用的刑罚,使“一人之身,一事之犯”,“既杖其脊,又配其人,且刺其面”〔11〕,成为宋代特立的一种刑罚方式。凡合刺配者,均先杖脊、黥面,再发配服劳役或军役。这种一人兼受三刑的处罚,是宋代附加刑罚加重的突出表现。
宋代的刺配之刑,主要是惩罚那些窃劫盗者、赃吏、犯罪军士等〔12〕,在实际中大量实施。为此,大臣多有上书劝谏。仁宗时,翰林学士张方平指出:“刺配之法,比前代绝重。”〔13〕到南宋孝宗时,校书郎罗点也称:“本朝刺配之法视前代用刑为重。”〔14〕明人邱浚亦说,“宋人于五刑之外,又为刺配之法,岂非所谓六刑乎”〔15〕。
两宋时期的刺配法对之后的元明清有着直接的制度性影响。宋朝之后,元有刺配(包括刺臂和刺颈),而对蒙古人及色目人,不在刺配之列。明亦“一罪三刑,不免,窃盗犯徒以上,又配、又杖、又刺”〔16〕。清有刺“强盗”、“窃贼”等字样(满人刺臂上)的刑罚,从中可以看到宋朝刺配之刑的影响。
四、两宋时期肉刑恢复之争与刺配之法实施的原因探析
思想往往是现实的一种表达。两宋时期有关于肉刑存废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的法治状况和法律思想脉络。结合刺配法在宋朝的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则可以对宋朝时期肉刑恢复之争的原因和刺配之法所显现出来的现实司法问题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判断。
1.论争双方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即儒家“仁爱”思想。从前述两宋时期有关肉刑存废的两次较大的争论中,无论是主张恢复肉刑的一方,还是反对恢复肉刑的一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即都秉持“仁爱”思想。
赞同的一方,如曾布、王安石、张载、朱熹,在其论证恢复肉刑必要性时,论据之一即是基于对当时死刑过多的形势判断,认为肉刑的恢复,可以减少死刑的执行数量,而保全人的生命。而反对的一方,如苏轼、冯京、陈亮等,同样是出于这一儒家理念,只不过他们所做出的判断方向与肉刑恢复论者恰恰相反,认为肉刑残民肢体,过于残忍,因此应该完全废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方采取的是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反对方则取绝对主义态度,因此,虽然出发点相同,但是结论却截然相反。
2.从刑罚目的论的角度来理解,可以看到双方对于肉刑目的的不同认识,是导致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
在肉刑恢复论者看来,肉刑可以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惩奸止恶,二是预防犯罪。正如同前述朱熹所言,肉刑的施用是为了“绝其为乱之本,而后无以肆焉”,就是使犯罪者失去其作案的工具,以免以后再危害他人;同时,被施以肉刑者的存在,也可以在社会上树立一种反面形象,时时提醒、警告潜在的犯罪者能够克制犯罪倾向,从而有效预防犯罪事件的发生。
而在反对恢复肉刑的一方看来,肉刑执行甚为残忍,不但有违仁义之道,而且这种威吓主义的法制原则本末倒置,是“以力胜之”的表现,不可能取得长久的统治效果。关于刑罚目的论的不同认识,使得双方对肉刑恢复与否产生了重大分歧。
3.对于流刑作用的重新评价,是两宋时期肉刑恢复论和刺配之法施行的重要依据。魏晋之际,肉刑存废之争之所以非常强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死刑和徒刑之间缺少中间刑,人们不得不从历史中寻找资源,遂把目光重新聚焦在肉刑,从而引发关于肉刑存废的大争论。不过,在北齐形成死、流、徒、鞭、杖五刑,并在隋唐时期最终定型为笞、杖、徒、流、死封建制五刑后,流刑成为死刑和徒刑的中间刑,解决了长期以来人们因为刑制不合理而产生的要求恢复肉刑的议论,所以肉刑存废之争遂在隋唐之际沉寂了数百年。
封建制五刑发展到宋朝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宋太祖实行“折杖法”之后,宋朝为遏制犯罪,宋政府通过颁敕和编敕,规定或创设新刑种,形成以臀杖、脊杖、编管、配刑、死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凌迟亦成为常用刑,结果使宋代刑罚较唐代更为严酷。宋代制定与实施《折杖法》,本欲轻刑,但导致刑种配置缺乏科学性,刑罚轻重失衡,反而促使刑罚重刑化。〔17〕正是在这种司法背景下,肉刑恢复之争在两宋之际几度死灰复燃。
在两宋肉刑恢复之争过程中可以看到,两宋时期,社会观念较之隋唐之际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于安土重迁的重视程度已经远远不如流刑设立之初那么强烈,并且此时的流刑犯到了流放地一年之后就可以附籍为民,流刑已经不能发挥作为死刑和徒刑中间刑的作用。这种形势的变化,是促成两宋之际出现肉刑恢复与否争论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出现一个可以替代流刑作为中间刑的新刑种出现,对于肉刑的重新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1〕张兆凯.论古代肉刑存废之争〔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2〕〔4〕宋史·刑法志(卷二百一).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四).
〔5〕张载.张子抄释·理窟周礼(卷三).
〔6〕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后集(卷十).
〔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郑景望(卷三十七).
〔8〕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9〕陈亮.龙川集·问答(卷四).
〔10〕陈亮.龙川集·铨选资格(卷十一).
〔11〕丘浚.大学衍义补·慎刑宪(卷一百五).
〔12〕范富.黥刑的演变及在宋代的发展〔J〕.宜宾学院学报,2010(4).
〔13〕〔16〕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八.
〔14〕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七(卷一百六十八).
〔15〕王圻.续文献通考补·刑法补四(卷三十三).
〔17〕吕志兴.《折杖法》对宋代刑罚重刑化的影响〔J〕.现代法学,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