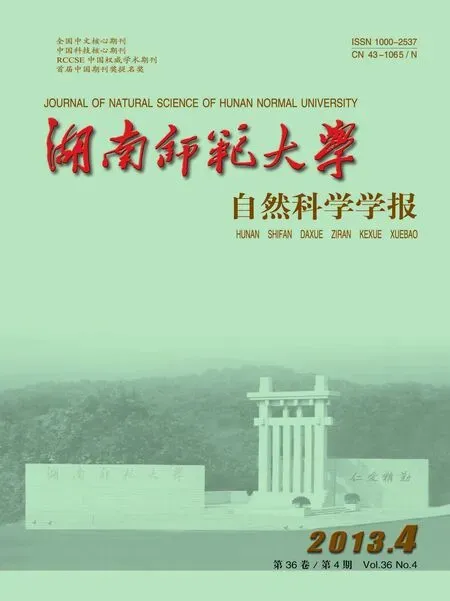基本农田抛荒形式的界定研究
夏卫生,林佳庆,唐雨蒙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 长沙 410081)
当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框架以1998年《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通过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基本农田保护、土地税费等制度安排,使其成为世界上现行的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之一.但保护耕地面积一直是许多科学工作者具有争议的观点之一[1],争议的焦点从表面上看是计算方法不同,而事实上是对耕地能否得到充分利用有不同的认识[2-3].耕地利用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土地使用者(农户)三者共同的行为,是在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及执行环境中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过程[4-6].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主要矛盾是耕地数量的增减问题.由于地方政府是中央的下属机构,尽管地方政府在不断增加建设用地,占用耕地,但耕地数量还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至少从形式上不存在太大问题[7-10].在现行的产权制度安排下,耕地的实际使用者(农户)对耕地面积保护的实际参与度很少,但对耕作过程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认为农户生产是自主而不需监督的行为;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业收入已不是农户的主要收入[11-12],其耕作过程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耕地抛荒日益严重,对粮食产量和质量的影响日益严重,因此有必要对抛荒形态进行分类界定,从而为其产生的后果进行科学评估.
1 基本农田抛荒的界定
土地抛荒是指对可以耕作的土地放弃耕种的行为.从目前抛荒的形式来看,可以分为显性抛荒、隐性抛荒和变性抛荒3种形式.
一是显性抛荒.这是最明显的抛荒形式,人们一般理解为由于各种原因对可耕作的土地放弃耕作.但从土地可持续利用角度来看,不能将简单的不耕作定义为抛荒.我国的耕地基本上处于连续耕作状态,尽管地力在不断下降,但由于及时地大量使用化肥,仍能保持较高的产量,许多土地需要一个自我修复过程,适当的休闲和修复才能使耕地得到可持续利用,因此定义连续二年不耕作的可耕土地为显性抛荒是比较合理的.由于这种抛荒形式表现非常显眼,加上政府对这种抛荒有较严格的政策约束,这种抛荒形式占全部耕地的比例目前还不是太高[4-5].
二是隐性抛荒.有些学者[13]在研究抛荒中探讨了季节性抛荒,如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可以耕种三季或双季水稻的而减少耕作茬数,只种两季或一季.这种耕作方式从表面上看没有抛荒,而事实上减少了粮食产量,使得耕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抛荒具有较强的的隐蔽性,综合实际情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可定义隐性抛荒为: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地资源和其他环境条件,由于人类和自然原因而使耕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现象.在太阳辐射充裕的水稻种植区,能种双季而没有种植的可以定义为隐性抛荒,而有的地方热量介于单季和双季稻之间,通过套种和移植等方法,也能种植两季,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这会有人认为这是对土地的过度利用,因此不能将这种情况定义为“抛荒”,这确实是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如果种植双季稻没有降低土地的地力,而年总产量有较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下改种单季稻仍可认为隐性抛荒.在实际耕作过还有不少的隐性抛荒现象,如没有施用足够的肥料以保证作物的生长,或者没有改良水利设施以保证作物的需求,或者没有将现在已有的科研成果应用于耕作等等,这些都有可以使耕地生产达不到应有的产量,因此可以看着是隐性抛荒. 由此可见,隐性抛荒不仅具有隐敝性,而且形式多样,在生产管理中有较大的难度.
三是变性抛荒.基本农田的根本任务是生产粮食,人们在计算土地承载力和国家进行宏观控制时也进行这样的假设.但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市场经济使得基本农田的利用走向多元化,农户种植作物种类随着市场需求和价格而发生变化.基于基本农田种植目标,种植非粮食作物其实也是一种抛荒,为有别于前2种抛荒形式,可定义为变性抛荒.变性抛荒仅从经济角度来看,有时是有利的.特别是我国目前粮食价格偏低时,变性抛荒已使许多良田变为经济作物基地.如在很多地方,一亩烟草的年收入可以达到5 000~6 000元,是种植水稻收入的5倍以上,而且种植烟草的人工成本较低,只要有人收购就能获得较大的收益.在这种经济驱动下许多耕地不再种植粮食(指谷物,含麦类、粗粮和稻谷类),而变为了烟草基地、药草基地和百果园等.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副产品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其价格也会快速上涨,变性抛荒的程度也会相应增强,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会日益加大;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其影响程度有可能超过前2种抛荒形式.
无论是显性抛荒、隐性抛荒还是变性抛荒都会对粮食产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个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的国家,必须保证耕地种植粮食才有可能保证粮食安全,因此有必要探究其产生的原因,以便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2 基本农田抛荒原因分析
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抛荒主要是农户对耕地的态度、耕作收益和耕作能力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近几十年土地所有权的剧烈变化影响了农户对耕地的态度.在生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将耕地作为生存之本,无论土地所有者是谁,耕作者只能依赖土地.这种依赖也是一种热爱之情,使得农户在耕作过程中自然而然有一种愉悦的心情,对土地也格外珍惜,对土地保护是一种自然行为,本能地穷尽一切办法增加粮食产量.近几十年我国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特别是经过20世纪三次大的变革之后,农民对土地的认识产生的严重的混乱,首先是解放初期,在村组范围内平分了耕地,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积极性自然较高,保护意愿也特别强烈,60年代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归集体所有,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耕地所有权主体是明确的,尽管积极性有所降低,但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第三次是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受近期利益驱使,生产积极性增强,但这种利益驱动型的积极性是以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这在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农户希望国家征用自己的耕地,并希望价格更高一些.这样在被征地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自己肯定不是土地真正或者完全意义上的所有者,对土地的保护意识自然降低.农户对土地只有利用而没有了热爱,对耕地进行合理利用和保护也就无从谈起,自然而然地追求利益或者短期效益的最大化,这样在利益的驱动下就会出现各种抛荒现象.
二是尽管粮食单产和价格在不断提高,但收益相对消费水平还是太低.在平原地区采取了较多的机械化作业,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也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在大多数丘陵区和山区,生产水平仍然很低.如按每个家庭耕作5亩计算,年收入最高15 000元,而不计农户工资,生产成本只少需要5 000元,净收入10 000元,这样每天收入不到30元.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下,仅依靠农业生产很难维持全家的生活,因此许多耕地甚至是基本农田只好改双季稻为单季稻以降低人工成本或改种经济作物来提高农田收入,这样势必造成隐性和变性抛荒.
三是耕地质量和劳动力水平的下降使得耕地无法充分合理利用.耕地质量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在利用过程中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使得其肥力水平降低,如除草剂使得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无法有效累积;二是土地环境恶化,土地承包责任制分割了土地与周边环境的联系,如农田水利设施在文革时得到了较好的完善,而近30年来只使用而没有维护,供水和排洪能力不断下降;加上相邻地块间没有较好地协调,农田生产力进一步下降,在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许多耕地也无法达到现代农业科技应有的水平,这其实也是一种更加隐性的抛荒.
另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劳动力和投入相对减少.大学扩招、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农民)进城务工不仅使务农人数减少,而且劳动力降低,知识水平也相对降低,现在从事农业生产者的年龄大多数在45岁以上,有的地方65岁以上还是主要劳动力,再过几年,这种现象会日逐严重,如不采取必要措施,耕地抛荒还会更加严重.国家对农村生产进行了适当的补贴,同时加大了科技投入,农村人员进城务工赚得了一定的劳务费,这都可能使得农业生产的投入量增大.但现实中投入量并没有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有的只是进行了转移.如国家投入经费开发新的高产种子,而种子价格相应提高,生产成本增加,尽管收获了较多的粮食,但收益增加较少,没有真正实现科研为农业服务的目标.国家的补贴也被CPI的增长而冲抵不少,因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相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物价的增长还是太少,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收益较低,因而无法阻止各种抛荒现象出现.
3 结语
农村土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抛荒,是当前新形势下“三农”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显性抛荒可见性较高,容易发现,国家已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控制;而隐性抛荒和变性抛荒随着农村劳动力水平降低,加上近期经济驱动和人们对土地依赖程度的放松,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会逐年加大,从而严重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有必要进行深一步的调查研究,更加清楚其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采取合理的措施,以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
参考文献:
[1] 唐 健,陈志刚,赵小风,等.论中国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与茅于轼先生商榷[J]. 中国土地科学, 2009,23(3):4-10.
[2] 陈念平,耿莉萍. 中国土地耕作成本及相关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10,24(1):3-8.
[3] 张海兵,鞠正山,张凤荣.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相关性分析[J].2007,21(4):12-17
[4] 赵华甫,张凤荣,等. 基于农户调查的北京郊区耕地保护困境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08,22(3):28-33.
[5] 邵晓梅,谢俊奇. 中国耕地资源区域变化态势分析[J]. 资源科学, 2007,29(1):36-42.
[6] 戴小枫.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技术战略与路线选择[J]. 中国软科学, 2010,24(12):1-26.
[7] 张东轩.关于耒阳市耕地抛荒问题的思考[J]. 湖南农业科学, 2008,18(6):136-139.
[8] 李 维. 我国农村土地抛荒的关键因素研究[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9(4):58-62.
[9] 陈静彬,岳意定.湖南省粮食产量波动分析[J]. 湖南农业科学, 2011,21(11):106-110.
[10] 肖大伟.关于实施土地流转补贴政策的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 2010,24(12):10-14.
[11] 陈美球,刘中婷,等. 农村生存发展环境与农民耕地利用行为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业经济, 2006,26(2):49-54.
[12] 陈百明,周小萍. 中国粮食自给率与耕地资源安全底线的探讨[J]. 经济地理, 2005,25(3):145-148.
[13] 田富强.试析耕票制度与有效遏制耕地季节性抛荒[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1,32(5):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