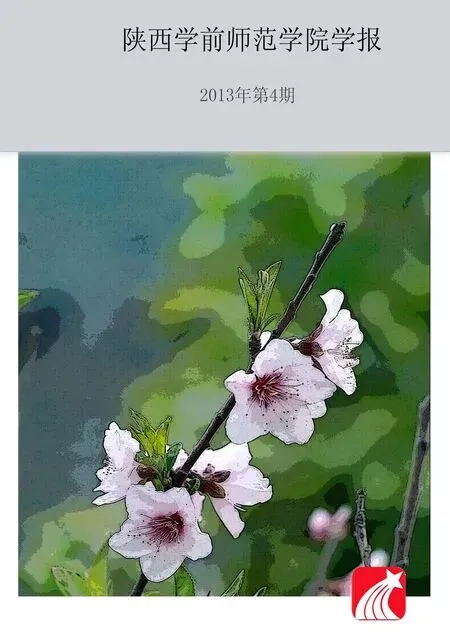“尔汝群物”与“强草木以还泪债”
——从钱钟书的“物我”观看古典诗学中的三种境界
马 涛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
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物”“我”关系,包蕴极为深广精微,它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更涉及到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与人生论,钱钟书先生对此文心艺理亦进行了精微的探讨。本文拟从钱钟书对抒情主体不同心性修养下所呈现出的“物我关系”入手,探讨古典诗学中因之而呈现的三种境界。此三种境界,笔者将其名之为“大我”之境、“小我”之境、“无我”之境。
一、“尔汝群物”的“大我”之境:具万物一体之爱的“我”
“尔汝群物”是钱钟书先生解读《诗经·静女》一诗时所提出的。原是清人对杜甫诗歌境界的评价,杜诗中常常直接用第二人称的“尔汝”来称呼无性灵慧觉的草木鸟兽,如“沧江白发愁看汝,来岁如今归未归”(《见萤火》),指萤火虫;“暮景数枝叶,大风吹汝寒”(《废畦》),指蔬菜;“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江头四咏·栀子》),指栀子花;“念尔形影干,摧残没黎荞”(《枯棕》),指棕树;“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秋雨叹》),指决明花。在一般实用功利的世界里,物只是僵死冷寂、或蠢蠢而生毫无精神情感可言的存在,是被人利用操控的工具、观照的对象。“尔汝”一词却将万物升华到了与人同等的高度,仿佛在诗人的视域里,万物“性灵已通”,与人可亲可友,是可以进行平等对视与深入交流的生命体。“尔汝”一词见出了物我之间彼此亲昵,不拘形迹,相互呼唤、相互诉吐的共融交汇的状态。在《管维编》中钱钟书极富诗情地对杜甫诗中“尔汝群物”的境界进行了阐发:
卉木无知,禽犊有知而非类,却胞与而尔汝之,若可酬答,此诗人之至情洋溢,推己及他。我而多情,则视物可以如人(I,thou),体贴心印,我而薄情,则视人亦只如物(I,it),侵耗使役而已。……盖尔汝群物,非仅出于爱匿,亦或山于憎恨。要之吾衷情沛然流出,于物沉浸沐浴之,仿佛变化其气质,而使为我等匹,爱则吾友也:憎则吾仇尔,于我有冤亲之别,而与我非族类之殊,若可晓以语言而动以情感焉。[1]144
钱先生对“尔汝群物”义蕴的解说极使人联想到《红楼梦》“情榜”中,曹雪芹给宝玉的名号“情不情”。所谓“情不情”即将草木虫鱼这些无生、无情之物都看作是有生命的对象,以至情爱之。宝玉常以一种平等体贴的态度与万物交流对话,将自然生命化、审美化,并用自已的痴情去体贴自然的情理,一片同情、慈悲之心。
在古代诗艺中所体现出的“尔汝群物”的境界,正是来自于儒家欲究天人之际的“仁”学。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亦着眼于杜诗中流露出了儒家所崇尚的民胞物与、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怀,而且在于诗人对万物怀有心息相通的满腔仁爱恻隐之心。缪彦威先生《诠诗》曰:“诗人敦厚之情,不能藏诸已而感乎人而已,兼能推其情而化万物,蠢然冥然之物,自诗人视之,皆有温柔敦厚之情焉。读杜甫《除架》、《废畦》二作,可以见矣。”可见少陵善感善觉的诗心,正是一脉温厚悱恻的仁心。
中国哲人认为人之所以能觉悟到物我同体,是因为人内心的“澄明”没有被一已之私心欲念所隔截、遮蔽。“天地万物与我同体,心无私弊,则自然爱而公矣。所谓仁也,苟事理不明而为私意所隔截,则形骸尔汝之分了无交涉。譬如手足痿痹气不相通,疾痛痾痒皆不相干,此四体之不仁也。”[2]17冯友兰言:“仁,已不是我们所谓的一种德,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有此种精神状态者,觉天地万物与其自已为一体,别人所感者,他均感之。”[3]89可见,仁爱是对万物的“怵惕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4]145,深怀此心之人,必然对宇宙间美好的一切存有无限的眷顾,见其生必不忍见其死,睹其荣必不忍思其悴,亦必有一份悲怜关切施于其身。《蕙风词话》云:“唐张祜《赠内人》诗:‘斜拔玉钗镫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后人评此以谓慧心仁术。金景覃《天香》云:‘闲阶土花碧润。缓芒鞵、恐伤蜗蚓。’与祜诗意同。填词以厚为要旨,此则小中见厚也。”[5]126“厚”与浅薄、轻薄、浮薄、薄情相对,“慧心仁术”正是“厚”的点睛之处,即那种至情洋溢,真情沛然,推已及它,民胞物与,深怀万物一体之爱的仁心善意。这种深深的恻隐之情、幽微感触之心使万物“性灵通透”、“变化气质”沉浸沐浴于爱怜与慈悲之光照中。
此外,钱先生对“尔汝群物”内蕴的阐发,与奥地利哲学家马丁·布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论述可谓潜流暗通。布伯按照人的生活态度把世界分为两重:一是“被使用的世界”(the word to be used),一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the word to be met)。[6]20布伯用“我─它”(I—it)的公式称谓前者,用“我─你”(I-thou)的公式称谓后者。所谓的“我─它”范畴实指人把世界万物(甚至个人以外的他者)当作使用、役使的对象,在这一关系中万物是没有独立自主地位的,它们是个体自我中心、无限权威下的附庸物,故而物我之间是障蔽隔绝的。因此在这种观照态度下,人对万物便没有情感,只有欲望与期待,万物仅是与我分离的“他者”或“对象”,正如钱钟书所说:“我而薄情,则视人亦只如物(I—it),侵耗使役而已”。而在“我─你”关系中,他人他物被提升到与自已同样独立平等、自在自由的主体性地位中,这是一种仁爱相待、互为主体的态度。在布伯看来,正是在这种仁慈(Grace)、仁爱(Tenderness)的观照下,我才能与做为“你”的万物相遇,赤诚相对,在彼此的灵魂深处见面,所谓“我而多情,则视物可以如人(I,thou),体贴心印”。其实布伯所说的“仁慈”与钱钟书所说的“胞与而尔汝”、“至情洋溢,推己及他”的诗性境界是互通的,它们亦与“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之爱”的儒家仁学同一精神。这样的诗性境界和仁者襟怀,唤醒、点亮了万物,使它们摆脱了凝固的存在状态,而成为一种与人流涟顾盼、真气远出的生命体,而呈现出宇宙的生生之美。于是众生也,万物也,一切都在人的观照、关切、用情、悲悯之中。故而钱先生言:“吾衷情沛然流出,于物沉浸沐浴之,仿佛变化其气质,而使为我等匹,爱则吾友也。”
于此可知,笔者之所以将“尔汝群物”式的诗意呈现,称之为“大我”之境,就是因为此“我”是对于万物具有担荷与慈爱精神的“我”,是觉解到万物一体之仁的“我”。前哲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孟子)、“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张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已也”(程颢),大“我”之“我”,当作如是观。
二、“强草木以还泪债”的“小我”之境:“挟私蔽欲”之“我”
从上文可知,“大我”之境中的诸种情绪根源于万物一体之“爱”。相比而言,笔者所谓的“小我”之境,其情绪是以个体的“欲求”、“祈愿”为中心辐射出的。借叔本华之论,则人生的诸种情绪,如喜悦、失落、无聊、向往、痛苦等皆是“欲求”的钟摆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心境。故而悲欢离合之情、羁旅行役之哀,进而身世之辽落,境遇之穷达所兴发的无限悲喜哀乐的情感,皆是个人由躯壳起念对世界或某种生存状态有所“欲求”、“祈愿”、“直执”而产生的。尽管这两类感情皆为人心所蕴蓄,在诗境中亦皆可达到浓挚深入的真诚力度,使人感动,然其境界却有高下之分。正如王静庵言:“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生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7]242可见“大我”之境与“小我”之境,虽皆达到“以血书之”的情感境地,然“小我”之境者,“不过自道生世之戚”,一已之私怀而已;“大我”之境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对于“小我”之境中所呈现的物我关系,钱钟书在《谈艺录》中,通过对李贺诗的评赏,进行了精微的阐发。钱氏发现身世悲苦,愁情抑塞的李贺好用“啼”、“泣”等字,如“芙蓉泣露香兰笑”(《箜篌引》),“幽兰露,如啼眼”(《苏小小墓》),“木叶啼风雨”(《伤心行》),“九峰静绿泪花红”(《湘妃》)等,并分析其人性情言“仆本恨人,此中岁月,都以眼泪洗面”,故而“连篇累牍,强草木使偿泪债”。在这一类诗歌中之所以草术虫鱼有了人的情感、情绪,皆是因为抒情主体的诗人“有所悲悼,故觉万汇同感,鸟亦惊心,花为溅泪”[8]155,而非万物一体之爱的修养下,汝尔群物,物若“通灵”有情。这时“物”在诗中只是诗人情绪的一种“对应物”或者外在化的呈现,这是“索物以托情”的模式。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有我之境者,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然而,当“我”的主观性因素过分强烈时,在诗境中所呈现的物我关系常是紧张的,诗的审美价值也便受到影响。
先入为主,吾心一执,不见物态万殊。春可乐而庾信《和庾四》则云:“无妨对春日,怀抱只言秋。”秋可悲而范坚乃有意作《美秋赋》,唐贾至《淝州秋兴亭记》、刘禹锡《秋词》旨言秋之可喜。汉《郊祀歌·日出入》篇曰:“春非我春,夏非我夏。”回黄转绿,看朱成碧。良以心不虚静,挟私蔽欲,则其观物也,亦如《列子·说符》篇记亡斧者之视邻人之子矣。我既有障,物遂失真,同感沦于幻觉。如孔德璋《北山移文》之“风云带愤,石泉下怆,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林惭无尽,涧愧不歇”,虽极嘲讽之致,无与游观之美。试以“北陇腾笑”,与“晚出淡笑”相较,差异显然。长吉诗中好用涕泪等字,亦先入为主之类也。[8]143
可见,当诗人观物之时,如果“心不虚静,挟私蔽欲”、“有所悲悼”,“感情用事”,“挟成见而执情强物”,则所观照到的外物便被遮蔽掉了自身的本性真情与自然状态,而成为个人情感意识下被幻化失真的存在。比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作者因要假借山灵来嘲笑周彦伦的假隐居,便写其所经之林木涧泉为其虚伪感到惭愧,故而“献嘲”、“腾笑”、“争讥”。正是因作者“先入为主”有私心与偏执,于是山水清音所具有的天机真趣、游观之美被戕丧,只成为作者嘲讽的假借物与工具。可见,在这一抒情模式中,由于抒情主体强烈的情感急需发抒,物我之间不是平等交流对话,灵气往还的关系,它只是被诗人求索以寄托情感的载体。在这种心理机制下的诗境,有时虽也能通过“借助”景物而使情感直切自然地呈现,而达到情景交融,但不可否认“物”在物我关系中是被动的,至少在诗人“观物”之时,天人之间,内处悬隔。
故而钱钟书言:“象物宜以拟衷曲,虽情景兼到,而内外仍判。只以山水来就我之性情,非于山水中见其性情;故仅言我心如山水境,而不知山水境亦自有其心,待吾心为映发也。”[8]138钱钟书的“就”字,下得极为精妙,也就是说在“小我之境”中,山水万象是被动的“牵就”于“我”的情感。所谓“牵就”即是对象的本性真情、自然自性被忽略遮蔽掉了,而只能随“我”歌哭。“于山水中见其性情”的“见”字,我们与其将它诠释为“呈现”,不如释为马丁·布伯所说的“遇见”,也就是说在“见”中,物我之间是平等对视、互相呈现的关系。即我之性情不仅要待山水之境来呈现,所谓“无物无以见我”;同时“山水境亦自有其心,待吾心为映发”,山水本身所秉具的性真也借灵明的诗者之心映发呈现。这种物我互见,相互映发的境界,在我国古代修养高卓的艺术家那里是十分常见的。
三、“以天合天”的“无我”之境:“喜怒哀乐未发”之“我”
“强草木以还泪债”的“小我”之境,常常“以人灭天”,在何种心性修养下方能最理想的呈现出物象的本真情态呢?钱钟书提出了观物之我,乃为“喜怒哀乐未发之我”的灼见。
物之神必以我之神接之,元僧觉隐妙语所云:“我以喜气写兰,怒气写竹。”……北宋以后,抉剔此秘而无遗。抑所谓我,乃喜怒哀乐未发之我;虽性情各具,而非感情用事,乃无容心而即物生情,非挟成见而执情强物。春山冶笑,我只见春山之态本然;秋气清严,我以为秋气之性如是。皆不期有当于吾心者也。……又《书范宽山川图》曰:“神凝智解,无复山水之相”;又《书李成画后》曰:“积好在心,久而化之。举天机而见者山也,其画忘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记曾无疑论画草虫云:“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曰“安识身有无”,曰“嗒然遗其身”,曰“相忘”,曰“不知”,最道得出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8]142
这种“喜怒哀乐未发”的境界,颇合于王静庵所标举的“无我”之境。《人间词话》言:“无我之境也。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7]221王静庵所谓之“无我”乃“无欲之我”,“吾人一旦因他故,而脱此嗜欲之网,则吾人之知识已不为嗜欲望之奴隶”,“无欲故无空乏,无希望,无恐怖”[9]4,如此方可摆脱了诸种情感的耽溺与纠缠。钱钟书所谓的“喜怒哀乐未发之我”与王静庵的“无欲之我”,其根本着眼点就是要使观物的主体变成“心性澄明”的主体,而非“心不虚静,挟私蔽欲”的主体。
钱钟书在上文所列述的唐宋人有关谈艺的诗文很显然是来自老庄哲学,故“喜怒哀乐未发之我”所象征的“澄明心性”,其赖以产生的思想文化渊源可追溯至此。老子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他所标举的虚静淡漠、超然远逸的心性修养,为以后澄明本体的意境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内涵架构,为庄子所直接继承。《齐物论》中庄子讲“吾丧我”,在《庄子》中“自我”一词蕴意极广,约言之有五,有“躯壳之我”“心理之我”“心机之我”“自我精神之本性”和“永恒临在之常心”。前三种结而成为“妄我”,只有舍尽小我妄我,才能恢复“大我真已”,显示无限广大的道性。世间功名物欲皆是“澄明心性”被遮蔽的尘埃,故而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通过“心斋”、“坐忘”,忘怀名利得失、智虑巧慧、甚至自我的肉身存在,进而将所做之事亦忘却,消除目的性对人的羁绊,一切皆忘之后,便摆脱了各种情感、欲望、观念成规的干扰,使“纯粹”、“虚明”、“恬淡”的“本心”呈现出来,以达到“同于大同”、“合于天德”的境界,呈现出宇宙与自我在本真状态下的自由、自足、自然地交融合一。钱钟书所说的“‘安识身有无’,曰‘嗒然遗其身’,曰‘相忘’,曰‘不知’,最道得出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即是着眼于庄学的“无我”之义。
可见,钱钟书所谓的“喜怒哀乐未发之我”与庄子在“心斋”、“坐忘”而后出现的心性“虚”、“静”、“明”的“我”是神理相通的。在这种心性修养下观物,以“人心”明觉虚灵的“本我状态”去应和天地万物的“本真情态”,以天合天,则人天各得其所,各葆其真,交融共在,彼此无所拘限而自鸣天籁,以此感发出天人相融的“天地精神”。如钱钟书所言:“春山冶笑,我只见春山之态本然;秋气清严,我以为秋气之性如是。皆不期有当于吾心者也。”正是因为观物之我乃“喜怒哀乐未发”之“我”,呈现出了虚静灵明的“心性”,如镜之鉴物,故能照物不虚不伪,呈其本然如是之性真天趣。
尽管对“澄明心性”的关注可以推源于老庄,但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我”毕竟出典于儒家的《中庸》。理学家关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我”所象征的“澄明心性”在观物中的妙用,邵康节的“以物观物”之论对此作了极精微的阐发:
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晦。[10]78
“以物观物,性也”,何谓“性”?朱子《中庸》章句释云:“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故而“性”是物得之于“天”的本然、自在之理。那么对人而言“性”为何物?在释“喜怒哀乐之未发”之条时云:“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11]17故而观物之“我”可分为“喜怒哀乐之已发”的“情我”与“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性我”。以“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性我”去观物,即为“以物观物”。理学家亦认为要达到“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其修养功夫即为“无欲”。故而“以物观物”就是要将陷溺执著于功利欲望、忧患得失中的自我解脱出来,其视外物不与我有利害之关系,无贪痴诸念,于是不生诸种烦恼忧虑。此时之“我”乃离形去智,葆有澄明无碍的心性,如同与宇宙万物平等对视之一物,安有我之私心、私情侧然其间哉!如此观物名之曰:以物观物。
故如此心性修养下所观之万象清景,如“鉴之应形,钟之应声”(邵雍),能实现物我之间情感的自然兴发,同时呈现出万物本真自然的天性。“以物喜物,以物悲物,发而中节”,应顺物之当喜则喜,物之当悲则悲,而不携私情而强物,使其本性为之遮蔽。同时,由于心体近于虚明,易使内心之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如光明自发一般,产生万物一体之洞见慧识和浑然的感受而进入物我冥合之境,从而不辨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钱钟书所说的“我以喜气写兰,怒气写竹。……北宋以后,抉剔此秘而无遗”,这句话的哲学背景正是程子所言“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情顺万事而无情”、“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可见我以喜气写兰,非将我胸中之“喜”强染于物也,乃是因为兰之自然天性中本蕴有一脉温清喜气,故我以灵虚之怀应之,顺物本有之情,喜气以写之。
王国维《人间词》序中言:“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7]246文学的意境来自于对宇宙人生的观照,然而“观物”之时的“我”在直观的刹那所具备的性情、襟抱、人格等内在化的心性修养,都会对所观照的“物”境造成影响,亦如佛典所言:“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故而,在诗艺中之所以反映出不同层面的物我关系,并因此种关系而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境界,推究其本源,乃在于观物之“我”的心性修养之异。钱先生对此问题所申发的洞见慧解,豁人耳目,如明珠翠羽,散见于沙汀湖渚,然若按其所指示之端绪。引而申之,正可妆成七宝楼台,见其高严巨丽,或对谭艺赏诗者有所助益焉。
[1]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9.
[2]叶采.近思录集解[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10.
[3]冯友兰.新理学[M]//冯友兰谈哲学.北京: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4]王阳明.大学问[M]//阳明先生集要.北京:中华书局,2010.
[5]况周颐.蕙风词话[M].屈兴国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6][德]马丁·布伯.我与你[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
[7]王国维.人间词话[M]//王国维集:第一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
[9]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M]//王国维集:第四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0]邵雍.皇极经世全书解[M]//邵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朱熹.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