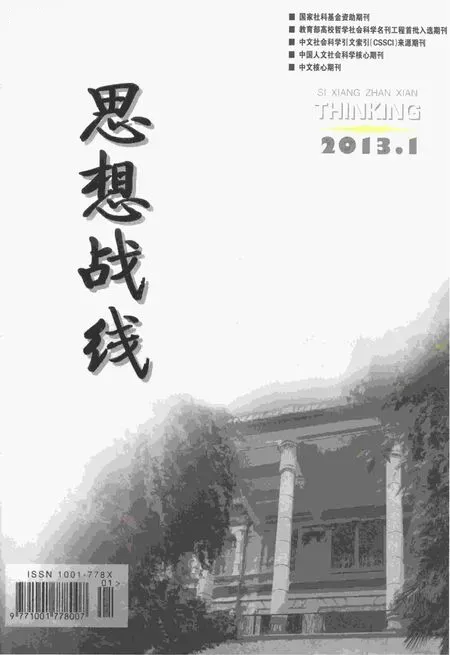如何正确作诗——柏拉图的诗人与立法者之争
林志猛
通过考察柏拉图《法义》 (Laws)①文中的《法义》引文为笔者根据希腊文译出,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的编码,不另作注。这部鸿篇巨制中诗人与立法者的论争,可以看清两者对文艺、模仿、劝谕和悲剧的理解有何不同,两者相互冲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一、如何正确作诗
在柏拉图看来,儿童最初的特征是喜欢喊叫和蹦跳,这就是音乐和舞蹈的起源。因此,结合歌舞的合唱训练乃是人最初的教育,好的教育要求唱好的歌、跳好的舞(《法义》654e4~5)。音乐包含曲调和歌舞,从而与教育息息相关。立法者不应让诗人们随便教育儿童和年轻人,而不管他们在诗歌的韵律、曲调或言辞中找到的是何种快乐。因为,若允许诗人们这样做,孩子们和年轻人的美德教育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实际上,诗歌的创作对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诗作寻求什么样的快乐、如何对待快乐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柏拉图批评诗人的一个原因在于,诗人的创作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不仅败坏了自身,还使观众成了诗人的裁判和老师。观众本应从剧场里看到好过自己的人,并体验到更好的快乐。由于诗人们一味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而没反对那些不恰当或不正确的快乐,观众只能得到完全相反的东西(《法义》658e6~659c5)。
为了防止诗人败坏观众也败坏自身,真正的立法者应说服或强迫诗人,“在他美丽而值得称赞的诗行中,通过描绘明智、勇敢和完美之人在节奏与和声中的姿势和歌,以正确地作诗”(《法义》660a3~8)。正确地作诗要求表现有德之人,好让观众效仿。悲剧展现英雄的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喜剧描绘小丑的插科打诨;抒情诗让各种情感放任自流。这些都不是“正确”地体现有德之人的“姿势和歌”,无益于塑造人的好品格。因此,立法者还应强迫诗人们说,明智而正派的好人是幸福的,不管他是强是弱,是富是穷;最正派的生活最快乐、最幸福,而不正派的人过得可怜、悲惨。倘若有人声称坏人活得快乐,或不把有益的东西视为正当,那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立法者应说服或强迫诗人说或做的事包括:表现德性完满之人,好人幸福而坏人不幸,正义与快乐、幸福直接相关。为何要强调正义与快乐、幸福的关联呢?柏拉图曾提到多数人的看法,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是健康、美貌、财富、敏锐的感官,甚至能成为僭主为所欲为。但是,若拥有这一切“好东西”却没有正义和整体美德,便是“最大的恶”(《法义》661a5~c5)。如果快乐不与正义同构,追求僭主式为所欲为的快乐,就会成为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最邪恶的生活也就成了最快乐的生活。因此,快乐不应成为评判文艺的标准,诗人应注意诗作提供的快乐恰当与否。②R.Stalley,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Laws,Indiana: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83,pp.62 ~63.要诗人描绘有德之人,就是要展现正确类型的快乐。
那么,最正派 (正义)的生活为何最快乐、最幸福呢?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最正派的生活可获得人们和神们的赞美,也就是好名声,它高于快乐。此外,不行不义也不让人行不义,也是好而高贵且不令人不快。源于好名声和人神赞美的快乐,与正义达成了一致。①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法义〉的论辩和情节》,程志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30页。不过,苏格拉底这类最正义者不行不义,却未能免遭不义,这种情形表明,正义与快乐、幸福其实无法完全同构。因此,说最正派的生活最快乐、最幸福乃是一个“高贵的谎言”。柏拉图认为,立法者有必要扯这样的谎,好让每个人自愿而非被迫地行一切正义之事。立法者可以凭借神话来说服年轻人的灵魂:播种龙牙,长出全副武装的巨人的神话就让人无比信服。这意味着,立法者可以像诗人那样编织神话,只是这种神话应着眼于让年轻人去追求正义,去过有德的生活,而非一味追求快乐。在《法义》中,柏拉图就改编了酒神狄俄尼索斯 (Dionysus)的神话。按照传说,人们得到酒这件礼物的原因是,狄俄尼索斯被继母赫拉剥夺心智后发了疯,为了报复,酒神使所有合唱队都陷入疯狂。因此,酒给予人类是为了报复,想让人发疯。但柏拉图主张,酒是一剂药饮,可让老年人恢复青春,灵魂变得可塑,也能使敬畏植入灵魂,让人变得节制(《法义》672b3~d9)。②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3页。而会饮则是教育的护具,可以洞察人的自然本性。柏拉图将逻各斯融入神话的改编显示,立法者创作的神话旨在塑造人的良好品性,说服年轻的灵魂向善,并有益于政治共同体。这也是立法者对诗人们的要求。作为神话的创作者,诗人们也应懂得神话的教育意义。
柏拉图指出,一切音乐都是形象的制作和模仿,正确的音乐应是对美的模型 (样式)的正确模仿。模仿要正确,必须首先了解被模仿物的原型,快乐并非评判模仿正确与否的标准。对于音乐、绘画等形象制作,一个明智的评判者应有3种知识:“首先,他必须知道事物本来的样子,其次是知道,在语词、曲调和节奏上,该事物的每种形象如何正确地制作,第三是知道这些形象如何制作得好。” (《法义》669a7~b3)显然,拥有这三种知识的明智评判者有如哲人。不过,诗人的制作并不含有这三种知识。③R.Naddaff,Exiling the Poets:The Production of Censorship in Plato’s Republic,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69;J.Elias,Plato’s Defence of Poet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4,pp.12 ~13.诗人混搭男女的言辞,或将自由民的曲调和姿势配上奴隶的节奏,或混合人、兽、乐器等声音,这种“大杂烩”是为了逗乐年轻人。诗人们由于过度受制于快乐,而混杂哀歌、圣歌、阿波罗颂歌和酒神颂歌,用一种乐器模仿另一种乐器的声音。结果,诗人们歪曲了音乐本身,甚至宣称没有正确的音乐,快乐就是评判音乐的标准。由此,观众们狂妄地认为自己是胜任的评判者,能理解音乐中的美丑。文艺的放任诱发的过度自由,导致一种“邪恶的剧场政制”取代了“音乐中的贵族制 (aristokratīas)”(《法义》700d4~701a3)。
柏拉图将音乐视为对好人和坏人性格的模仿,用于培育灵魂。但诗人族无法透彻理解什么东西好和坏,倘若某个诗人创作的作品在祈祷方面不正确,他就会使公民们在“最重大的事务”上错误地祈祷。因此,诗人制作的东西不得有别于城邦的合法之物,有别于正义、美和善的东西。柏拉图将法律方面的正义和美同真正的善(哲学意义上的善)结合起来,由此暗示,诗人书写的祈祷文应以真正的善为标准。诗人混淆善恶,也就可能分离法律的道德与善。④Seth Benardete,Plato’s“Laws”:The Discovery of Being,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205.柏拉图要求诗人制作歌曲的祈祷文时运用“理智”,并正确地分辨善恶,就透露诗人应向最高的善看齐。诗人对公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创作应当非常审慎。诗人的祈祷文如果将财富视为最重要,公民们就会不断地向诸神祈求金银财宝,而遗忘了自身的修养。
诗人们书写了无韵律的词,并创作了无词的曲调和节奏,从而错误地将节奏和曲调跟歌词分开,无法让人了解音乐的整体意图及其模仿的价值。可以说,这样的制作并非正确的制作,也没制作得好。尽管诗人了解和声与节奏,诗富有迷人的魅力,但诗人不知道模仿高贵还是不高贵。因为诗人不晓得最好的文艺 (音乐)“是什么”,及其“本来的样子”,也不知道其意图所在。这根源于诗人不具有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对人的灵魂和自然本性没有整全的知识——诗无法像哲学那样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低于缪斯的凡间诗人难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既非何为高贵和低贱的合格评判者,又非何为诗或非诗 (哲学)的最好评判者。⑤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法义〉的论辩和情节》,程志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35页。因为,诗在人类事务上不具有真正的知识,只是模仿意见或德性的幻影。诗根据城邦的立法者或缔造者的教诲进行赞扬或谴责,实际上是模仿立法者,而立法者才模仿正义的样式。①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在此意义上,强迫诗人表现高贵之物而正确作诗的立法者,成了诗人的老师,诗人从属于立法者。
二、诗人与立法者的劝谕
由于实际立法的人未必拥有整全的知识,其制定出来的法律就不会十全十美,有些人便不会服从,因此需要强制。“法律仅仅作为强制命令的话,那只是下限;而法律作为由理智完成的分配,必须归为上限。劝谕调节着这两个极端。”②[美]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法义〉的论辩和情节》,程志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61页。劝谕可使人们相信法律的正当,更容易认同法律。那谁最具有劝谕的力量呢?无疑,诗人最能劝谕人们。柏拉图原本表示,立法者不许诗人们随心所欲地创作,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违背礼法,损害了城邦。但柏拉图随后似乎推翻了前面的说法,竟代表诗人们来答复立法者关于公民们应该做什么和说什么。柏拉图模拟诗人的口吻说,诗人一坐上缪斯的三脚凳,就灵感喷涌,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他塑造各种相互矛盾的人物,但他不知道笔下人物相互对立的说法何者为真。不过,诗人对同一主题可以发表多种不同的看法,立法者却只能在其法律中明白无误地呈现一种说法。例如,关于葬礼,诗人可以根据富人、穷人和中产者各个不同阶层的人,描述繁复、节俭和适度的葬礼,而立法者却只称赞适度的葬礼(《法义》719c1~e5)。看起来,诗人能以合宜的方式对不同类型的人说不同的话,诗人了解灵魂类型的巨大差异。正是通过塑造多种相互矛盾的人物,诗人呈现了人类品性的纷繁多样。诗人能就人事的原本面目来展现人事,似乎值得立法者学习。
像葬礼这类事情,诗人会要求立法者,在立法之前先谈谈什么和多大是适度。柏拉图由此提出了置于法律规定前的“序曲” (prooīmion)。法律不应只有硬邦邦的条文,规定什么该不该做,要施加何种惩罚,而是要加入一些劝谕(paramuthīas)或说服的话(《法义》720a1)。为了阐明这点,柏拉图引入了奴隶医生与自由民医生的类比。奴隶医生不听取奴隶诉说病情,就凭经验下药,像个刚愎自用的僭主发号施令,而不解释为何那样做。自由民医生则“依据自然从源头探究病情”,并同病人及其朋友交流,在没有教导和劝谕病人之前,他不开药方(《法义》720b1~e1)。因此,立法也应像自由民医生那样,运用双重方法,将劝谕与强制结合起来,而非像奴隶医生那样仅使用强制这种单一的方法。双重的法律包含法律和“法律序曲”。法律序曲旨在劝谕而非命令,以让人更认同法律的规定,更容易学到东西。
由于诗人最能进行劝谕,极具适应性和灵活性,看起来更适合作为法律序曲的作者。③T.Pangle trans.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ive essay,The Laws of Plato,New York:Basic Books,1980,pp.446 ~447.但自由民医生的类比促使我们思考,这种法律序曲的劝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劝谕。自由民医生“依据自然从源头探究”,这不正是哲人做的事吗?哲人善于追根溯源,探究人的自然本性,难道自由民医生有如哲人?在《法义》惟一一处提到有关“哲学”这个语词的地方,柏拉图假设,有位自由民医生同患病的自由民对话,他“运用接近哲学化 (philosopheīn)的论述,从根源上把握了疾病,并回溯到身体的整体自然本性”(《法义》857d1~4)。如果一个根据经验而非理性下药的奴隶医生撞见这位自由民医生,就会嘲笑他,说他是在“教育”病人,好像病人要的是变成医生,而非健康。柏拉图并不在意奴隶医生的指责,因为,像他们这样讨论法律的人,乃是在教育公民,而非立法。这个类比表明,公民们如同患病的自由民,他们灵魂的疾病可以说是情欲、肆心、无知、爱牟利、懦弱,还有各种痛苦和恐惧,以及不虔敬,甚至包括沉溺于各种快乐和希望。立法者也应该“运用接近哲学化的论述”,从根源上把握公民们的这类疾病,并回溯到灵魂的整体自然本性。用暴力惩罚公民不是立法者的首要目的,教育公民走向美德、培育灵魂才是立法的要义。而教育正是制作法律序曲的目的所在。
真正立法者的法律序曲应对高贵、善和正义给出忠告,告诉公民们关于诸善的秩序,公民们应从中学习如何高贵、正派地行事,并依此评判自己的行为、选择和生活。④R.Mcneil,An Approach to the“Laws”:The Problem of the Harmony of the Goods in Plato’s Political Philosophy,Boston:Boston College,2009,pp.188~189.显然,这样的法律序曲只有接近哲学的立法者才能书写。如此看来,诗人似乎无法完全胜任制作法律序曲。柏拉图以葬礼为例来谈诗人,就暗示诗与可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婚礼和葬礼涉及人的生生死死,贯穿人一生的起点和终点,两者都是人生中的大事。柏拉图提出的第一个法律序曲就涉及“出生的起因”——婚姻。单一的婚姻法只会规定,在30岁和35岁之间,人人必须结婚,没结婚将受到什么什么惩罚。加上法律序曲的婚姻法会在提到惩罚前先说,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分有并渴望不朽,渴望成名而不希望死后默默无闻,便是对不朽的渴求。人通过传宗接代而分有了不朽和永恒,自愿舍弃这份不朽的人绝非虔敬,凡是不愿照顾妻儿的人,便是自愿舍弃了不朽(《法义》721b1~d5)。在这个法律序曲中,对结婚的鼓励融合了两种异质的要素。一种是传宗接代的实际考虑,另一种则是对不朽的高贵渴求——习俗要素与哲学要素融为一体。可以看到,这个序曲是在对两类人说话。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极有必要结婚并生儿育女,照顾好家庭,这对城邦的稳固和个人健康的生活都必不可少。对于少数人,成名的渴望使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来 实 现 不朽——这个序曲提到这点,无疑是在鼓励这类人超越家庭和城邦,但这只是深深地隐藏于其中。因此,针对所有人的同一部法律并非铁板一块,丝毫没有灵活性,恰恰相反,借助法律序曲,它可以鼓励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选择,而这些选择都有益于城邦和个人。
柏拉图以婚姻为例制作的这个法律序曲,是在针对或效仿诗人吗?婚姻法的序曲针对所有人,又暗中区分了多数人和少数人,就像诗人那样对各个阶层的人言说。但诗人用的是不同的言辞,而立法者用的是同一种言辞。立法者一题一说,却又能让不同的人听出不同的意思。这是因为,立法者暗中区分的灵魂类型,是按智性的高低来划分,诗人则是按财产等级来划分。可以想见,如果将诗人关于葬礼的说法写入法律序曲,必定会激起多数人的愤怒,因为这无异于在公开彰显不平等。但这个婚姻法的序曲通过暗中区分并模糊不同类型的人,实现了所有人的和谐。同时,这个序曲兼顾了诗性和智性,能激起人的深切渴求 (爱欲),有如完美的诗歌。这也回答了诗人所问的什么是适度。适度就在于贯通上上下下、高高低低,使不同类型的人的诉求协调一致。而诗的难题就在于无法呈现最高类型的人,因此从根本上讲,诗人无法获得适度,制作真正的法律序曲。那为何要鼓励立法者向诗人学习呢?毕竟,能运用哲学化论述的立法者可遇不可求,后世的立法者大多低于柏拉图这类立法哲人,有必要向诗人学习区分不同种类的灵魂和习性,学习诗人的修辞技艺和劝谕能力。据说,悲剧是“最能迷住灵魂的诗”。①[古希腊]柏拉图:《米诺斯》,林志猛译/疏,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321a5。法律要有像诗一样的魅力和优雅,而非只是干巴巴的宣传手册。②André Laks,“The Laws”,in C.Rowe and M.Schofield ed.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264~266。亦参[法]布舒奇:《<法义>导读》,谭立铸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41~242页。立法术应将推理性的知识转变为大众所能理解的诗,将知识转化为有益的意见,将逻各斯转化为诗或神话,借助诗的想象力和平易性弥合多数人与少数人的鸿沟。
三、最真的悲剧
对于诗人们用各种音步创作的诗——包括悲剧和喜剧,无数人认为,年轻人要获得正确的教育,必须用心学习所有的诗,沉浸于其中。另外,还要摘录出一些诗,编成“诗集”,让学生们认真学习并牢牢记住,通过各种体验和学习成为“好人和睿智者”(《法义》810e6~811a7)。但柏拉图怀疑这些说法是否为好,因为,诗人们有许多说法并不高贵,让年轻人学习他们的作品存在很大的危险。那么,谁的作品适合年轻人学习呢?在柏拉图看来,《法义》中的对话汇集起来看,各个方面都像是“一种诗”。这种“诗”比其他任何诗或散文都更适合年轻人去听,是评判其他作品最恰当的标尺。法律维护者和主管教育者应强迫教师们去教导并称赞这种诗。柏拉图甚至说:
我们本身也是诗人,我们已尽全力创作了最美而又最好的悲剧;无论如何,我们整个政制的构建,都是在模仿最美而又最好的生活方式,至少,我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确实是最真的悲剧。(《法义》817b2-5)
为何柏拉图称自己的言辞为诗呢,甚至是所有诗的标准?他的诗中又有什么动听的故事,值得年轻人去听?或许,年轻人应该听听关于法律的故事:他们的法律如何产生,立法者如何开始犯错,为何拒绝接受许多论点,并根据自己的权威“补充、舍弃、纠正和改变一位匿名的雅典人留下的东西”。③Seth Benardete,Plato’s“Laws”:The Discovery of Being,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215。年轻人可以从《法义》这种融入论证的故事中,获得许许多多有益的教诲。因为,这种关于法律的故事着眼于教育,而非立法或对惩罚的强调。《法义》那些高贵的言辞乃是教育的依据,为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样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听到贯穿人一生的事情:出生、成长、结婚、死亡,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灵魂、身体和财产,如何妥善处理自己的各种情感,如何崇敬诸神、祖先、父母,并加入这个政治共同体,承当相应的职责,在其中实现自己的高尚人生,过上有德的、从善的生活。这种砥砺灵魂、激发人追求智慧的故事,有必要让年轻人好好学习。
立法者创作的悲剧最美、最好而又最真——将真、善、美集于一身,因为,他们构建的“悲剧”(政制)是对最美、最好生活方式的模仿。政制体现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悲剧也展现人的生活和命运,但悲剧并没有呈现最美、最好和最真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在于,诗无法模仿智慧者、纯粹的好人,亦即哲人,而只能模仿各种低于哲人的有趣角色。因此,诗无法模仿最好的生活方式,即哲学的生活方式,诗表现的是低于哲学的种种生活方式。而人的问题或政治问题要获得根本解决,只能依靠哲学,惟有哲学才能揭示政治的本质及其界限,并提供解决之道。悲剧或喜剧的解决乃是不适宜或荒谬的解决。①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50~252页。对于悲剧,最好的生活是政治生活。但政治本质上讲是不完善的,不存在完美的政治,由智慧者统治的生活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柏拉图为何要把立法者的作品比作悲剧呢?两者又有什么异同?可以看到,两者有着共同的主题:灵魂问题,人与神的关系,善与恶的关系,道德与政治问题等等。两者也都包含各种戏剧要素。《法义》采用对话的形式,并让各种主题 (政制、法律、宗教、伦理等)交织在一起,这些主题的相互作用如同悲剧中人物的相互作用。不同的是,《法义》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宗教剧”,诸神只是出现在背景之中,而非像诸多戏剧那样,诸神直接出现在剧中。②Angelos Kargas,The Truest Tragedy:A Study of Plato’s Laws,London:Minerva Press,1998,pp.36 ~39.在《法义》里,诸神没有成为戏剧人物的主宰者,控制其行为和命运。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载沉载浮的是言辞,而非某些具体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言辞中的论证与人的戏剧构成一个整体。柏拉图使三名对话者通过充分的论述,而在最好的政制与法律上达成一致,这样的论述并没有受到诸神的干预,尽管保留着对诸神的崇敬。
柏拉图的悲剧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悲剧,既有故事又有论证,既是诗又是非诗,既涉及政治又指向哲学,这种悲剧关注整全,而非只是某些事物。柏拉图这种最真的悲剧的核心精神在于正确的教育,包括对公民的教育,乃至对立法者本身的教育——柏拉图的对话就呈现了对两位年老立法者的典型施教。一般的悲剧主要通过激起怜悯和恐惧的情感,而使之获得洁净,甚至变得高贵,但它们并不晓得洁净这些情感的真正目的何在。一般的悲剧无法像“最真的悲剧”那样,清楚地定出诸善的等级秩序,引导公民们完善自身的灵魂,摆脱情感的奴役,并指导立法者—缔造者进行立法和创建城邦。最真的悲剧模仿克诺洛斯 (Kronos)统治下的生活——让高于人的精灵来统治人。因此,最真的悲剧构建的政制是对神制的模仿,这种政制将使人获得最可能的幸福。不同的是,在神意消失的时代,在人统治人的时代,克诺洛斯的精灵将由具有哲学心性的立法者来取代。一般的悲剧强调英雄的伟大及其死亡,并突显诸神对人的错误的惩罚。③Angelos Kargas,The Truest Tragedy:A Study of Plato’s Laws,London:Minerva Press,1998,p.47.但最真的悲剧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也彰显理性、智慧的重要作用。
柏拉图还表示,身为艺术家和“最美戏剧”的表演者,立法者是诗人们的对手。因为,惟有真正的法律才天然能使最美的戏剧趋向完善(《法义》817b7~8)。最美的戏剧展现最美而最好的生活方式,惟有真正的法律才能实现这种生活方式。诗人们并非真正的立法者,他们无法制定出真正的法律和政制,相反,他们的作品可能与法律的教诲相冲突。立法者的作品对高贵、善和正义给出了告诫,是城邦中最高贵和最好的作品。在柏拉图看来,荷马等诗人对生活和习俗写下过糟糕的看法,相比吕库古、梭伦这些立法者,他们更应感到羞愧。最古老、最聪明的诗人也应在真正的立法者面前感到羞愧,因为,他们不懂得真正的高贵、善和正义,未拥有关于灵魂的整全知识,他们应附属于创作最真悲剧的、追求真知的立法者。
从诗人与立法者之争可以看到,如何正确作诗的关键在于,如何展现有德之人和正确类型的快乐,并创作出恰切的“法律序曲”和“最真的悲剧”。无论诗人还是立法者,惟有认清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类事务的本质,才可能制作出合适的音乐和“悲剧”(政制),以劝谕并引导不同类型的人过上符合自己本性的善的生活。诗人和立法者对城邦公民都拥有教育权,但要塑造完美的公民,诗人必须向真正的立法者学习,创作最好的音乐和最真的悲剧。这意味着,诗人要像真正的立法者那样关心美德和爱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