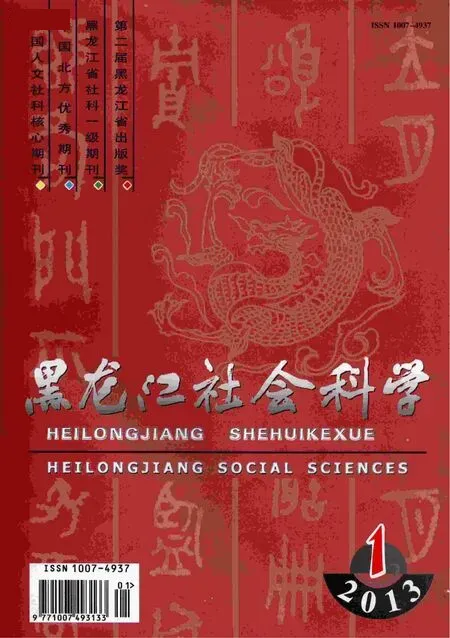“80后”社会群体特征及变迁(专题讨论)“80后”现象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80后”是一个独特的中国概念,指出生于1980—1989年的青年一代,据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在这十年间出生的人口约2.2亿。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和与之同时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持续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构成了“80后”生命历程中最关键、影响最深远的社会事件。如果说“80后”的父母们是“新中国的一代”,他们的生活史就是新中国国家建构(state-making)史;那么,“80后”们则是不折不扣的“转型的一代”,他们的成长经历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演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从相对封闭的社会向对外开放的社会的转型。“80后”在社会巨变环境中成长,体验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并通过互联网这种前所未有的交往工具,分享和交流共同的感受,形成代际认同和集体意识,这使他们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代际群体。
在讨论代际关系和定义代际群体时,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不同含义的“代”的概念:第一种是年龄差别产生的代际关系,如青年与老年;第二种是血缘关系产生的代际关系,如父辈和子辈;第三种是以共同的观念和行为特征产生的“代”,如“第五代导演”、“文革造反一代”等等。“80后”这个代际群体概念,虽然从名称上而言是一个出生同期群——出生在同一个十年里的一批人,但“80后”不仅是一个“年龄群体”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群体”概念,或可称之为“社会代”。“社会代”的意思是一群同年龄的人由于他们共同经历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使他们产生了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和相同的行为方式以及利益诉求。
“80后”青少年时期生活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第一,他们生长于开放的环境,广泛地受到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第二,他们生长于市场经济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身处竞争和谋利的氛围;第三,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使他们较少生活逆境和挫折;第四,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独生子女,而非独生子女也生长于少子化家庭,享受着祖辈和父辈的多重关爱;第五,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这使他们拥有前辈从未可能享有的丰富快捷信息、广泛的社会交往渠道和开放的自我表达空间。这些社会环境因素建构了他们的鲜明时代特征,使他们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代人。“80后”这个概念真正所折射的,是巨大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型塑了他们的观念与行为,而他们的观念与行为又在推进社会的变迁。“80后”从一出生就引人关注和争议,公众媒体赋予他们各种社会标签,伴随着其成长历程,他们的社会形象不断流变。“80后”社会形象和行为表现的种种变化,是两个发展轨迹交错影响的结果,一个是社会宏观层面的重大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转型的演进轨迹;另一个是个人层面的生命历程演进过程:从幼儿期成长为青少年期,再由青少年期成长为青年期,之后步入成年期。在“80后”的每一个人生转折期,剧烈的社会变迁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型塑着“80后”的观念与行为。
一、被贴上“小皇帝”标签的一代
在“蜜罐”里成长的“小皇帝”是人们对幼儿及儿童期的“80后”的称谓标签。这一时期的“80后”遇到的重大事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以及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80后”们享受到了其父辈从未享受过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四二一”家庭结构中,“80后”可以说是集千万宠爱于一身。虽然“80后”人群中独生子女的比例大约只有20%(主要是城镇家庭子女),但大多数的农村家庭出身的“80后”也成长于少子女家庭(大多数是2—3个子女)。在家庭收入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80后”享受着比其父辈童年期多得多的家庭资源和父母关注,他们无疑是幸运的一代。
1979年,中国政府出台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人口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年,610万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到1984年,全国育龄夫妇中,有2 800多万独生子女的父母领取了“独生子女证”。1986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中国大陆独生子女总数已达3 500万人(1987年《半月谈》杂志报道为8 000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87年,领证家庭增加到3 200多万。据粗略估计,80年代末全国领证的独生子女达3 500多万人。加上一大批未领证的独生子女,全国14岁以下独生子女超过5 000万。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城市,是城市的人口现象。据1990年的统计,中国已有5 000多万独生子女,未满一周岁儿童的独生子女率为52%,而在大城市,0~8岁儿童95%以上是独生子女[1]。
独生子女的大量出现,对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及相关生活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中国家庭观念崇尚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资源和父母关爱不得不在多个子女中进行分配,在有些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还不得不相互竞争,而独生子女则可以享有家庭的完全支持和父母的所有关爱。“80后”独生子女的父母是极其独特的一代,他们经历过多重磨难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迁。风笑天这样来描述这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不平常的人生经历: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度过他们的小学时代;在十年“动乱”和“上山下乡”中,度过他们的中学时代和青年时代;在恢复高考和抓经济建设的背景中,开始他们的婚姻和学习;在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关键时刻开始生孩子;当他们开始培养他们唯一的孩子时,社会改革、企业竞争的大背景又一次绷紧了他们生活的弦[2]。“80后”父母的挫折人生使他们对于子女寄予厚望和特别关注,他们不想让子女再经受他们所经历过的磨难,他们要给子女提供最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在“80后”的幼儿期和儿童期,祖父母们常常与他们居住在一起,即使不居住在一起,祖父母们也极热心地帮忙照顾孙子孙女。他们对“80后”孙子孙女们的溺爱程度更为突出。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的“80后”独生子女,表现出与以往儿童不同的一些个性特征,这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引起人们的关注。
1985年3月18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两名记者所写的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借独生子女父母之口,第一次给这一代独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拜倒在孩子脚下的父母称孩子们是‘小皇帝’”,中国的报刊称他们是“娇生惯养的孩子”。《一大群“小皇帝”》发表短短的11天之后(即1985年3月29日),《工人日报》就发表了这篇文章的摘译稿。1986年《中国作家》第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小皇帝”》的报告文学。该刊在扉页的编者按语中深沉地写道:
本期以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为开篇。中国有3 000多万独生子女,他们目前的生活和教育现状,已愈来愈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忧虑。愿本刊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会从这篇文章中得到启发,学会真正地关心这些“小皇帝”。我们愿和作者一起呼吁:为了中国的将来,不要溺爱!不能溺爱!
这篇报告文学向全社会发出了警告:“中国的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一起来临,其中就包括出现在每个家庭里的宠儿,更确切地说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养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上了‘四二一’综合征的孩子——独生子女们……也就是说,凌驾于家庭、父母及亲属之上的‘小皇帝’,已遍及千家万户,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皇帝’。”这篇报告文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小皇帝”这一称呼广为流传,它逐渐成了这一代独生子女的代名称。由于独生子女现象是伴随着“80后”们的出生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因此“小皇帝”也成了“80后”儿童的典型形象。
一些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指出这批独生子女存在某些个性弱点,比如:胆小、谨慎、恐惧、不合群、孤僻、任性、娇气、利己、嫉妒、易怒、固执,心理上极不稳定,社会适应能力差,性格不健全,品质、道德落伍。这些缺点被称之为“独生子女综合征”[1]。
20世纪90年代,在父母溺爱和社会担忧的环境中慢慢长大的“80后”进入了小学和中学,一个新的社会标签落在他们的头上——“垮掉的一代”。主流媒体和教育家们认为,这一代人生活条件太优越,没有经受过挫折,导致他们自私、叛逆、脆弱和没有责任感,难以承担国家未来使命。媒体上有关“80后”的新闻报道常常是娇宠任性的行为表现和为一点小事而离家出走或自杀。成人社会对他们的评价是:“垮掉的一代”,“最没责任心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最叛逆的一代”,“最娇生惯养的一代”,是“喝可乐、吃汉堡”长大的“享乐的一代”。“80后”的父辈们越来越担忧,这一代人如何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
二、“另类”与“反叛”的“80后”作家
20世纪90年代后期,“80后”们在主流媒体的负面评价、批评指责以及父辈的担忧中步入他们的青春期。“80后”由青少年期向青年期转变之时,一个新事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80后”的社会生活,那就是互联网的出现和迅速普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互联网造就了“80后”。“80后”的前辈们(“60后”和“70后”)在青少年时期也曾遭受过成人社会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只能听从长辈的批评而无法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因为主流媒体掌控在成年人手中。然而“80后”们有了互联网,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反击成人社会对他们的种种指责和负面评价,并主动出击挑战文化权威和精英名流。
在这之前,无论是“独生子女”、“小皇帝”或“垮掉的一代”,都是成人社会赋予“80后”的称谓标签,“80后”没有机会公开表达他们对自身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之初,一批少年文学写手通过文学形式表达他们的自我感受,以及成人社会规范对他们的压抑。虽然主流文学界对他们的作品不屑一顾,但市场经济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这类作品在图书市场上受到追捧,尤其受到“80后”青少年的欢迎,因为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情绪能引起他们的共振。韩寒的《三重门》、春树的《北京娃娃》、郭敬明的《幻城》相继推出,“少年写作”、“青春文学”、“新概念青春派”等命名成为图书市场上保障畅销的标签。
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出现,这些文学作品和青少年文学写手很可能像以往的青春文学一样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或者文化现象,然而,由于有了互联网,这种文化现象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21世纪最初的几年,正是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刚刚出现的时期,大多数中国人还不太会使用它,而青少年文学写手们则很快地精于此道,成为网络写手。正是通过互联网的渠道,这些青少年文学写手扩大了他们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大量同辈青少年的支持,而由他们组成的个性特征鲜明的“80后”作家群在中国社会异军突起。
“80后”一词最初就是指这批青少年文学写手,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有少数人出生于70年代末期,他们被称之为“80后”作家。“80后”这一词汇最早由“80后”作家代表人物恭小兵提出。2003年,恭小兵在某个论坛里发表了题目为《总结“80后”》的帖子,那是他对身边的一帮同龄人的生存状态及精神状态的总结。随后,这一词汇很快流行起来,几乎每一本新出的青春文学类书籍的封面都会出现“80后”字样,但其含义主要还是指“80后”作家群。2004年2月,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周刊将春树、韩寒等称做中国“80后”的代表。这一明确命名与定位,使“80后”迅速取代其他称谓成为一个广泛应用的语词,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80后”写作的关注。在2005年6月25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全球版)上,又出现了中国青年作家李傻傻,周刊认为中国的“80后”成为当下文化的关键词。
如果说“80后”作家们在其线下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对成人社会不满是温和的情绪宣泄,那么他们在网络上的不满表达则张狂、好斗和尖锐得多,而张狂和好斗性表现得越鲜明,越可能赢得“80后”们的喝彩。“80后”作家代表人物恭小兵的成名之路可以看到这种好斗程度。恭小兵于2000年5月注册网络ID,正式成为互联网中文用户。2001—2003年期间,他“怀揣硬砖无数,游荡于各大论坛,中文互联网每有战事,内外围必有此人身影”。挑起和参与各种网络论战使他成为2004年天涯社区年度网络风云人物。同年,“因其处女作兼自传体小说《无处可逃》,在天涯社区连载后引发大规模讨论,被出版商借机炒作为‘80后文学领袖’后天价买断《无处可逃》的10年版权而一夜间蹿红网络。”①参见百度百科上“恭小兵”条目(http://baike.baidu.com/view/665608.htm)。“80后”作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韩寒也是通过网络上的数次文坛大论战而名声大噪,赢得无数追随者和粉丝,最终成为“80后”的精神领袖和代言人。其中最为著名的论战是“韩白之战”(韩寒与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之间的大论战),韩寒针对白烨的《“80后”现状与未来》的回应文章《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充分显示了张狂个性,以及对文化权威的不屑一顾。这种张狂个性和挑战权威的精神受到大量“80后”的追捧。
“80后”作家通过互联网扩大了他们的社会影响,通过他们在网络上的意见表达,把“80后”们集结和动员起来,与成人社会形成对抗。对抗的最初阶段是“80后”们反击成年人权威对他们的批评指责,而后转向“80后”们主动出击,挑战社会文化领域的权威。这种对抗已经超越了文学范畴,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价值领域。在愈演愈烈的论战对抗中,“另类”和“反叛”的“80后”作家成为“80后”的精神领袖,他们带领着大批“80后”支持者们与主流媒体和文化权威们进行论战,挑战主流价值规范。2005—2008年期间,网络上爆发了几轮文化大论战,文化权威和精英名流们无一例外地落败而逃。“80后”网络写手成为社会风云人物,他们毫无顾忌地表现他们与老一辈人的不同,以及对于传统权威的蔑视。
通过网络论战,“80后”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一种社会势力,主流媒体和社会名流们在论及“80后”时变得小心翼翼、措辞谨慎,人们感到这群“另类”、“自我”、“张狂”与“反叛”的“80后”不太好惹。在这一过程中,“80后”们逐渐显示出一种代际认同感,或者说他们形成了某种集体意识,他们觉得,我们“80后”是同样的一群人,我们有共同的想法和追求,我们都感受到了现存社会规范对我们的压抑和束缚,我们不想再像老一代人那样生活与思考。正是在这一时期,“80后”这个词汇由“80后”作家的代名词转变为对整个“80后”一代人的称呼,“80后”一代成为具有代际认同和集体意识的“社会代”。他们所制造的“反叛性”的青年文化由互联网向大众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渗透。
2005—2008年中国“80后”反叛性青年文化现象,在某些方面类似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社会出现的青年反主流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发达国家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出现了“富裕社会”现象,随之而来的就是六七十年代大规模的青年反叛文化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反叛传统、反叛道德的权威和规范。这种青年文化成为当时欧美社会变革的一种推动力,尤其促进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变革。
在2005—2008年期间,中国的一批“80后”青年也给人同样的印象,他们的文学写作和网络论战形成了一种反叛性文化,挑战主流社会规范和理念。六七十年代的欧美青年是以摇滚乐作为载体对抗成人社会,而中国“80后”青年则是以网络写作作为载体对抗主流媒体和文化精英。
三、“80后”社会形象的逆转
2008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80后”青年在这两次事件中的行为表现彻底颠覆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形象。“80后”在汶川地震后的救援行动中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和感人事迹,在西方部分媒体和人士抵制北京奥运会风潮中表现出的高度爱国主义热情,以及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志愿者工作中的良好精神面貌,使主流媒体对其评价由负面转向极为正面,而“80后”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似乎也由“对抗”、“反叛”转向合作和支持。
2008年4月7日,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遭遇部分“藏独”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干扰破坏,其后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火炬传递也受“藏独”分子的滋扰。与此同时,在西方部分媒体和文化人士的鼓动下,出现了一股抵制北京奥运会和反华倾向的风潮,导致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损害,北京奥运会组办方承受极大压力。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海外大批“80后”中国留学生自愿组织起来,沿途维护火炬传递,与“藏独”分子对抗,指责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国内的“80后”青年与此相呼应,在网络上猛烈回击西方媒体和名流们的反华言论,充分显示其爱国主义热情,强烈支持中国政府举办奥运会。
在奥运火炬传递进程之中,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和北川发生8级强烈地震,导致6万多人死亡。在随后的一个多月的救援行动期间,众多媒体热情洋溢地报道了“80后”青年的杰出表现。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中国周刊》节目,以“汶川大地震:‘80后’撑起中国脊梁”为题所进行的报道采用了下述激动人心的语言:
这一刻,“80后”让我们动容!在汶川大地震中,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以无私无畏的勇敢与坚强,令世人刮目和动容:舍身护佑学生的教师袁文婷;失去10位亲人仍坚持在抗震一线的民警蒋敏;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地震孤儿的民警蒋小娟;背着病人转移导致自己流产的护士陈晓泸……在他们身后,挺立着更多与他们同样优秀的同龄人,冒险在废墟上搜救的普通士兵,奋不顾身的白衣天使,活跃在前线后方的志愿者,去而又返的献血者……他们有相同的年纪,他们来自一个共同的群体——“80后”。
2008年6月11日的《国际先驱导报》上的一篇报道声称:
2008年以来,包括地震在内一连串的危机,成了“80后”的成人仪式。这个素来强调自我、个性张扬的群体,“突然”变得勇敢和坚强起来。19岁的王君博在帐篷医院里一边工作一边擦着汗。“这对我们是一次机会,表明自己不只是温室中长大的孩子,也不是毫无用处。”“……我们就要从心灵上彻底脱掉脆弱的壳,用坚强的意念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接过前代手中的权杖。”汶川大地震,也是“80后”的一次嬗变。地震过后,“80后”在灾难中巍然挺立。
2008年6月12晚,湖南卫视在黄金时间举行了一场题为“我们正年轻”的晚会来祭奠汶川大地震一个月,整场晚会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弘扬“80后”,无论是受灾的“80后”,还是伸出援手救助的“80后”,晚会都对其颂扬赞歌。
对于“80后”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高度赞誉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达到了顶点,“80后”志愿者的表现尤其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在庞大的奥运志愿者队伍中——北京奥运会赛场约7万志愿者以及其他各方面为奥运服务的几十万志愿者,绝大部分是“80后”青年,特别是“80后”在校大学生。他们在志愿服务中表现出的良好素质、责任心、吃苦耐劳和维护民族荣誉的勇气都令人印象深刻。当然,“80后”运动员的表现更加夺人耳目,他们是为中国军团争夺奖牌的主力军。2008年8月14日《烟台晚报》以“80后奥运新势力”为题,颂扬“80后”在奥运会上的表现:“‘80后’无疑是2008年奥运会最大的支持势力,从运动员到志愿者,‘80后’在北京奥运会上成为领衔主演。”
2008年,“80后”社会形象的这一逆转表面看来似乎十分突兀,但这一转变有着社会变迁影响的逻辑,是中国崛起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80后”进入青年期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遭遇某些发达国家的遏制,与西方世界发生意识形态冲突。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20年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较为落后而社会政治制度与西方价值理念相左的国家,一直处于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体系较为边缘的位置。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转折点,之后中国经济规模猛增,中国制造商品大规模涌入欧美市场,中国的经济成就引起世人注目,它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世界上崛起。“80后”见证了这一过程,或者说他们伴随这一过程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中国的定位。这样的成长背景,使他们生成了某种大国心态: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中国及其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另一方面,政府长期实施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强化了“80后”的强国梦想。2008年之后持续数年的金融危机,又加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这一系列冲突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要走向世界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一进程无疑对“80后”的世界观念和国家理念产生了极大影响。最近发生的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也将进一步强化“80后”一代的国家意识与民族荣誉感。
四、市场竞争威力下的奋斗者
在成人社会对“80后”的评价彻底改变之后,“80后”的形象又有了新的变化。近十年来“80后”逐渐步入成人世界,他们由学校走向社会和劳动力市场,他们要成家立业和生育子女。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就业的压力、高房价的压力、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他们遭遇了大学扩招后的就业难,遭遇了房价和房租的疯涨,遭遇了全球性金融危机,遭遇了连续几年的通货膨胀。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他们开始生育子女之时,还遇上了上幼儿园难的问题。这让许多“80后”感到,他们真是何其不幸、生不逢时。正如网络上流行的“80后的自述”所表达的情绪:
我们读小学时,读大学不要钱。我们读大学时,读小学不要钱。我们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当我们不到结婚的年龄的时候,骑单车就能娶媳妇。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没有洋房汽车娶不了媳妇。当我们没生娃的时候,别人是可以生一串的;当我们要生娃的时候,谁都不许生多个的。
“80后”无疑是面临全面市场竞争的一代,他们需要应对的是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在市场竞争压力下步入成人社会的“80后”,逐渐淡化了他们身上的“另类”和“反叛”的特性,无奈而焦虑的奋斗者成为他们的新形象,“房奴”、“蚁族”、“孩奴”等都是“80后”对自身状况的描述。但与此同时,“80后”也拥有其父辈所未有的机遇,一批“80后”精英人物在文化领域、体育领域、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中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在以往的论资排辈的社会中,在规则完全由成人权威所制定的秩序中,年轻人不太可能拥有那么多的机会,以那么快的速度获取成功,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功成名就。“80后”的精英们自信而自我,一改传统中国社会成功人士的自谦和自敛的形象。网络上流行的“80后名人语录”反映了这批青年精英的个性特征:
我想我的时代来了,我那时候特别高兴。我从不感觉压力,我等待这么多年,终于来到,我不会错过每一个机会。
——郎朗(钢琴家、生于1982年)
你拍我时我都大度过N次了,难道就不许我踹你一脚。
——范冰冰(演员、生于1981年)
我不在乎起点有多高,最重要的是终点。
——姚明(篮球运动员、生于1980年)
中国有我、亚洲有我、世界有我。
——刘翔(田径运动员、生于1983年)
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
——韩寒(作家、生于1982年)
世界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
——一位“80后”的声音
当前的“80后”们在机遇、挑战、竞争和压力环境中生存,一批人脱颖而出,登上了社会的顶端,而大部分人还在努力奋斗。他们的奋斗目标前所未有地具体——为了工作、为了房子、为了爱情、为了友谊。他们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受到大众媒体的追捧,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现今的“80后”开始以成年人自居,像他们的父辈当年看他们一样,对其后辈“90后”们多有微词,当然他们绝不会像他们父辈那样严苛指责,“80后”们有更开放和宽容的心态。他们还在继续成长,他们的社会形象和个性特征还可能发生变化。但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发展,他们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共同经历了社会剧烈变革的“80后”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代人,他们是改革开放所造就的一代,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走向世界的一代。这些重大的社会变迁和历史事件建构了这一代人的个性特征,同时这一代人也在引领和推进进一步的社会变革。这一代人分享着共同的社会经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很强的利益表达愿望和能力,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和竞争压力,对自我现状不满意但对未来有信心。不过,“80后”是一个内部分化的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大学生们是“80后”社会形象的典型代表,而人数更为众多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们绝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是“80后”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只不过在“80后”最初崛起时被忽视了。“80后”是一个共性特征突出的代际群体,但同时内部的差异仍然鲜明,这种差异性体现了社会结构层面的城乡鸿沟和阶层分化的影响。
[1] 陈功.家庭革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从小皇帝到新公民[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