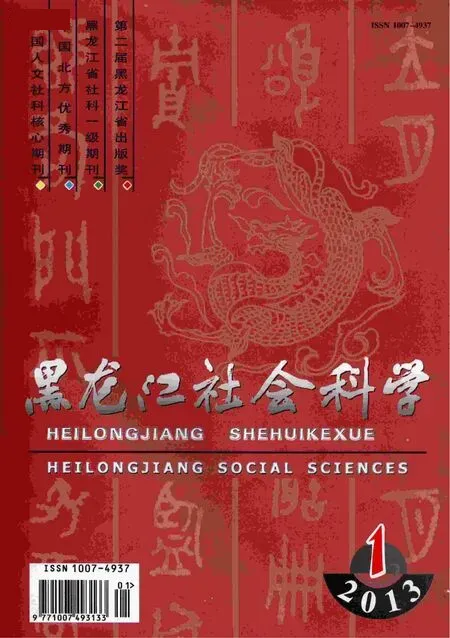简论训诂的释与译
张 望 朝
(1.中共黑龙江省委政法委,哈尔滨150001;2.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哈尔滨150001)
宋郑樵在《通志·艺文略·春秋左氏传》中说:“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如何使“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能够“通于今”?办法似乎只有两个,就是注释与翻译。这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叫做“训诂”。张舜徽先生说:“训是解说,诂是古言,解说古言使人容易通晓,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1]早期的训诂,主要是对词、句的解释,后来其范围一直扩大到整句、整段的翻译。正如张舜徽所说:“训诂二字,可以合起来讲,也可分开来讲。合起来讲,便成为注释、翻译古书的代名词。”笔者以为,也许正是这种“合起来讲”的观念让训诂从单纯的“释”扩大为“释”与“译”。这种扩大并没有使训诂变成“一件轻松的事”,相反,“古人之言”因此而显得离我们更远了,以至于我们常常把读古书同读外语书等同起来,忘记了“古人之言”恰是我们今天正在使用的语言的前身。因而笔者又认为,我们应当恢复早期的训诂,即以对词、句、段落以至全文的注释为主,最大限度地减少整句、整段、整个著作的翻译,让今人读“古人之言”时不再觉得“古人之言”是类似于英语的外族语言。
一、“释”的通达与“译”的局限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严格界线在哪里?这恐怕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论证得非常清楚的问题。作为同一民族的语言,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而来的,尽管发展、演变得有些突然和激进,但终究无法同古代汉语完全割裂开来。古代汉语里的一些字和词至今还活在现代汉语里而且活得生机勃勃,而没有学过文言文的人读起唐诗宋词,读一些浅显的文言文,似也不觉得如何吃力。这就决定了要让今人读懂古书,注释比翻译更为适宜。注释,是把古汉语中异于现代汉语、不注释一下今人就难知其所云的字、词、句子、段落挑出来,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和解释。比如《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汉马融只注释了一个“子”字:“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因为注释一个“子”字就够了,就可以让当时的人读懂这句话了,甚至可以让今天的人读懂这句话了。这就既保持了古代汉语的“原汁原味”,又不妨碍我们读懂文义,且操作简便,一通百通,事半功倍。译,不行吗?也行,问题是,怎么译。除了这个“子”字,其余的文字都是不需要译的,可恰恰正是这个“子”字,不管怎么译,都说不通。译成“孔子”?在这段话,是对的,但能说文言文里的“子”就是“孔子”吗?当然不能。译成“某个男子”?也不行,因为这个子在这里就是“谓孔子也”,不能译成“某个男子”。为什么译起来如此困难?因为译是一种词句的取代,是找一个大家都读得懂的词句取代大家都读不懂的词句。古代汉语里的很多词句,在现代汉语里无法找到在文义上与其对应得十分准确的词句,准确的全面的译,几乎成为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释,是“训诂”唯一通达可行的道路。
二、“串讲”的本质
串讲,也叫串解或者释句,就是对一句或者几句做出整体的解释,跟语文试卷中“把下列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的“译”很有几分相像,但又不是一回事。《楚辞·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汉王逸《章句》:“言万言禀天命而生,各有所乐,或乐谄佞,或乐贪淫,我独好修正直以为常行也。”这是典型的串讲,而非机械的翻译。串讲,不是一句对一句、一词对一词地翻译,而是在准确、完整把握一个句子或几个句子意思的基础上,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把这些意思表达出来,表达过程中可以有补充,可以有说明,如“或乐谄佞,或乐贪淫”,就是串讲者根据原句的意思加进去的,使原句中的“各有所乐”得到更好的解读。译,不管是意译还是一词对一词、一句对一句、一段地一段、一文对一文的硬译,都不可能如串讲这般灵活而达意。串讲的本质是“释”,不是“译”,其与“译”的不同在于其不会像“译”那样以词换词、以句换句,而是以意解意,力求意思的准确与完整。当然,串讲要求串讲者有足够的学识,且要有足够的“职业道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相当于“二度创作”,没有足够的学识,你创作不好,只有学识没有职业道德,你同样创作不好,你可能出于一己之偏私而对所串讲的文章进行歪讲、戏说。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发生过一场“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其中对法家的赞扬和对儒家的批判,所有手段主要是恶意串讲。比如,把柳宗元誉为“中唐后期卓越的法家代表”、“有唐三百年间最大的法家思想家”,而其依据是柳宗元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说的一句话:“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次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当时有人对此做了如下串讲:“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值得熟读的尊法反儒的政论。柳宗元一面批评儒家的‘圣人之道,不尽益于世用’(《与杨京兆凭书》);一面提出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说,‘皆有以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表明他的尊法反儒的态度。”[2]其实,柳宗元是以元生为例,提倡吸取各派学说的长处,清除怪诞邪僻的东西,以期与孔子的思想保持一致。究其实质,还是宣传儒学,维护儒学。
三、“释”的信、雅、达
翻译家严复在所译《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雅,达。”他的所谓信,雅,达,是就外文译成中文而言的,但有人认为,就古文今译而言,这三个标准也是成立的。对此,笔者以为,古文今译,求信、达即可,求雅是不必的,也是不可能的。原文雅,准确(信)、通畅(达)地译过来后,自然雅,如果原文不雅,你硬是给译雅了,则构成了对原文的一种背叛。《史记·项羽本纪》中范增有一句话,有人说骂的是项羽,有人说骂的是项庄:“竖子不足与谋。”范增骂谁,在此不论,且论这句话译法。“竖子”,是骂人话,相当于“小子”、“家伙”,无论如何也没法译出“雅”的效果来。何况,如果译出了“雅”的效果,“信”就没了:范增的恼怒很可能因为你的“雅”而没有表现出来。更重要的一点,古代汉语的“雅”与现代汉语的“雅”不是一回事,例如我们把一首古诗译成现代诗,可以“信”,可以“达”,恐怕就是做不到原诗的“雅”。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倘不译,则几乎人人读得懂,人人可从中领略诗中清凉幽雅的意境和这种“五绝”的建筑美,非译不可,则只可译成:
床前亮着月光,
好像地上有霜。
抬头看看月亮,
低头思念故乡。
这么译,诗的建筑美尚存,意境美则全无,一首幽雅而略带苍凉的五绝诗变成了没滋没味的打油诗。换一种译法也可:
床前啊,月光明亮,
好像在地上染了白霜。
抬起头,望着明月,
低下头,思念起我的故乡。
这么译,诗的意境美、建筑美,就都没有了。
不唯古体诗如此,其他类古汉语文体也是如此——只可释,不可译,一译,意思是说明白了,原文字中特有的意趣、节奏和规范感就没有了,而一释,即在不破坏原文完整的古雅之美的前提下,把今人不甚明了的个别字、词、段落解释清楚,方可达到信、雅、达的境界。《诗经·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宋朱熹释之曰:“呦呦,声之和也。苹,簌萧也,青色,白茎如筋。我,主人也。宾,所燕之客,或者本国之臣,或诸侯之使也。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3]有了这样的注释,再读原诗,信,雅,达,自然都来了。显然已经不需要再把《诗经》译成白话文了,硬要译,怕也只能造成对原诗意趣、韵致的一种破坏。信,雅,达,只能存在于原作中,不可能出现译作里。译出来的信、雅、达,并不是原来的信、雅、达。
四、训诂的最高境界
陆九渊说:“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读古书,如果能达到“六经注我”的境界,即走到古人跟前,让古人说出我要说的话,则是达到了训诂的最高境界。笔者以为,训诂的最高境界不是把古人变成今人,让他们用今人的语言跟我们对话,而是让今人变成古人,让我们走回到古人跟前,用古人的语言去理解古人。这就像看外国电影,不是让电影里的人变成中国人,而是要让自己变成外国人,走到电影里的人物身边去,欣赏他们的故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训诂的由来得到启发。在被认为是中国训诂开山之作的《尔雅》中,第一篇与第三篇分别以“释诂”“释训”命名,其中“诂”与“训”是分开的,“诂”与“训”都是“释”的客体,是作为两个实在对象出现的。“释,解也。诂,古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清代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豫部第九》说:“《尔雅·释诂》者,释古言也;《释言》者,释方言也;《释训》者释双声迭韵连语及单词、重辞与发生助语之辞也。”请注意,《尔雅》的“尔”,是接近的意思,“雅”,是古代较为规范的语言,也作“雅言”、“尔雅”,意为接近雅言,也就是引导我们主动地走近“雅言”,而不是让“雅言”主动地走近我们。西汉《诗诂训传》中,“诂”、“训”、“传”是三个并列的概念,这可以视为汉代毛亨在《尔雅》的基础上创立的三种“释”的方法,其中,“诂”大致为训解古词古义及其他基本词,“训”大致是训释联绵词及重言词,“传”是在“诂”与“训”的基础上阐释诗的内在涵义等。为什么要“诂”与“训”的基础上再“传”一下呢?因为仅仅依靠“诂”与“训”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完全通晓“诗”的内在涵义的,再“传”一下,把我们“传”回到“诗”的跟前去,才是《诗训诂传》的终极目的。东晋郭璞在《尔雅·序》在《尔雅·释诂第一》中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笔者以为,这里的“通”字用得极妙,妙就妙在它让我们感觉到一种运动,一种归向。什么运动?当然是我们和古人相互通达的运动。什么归向?让我们归向古人,不可能是古人归向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其一,古人是古人,把古文字翻译成今文字,是今人代古人说话,不是古人在对我们说话,代说话,不是原话,如前所述,不可能让我们感受到原汁原味。其二,只有把今天的我们变成古人——通晓古人语言文字的人,才能保持我们对古语言文字的感觉,而失去了对古语言文字的感觉,即使通晓每个古词的词意,能够准确地把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古文在我们的心目中也只能是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文字符号,那样的话,训诂就成了一门机械或者技术,没有什么学问可言了。
五、“释”的语言学价值
研究古代语言文字,首先要从中发现古人使用语言、文字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的训诂之学不能停留在“译”的层面,即仅仅是把古文字的语意用今天人人都听得懂的语言说出来,还要对古人的用字习惯、修辞方法、表现方式做深入研究。而这,只能通过“释”来完成。在这方面,古书中的注释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晋杜预注曰:“已死复生,白骨更肉。”[4]957这就让读者明白,“生死”与“肉骨”都不是并列结构,而是动宾结构,“生死”,是说使“死”变成“生”,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起死回生”,“生”,在这里是动词,使动用法,相当于“使……生”。与之相同,“肉骨”是说使“骨”生出“肉”,“肉”在这里也是动词,也是使动用法,相当于“使……生出肉来”。名词直接用作动词,这样的实词活用是古代汉语的一大特色,至今对现代汉语产生着重大影响。比如,今天我们常说的“有事就电我一下”,这个“电”,是名词“电话”的简略,“电我一下”,是说“给我打个电话”。再比如,“你别气我”,这个“气”,现在已经完全是动词了,意思是“使……生气”,不难发现,这完全是古代汉语的使动用法造成的,也就是说,“气”,本来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之后,可以是“生气”,也可以是“使……生气”。这种现象,只有“释”能只将其说清楚,“译”是做不到的。此外,古代汉语一些特有的表达方式、修辞手法,也只能通过“释”来解读。赋和兴是《诗经》常用的表达方式,对后来的诗词写作影响很大。宋朱熹在其《诗集传》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又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兴也。”[4]273《诗结·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毛传:“兴也。”[4]279这样的注释,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阐释《诗经》,都是对我们的古人如何使用语言的一种规律性解读。这样的解读,“译”同样是做不到的。古人为文,喜欢用典。对于典故的诠释更能体现“释”的语言学价值。晋左思《咏史》:“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唐李善引《史记》注曰:“荆轲之燕,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5]用一段史料解释一句诗,这有什么语言学价值呢?表面上看,没有,但细思之,大有——中国的很多成语就是这么形成的:一段史事发生后,有人记录此事,有人利用此事,比如用它作诗,用它作比喻,用它说明道理,等等,无论是记录还是利用,都无意中生成出可资再利用的成语。这个过程本身表征着中国古代汉语的某种生成规律。“旁若无人”这句成语,不正是这样生成的吗?荆轲和高渐离都死了,这句成语却活了,至今还在被我们使用。“围魏救赵”、“揭竿而起”、“项庄舞剑”等等,都是史事,又都是成语。这样的成语,译是译不透的,只有通过释把相关史事说清楚,才能解读出它的全部信息。
六、释的自身文献学价值
请看《水经注》中的一段: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怎么看这一段文字也不像是“注”,更不像是某个“注”中的一段。然而,它偏偏就是,因为它来自一部了不起的专“注”——《水经注》。中国古代有一部记载河流的专著曰《水经》,关于其作者,历来说法不一。一说其为晋郭璞撰,一说其为东汉桑钦撰,又说其为郭璞曾注桑钦撰的《水经》。当代“郦学”家陈桥驿认为,即使汉桑钦撰有《水经》,晋郭璞为其作注确有其事,但这部《水经》和《水经注》也都已失传,今本郦道元所注的《水经》当是另外一部,是无名氏所为。关于《水经》成书年代,诸家说法也是不一,全祖望认为是东汉初,戴震认为是三国时作品,今人钟凤年又认为是新莽时所作。诸说虽难确认,但大体可以将其确认为汉魏时期之作。富有戏剧性的是,《水经》作为失传之著,早已退出人们的视野,为其作注的《水经注》却作为重要的文学文献和地理学文献流传至今且依旧光芒四射。余秋雨先生对其文字之美赞叹连连,称“清荣峻茂”、“林寒涧肃”等文字让后人“再难调动修饰的辞章”。至于它的地理学价值,一些方家认为也是前无古人的。我国古代也是有过一些地理书籍的,但没有太成体统的,《山海经》过于荒杂,《禹贡》、《周礼·职方》只能算是个地理轮廓,《汉书·地理志》的记述过于粗略,而一些诗赋限于体裁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地理学价值。就《水经》一书而言,虽专述河流并且具系统纲领,但其没有记载水道以外地理情况。郦道元游历大好河山时所见所闻十分丰富,为了把这些丰富的地理知识传于后人,他决定以《水经》一书为纲目,对全国地理情况特别是水文情况做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注释。正如王先谦所说,郦道元注《水经》的目的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王先谦合校本序》)。郦道元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水经注》虽是注释《水经》之著,但其自成一体,自成一格,自成一家,自成一脉,把训诂学的释推向一个近乎完美的境地:对中国古典文献的“释”,本身就可成为一种著述,一种文献;而“译”,似永难达到这样的境地。
[1]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0-131.
[2] 简明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67.
[3] 朱熹.诗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9.
[4] 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李善.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