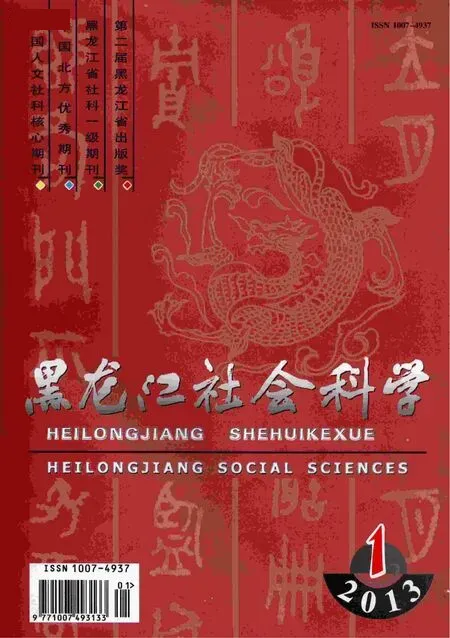儒家自然观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王 国 良
(安徽大学 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合肥 230039)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任何哲学思想在其发生发展和发展的过程中,都要认识和处理两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他人、社会(历史)的关系。两种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又是首要问题。传统儒家哲学主要是从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立场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如果借用思维模式的术语,可说儒家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式。儒家哲学文化中包含不少对自然的客观认识,这些客观认识体现了儒家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界万物的本质同源、和谐交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儒家自然观就是儒家对自然的总体看法。儒家自然观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其次是人与自然的本质同源。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乃是人与自然本质同源的认识基础,而后者则是前者的理论深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自然观是中国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农业生活使人能够最近距离地接触自然,从而能够对四时的交替、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积累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发展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中国较早的经典之一《诗经》中的许多诗篇表现了人类跟随自然的节奏而生活的过程和情趣,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体验到与生动的自然界有不可名状的息息相通之处,由此积淀为人与自然和谐冥契的统一心理。《豳风·七月》便表现我华夏先民跟随自然的节奏而生活的时新情绪:“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四月秀葽,五月鸣蜩”,“七月食瓜,八月剥枣”,“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朋酒斯享,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中表现华夏先民通过劳动而感受到自然的生生不息以及人的性情与自然性情水乳交融的和谐统一。《王风·君子于役》和《小雅·无羊》诗之可贵在于写出鸡群、牛羊以及牧人的悠然自得之态,写出人与生物的亲切和谐。《诗经》中许多诗篇都表现了华夏先民凿井耕田的生活自在,对万有生命的欣喜以及对自然全盘溶入的愉悦安足。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在继承发展了春秋以来的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万物一体的自然观。《论语·先进》记载,一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请众弟子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以积极入世、有所建树为志,孔子皆哂之。轮到曾点时,曾点“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慨然叹曰:‘吾与点也!’”可见孔子眼中人生的极乐境界正是人与万物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儒家自然观指出,人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也有责任维护自然,而保护自然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条件与家园。儒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还体现在农为本的生产生活顺应自然节奏、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史记·孔子世家》曾记录孔子的话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我们无从考证这句话究竟是否为孔子所言,但此句话却是代表了儒家的自然观,即表达了孔子对破坏生态平衡、破坏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举动的义愤。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告诫人们要有节制的利用自然:“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数张渔网不能同时在一个池塘里捕鱼,鱼类生物才能持续繁衍,上山伐木必待冬季,春季万木生长季节不能砍树,才能保证林木不可胜用。荀子则认为,要想达到政治稳定、国富民安,其总要基础之一就是维持生态平衡:“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蟮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犹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还认为,人只要爱护自然,就能够与自然相生相养,长期和谐共存。《礼记·月令》要求人们根据一年十二个月天文以及气候的变化节奏开展农事活动以及政治活动。例如春季,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母畜),禁止伐木,毋覆巢(倾覆鸟巢),毋杀孩虫(幼虫)”,“毋竭山泽,毋漉陂地,毋焚山林”。许多国家政府都规定春季禁止伐木采樵、在动物繁殖期间禁止捕杀鸟兽等等,都是受到儒家自然观的影响。
传统儒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朴素而又精辟的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资源。积极继承和有效开发这些思想资源和生态智能,无疑将对现代社会条件下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有所启发和助益。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即正德、利用、厚生的思想,《易经》中包含丰富的认识自然的思想,神话传说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蕴含着丰富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但儒家思想中重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人类要有节制的利用自然的思想显然具有更为高远的人文价值。
二、人与自然本质同源
儒家自然观的第二方面含义是人与自然的本质同源。人与自然万物、植物、动物同根同类,人是天地万物之一部分,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万物虽然由于物种的不同而各有特殊性,但在动物性与所遵循的自然规律方面都与自然一致,这种一致是人与天地万物共同遵循的最高原则。《易传·系辞》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传》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辞上》,肯定自然界生生不息,天地的根本德性就是“生”。孔子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荀子虽然“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但只是否定天具有神性,而充分肯定天的自然醒,并有自身的自然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荀子认为人与自然万物相生相养的前提依然是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并肯定“生”为自然之本:“天地,生之本也”(《荀子·礼论》),万物与人都是由自然的长期演化发展而产生:“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也是因自然天功的作用而“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这个“生”字,表明儒家认为自然的本质就是“生”,北宋理学家确立儒家的生命本体论即是依据此“生”字。
北宋儒家学者继承了先秦儒家提出的“生”的概念,并将《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与孔孟的仁学结合起来,提出仁的重要内涵即是“生”,认为宇宙最高本体“理”就是“生之理”,仁、生、理本质相同。
朱熹对生生之理之仁作了总结提高,提出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1]“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2]朱熹反复说明的“天地生物之心”,就是指天地之“生意”、“生理”,天只有一个“生理”,天地“别无所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3]
理学家把本来标志人的伦理性、精神性品格的仁范畴与大易的生生易道结合,把仁提升为本体范畴,这一作为本体的仁既概括了自然界与人的无穷发展过程的统一,又是两者实质的提炼,即把自然界的生理与人的性理结合起来,以生生不息之仁实现天人合一。仁有了新的内涵,从人道、人的精神性品格的范畴上升为天道,体现了自然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生不息,无有穷尽的过程。
儒家学者认为,人与自然本质同源,又与自然万物同根同类,那么,人就能够从自然万物中提炼出审美的价值以及人格的标准,并化自然万物的品质为人的品格。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论语·子罕》)秋尽冬来,万木凋零,松柏却郁郁青青,傲立苍穹,这分明是崇高美的境界,更可以启发人的坚贞不屈的品格。孔子对山水亦有独特见解:“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这是孔子从山水中获得了培养人的品格的启示:“仁”这一品格应像高山一样巍然耸立,而“智”这一品格则应像水一样具有流动性与灵活性,并能够永不停歇地向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对于水的看法,指出流水象征君子之“志于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流水所到之处,满盈之后才继续前进,君子也要像流水那样,为了实现志与道而坚定地一步步前进。美玉则具有仁、知、义、行、勇等多种君子的品德,荀子认为“夫玉者,君子比德也”(《荀子·法行》)。荀子则记载了孔子对于水具有多种品质的话语,“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其万折也必东,似志”(《荀子·宥坐》)。北宋理学家喜欢观天地生物气象,体验自然之生意,周茂叔窗前草不除,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张载观驴鸣,体会自然之生命气息。二程则以自然现象来类比儒家学者的圣贤气象:“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4]从以上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儒家的自然观不仅具有认知的价值,同时也饱含审美的体验与伦理的观照。
三、人高于自然的生存观
在被儒家奉为《五经》之一的《尚书》中,就提出了人高于自然的观点:“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天地生万物,人是万物之精华与灵长。荀子与《礼记》都表述了“人最为天下贵”的思想。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固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在荀子看来,人之所以高于自然,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人具有德性伦理以及团队精神。周敦颐和王阳明都认为人高于动物,原因就在于人在宇宙自然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中正仁义”之德性。因此,“惟人焉,得其秀而最灵”[5]。可以说,人之“知”与动物之“知”是有本质不同的,动物之“知”完全产生于动物性的本能,而人之“知”则能够认识自然万物,并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万物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而人类正是通过认识与利用自然而达致高于自然的生存境界。最明确的表达人利用自然而生存的观点的大儒应是王阳明。王阳明则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人的良知提升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提升到“与物无对”的绝对高度,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本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霜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系统,人是该系统的最高目的,其他事物都是为了人而存在,如果没有人的良知,其他事物的存在都失去了意义。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这一气流通说是存在意义的连续,故“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人的“一点灵明”决定了天地草木瓦石的意义。自然万物,包括动物,都在与人的关联中才物尽其用,各遂其性。天地万物不能认识、支配自然,只有人能够认识自然、规定自然。王阳明认识到,自然万物是互相依赖、互相为用的序列,低一级的生物服务于高一级的生物,人处于这一序列的最高处,人虽然要关爱万物,但不得不取万物以为用,这是具有合理性的极有价值的哲学推理。
应该强调的是,儒家认为人高于自然,必须利用自然而生存生活,但正如前述,儒家更强调人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要保护自然,平等对待自然万物,因为自然乃是人的生存家园,必须维护自己家园的生态平衡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绝不允许破坏自然。儒家认为要把核心价值仁爱的精神施及于自然,孟子就提出了为后世儒家一致尊奉的对待自然万物的基本原则:“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礼记·中庸》提出通过尽人之性达到尽物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就是,使物成之为物,即使物各得其所,按照其自身固有的秉性和规律存在与运行。《中庸》还提出“成己成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成己成物是指由己及物,自身有所成就,也要使自身之外的一切有所成就。从张载到王阳明,也都主张人与万物为一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人类要利用自然而厚生,但人又要像关爱人类自身一样关爱自然,保护生态,而不是破坏自然,毁坏自己的生存家园。
四、儒家自然观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应该承认,儒家传统的万物一体的自然观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与不足。儒家传统不重视认识论,对人如何在认识、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没做认真具体的、实际可操作的探究。西方哲学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支配自然方面自有其长处。但与儒家自然观的缺陷相比,儒家自然观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更多的合理价值。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越来越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西方哲学受到犹太教与基督教支配自然、征服自然思想的影响[6],过度张扬主客二分,导致滥用自然,剥削自然,破坏自然,结果是破坏人类自己的生存家园,过分地突出人与自然的区分,没有看到人与自然、植物、动物虽有级差区别,但根本一体的本质特征,缺乏怜惜、关爱自然之心,甚至受到进化论的消极影响,把人类也分出优劣等级,蔑视所谓“劣等民族”,缺乏人类平等同类的关爱同情心,过分夸大自然界的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并运用于人类社会,把人类社会变成屠场,对天神天意缺乏敬畏之心,导致天命的沦丧,诸神的退隐。现在,保护环境、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几乎成为全球共识与普世价值。儒家万物一体的自然观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对人类中心主义为满足人类需求而牺牲自然环境的弊病起到矫正与遏制的作用,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视角看待自然。西方许多环境哲学家在分析环境危机的思想与文化原因、探寻环境哲学智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儒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又有序列阶段差别的思想被西方学者概括为“在自然之中生存”的合理生态思维[7]。
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污染、环境破坏只有通过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而不是到古代思想中找出路。这种看法是狭隘的进化至上主义者。事实证明,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而有些问题科学技术根本无法解决。水污染可以通过污水处理来解决,但河流湖泊、海洋污染导致1 000多种鱼类灭绝,科学技术是无法复原的。同样,荒山秃岭只有通过重新植树造林来解决,水土流失也只有通过在江河上游退耕还林、恢复植被来解决,特别是石油的开发与利用,造成大量的废气、毒气,造成大气污染、温室效应,而无限制地开采石油对地球本身会造成什么破坏、或已经造成什么破坏,我们是根本不知道的,要避免环境危机的发生,只能是减少开采,改换思路,寻求可替代的清洁能源。
儒家人高于自然的生存观,不同于西方的征服自然观,对正确认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积极意义。在当代西方,一些人完全抹杀人与自然物的区别,认为动物与人具有同样的权利,具有同等价值,以致主张在夜间宁可让蚊子叮咬也不要打死它。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在保护生物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是抹杀人与动物的区别,主张割肉贸鸽、以身饲虎,忽视了人与动物的级差区别,不惜牺牲人类来维护动植物,过度地伸张了人类的慈悲之心。
总之,我们现在建设生态文明、探索现代环境伦理时,可以运用儒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境界为指导,充分汲取其合理因素,重视、吸收西方哲学中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精神,合理地利用自然,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也使自然得到按其自身规律要求的发展,使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存,使自然环境成为人类的美好家园,使天地本身所具有的无言之大美,既按其本性、又符合人类最高审美境界追求的面貌展现出来,让万物一体同时也成为真善美的统一。
[1]朱熹.仁说[M]//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朱熹.孟子或问[M]//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五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程颢,程颐.二程集: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周敦颐.周敦颐集:太极图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60-161.
[7]彼得·S·温茨.现代环境伦理:代总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