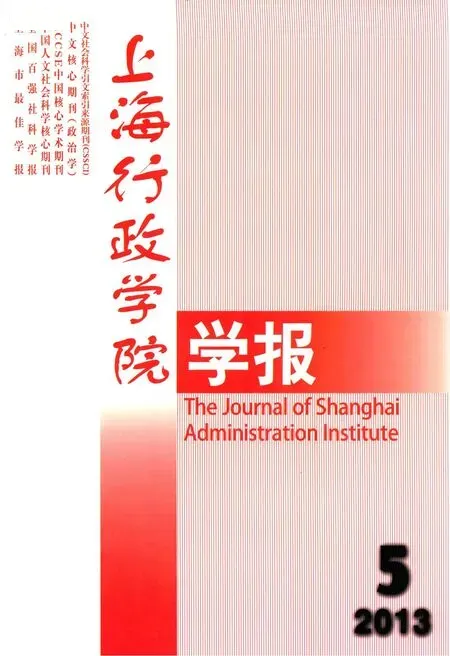论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辩证关系*
衡 霞 付亚萍
(四川大学,成都 610066)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急剧的经济变革与社会转型,在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伴生着较大的社会利益冲突,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为表征的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也呈上升趋势。有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每年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8万起,平均每天多达200余起,年均增长22.2%,参与人数年均增长17.8%,①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实质上,危害性大、感染性强的群体性事件并非突发,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②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是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源头,群体性事件中利益诉求者愿望一般能得以满足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又成为其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源,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
一、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相互依存关系
1.城乡基层社会风险决定群体性事件的形式与程度
过去的数十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也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时代,然而转型中的种种社会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也就逐渐成为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滋生的“养料”,随着我国转型的不断深化,所积聚的风险也越来越多。正如贝克所言,“原本无害的东西突然间怎么就有危险了:酒、茶、面条等等。肥料变成长期毒药,造成全世界的后果。过去一度被大肆夸赞的财富来源(核子、化学、基因科技等等)一变而为不可见的危险来源③。”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特征也同样明显。新中国成立以来,虽时有群众闹事、工人罢工、学生请愿等群体性事件发生,但其始终是极少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群体性事件保持高发多发态势。种种实践表明,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
(1)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中的受挫者构成决定群体性事件的具体形式
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中的受挫者的界定有着浓厚的建构主义色彩,随着社会风险内涵的拓展和人们风险意识的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是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中的受挫者,其范围不再囿于传统的弱势群体,除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以外的许多人,甚至大学毕业生、公务员都时有社会挫败感,越发倾向于把自己归为弱势群体,于是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中的受挫者群体队伍越来越大,且来源多元化,素质高端化。大部分受挫者最主要的期望是捍卫其合法权益,得其应得,而少数受挫者则不满、愤怒情绪高涨,主要期望是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由此可见,大部分受挫者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尚能选择以法抗争、以理维权。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具有打砸等暴力色彩的社会泄愤事件大有抬头之势,如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的海南东方市暴力袭警事件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煽动了广大不明真相的普通公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还涌现出一些新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如厦门PX事件中的市民散步事件、广州出租车司机集体喝茶事件等,这些温和而文明的形式也不乏力度的充分表达了民意,使其所在群体能够更加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
(2)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大小决定群体性事件的剧烈程度
从牛文元的社会燃烧理论视角来看,社会堆积的燃烧物质的数量与火势大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可燃物越多,社会燃烧的火就越旺,燃烧时间就越长,破坏力就越大,而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无疑就是燃烧物质,其大小直接决定着群体性事件的剧烈程度。例如瓮安事件表面上看似由简单的“学生溺水案件”点燃,但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当地民众对基层政府与民争利、强势打压群众、利益分配不公平等现实的长期不满,导致社会风险长期积聚,难以释放,在细小事件触动下,许多利益无关的民众却情绪激动,积极响应,从而发生了破坏性极强的群体性事件。与这些剧烈的群体性事件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年成都市锦江城市花园事件,小区业主通过举横幅、散发传单、围墙喷墨等方式,对在小区附近修建变电站的做法提出抗议。该群体性事件构造较为简单,引爆的只是单纯的环保风险,属于城市新兴风险,民怨虽大但不深,因而性质较为温和。另外,环保风险社会后果虽大,但因其并不如事关利益分配、社会公平、官民冲突等社会风险那般触及公众道德底线,故其一般情况下不会引发过激的公众言行。
2.群体性事件是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集中显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迅猛增长之势,到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4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陷阱”,将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局面。中国政府和学者为绕开这一怪圈做了诸多前瞻性部署,使得经济继续稳步增长,2010年人均GDP达4300美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济高增长背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也在增多,城乡基层社会蓄积了各式各样的社会风险,近年来不断涌现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社会风险的集中显现。
(1)群体性事件集中显现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雷区”
从近二十年来的全国性群体性事件来看,八成以上是维权事件,而农民维权中的土地问题又占了六成以上;城市发生概率为群体性事件总量的九成左右,集中于医疗、教育、企业改制、执法等领域。由此可见,群体性事件集中显现了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雷区”所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风险无疑是农村社会风险的主要“雷区”,而城市社会风险的“雷区”则呈现多元化趋势。另外,官民矛盾也是极其显著的社会风险而且起着巨大的助燃作用,在很大一部分群体性事件中,当地前期蓄积的官民矛盾会被轻易引爆,助长民众的愤怒情绪。官民矛盾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尤为凸出,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亟待提高。
(2)群体性事件集中显现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防控“软肋”
从群体性事件的区域分布特点来看,当前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主要发生在正处于经济开发的地方,社会创造出大量新的社会财富,但是利益分配格局混乱复杂,冲突纠纷层出,于是这些地方成为社会风险的渊薮。事实上,经济越发达,群众权益意识越强,对社会不公平的容忍度越低,致使这些区域的群体性事件不断。从群体性事件的高发领域来看,每一次官民冲突都可能是对公共部门权威和合法性的冲击、蚕食,影响到党和政府执政根基的稳固程度。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来看,基层政府在风险防控时普遍强调制度建设,忽视公民风险防控能力建设;局限于静态防控,动态不足;部门各自为战,缺乏协同联动;专业性、可操作性不强等等。现代社会的风险更加复杂、隐蔽,防控难度系数较大,但风险防控是公共部门提升治理水平,构建和谐社会之路上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二、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相互消长关系
1.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是群体性事件防治的抓手
群体性事件是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显性化,社会风险是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源头,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有很强的解释力,所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最终无疑还是要回归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防控,以社会风险为抓手,从源头上根治群体性事件。
(1)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意识的强化是群体性事件防治的起点
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意识的强化重在风险文化的构建,整个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关注高速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的氛围,这是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但是旨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我们绝不应该盲目乐观地陶醉于美好的现状,麻痹大意,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地提醒着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当然,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应对者不只是公共管理部门,公众也是责任主体。公众对社会风险的认知、风险偏好、对风险的心理承受度、应对风险的能力等等都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度,例如公众对社会风险的心理承受度越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越小,即使发生了,公众产生恐慌、骚乱的可能性也越小。
(2)城乡基层社会风险预警是群体性事件防治的关键
社会转型期是风险高发期,城乡基层社会风险预警尤为必要,它包括社会风险的监测、预测、预报和预控。④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和科学的风险预警方法可以让预警者准确地把握社会风险产生条件、现状、演变规律等,削弱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为公共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大大降低风险管理和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社会成本,低耗维系社会稳定。目前已有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等,包括美国的汉厄设计出的 “富兰德指数”,埃·蒂里阿基安提出社会动荡发生的经验指标,美国国际报告集团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的风险分析指标体系(ICRG),美国外文政策研究的“政治体系稳定指数”(PSSI),宋林飞的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标体系(SRSS,1995年)等。这些指标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量化社会风险,但其的普适性、精确性、可操作性等始终无法保证,这也是社会风险失控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的财政体制对预防工作重视度不足,拨款有限,而社会资本更是不发达。为了更有效的防治群体性事件,加强社会风险预警建设势在必行。
(3)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控制是群体性事件防治的本质
群体性事件都是由城乡基层社会风险孕育发展而来,所以在群体性事件防治过程中要透过现象抓本质,以社会风险为主线开展工作,故在一定程度上,群体性事件防治的本质就是识别风险、防止风险扩大和及时化解风险。一是加强对社会风险的日常监控,迅速、准确、全面地识别群体性事件中显性的和隐性的风险源,辨别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准确判别社会风险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的临界点,加强群体性事件的信息管理,控制社会风险燃烧温度,防止群体性事件扩大化。三是理顺利益关系,重建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利益格局。但是由于利益关系一般都是错综复杂的,加之许多社会风险之间又有交织,所以局部的小调整往往只能治标,维系暂时的稳定。其实当前的不少社会风险都是体制性原因造成的,迫切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和社会建设,从而方能从根本上有效化解社会风险,走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困境,让社会更加公正和谐。
2.群体性事件是城乡基层社会风险防范的动力
(1)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后果是城乡基层社会风险防范的直接动力
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者往往情绪激动、破坏欲望强烈,尤其是在一些社会泄愤事件中,不仅使广大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还使当地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软化甚至瘫痪。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选择体制外的非常渠道表达利益诉求的行为充分表现出其对公权机关的不信任,甚至愤怒。若其利益诉求在群体性事件之后仍得不到满足,那么负面情绪还会升级,对公权机关更加不信任;社会旁观者被这种负面情绪感染后,同样产生对公权机关的不信任感,造成政治信任的整体性坍塌。此外,由于官民互动渠道不畅,许多利益诉求只有通过群体性事件的形式提出时才会得到官方的重视和回应,这种被动地、撞击式地化解社会风险的做法会给城乡基层民众造成“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觉,形成负面的利益诉求表达示范。基于此,为了确保社会文明和法治民主的稳步前进,公共部门需要重视群体性事件泛滥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防范城乡基层社会风险,降低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2)群体性事件的经济后果是城乡基层社会风险防范的外在动力
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增长的关键所在,而群体性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暴露出的制度不合理等社会现实会对公众的生产热情造成不良影响。据香港《大公报》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天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多达200起以上,换言之,也就是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脱离正常的生产岗位,在造成自身生产活动中断的同时,干扰、妨碍着他人的生活、生产,这不仅增加了社会人力成本,还阻碍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对既有财富的破坏,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在利益分配链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预期无法共享发展改革成果时,自然无法全心全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共谋发展。无疑,群体性事件给公众带来的种种顾虑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社会风险,需要公共部门加以高度重视。
(3)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后果是城乡基层社会风险防范的内在动力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关系结构性紧张的后果,不仅扭曲社会心态、滋生社会摩擦、动摇社会向心力,降低公众的安全感、信任感、认同感、归属感,还会加剧公众对公权机关的不信任,成为滋生动荡的社会土壤。一方面,群体性事件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发生连锁效应,会形成不良的社会示范。例如2008年重庆发生“11·3”八千辆出租车罢运事件,在紧接着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湖北荆州、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广东汕头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罢运事件。⑤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将降低社会凝聚力。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使冲突双方的矛盾激化,如果协调、化解不力,会滋生更大的分歧和冲突,彼此之间的尊重、信任和合作崩溃,加大社会整合的难度,社会秩序难以维系。在这样涣散的社会面前,纵使我们有再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也终将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
三、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相互转化
1.城乡基层社会风险向群体性事件的转化
群体性事件是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不断积聚与激化的过程,社会风险直接决定和塑造着群体性事件。朱力指出,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源是当前社会结构中最易滋生社会不稳定的三大风险源,⑥虽然不同类型的社会风险不一定会以相同的演进逻辑转化为不同样式的群体性事件,但是其内在机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1)政治风险向群体性事件的转化
政治风险是指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域所存在的社会风险,⑦该风险是由政治原因引发的,对一国政治运行甚至整个社会的运转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将其精辟地概述为“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党员干部作为社会管理监控者,缺乏对社会现状的了解和社会变化的把握,也就会丧失及时发现、缓解、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良机,最终酿成社会风险升级为群体性事件的严重后果。如果没有能力作出英明的战略选择和高质量的日常决策,很难发挥“领路人”、“服务者”等作用,当在“官本位”价值观念驱动下,“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受到严重动摇。官民之间的这种冷漠和疏离即是群体性事件萌生的原因也是催化剂。尤其是当“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成为常态,缺乏渠道消解时,由政治风险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将不可避免。
(2)经济风险向群体性事件的转化
公共管理领域的经济风险包括,收入分配、经济发展模式、失业等引发的风险等。在收入分配领域里,东部地区的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分别是西部与中部的2.03倍和1.98倍;⑧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一直保持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以上,若严格算上医疗、教育、养老等隐性福利,我国城乡差距高达6:1。⑨在追求经济增长方面,部分地区引进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或是无节制地滥挖滥采,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生产经营活动,恶化了当地的气候、水资源,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此以外,就业与否跟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直接挂钩。以高校毕业生为例,2010年就有约380万的毕业生不能进入白领岗位,⑩许多人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作为“蚁族”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和底层。该群体属于高知热血青年群体,风险隐患极大。当上述各类经济风险累积值超过临界点,或叠加后超过临界值时,经济风险将向群体性事件转化。
(3)社会风险向群体性事件的转化
本文所指的社会风险是狭义上的,与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相区别而并列的一种风险,主要包括社会阶层结构失衡风险、社会保障滞后风险、社会心理失调风险等。亨廷顿曾指出“中间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⑪如果缺乏良性的中间阶层赖以形成的土壤,社会将极化发展,呈倒金子塔型,从而滋生冲突、反抗、动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倒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中广泛群体的社会保障,不少民众无法享受国家和制度的庇护,只能独自应对社会风险,使得其产生被体制抛弃的感觉,从而走上对抗体制的道路。社会心理失调使社会心理走向混乱和扭曲,对社会和政府的焦虑、迷茫、不满、怨恨、愤怒等消极情绪增多,相对剥夺心理、落差与攀比心理、保守与惰性心理、“今不如昔”的怀旧心理、短期行为与浮躁心理、冷漠与无助心理等普遍存在。⑫如果放任其滋长蔓延,终会衍生为现实层面的不和谐,即社会冲突;当许多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心理失调者聚集在一起时,群体性事件就可能会生成;非利益相关者加入后,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后果将扩大。
2.群体性事件向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转化
(1)维权类群体性事件向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转化
由于对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公共部门对群体性事件回应性很高,长期积压的群众利益诉求一般能迅速地得到满足,事态得以平息。当地既快速地恢复了社会秩序,实现了社会稳定,维权者又捍卫了权益,二者各得其所,貌似没有不妥之处。殊不知这种群体性事件维权模式隐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即诱发“政策激励型”群体性事件⑬的形成,公众发现群体性事件这一维权手段屡试不爽,而且群体性事件规模越大,自己就越有话语权,在维权谈判中越是处于优势地位,所以越来越多的维权者在经过权衡后会拿起群体性事件这一武器进行维权。某种程度上,维权类群体性事件给维权者带来的利益满足产生示范效应后,又将给城乡基层社会带来未知风险。
(2)泄愤类群体性事件向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转化
泄愤类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者与导火线并没有直接利益冲突,而是借偶发事件,通过围堵、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宣泄焦虑、不满、愤怒、怨恨等负面情绪的群体行动,且泄愤对象一般是政府、公安、法院等公共部门及其公务人员。辩证地来看,该类虽然以破坏为主,却让民众宣泄了不满,警醒着公共管理部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使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显性化,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但又会制造新的社会风险。如泄愤者们面临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当地民众面临正常生产生活中断的风险;公共部门面临社会失控的风险;社会心态面临深度扭曲的风险;社会风气面临恶化的风险;法治和文明面临倒退的风险等等。也就是说,泄愤类群体性事件并不必然会如行动者预期般改善当地民众的生存现状,反而会必然地让社会风险激化,并滋生新的社会风险,由此可见,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且危害极大的行为。
(3)网络群体性事件向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转化
网络群体性事件虽然发生在虚拟社会,但是其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因为其参与者也是现实社会的主体,它是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在网络社会的折射,也可能会激化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即遵循“从现实社会中来,到现实社会中去”的演进逻辑。在我国,超过4.57亿的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达18.3小时,如此庞大的群体足不出户,若为了吸引眼球等,动动嘴就有可能夸大、扭曲事情真相,极易造成社会精神层面的波动,从而埋下社会安全隐患,为现实层面的社会动乱准备了心理土壤,这就是纯网络态群体性事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所在。但是,大多数纯网络态群体性事件在网络社会生成后,还向现实社会蔓延,与现实社会互相呼应、相互推动,如“天价烟局长”事件。网络与现实的交互使得这类网络群体性事件尤为不好控制,公共管理者对事态发展往往难以把握,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如何控制,这使得网络向现实转变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公共管理的薄弱环节甚至盲点所在,从而成为挑战社会秩序的风险。
从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分析中可以看到,许多社会不和谐因素都与社会管理缺失相关,公共管理部门与人员必须要正确认识两者的相互依存、相互消长与相互转化的关系,从提升理念、健全机构和完善制度着手,建立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动员社会力量,化解城乡基层社会风险,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注释:
①胡联合、胡鞍钢、何胜红等:《中国当代社会稳定问题报告》,红旗出版社,2009,第139页。
②童星、张海波:《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学术界》2008年第2期。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著),汪浩(译):《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性的路》,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第52页。
④陈元章:《转型期中国突发事件社会风险管理研究》,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5月。
⑤ 宋宝安、于天琪:《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9期。
⑥曹钰:《构筑和谐社会创建幸福家园——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与方略专家访谈》,《人民论坛》2005年第2期。
⑦ 谢俊贵:《当代社会风险源:特征辨识与类型分析》,《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⑧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9年:社会经济与形势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⑨ 张劲松、陈璐:《论仇富现象的原因及化解》,《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⑩《教改纲要专家:今年380万高校毕业生不能当白领》,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
⑪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51页。
⑫ 张宇:《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心理失调与调适》,《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7期。
⑬王德福:《政策激励型表达: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一个分析框架》,《探索》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