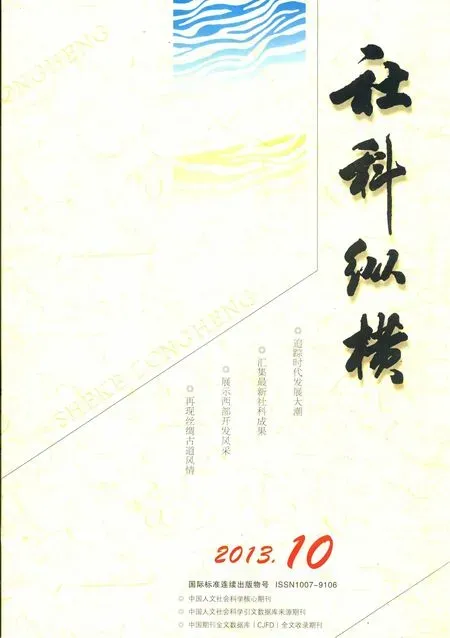生育权行使路径构造及规范依据之审思
姜大伟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重庆 401120)
我国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但对生育权行使的要件未予明确,这不仅导致理论上的争论不休,而且实务中出现的生育权冲突亦难化解。生育权是自然人因生理本能而享有的人格权利,但享有生育权并不必然等同于能行使生育权,生育权行使是生育主体实现生育愿望的现实状态,是生育主体之生育权从应然到实然的过程。在现代社会,自然人如何行使生育权尚需设计出一条合理的路径。
一、理念澄清:生育权行使是否必以缔结婚姻为前提
自人类进入个体婚时代以来,生育与婚姻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是生育的前提和基础,生育则是婚姻的基本目的之一。现代社会以来,虽然传统的生育观念有所变化,婚姻并不必然生育,生育亦并不必然依赖婚姻,但无可否认,婚内生育模式仍是社会主流,婚姻与生育的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生育权行使以缔结婚姻为基础,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生育以婚姻为基础,符合子女最大利益原则
缔结婚姻,组建家庭,是进行生育的前提条件,以家庭为单位的生育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基础。费孝通指出,社会所容许出生的孩子必须能得到有人抚育的保证。在孩子出生以前,抚育团体必须先以组成,男女相约共同负担抚育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合作,两性分工与抚育作用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配合夫妇,组成家庭,抚育作用之所以能使男女长期结合成夫妇是出于人类抚育作用的两个特性:一是孩子需要全盘的生活教育,二是这教育过程相当长。孩子所依赖父母的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1]。在健全的家庭里,孩子所受到的教育与关爱远比单亲家庭多。在单亲家庭里,无论缺乏父爱抑或母爱,皆使孩子的身心发育存在欠缺,不完整的家庭环境让他丧失来自健全家庭的同龄孩子般的关爱。久而久之,孩子易形成自卑或自闭的性格,从而使其在幼年时期人格得不到健全发展,影响健康成长。因此,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计,生育应以缔结婚姻为基础。
(二)生育以婚姻为基础,是实现优生优育的必然要求
生育以婚姻为基础,有利于优生优育,是贯彻提高人口素质基本国策的应有之义,这就要求必须防止残疾婴儿的出生。一旦子女出生时生理上存在先天性缺陷,不仅难以正常生活,而且易形成心理创伤,这不仅对子女健康成长不利,还易造成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额外负担。然而若生育在婚内进行,则子女患先天性疾病的概率相对要比婚外生育低,因为婚姻法已经对结婚的禁止条件予以明确规定,而诸禁止条件的设立,正是基于优生优育的考虑①。研究表明,血缘关系接近的亲属之间结婚生育,极易将一方或双方生理及精神上的弱点和缺陷遗传给后代,致使后代的死亡率较高、畸形和遗传病发病率较高[2],故禁止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结婚生育存在科学依据。同时婚姻法还禁止患有一定疾病的人结婚,主要是避免人类不良遗传基因遗传给后代或将传染度较高的疾病传染给后代,影响其健康成长。在现实生活中,若存在结婚禁止情形的男女违背禁止性规定,以非婚同居方式生活并生育时,则其后代患病的概率相对要大,此即违背了优生优育的要求。因此,生育权行使坚持以婚姻为基础,是优生优育、关爱下一代的集中体现。
(三)生育以婚姻为基础,是尊重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体现
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婚嫁之事,《礼记·昏义》中写到:“婚姻者,合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在国人看来,婚姻功能之一就是生育后代,延续种族,因此生育须在婚内进行,未婚生育要受到道德诘难。虽然我国古代的婚姻与生育制度存在令人诟病之处,但坚持婚内生育不仅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而且有利于文明生育秩序的形成。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繁衍,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所以,现代社会仍然要坚持婚内生育,这不仅是尊重传统文化的要求,亦是维护已然建立的社会文明生育秩序的应有之义。
另外,从我国人口与生育立法来看,国家主张婚内生育,对婚外生育则给予否定,主要表现在:首先,立法虽规定公民享有生育权,但生育权行使的主体却规定必须具备夫妻身份;其次,各地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条例》规定生育子女必须申领生育证,而申领生育证的主体则是夫妻②;再次,婚外生育的子女则被贴上“非婚生子女”的标签,虽其权利义务与婚生子女无异,但在身份层面却易遭社会的歧视和非议,身份上的差别对待,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
综上分析,在我国,生育权行使应以缔结婚姻为前提,以维护子女最大利益为原则,坚持婚内生育。对于现阶段存在的非婚生育者,应采取补正措施,及时补办结婚登记,为子女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二、夫妻生育权行使——以生育合意为基础
在我国古代,生育问题通常由夫决定,妇仅有积极配合的义务。然而在现代,基于社会对生育权极具人格属性的权利认知,是否生育之决定就不再专属于夫,相反应由夫妻双方就生育问题形成合意,而后共同完成生育过程。
(一)生育以合意为基础之正当性论析
之所以主张生育由夫妻合意进行,反对由夫或妻单方面决定,原因在于:
第一,生育权之人格权属性。生育权是生育主体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受他人奴役的人格权。任何一方欲行使生育权,皆须征得对方同意,在对方不愿生育时,不得采取胁迫或暴力手段使其就范。所以夫妻之间必须互相尊重,就生育问题展开对话,共同协商,形成共同的生育意思表示。
第二,生育观念向多元转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认知亦在不断变化。就生育而言,人们的认识亦呈多元,有的人仍然信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的人则崇尚自由,喜欢自在生活,认为“带孩子麻烦”,夫妻之间甚至也存在这种认识。假若夫妻都不希望生育(如丁克家庭),对家庭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若夫妻各方对生育有不同意愿,生育观念发生冲突之时,问题随之即来,一旦冲突不能化解,势必影响夫妻感情,甚至冲击婚姻,酿成悲剧。所以生育观念的多元化要求夫妻双方沟通协商,形成生育合意。一方在欲行使生育权时,应向对方提出请求,征得同意后,才能决定是否生育,这不仅尊重对方,而且亦有利于增进感情,在愉快融洽的氛围中,更能体验到生育本身所带来的快乐与幸福。
第三,现代医疗技术为性活动和生育的分离提供技术基础。无可否认,性活动与生育有着密切联系,在生育能力健全的情形,生育是夫妻间性活动不可避免的客观结果,然而在医疗技术水平发达的今天,随着对性与生育的认识不断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采取一定的避孕措施可以阻止怀孕生育的可能。而且医疗技术的发展使避孕方法更加科学有效,这就为性活动与生育的分离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避孕技术的出现使性活动与生育相分离,这就为夫妻一方意欲生育而须向对方请求予以配合,形成生育合意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二)生育合意形式要件之体系构造
生育合意是夫妻就是否生育、生育时间、数量、方式等问题形成的共同意思表示。然生育合意是否要式?其法律效力如何?笔者认为,为有效规范夫妻生育权行使方式及解决夫妻生育权冲突问题,可以借鉴法律行为理论对生育合意之形式要件进行体系构造。
第一,生育合意之成立。判定生育合意是否成立,可以准用合同法关于合同订立之要约承诺规则予以识别。夫妻一方有生育意愿时,应向对方示明,此可视为生育要约,对方可以作出是否生育之表示,此可视为生育承诺。若对方对生育有异议且提出相反意见,则视为反要约,有生育意愿一方须就此作出生育承诺。故唯夫妻一方之生育要约,已获对方生育承诺时,生育合意始能认定成立。
第二,生育合意之形式。生育合意是否应以书面形式进行?笔者认为,为有利于保存证据,避免因生育问题发生纠纷考虑,生育合意应以书面形式进行,但若夫妻双方对生育合意未有异议,则口头形式亦可。
第三,生育合意之内容。夫妻双方可以就生育时间、数量及方式进行约定。须注意的是,因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故就生育数量之约定应以不违背我国计划生育法律、行政法规为限。
在生育方式上,夫妻可以约定选择自然生育或人工生育方式进行。人工生育是指生育主体不能以自然生育方式生育时,通过医疗技术来辅助生育的生殖方式。人工生育的出现改变了人类自然生育的单一模式,作为重大科技进步,给广大患有不孕不育疾病的人带来福音[3]。它不仅解决了生育能力欠缺之主体不能行使生育权的难题③,而且亦避免了因不能生育导致家庭出现裂变的可能。
这里值得讨论的是,代孕可否作为人工生育方式?这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代孕所引起的法律问题颇为复杂,如孩子的法律母亲是谁,妻子或代孕者?若代孕者有丈夫,则其丈夫与孩子关系又当如何?代孕合同是否有效?诸如此类问题因涉及传统人伦道德,因此在现有法律范围内,其关系难以明晰。有学者指出,由于代孕弊多利少,易起纠纷,因此我国法律应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趋势相吻合,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均禁止使用代孕[4]。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已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代理孕母④。笔者认为,以代孕所产生的法律关系难以明晰为由,从而绝对否定代孕的存在价值,值得商榷。代孕并非洪水猛兽,代孕所带来的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并非不能克服。若能允许兄弟姐妹间经相互同意可以实施代孕技术,如此不仅不会导致近亲属间身份和辈分的混乱,而且还有助于实现不孕者的生育意愿。
第四,生育合意之效力。夫妻之间的生育合意,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双方应依据合意行使生育权,但若存在下列事由的除外。首先,形成生育合意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等使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不自由的,已形成之生育合意应认定无效。其次,生育合意形成后出现客观上事实不能的,应作可变更、可撤销处理,如女方因妊娠有严重损害生命、健康之虞的情形,此时不能强迫其配合对方行使生育权。
第五,生育合意翻悔之责任承担。生育合意若不存在无效、可变更、撤销之事由,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如一方故意翻悔,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十种民事责任,诸责任方式是否皆可适用于生育合意翻悔之场合?笔者认为,鉴于生育权的人格权属性,强制任何一方行使生育权,皆有失公允,故除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两种责任承担方式外,其它皆不可适用。即若夫妻就生育合意翻悔情形约定了违约金的,基于民法上自愿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守约方可以请求对方支付违约金,但应注意违约金数额应与所受损失(一般表现为精神损害)数额相当。若夫妻并未约定违约金,则守约方可以就因此受到的损失请求赔偿。
(三)夫妻未形成生育合意之解决路径
夫妻双方就生育问题达不成生育合意,如何解决?
有学者指出,若配偶没有生理上或其他的正当理由就不应拒绝,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如此,女性对男性的要求亦然[5],其意在强调,无论男女双方,只要对方提出生育要求,己方皆有服从之义务。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它违背了生育权是平等的自由决定权的价值意蕴。无可否认,生育是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到法定年龄之男女缔结婚姻,应当视同其已对婚姻包括生育在内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的默认,婚姻关系中之男女理应配合他方行使生育权,抚育后代,但更无可否认,生育权是自由决定权,任何人不得强迫。若夫妻就生育问题多次协商无果,可以视为感情破裂,生育权行使事实不能的一方有权请求解除婚姻,另行与愿意生育的主体缔结婚姻。
另外,夫妻未形成生育合意,且女方已怀孕,当又如何解决?
笔者认为,在未有生育合意,女方怀孕的事实皆违背不想生育一方之意愿,此时应分别情况解决:假定女方不愿生育,其可采取终止妊娠等事后补救措施,因未有生育合意,并不构成对男方生育权之侵害,若因此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且调解无效,可解除婚姻;假定男方不愿生育,为保护其生育权,男方可向女方提出终止妊娠请求,女方应予配合,但实施终止妊娠手术有损害女方身体之虞的除外。若因此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且调解无效,可解除婚姻,但男方仍应对生育之子女承担抚养义务,因为此为法定义务,不得约定排除。
三、独身者生育权行使:制度困境及路径探微
(一)制度困境——兼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
现代社会是个人权利备受推崇的时代,传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价值观念已趋淡化,为追求自由,一部分人选择单身。从尊重人权的角度言,独身者的生活方式应予充分尊重,独身者的权利应受充分保障。然而就生育权行使而言,现实语境下我国独身者行使生育权确有制度上的窒碍难行之处。从我国现行生育法律法规看,公民欲使人格意义上的生育权转变为现实意义上的生育权,必须缔结婚姻,以此为媒介,才能行使生育权,然而这却与其所追求的“单身”生活模式显然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吉林省2002年《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医学辅助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对此规定,我国有学者表示质疑[6]。理由在于:第一,从立法位阶看,该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根据《立法法》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显然该条例之规定与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相冲突,又因吉林省并不属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并不享有对法律的变通制定权,所以该条例第30条第2款之规定的合法性不无疑问。第二,从维护子女最大利益看,规定独身女性可以利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行使生育权,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完全忽视了出生子女的利益,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不符合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其中道理,上文已作分析。因此该条例之规定在合法性及合理性方面均存在商榷之处。
(二)独身者生育权行使之路径探微
现实语境下,独身者如何行使生育权?仅从生殖技术层面考量,独身者可以实施人工生殖技术行使生育权(女性运用人工授精技术,男性运用代孕技术),但如此做法不仅挑战了现阶段社会公众所能接受的伦理底线,更忽视了出生子女的最大利益。在技术与文明之间,理性人是不会选择以近乎自私、残忍的手段实现生育权的。事实而言,人之行使生育权的目的抑或价值无外乎两种:其一为抚育子女,以享父母子女天伦之乐;其二为使老有所依,以颐养天年。为达此目的,独身者可以通过收养子女的方式来实现生育权。以收养方式行使生育权,不仅可以摆脱我国生育制度的束缚,而且亦不违背子女最大利益原则,是可行的。
首先,养父母子女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婚姻法》规定,养父母有抚养、教育养子女的义务,养子女有赡养养父母的义务,养父母子女之间相互有继承权。独身者通过收养子女,不仅可以获得抚养子女过程的快乐抑或艰辛的精神感受,而且亦可实现老有所依,此正是行使生育权的目的或价值的所在。
其次,通过收养方式行使生育权与通过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比较,前者更符合子女最大利益原则。虽然,独身者通过上述的任一方式行使生育权,其子女皆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环境中,均不符合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的生活模式。但“两害相较取其轻”,通过收养方式更能最大程度上维护子女的最大利益。从我国《收养法》规定的被收养人的条件看,被收养人在被收养前,已处于非常不利的生活境地,不利于健康成长。从该法规定的收养人条件看,被收养人在被收养后的生活环境要比被收养前优越,被收养人在生活、学习上的条件能够得到基本满足,这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因此符合其最大利益。
四、生育权行使:规范依据之审思及完善建议
(一)生育权行使之规范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宪法》为依据,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基本法,以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配套规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体系,这为我国公民行使生育权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我国生育立法还存在不足之处,亟待完善。
1.尚未明确规定生育权是民事权利
生育权本质是民事权利,理应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然我国生育立法从性质看多属公法。无论是具有生育基本法之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还是如《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地方法规,皆将生育行为视为行政管理对象,极具行政强制性色彩,丝毫体现不出生育属公民意思自治范畴之私法底蕴。因此立法应树立生育权是民事权利的理念,将其纳入到民事法律规范中来,从而有效规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夫妻生育权冲突和纠纷,保护双方的生育利益。
2.尚未对生育权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从立法内容看,我国生育立法仅仅确认了公民享有生育权,但对其具体内容却未予规定⑤。立法应明晰生育主体就生育问题的权利义务、权利的行使方式及受侵害时的救济措施等。唯其如此,现实生活中公民行使生育权才能有章可循,在生育权益遭到侵害,寻求司法救济时,才能有法可依。
(二)生育权立法之价值取向
笔者认为,未来我国生育立法,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公民的生育自由,平等保护公民的生育权利;二要立足国情,坚持从实际出发,统筹保护公民生育自由和规范生育管理,使人口、资源与社会三者健康可持续发展。
1.尊重和保护一定限度内的生育自由
“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的任务是尊重和保护人民行使权利的自由,在法律的范围内,人们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免于一切外来的干涉和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讲,生育权亦应为法律所尊重和保护,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有依其意思自主决定生育的自由,因为这是由生育权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首先,生育权的人格权属性要求法律尊重人之生育自由,生育权本质上体现了一切生命个体(自然人)享有的不可剥夺的人格利益。其次,生育权的人权属性要求尊重人之生育自由。生育权关乎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对个体而言,生育是实现自我繁衍和种族延续的前提;对社会而言,是人类进行人口再生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育的直接后果就是新一代人的产生,于此往复,生生不息,人类正是在自身新陈代谢的基础上,才创造了今天的辉煌成就。
然而,诚如罗尔斯所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7],生育自由并非个人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一定限度内的自由。生育最直接后果就是增殖人口,单个家庭毫无限制的生育自由造成人口大规模地增长,不仅会消耗有限的自然资源、恶化脆弱的生态环境,而且易滋生社会矛盾,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难以逾越的障碍。未来我国生育立法应依据国情,建立完善的生育权规范体系,使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确保人口、资源与社会三者健康可持续发展。
2.平等保护生育权利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价值观念趋于多元,生育观念亦由传统的单一型向多元化转变,在地区之间、不同年龄层之间悄然发生变化。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早已改变传统生育观念,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依然相信多子多福,相信传宗接代,重男轻女。在中年以上的年龄层中间,他们依然固守“生儿为了防老”的观念,而在年轻一代,则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有的人甚至认为,“生男是名气,生女是福气”[8]。生育观念是生育利益的主观反映,主体生育观念不同意味着主体对生育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当生育主体之间对生育利益有着不同追求时,必将造成冲突。因此,应当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平等保护公民的生育权利,未来我国生育立法应当秉持“平等保护公民生育权利”的立法理念,于生育主体就生育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之情形,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
3.国家职能从控制管理向以服务主导转变
自1978年国家正式将实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各地将控制人口数量作为实行计划生育的硬性指标,并采取包括经济的、行政的等手段实现之,这种至上而下的计划生育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上行压力,然在尊重和保护人的权利时代,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严厉的控制管理模式似乎与保护基本人权相悖违。生育权是基本人权,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数量等关涉生育权问题,应由生育主体自己决定。诚然,在寻求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协调的今天,个人在行使生育权方面应负有责任,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亦应履行职能,但绝非强制性控制管理,而应强化国家服务职能。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一方面国家应以实际行动,切实改善生育技术服务设施条件,提高服务水平,以保障公民享有生育技术服务,提高生殖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应建立生育利益诱导机制,以引导和激励公民转变生育观念。即国家应当尽快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解决独生子女户的养老问题,完善和落实对独生子女户的政策优惠措施,激励公民从根本上转变“养儿为防老”的生育观念,以此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生育权规范之完善
第一,在《婚姻法》中规定生育权行使的具体内容。《婚姻法》是调整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生育是夫妻乃至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规定在《婚姻法》中。具体言之,应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就生育问题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权利的行使方式以及就生育意见不一时的处理方式等内容,据此应将《婚姻法》第16条修改为:
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生育权,任何一方就生育问题有知晓对方生育信息、请求对方予以协助以及自主作出生育决定的权利。
夫妻双方应当协商,形成生育合意,生育合意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使用欺诈、胁迫手段形成生育合意的;
(二)因客观原因,事实不能履行的。
夫妻一方故意翻悔的,应承担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相应的民事责任。
夫妻双方都有按国家规定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另外,《婚姻法》应将“夫妻就生育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一方提出离婚,调解无效的”情形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之一,因此,应在第32条第2款中增加一项,即:
“夫妻双方就生育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一方已提出离婚的”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之一。⑥
第二,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相应修正,补充规定独身者的生育权行使路径。一方面明确规定生育权的行使应以缔结婚姻为基础,另一方面从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的角度考量,尊重单身者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作相应修改。即: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公民行使生育权利时,应当按照《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缔结婚姻;夫妻双方应以形成生育合意为基础,在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决定不结婚的公民可以采取收养子女的方式行使生育权,但不得违反《收养法》的有关规定。
注释:
①我国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我国立法之所以如此规定完全是基于遗传学规律和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考虑的。
②如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19条;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0条;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6条。
③目前,公认的人工生殖方式有:人工体内受精、试管婴儿、胚胎移植。上述三种人工辅助生育方式是目前技术上已成熟,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生殖方式。
④我国2001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⑤如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16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⑥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已将“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作为认定法定离婚理由之一。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1-122.
[2]吴履平主编.人口学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292-294.
[3]朱凡,陈苇主编.当代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人工生殖立法比较研究[A].家事法研究(2010年卷)[M].群众出版社,2011:89.
[4]冯建妹,梁慧星.生殖技术的法律问题研究[A].民商法论丛[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0-102.
[5]庆玲.论婚姻关系中的男性生育权[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3(6):50.
[6]高玉玲.论生育权的主体[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4):288.
[7][美]罗尔斯著.何怀宏译.正义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34.
[8]武秀英.法理学视野中的权利[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