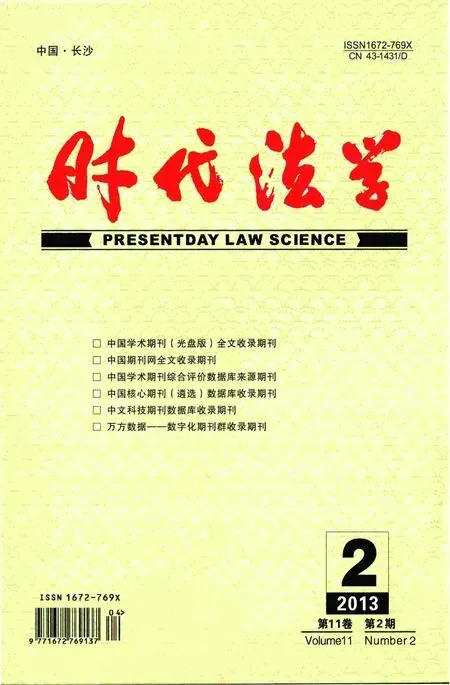“法律行为”解释论——基于语言、逻辑和语言哲学三个向度*
李康宁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
一、问题与目的
长期以来,中国民法学界对“法律行为”概念、理论和规则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性的批评和矫正,目的在于正本清源,使其回归“法律行为”的本质要旨——意思表示。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批评和矫正讨论清楚之后,关于“法律行为”的问题是否已然全部解决?当然不是。在汉语语境中,对于“法律行为”概念的理解和解释,从语言学、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等方面进行方法论上的探讨,依然甚有必要。
“法律行为”系德文Rechtsgeschaeft一词的汉译词汇。在古罗马时代,法学家仅仅认识到具体的法律行为,而并没有“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彼时,“法律行为”还没有统一的表述方式,在法律文献中,人们既用拉丁文表示,也用德文表述,直到18世纪末期,Rechtgeschaeft一词才确立。Rechtsgeschaeft的概念和理论,由德国潘德克顿法学肇创,经胡果提出、海瑟完善,直至萨维尼集大成,最后在德国民法典中实现了制度化。“法律行为”理论在大陆民法中的地位如此显赫,以致于赞誉者认为它就像民法皇冠上的明珠一样,是“民法规则理论化之象征”,是“大陆法系民法学中最辉煌的成就”。①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英国学者梅特兰在谈到19世纪德国诸多学者对法律行为的研究成果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如此多第一流(思想家)的大脑被用于对某种行为的立法研究上。”②K.Zweigert&H.Koetz,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Vol:2,North Holland Co.,1977,p.3.在方法论上,实现“法律行为”理论的制度化与规则的理论化相互沟通的基本工具,正是二者均秉持的同一方法——逻辑塑造。通过逻辑的塑造,“法律行为”理论和制度得以自恰地归纳和演绎。然而,逻辑塑造又像一把双刃剑,德国民法典因逻辑缜密著称于世,同样也因将逻辑的抽象功能发挥到极致而招致诟病。耶林就认为,“人们对逻辑的渴慕,把法学变成了数学,这不仅是错误的认识,而且还会误解法律。生活不因概念而存在,相反,概念因生活而存在。有权存在的,不是逻辑,而是生活、社会关系的需求以及对正义的感知;逻辑的可能或不可能都不是物质的。”③Jehring,Der Geist des Romischen Rechts,Ⅱ.2.Introd.69.quoted in Peter Stein,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Cambridge univ.Presss,1999,p.121.乌拉沙克和弗卢姆也认为,法律行为是一个“真正的灰色理论的产物”。④Siehe Werner Flume,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Bd.2.Das Rechtgeschaft,3 Auflage,Springer-Verlag,1992,s.32.茨威格和克茨也指出,法律行为是德国法上的一个人为概念。它虽然有阐释和体系化价值,但作为一个认知工具,它对于私法的社会秩序而言,并不是非常有用⑤See K.Zweigert&H.Koetz,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Vol:2,tr.by Tony Weir,2nd.Clarendon Press,Oxford 1987.pp.5-6.。
可见,德国法学家对“法律行为”理论和制度的看法褒贬不一由来已久。尽管如此,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洗礼,这一理论和制度还是向域外广泛传播开来。在现代民法的土壤中,“法律行为”不仅像常春藤一般历久不衰,而且有如迷一样的精灵,引发人们无尽的思考。事实告诉我们,依据潘德克顿法学理论和技术规则制定的德国民法典,不失为当代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翘楚之作,而“法律行为”制度正是德国民法典总则的核心部分。德国民法典之后,大陆法系国家仿其体例制定或在此体例基础上加以改动而编纂的民法典中,直接以“法律行为”之名规定法律行为制度的有很多,未直接以“法律行为”之名作出制度安排的也不少。是故,“法律行为”从诞生之日起便魅力无穷。新中国民法在立法上虽然移植了“法律行为”的概念,但在理论体系和制度规则的继受上,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呈现出既采纳其概念又不完全接受其理论体系和制度规则的状态。“法律行为”,这个充满魅惑色彩的抽象概念及其理论塑造,至今仍使中国大陆众多民法研习者感到好奇和迷惘,多年以来着墨不辍,提撕纷繁⑥中国知网(CNKI)统计数据显示,1979年至今(本文成稿时),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期刊中,以“法律行为”为论题发表的文章共计421篇,以“合同”为论题的文章共计34829篇,以“物权行为”为论题的文章共计316篇。[2011-12-28].http://www.dlib.cnki.net/kns50/scdbsearch/cdbindex.aspx.。本文的问题仅限于,在方法论上,“法律行为”概念的解释遇到了哪些障碍?发生解释歧义的原因何在?应当如何理解“法律行为”的语义蕴含并合理解释?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从“法律行为”原初的概念生成和语义设定中获得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启示,准确把握“法律行为”的本质要义。
二、“法律行为”概念的语言学与逻辑学解释
(一)“法律行为”概念的生成及其语义蕴含
中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是由日本学者自德文翻译而来的。“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一个组合词——Rechtsgeschaeft,由Recht和Geschaeft两个词中间加连词符s而合成。Recht本身意为“权利”、“法律”、“公平”、“公正”等,Geschaeft则意为“交易”,指权利的转让、让渡等。“法律行为”中的“行为”一词,在海瑟的著作里使用的是Handlungen,这个词才是德文中表示“行为”的最常见的词语,而Ge-schaeft并非表示“行为”的常用词语。将Recht和Geschaeft合成为Rechtsgeschaeft,实质上是德国民法基于理论塑造和立法技术的需要而创造的词汇,它与现实生活中表示“行为”的词汇含义并不吻合。因为表示人的行为的专门词汇是Handle,它跟英文hand一词的词根是一致的。个人所为的、能够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在德文中表示为Rechthandlung,但Rechthandlung并不要求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可是,作为交易行为来讲,又必须有当事人内心希望交易的意思并将其表达出来,因为转让权利必须符合出让人和受让人双方的意愿,所以才创造出Rechtsgeschaeft,专指民法上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并以此和生活中的其他“行为”相区分。因此,Rechtsgeschaeft被萨维尼解释为“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⑦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475.严格而论,将Rechtsgeschaeft译为“法律行为”并不确切,但由于Rechtsgeschaeft是一个德国法学家创造的词汇,在汉语里根本不存在与其恰当对应的词语,日本学者将其译为“法律行为”,实为不得已而为之。
在德国,尽管法学界的硕儒巨匠对Rechtsgeschaeft理论、制度和作用的认识与评价从来不乏分歧,但是,对Rechtsgeschaeft概念本身的语义蕴含,百余年来几无质疑之声。这说明,在Rechtsgeschaeft的故乡,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不需多加解释,也毋庸置疑。它发端于民法,运用于民法,在私法法域中的语义非常明确,就是萨维尼所说的“意思表示行为”。或者像拉伦兹和沃尔夫表述的那样,是“以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为目的的,促成个人私法关系变动的单个人或者多数人的单个或多个有内在关联的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追求发生私法上的效果,改变或者引起具体的法律关系。每一个人都通过法律行为,与其他人发生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之所以产生法律效果,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规定,而是首先因为当事人意欲如此”。⑧Siehe Karl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8.Auf.C.H.Beck,1997,s.432.可以更通俗地讲,德国民法语境中的Rechtsgeschaeft,就是行为人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而创设的追求发生私法上效果的行为,其核心构成要素有二,一是意思表示,二是私法效果。在德国法学界,由于学者对Rechtsgeschaeft的含义和构成要素有着统一的认知,因而在理解上根本不成问题,它就是私法上的一个专有概念,与其他部门法无涉。
(二)“法律行为”概念的泛化误读与解释局限
中国大陆学者对“法律行为”的理解和解释的分歧,发生在《民法通则》(1986)颁布之后。由于《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法学话语系统中便出现了“泛法律行为论”。从立法目的上讲,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与德国民法中规定Rechtsgeschaeft是相同的,但《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表述和制度规定明显不妥。其一,《民法通则》未强调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而强调行为的“合法性”,偏离了Rechtsgeschaeft的本意,这也是招致学界诟病的关键。以“合法行为”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不仅无法解决有效行为与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与效力待定行为之间的矛盾,而且必然导致民法一般规则与特别法具体规则之间的冲突。其二,《民法通则》创造出“民事行为”一词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以弥补“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不周延,然而却顾此失彼,在语言逻辑上完全颠倒。语言的逻辑应当是,定语越简短,内涵越丰富,概括力越强,而《民法通则》中“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两个概念在逻辑上恰恰是相反的。一个科学的概念应当符合这样的逻辑规律,即整体上不具有的,部分中也不可能具有。怎么可以说,作为一般概念的“法律行为”只能是合法有效的行为,而作为“法律行为”的具体形式——合同、遗嘱等却有合法与不合法、有效与无效之分呢?况且《民法通则》在“法律行为”之前加上限定词“民事”,虽然是为强调这种行为的民法属性,但实为蛇足之举,并因表述失当而给“泛法律行为论”留下了借题发挥的逻辑推理空间——既然法律不仅仅指民法,那么“法律行为”也就不是专指民法上的行为,更不是“意思表示”行为,连《民法通则》自身都未表明它是“意思表示”行为。既然民法上的行为称为“民事法律行为”,那么行政法上的行为就是“行政法律行为”(简称行政行为)⑨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41.王清云,迟玉收.行政法律行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9.,经济法上的行为就是“经济法律行为”,⑩吕忠梅.论经济法律行为[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程宝山.略论经济法律行为[J].中州学刊,1988,(6).等等。基于这样的逻辑,法理学者索性推而广之,认为法律行为就是人们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或者说,凡是具有法律意义和法律属性的行为都是法律行为[1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67.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1.卓泽渊.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24.。如是理解“法律行为”,使得原本在民法上创设并只在民法上使用的“法律行为”概念,被泛用到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其核心构成要素也被偷梁换柱,将Rechtsgeschaeft原初的“意思表示”和“私法效果”,转换成“法律效力”和“法律效果”或“法律意义”和“法律属性”等等。这种抽去“意思表示”要素并将“私法效果”扩大为“法律效果”的“泛法律行为论”,远远背离了德国民法创设Rechtsgeschaeft概念的初衷,不但误读了“法律行为”,而且造成了学理上关于“法律行为”概念表述的混乱和解释的困扰。
在解释论上,“法律行为”作为一个由法律家创造的法技术词汇Rechtsgeschaeft翻译而来的概念,既无法按照语法规则作出符合其本意的语义解释,也难以按照定义规则完成符合其本意的逻辑推演。
从语法上来看,汉语中“法律行为”的构词是由“法律”和“行为”两个名词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名词性词组。名词性词组有三种基本结构形态。第一种是互指性同位结构,即构成词组的各部分含义相同,彼此互指,两者之间不能加入任何助词或连词,例如“人民群众”。第二种是非互指性同位结构,例如“专家教授”,“专家”和“教授”不一定互指,二者之间可以加入连词“和”或“与”表示并列关系。第三种是偏正结构,即构成词组的各部分含义不同,前者作为限定词修饰后者,两者之间一般可以插入助词“的”,且含义不变,例如“本科课程”。由是观之,“法律行为”应归于偏正结构的名词性词组。然而,如果按照语法规则在“法律”和“行为”之间插入助词“的”,将“法律行为”扩展为“法律的行为”,其含义却气象万千:“法律的行为”究竟是“法律上的行为”还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是“能够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还是“具有法律属性的行为”?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得出其中含有“意思表示”要素的结论。因此,根据“法律行为”概念的语法构成,在语义学上的各种解释均不能还原到“意思表示行为”的本意。
从逻辑上来看,概念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即逻辑思维的最基本单元和形式。当一个词语作为概念使用时,逻辑和语言自身一般能够为其应当具有的含义作出界定。所以,逻辑解释方法经常被采用,且于诸多情形均可得出合理的结论。但是,逻辑的解释并非万能,生活中也有许多不合逻辑的现象,如果用逻辑的方法进行解释,结论将是它们不可能存在,但事实是它们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在对“法律行为”的解释上,逻辑的推演显然难以令人满意。首先,“法律”是“民法”的上位概念,二者在逻辑上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在逻辑推理上难以得出“法律行为”是专指民法上的行为的结论,而符合逻辑的解释恰恰是这样:首先,部门法均是法律,所以,“法律行为”指的是各部门法上的行为;民法是法律之一种,故“民事法律行为”是“法律行为”之一种。这也正是“泛法律行为论”的逻辑依据。其次,“法律行为”对应的是“非法律行为”(如“道德行为”、“情谊行为”等),“合法行为”对应的是“不合法行为”,逻辑上也无法得出“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或“不合法行为”的结论。再次,“意思表示”要素在逻辑上无从体现,行为人是否所追求“私法效果”也不能证明。所以,逻辑的解释同样不能使“法律行为”还原到Rechtsgeschaeft原初的、本质的含义。
采用通常的方法解释“法律行为”为什么不能还原Rechtsgeschaeft的本意?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Rechtsgeschaeft的翻译问题。翻译问题的实质是语言问题,由于翻译欠准确,造成Rechtsgeschaeft的译词为“法律行为”的既成事实,因而易使人陷入理解和解释的困境。有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应以“设权行为”取而代之[12]宋炳庸.法律行为概念应更名为设权行为[J].中外法学,1999,(2).。但对这种见解,本文不予苟同。诚然,与“法律行为”相比,“设权行为”似乎更接近Rechtsgeschaeft的含义,因为要设权就必定要有行为人的设权意思,否则权利设而无据。但是,从历史角度考量,自清末民初中国继受德国民法算起,“法律行为”作为一个汉译概念的确立已逾百年,在民法中居于核心地位,学术界和实务界均早已接受它。如果仅为理解与解释之便而彻底改变一个历史形成的惯用概念,不仅在学理上要改变百余年来的使用习惯,而且在立法上要启动相应程序,修改大量生效法律文件,这显然是不易做到的。
二是Rechtsgeschaeft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Rechtsgeschaeft概念的创立,与构建德国民法科学体系的需求有关,也与浪漫主义和精神科学对“理解”和“意义”的探求有关,这一根源在法学上体现为罗马法学派与日耳曼学派的对立,但是更深刻的根源在于德国当时的社会背景[13]谢鸿飞.论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与法学方法[EB/OL].[2012-01-26].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1714.。中国未经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罗马法继受,未经历解放思想和追求自由的启蒙运动,不具备德国那样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社会背景,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直接继受了代表19世纪大陆法系最高水平的垄断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德国民法,因而缺乏准确认知Rechtsgeschaeft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基础。
三、“法律行为”解释与Rechtsgeschaeft发生错位的社会原因
将Rechtsgeschaeft和“法律行为”置于相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解释“法律行为”。
(一)Rechtsgeschaeft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历了13~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的封建势力和教会桎梏被铲除,人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人们崇尚自由、平等、博爱,自由主义弥漫到社会各个层面,彻底激发了人们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热情。启蒙运动不仅培养了大量自然科学人才,推动了科技进步,引发了工业革命,而且导致了整个社会革命,催生了大批思想家。政治上,他们主张以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信仰上,他们倡导以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法律上,他们提出以“天赋人权”来反对“君权神授”,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这样持久、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像春雨一样滋润整个欧洲大陆,孕育科学的萌芽破土而出,许多人文理齐发、兼收并蓄,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例如,微积分之父莱布尼兹、解析几何之父笛卡尔等,都既是著名的数学家,又是哲学家和法学家,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建树丝毫不逊于他们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在探讨自然科学的同时,他们运用数理的方法对社会科学进行深入的思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罗马法继受运动之后的德国,同样涌现出一大批博古通今的法律思想家,他们被梅特兰誉之为“第一流的大脑”。这些法学家谙熟罗马法,不仅对部门法学、法理学和法哲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历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具有深厚的学养,诸如萨维尼、格林兄弟等。他们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足以使其完成不同学科和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的语言沟通。基于民法理论和民法规则体系化的需要,潘德克顿法学采用数理逻辑中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多发的关于权利变动的行为抽象出来,诸如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人自主自愿设定权利义务的行为,并创造Rechtsgeschaeft一词加以涵括。这个概念产生之后,德国学者并未对其含义进行争论,因为它就是一个由法学家创造的法技术词语,法学家赋予它“意思表示”和“私法效果”两个要素,人们就认可它是具备这两个要素的一个概念而已,根本无需争论。所以,在私法域之外,法学家从不使用这一概念,更不会把它移植到行政法、经济法等公法域。但是,这种局面在中国大陆却大相径庭。新中国学者对Rechtsgeschaeft的产生背景、内涵设定和使用范围了解不够,加上翻译欠准确和自身知识结构的不足,导致对“法律行为”概念的理解与解释一度发生歧义,语言沟通便出现了偏差。
(二)“法律行为”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
“法律行为”概念在中国的产生始于清朝末年。晚清变法图强之际,“法律行为”由日本学者自德文Rechtsgeschaeft译至中国。由于在此之前国人不知Rechtsgeschaeft为何意,日本学者将其译为“法律行为”,《大清民律草案》即全盘接受了它。虽然之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导致清朝覆亡,《大清民律》未颁行,但西法概念的译文却保留下来,并为日后民国民法典所沿用。国民政府组织制定民国民法典时,已有大批法学学者从德、瑞、日、法等国留学归来,参与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他们经过欧陆法学教育的洗礼,熟谙其概念产生的背景。对晚清时期业已继受的“法律行为”概念,他们完全按照Rechtsgeschaeft之本意而理解和应用,解释上也是按照Rechtsgeschaeft的内涵——“意思表示”与“私法效果”进行的。《六法全书》及民国时期所有的法学著述均已证明,“法律行为”一词在民法之外的其他法域是不见踪影的。正如梅仲协先生所言,民国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14]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Rechtsgeschaeft作为德国民法总则的核心部分,当然被继受下来。
新中国废除了《六法全书》,而将前苏联的法学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法学的样板全盘继受。前苏联民法虽然也继受于德国民法,但出于维护新兴社会主义政权和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之考虑,“将民法作为改造的中心,而作为市场经济立法核心的法律行为理论当然被放弃了。这一改造的结果,否定了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石——私法自治或者意思自治原则,极大地压缩了民众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权利义务关系的空间。这种改造对法律行为理论造成根本的破坏,因为,法律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建立法律行为制度的目的,就是承认和保护民众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和变更涉及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法律关系。前苏联人的这种改造导致民法学整体的癌变,它的基本概念到逻辑体系虽然从语词上看还是大陆法系的,但是本质却与传统民法背道而驰。”[15]孙宪忠.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与民法典的制定[DB/OL].[2012-02-10].http://www.civillaw.com.cn/wqf/weizhang.asp?id=17413.由于受前苏联极左意识形态的熏染,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极端行政化,加上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干扰,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法学教育被彻底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激观念禁锢了整个中国社会思想,人们对已成为批判对象的资产阶级法学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一步。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法学人才严重断档,仅存为数不多的法学专业人才,其知识结构大多仍维持在前苏联极左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法学知识系统内,法学教育资源非常匮乏。中国法学百废待兴,在废墟上边建设边发展,但法律学人的相关学科知识储备不够,知识系统残缺,视野受限,学术研究也呈条块分割状态。这种现实造成许多学者习惯于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自说自话,不仅缺少像欧陆那样能够在自然科学领域与社会科学领域自如沟通的大家,而且,即便在社会科学领域,甚或在法学领域,不同学科之间的语言也缺少沟通。法理学、部门法学和法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对“法律行为”的观点足以证明,不同领域的学者未能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严肃而认真的对话,而是在各自学科话语系统中花开数朵、各表一枝,导致学术语言严重错位,未形成统一的认知。因为语言错位,“法律行为”概念的解释瓶颈便难以在语言学和逻辑学上得到破解,故必须探寻解释“法律行为”概念的新路径。
四、“法律行为”概念解释的语言哲学思辨
“法律行为”概念在中国法学界的理解分歧与泛化使用,固然有语言学和逻辑学上的原因,但这只是现象而非本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话语系统语言错位才是更为根本的原因。语言错位的表象是语言和逻辑问题,而本质则是语言哲学问题。
(一)语言哲学的研究方向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16]
语言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成果最为卓著的一个哲学流派,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特指语言学哲学,是对意义、同义词、句法、翻译等语言学共相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式进行研究的学科,是科学哲学中与物理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等并列的特殊分支。其二,语言哲学包括基于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任何一种概念的研究。例如,亚里斯多德关于“存在”的哲学思考,罗素的“特称描述语”理论,莱尔关于“心灵”概念的著作等,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其三,语言的哲学,是对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内容的哲学分析。语言哲学的研究以逻辑实证主义、言语行为理论和生成语言学这三条线索进行。
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起初,维氏的哲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其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整个文明的基础,他想揭示当人们交流时,在语言表达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认为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他的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他一生两个阶段的哲学体系。前者主要是解构,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7][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哲学无非是把问题讲清楚。后者又把哲学回归哲学,在解构之后是建构。但是,在建构时他又发现,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表述哲学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这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
(二)“法律行为”概念解释的语言哲学视角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作为一种持久而忘我的努力”,研究者总是试图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提供的概念的箱子里”,而这些“概念的箱子的历史起源中及偶然地在它们尔后的发展中都存在着随意性因素”。[18][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法律行为”这个“概念的箱子”,就是德国法学家对生活中多种行为事实的共同特征进行抽象的产物。这个经过逻辑抽象而形成的概念,便成了为实现民法科学体系的建构而创造出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直接对应的“行为”的思维符号。建立这个符号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对民法上的权利产生、变更和消灭进行体系化研究和思考的基本工具。而这种研究和思考的过程和结论需要通过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描述。问题在于,作为这个概念外在表现形式的文字或词语,能否准确表达出作为思维工具的概念的准确含义?人们在理解这个承载着概念意义的文字或词语时,是否会产生误解?如果产生了误解,如何来确定文字或词语的含义以消除误解?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过程极具启示意义。
维氏早期的《逻辑哲学论》充分强调了“逻辑要素在确定语言含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学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8.他认为,如果要准确理解语言的含义,就必须对于组成语言的要素进行分析,直至分解为最基本的要素。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含义及其逻辑关系的理解来确定语言的具体含义。维氏认为,哲学的任务只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即日常语言的明确化。这种思想对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在其晚年的总结性著作《哲学研究》中,维氏却否弃了自己长期坚持的观点。因为经过近一生的思考、探索和检验,他最终发现,在确定语言具体含义的过程中,逻辑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作为符号的语言,自身都是死的,这些符号只是“在使用中才有了生命”,[20][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97.33.而作为语言外在表现形式的文字或词语所具有的含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21][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97.33.当人们在使用中确定这些文字和词语时,逻辑对于其含义的具体确定或许会有一定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在使用这些语言的过程中所赋予它们的含义或许不合逻辑,但人们就是这样来理解和使用的。维氏这个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中“存在着随意性因素”的观点,或者说,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并非时刻都遵循逻辑。
维特根斯坦最后的发现和托马斯·库恩的观点,与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相当契合。索绪尔认为,在理解语言的过程中,决定语言含义的是语言处于什么样的联系中,而不是语言自身的逻辑。正是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中,语言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含义。而决定语言将处于什么联系之中的是语言使用者的意图、目的及使用背景。作为一种符号的语言,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语言自身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结构,具有独立自主和自我界定的性质。因此,在确定语言的具体含义时,是具有任意性的[2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7-116.。这种观点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呼应,梁治平认为,作为一种思维符号,语言“连同它所传达的意义,完全是出于人类而非事物本身;它们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物体、行动或过程本身所固有的……符号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科学上可以验证的关于真实世界的描述”。[23]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5.8.因此,作为语言外在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字或词语,比如“法律行为”,也不能仅从逻辑的途径来确证其含义。要准确理解“法律行为”,必须考察它处于怎样的联系之中以及使用者的意图、目的以及其使用背景。因为从语言本身来讲,“每一个词都仅仅在它所适合的一定联系中才有一定的意义,在任何其他的联系中,除非我们在这种新的联系中为这些词的用法提供新的规则,否则这些词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新规则的提供,至少在原则上是十分任意的。”[24][德]莫里兹·石里克.意义和证实[A].陈波,韩林合.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C].洪汉鼎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215.
通过语言哲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正确理解“法律行为”的本意,必须走出逻辑和语法刻板的解释方法,回到诞生“法律行为”的背景中,考察“法律行为”概念的创造者、使用者的意图和目的,分析对“法律行为”概念的理解产生歧义的因由,然后站在语用学的角度解释“法律行为”,才能够让死的语言和逻辑活起来。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否认语言和逻辑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应当能动地运用语言和逻辑。因为作为思想表达工具的语言,总会在表达的过程中造成一些思想内容的流失,正如电流经过输送会有损耗、热量经过传导会有衰减一样。而作为法律体系化安排工具的逻辑,同样存在着难以使被安排的思想内容完全归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客观存在,既不会因人的主观愿望而消失,也不会因技术的进步而彻底革除。只有客观认识它,才能正确理解语言和逻辑的作用,进而合理解释“法律行为”。
五、“法律行为”概念解释的语用学分析
作为语言学各分支中一个以语言意义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领域,语用学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学问,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用学因其本身的目的性和价值性而不同于语法学,它所研究的是语言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时体现出来的具体意义。可以说,语用学是语义学的动态延伸。在语言的使用中,说话人往往并不是单纯地要表达语言成分和符号单位的静态意义,听话人通常要通过一系列心理推断,去领会说话人的实际意图。在“表达”与“领会”之间,表达者的意思与领会者的意思不一定完全吻合,于是就可能会发生多种情况。比如,表达真实而被受领;表达不真实而被受领;表达不自由而领会自由、表达真实而领会错误等等。
“法律行为”是潘德克顿法学在对各种具体行为进行抽象的基础上创造的技术语言而非生活语言,必须使经过抽象而形成的法技术概念能够涵括民法生活中各种表意行为的具体情形,这种抽象才具有技术价值。所以,创设“法律行为”这个抽象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不真实、不自由等多种具体情形纳入一个统一的概念之下,然后,根据实施每种具体行为的背景和意图,才能判断或者决定行为人能否达到其内心欲求的私法效果。
在语用学中,有两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意义,另一个是语境。对于“法律行为”,如果我们能够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去认识这一概念,再从语用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产生的背景、使用的意图和目的,那么,对“法律行为”的解释就有了各种特定的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以“法律行为”的源概念Rechtsgeschaeft的构成要素为核心进行解释,才能够避免望文生义的字面解释和不恰当的逻辑推演,正确把握“法律行为”概念的实质蕴含。
(一)语用学意义上的“意思表示”
“法律行为”技术构造的目的在于贯彻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原则,即在市民社会生活中允许行为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进行权利的设定、变更和终止。这种意愿旨在发生私法上的效果,故在民法上称之为“效果意思”。“效果意思”需要用相应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语言则有口头、文字和肢体等多种表达形式。由于“意思”属于心素,“表示”属于体素,心、体之间未必能够时刻保持同一,所以“意思”和“表示”出现种种偏差也非常普遍。正因如此,意思表示真实和意思表示自由是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核心要素。意思表示真实或自由与否,取决于行为人进行意思表示时所处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背景。在语用学上,效果意思属于“意义”,而表示意思时的客观背景则是“语境”。表示的自由程度不同,意义的实现程度也不同。当行为人在不受外在约束和限制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真实意图做出表示时,意义完全符合行为人的愿望,则意思表示有效。即便其保留真意而做出了单独的虚伪表示,原则上也是有效的,除非相对人明知其保留了真意。当表意人和相对人通谋而做出虚伪表示时,原则上应无效,但不得以其无效对抗以上第三人。当表意人利用契约自由以迂回手段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旨在达到法律所不许之效果时,意思表示的效力“应解释法律行为上之构成要件及涵盖此项构成要件之规范而定”[25]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76.。因表意人误认或不知导致意思和表示不一致时,意思表示的效力在各国立法上有显著差异。如德国民法规定为可撤销,而日本民法则规定为无效。这种情形下,“意思表示”的语境不仅涉及当事人行为时的自由状态,而且要考虑立法机关的立场和态度。故当事人内心的效果意思与表示上的效果意思不一致时,究竟以意思主义还是表示主义抑或折中主义来判断意思表示的效力,取决于立法机关的立场。因为立法机关的立场一旦确立并体现在法律上,即成为客观事实,非行为人能够左右或改变,只能适应它。在此情形下,立法机关的立场亦构成“意思表示”语境的组成部分。
在表意人受到欺诈或胁迫的场合,因受欺诈而陷于错误判断,进而做出意思表示,或因受胁迫而不得不做出其本不情愿的意思表示,均属于意思表示不自由状态。在不自由的语境中表意人做出的意思表示非出于自主自愿,故其最终效力若何,应取决于表意人。表意人认可时,意思表示有效;表意人申请撤销时,意思表示无效;表意人申请变更时,法院不得撤销,且变更后的意思表示有效。
(二)语用学意义上的“私法效果”
作为法律行为的另一构成要素,“私法效果”即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手段,意欲实现权利义务关系变动的目的。这种变动需要得到民法的肯认,即发生私法效果。与事实行为、事件等引起的权利义务变动由法律直接规定不同,当事人实施“法律行为”是否能够如其所愿地引起权利义务变动,从而实现其意欲达到的“私法效果”,情况则颇为复杂,在语用学上需要分别判断。在“意思表示”中,意思属于语用学上的“意义”,而“表示”的外部环境对意思生成与表示行为的影响,则为“语境”。“私法效果”是“意义”和“语境”在符合法律要求的前提下行为人所追求的结果。在法律无特别要求的情形下,只要“意义”真实,“语境”自由,则“私法效果”即可满足;在“意义”不真实时,“私法效果”的实现则区分“真意保留”和“虚伪表示”等诸情形,以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分别处之。在“语境”不自由时,法律当允许行为人再行选择,即通过法院行使变更权和撤销权,进行意思补正,方能实现“私法效果”。在法律有特别要求的情形下,仅有意义真实和语境自由尚不足以发生当事人欲求的私法效果,必须满足法律的特别要求,如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须经批准才能生效的合同经过批准等等,方可实现行为人意欲的“私法效果”。
概而言之,“私法效果”是行为人追求的一种具有私法效力的结果,这种结果能否达到、能否实现,先决条件是“意义”真实和“语境”自由。“意思表示”是手段,“私法效果”是目的,手段和目的结合,构成“法律行为”之全部内涵。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Rechtsgeschaeft是潘德克顿法学创造的法技术词汇,作为民法体系化的工具,其功能在于涵括市民社会中私人之间发生的引起权利变动的多种具体行为。它根源于民法,而且被创造者和使用者赋予了特定的要素和含义。如果选择了继受潘德克顿法学的概念体系,就应当尊重体系中的概念在最初创设时的语义蕴含,不管它们在传播中被翻译为“法律行为”还是其他词语,均不应就译词本身做出望文生义的语言解释和逻辑推理,更不在私法域之外滥用。对“法律行为”的解释和运用,应当恪守其私法域属性,把握“意思表示”和“私法效果”两个核心要素。在对“法律行为”进行语法学和逻辑学解释难以切合Rechtsgeschaeft本意的情况下,应当究问“法律行为”如何运用。认识到语言和逻辑在“法律行为”概念解释上的局限性,并能动地解释和运用“法律行为”,其价值才能够充分体现出来。语言哲学给予我们的启示,不在于“法律行为”不可言说,而在于要在使用中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