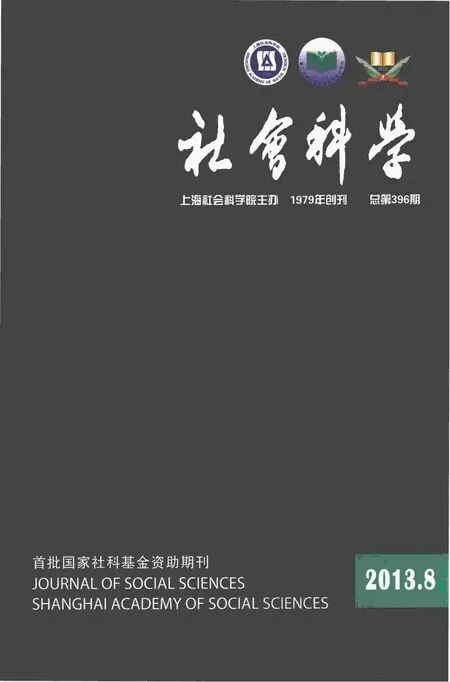从制度范式到权力范式*——海外视角下的中国人大制度研究
王 雄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政治体制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革①Walder Andrew,“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Economic Refor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in Walder,Andrew(ed.),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1-24.。在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中国共产党试图找到某种均衡,使国家既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又能在不触动执政党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改革。比如,建构制度化的政治精英游戏规则、重构国家基本政治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强化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简言之,中国政治改革的目的并非走向西方式民主,而是通过政治制度化的方式,使“硬性威权统治”变成“软性威权统治”②Nathan Andrew,“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ournal of Democracy,2003.14(1):6-17.,以此增强政权的合法性,提高其执政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大是否也依循制度化的路径,重构了与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而改变其既有的角色与作用,便引起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们的广泛兴趣③O'Brien Kevin,“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ing China”,The China Journal,2009.61(1).pp.131-141.。有些学者认为:“转型社会的议会要么是行政机构温顺的附庸,要么是一个好斗的挑战者。就前者而言,在官僚等级制的控制下,处于支配地位的行政机构常常限制立法机构的发展。议会被边缘化,要么成为与经济转型毫不相关的主体,要么只是行政机构或者党国体制的依附。就后者而言,在多元主义的竞争模式下,自由化的议会通常与其他权力主体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和对抗。”①Xia Ming,“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gime Transition(1978-98)”,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1998.4(4):124.
如果上述学者所言非虚,那么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大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具体而言,人大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积极有为的角色,还是边缘化的角色?它与其他权力机构之间是竞争、对抗关系,还是合作、妥协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海外学者是如何论述的?本文主要基于对海外英文文献的阅读和分析,从理论层面梳理出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的制度范式与权力范式,分析其研究趋向,并就上述问题作出尝试性的回答。
二、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的两种范式
(一)制度范式
政治制度的发展是衡量政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运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等指标衡量政治的制度化水平②[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0—19页。。借用亨廷顿的制度化概念,波尔斯比 (Polsby)对美国众议院的制度化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③Polsby Nelson,“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8.62(1):144-168.。其后,查菲 (Chaffey)等学者对美国、英国等国议会的制度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而形成议会研究中的制度化学派④Chaffey Douglas,“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tate Legislatures:A Comparative Study”,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970.23(1):180-196.Haeberle Steven,“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ubcommittee in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Journal of Politics,1978.40(4):1054-1065.Shepsle Kenneth,“Representation and Governance:The Great Legislative Tradeoff”,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88.103(3):461-484.Hibbing John,“Legislative Institutionalization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8.32(3):681-712.Squire Peveril,l “The Theory of Legislativ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California Assembly”,Journal of Politics,1992.54(4):1026-1054.。这种研究学派也影响了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的研究,形成了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的制度范式。在该范式下,研究者主要从制度建设与制度行动者两个方面讨论人大的制度变迁与角色扮演。
1.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视角关注的是人大的制度化过程。在该视角下,人大的制度化表现为理性化、内嵌化、网络化和宪政化等若干特征。
第一,制度的理性化。这是指国家能力的增长以及政治权力的制度化⑤O'Brien Kevin,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5.。在中国,虽然人大在法律上是权力机关,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它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由此需要通过发展理性的官僚制度来增强其政治能力。对此,人大进行了两方面的努力:其一,进行横向的官僚制度建设,比如,设立专门委员会,强化专门委员会的职权;提高常委会专业化程度,增加常委会的例会,缩减代表人数和延长会议时间;引入半竞争性选举,改善人大代表结构,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制定《立法法》等立法规则与程序,规范人大立法过程;等等。其二,加强纵向的官僚制度建设。比如,地方人大试图与上级人大建立起类似于政府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官僚科层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各级人大之间构建起某种弹性边界,人大与政府之间则建立起相对明确的职能界限,从而增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大的能力,并理顺了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劳动分工”关系⑥O'Brien Kevin & Luerhrmann Laura,“Institutionalizing Chinese Legislatures:Trade-offs between Autonomy and Capacity”,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1998.23(1):91-108.。
第二,制度的内嵌化。一些学者发现,在早期的人大制度发展中,人大比行政机构拥有更少的资源,它必须通过内嵌于行政机构的方式,在不与其他权力机构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来实现制度发展⑦O'Brien Kevin,“Chines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Legislative Embeddedness:Understanding Earl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94.27(1):80-107.。这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建立正式联系制度。如工作联系制度、列席会议制度、工作会议制度、法律工作指导制度、干部培训制度、文件交流制度、请示汇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代表联系制度、人民信访制度、工作经验和信息交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人大宣传制度,等等①Xia Ming,The People's Congres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Toward a Network Mode of Governance,Routledge.2008.pp.77-100,p.74.。其二,建立非正式的制度联系。比如,不定期的座谈会、由退居人大的政府各部门前任领导者建立起的与原任职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其三,建立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非常规的制度联系,形成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共生和依赖关系②Cho Young Nam,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3-142.。
第三,制度的网络化。人大制度的网络化是人大制度内嵌化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人大与行政机构之间存在着“内嵌化”的制度联系,而且实际上这种“内嵌化”制度联系已经形成了某种制度化的“网络”。这表现为:在横向上,人大与党委、行政机构、法院、检察院等机构之间建立起复杂的制度联系;在纵向上,各级人大之间也建立起复杂的制度联系。并且,在制度发展过程中,把人大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看作要么是合作的、要么是冲突的关系,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它们之间更多是以一种既合作又冲突的方式来彼此磨合③Xia Ming,“Informational Efficiency,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 Linkages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1997.3(3):10-38.Xia Ming,“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Power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a Network Explan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0.9(24):185-214.。事实上,人大自主性的提高,以及它与其他机构的冲突也相应增加,并没有让人大远离权力的中心。相反,这让整个政治体系获得了收益④Xia Ming,The People's Congres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Toward a Network Mode of Governance,Routledge.2008.pp.77-100,p.74.。
第四,制度的宪政化。衡量宪政化有多重指标,比如政治参与、自由选举、多元竞争、权力制衡,等等。简言之,“政治自由”是政治体制宪政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在人大的发展过程中,有学者认为,受苏联集权主义官僚体制的影响,早期全国人大只专注于理性化、内嵌化等层面的制度建设,是一种没有自由的政治改革⑤O'Brien Kevin,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不过,随着制度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宪政的萌芽开始在人大制度化过程中出现,突出表现为人大开始将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代表吸纳进其决策体制,以便在中国的宪政框架内增强人大的代表性功能。同时,通过听证会等形式,支持公众和社会团体参与立法,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催化剂,构建了中国宪政体制内的政治公民身份⑥Dowdle Michea,l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1997.11(1).Dowdle Micheal,“Constructing Citizenship:The NPC as Catalyst for New Norms of Publ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in Goldman Merle and Perry Elizabeth(eds.),Changing Mean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330-349.。甚至,公民参与人大立法的某些形式和程序还被写入《立法法》,例如听证会⑦Paler Laura,“China's Legislation Law and the Making of a More Orderly and Representative Legislative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2005.182(6):310-318.。因此,虽然由《立法法》所确定的人大立法制度仍然被一些学者批评为形式大于内容,但它的确为人大今后的进一步宪政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⑧Li Yahong,“The Law-Making Law: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in the Chinese Legislative System?”Hong Kong Law Journal,2000.(30).。
2.制度行动者
制度行动者视角主要关注的是人大制度化背景下,人大代表和选民等制度行动者的行为模式的变化及其对人大制度的影响。
第一,人大代表的行为模式。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试图将人大代表加以类型化,并分析了他们的类型转换和角色冲突。比如,谭睦瑞把1980年以前的全国人大代表分成荣誉代表与党和国家高级官员两种类型。这两种代表都存在议政能力不足、议政时间不足和议政精力匮乏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大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提高代表的学历和专业技能;二是推动干部“四化”,将大批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干部作出制度性“退休”安排。这使得一些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良好政治关系网的老干部,包括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等被安排进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全国人大的制度发展赢得了政治空间①Tanner Murray,“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In Goldman Merle and MacFarquhau Roderick(eds.)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s Series 12,1999.pp.100-128,p.123.。
欧博文把20世纪80年代的人大代表分为消极行动者、代理人和谏诤者三种类型。消极代表往往把代表当作一种荣誉,经常性地缺席人大会议,也不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有意义的提案,是一群“有很大的办公室却没有一张桌子”,“只知道感谢国家的信任”,把代表的责任当作“政治上的装饰品”,“只会举手、鼓掌和点头”的代表②O'Brien Kevin,“Agents and Remonstrators:Role Accumulation by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8(6).p.365.pp.359-380.。扮演代理人和谏诤者角色的人大代表属于相对活跃的人大代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人大代表是国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者,负责对具有同样背景的社会群体宣传、解释国家政策。因此他们是政府的小帮手,而不是对政府政策品头论足的异议者。与代理人的角色有所不同,谏诤者则试图通过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异议以及纠正政府的错误,以此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③O'Brien Kevin,“Agents and Remonstrators:Role Accumulation by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8(6).p.365.pp.359-380.。
人大代表的行为模式变化也体现在全国人大的投票领域。首先,全体一致自动通过法律的现象已经变得极为少见;其次,不是所有的法律都能在人大获得通过;最后,大量不满意投票现象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出现已经司空见惯。一些人大代表的代表观念也发生改变,他们越来越视自己为联系社会的桥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社会上的不同声音。以前那种“高高在上”的代表意识转变为“自下而上”联系选民的心态④Tanner Murray,“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In Goldman Merle and MacFarquhau Roderick(eds.)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s Series 12,1999.pp.100-128,p.123.。甚至,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代表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并试图在人大立法的过程中维护这些团体的利益。由此,有学者认为,人大代表的角色转变,将推动人大在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扮演关键的制度角色⑤Hu Shikai,“Representation without Democratization:The‘Signature Incident’and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3.2(2):3-34.。不过在欧博文看来,尽管以“谏诤者”人大代表的身份出现确实反映出其角色的某种积极变化,但这种“谏诤”只是类似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进谏和“清议”,而非代议制中的政治反对派⑥O'Brien Kevin & Li Liangjiang,“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Question of‘Deputy Quality’”,The China Information,1993-1994.8(3):20-31.。
人大代表的角色转变与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代表更替、社会变迁和自我期待等因素相联系。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激发了代表的责任意识;代表的阶层比例配备要求的放松以及多轮选举改善了“代表的素质”;社会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各级人大领导面临着纠正社会不公现象的巨大压力,这些使他们倾向于利用人大代表来扮演谏诤者的角色,表达社会诉求、反映社会公益、舒缓社会压力和矛盾⑦O'Brien Kevin,“Agents and Remonstrators:Role Accumulation by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8(6).p.365.pp.359-380.。
欧博文等海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人大代表的角色变化,并且其研究的对象多为全国人大代表。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地方人大代表的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赵英男认为,90年代以来,地方人大代表分别扮演着四种角色:监督、反映、政策提供和榜样。人大代表的主要角色是“公共监督”和“意见反映”,而不是欧博文所说的“政权代理”和“谏诤”。不同职业阶层背景的代表倾向于扮演不同的人大代表角色。工农阶层的代表趋向于成为“公共监督者”和“意见提供者”;知识分子和官员倾向于成为“政策提供者”;私营企业主和商人则热衷于扮演遵纪守法、热爱社会公益事业的“榜样”角色,这也是最接近欧博文所说的“政权代理者”的角色。此外,越是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其参政议政的活动越是频繁和活跃⑧Cho Young Nam,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83-112.。而墨宁则发现,身处不同层级的人大代表有着不同的选民意识。基层人大代表的选民意识较强,高层人大代表的选民意识则较弱①Manion Melanie,Chinese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as an Institution,APSA 2009 Toronto Meeting Pape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9 Annual Meeting).。总之,人大代表的角色转变给人大制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影响。人大代表和各级人大通常以“人民”的名义争取党的支持,破除政府等机构对其工作的干扰,从而提高其政治地位。
第二,选民的行为模式。在人大代表选举的过程中,人大制度建设所导致的选民的行为模式变化也引起了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者的注意。首先,他们就选民的投票动机进行了讨论。史天健认为,1979年基层人大的选举制度改革,使基层人大选举成为一种半竞争性的选举。在此情况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相对广泛信息和资源的选民,不再用不投票来表达其对政治的不满,而是开始站出来投票。他们把半竞争性的人大差额选举看作是表达自身利益、惩处腐败官员,推动民主转型的政治机遇②Shi Tianjian,“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Voting Behavio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Choice Elections”,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99.61(4):1115-1139.。不过,陈杰与钟扬却认为,受政治动员的驱使以及对政权的支持等影响,相比那些受过教育、拥有资源、对民主有着特别偏好的选民,那些与政治权威有着密切联系的或者本身就是政权代言人的选民更容易出来投票③Chen Jie & Zhong Yang,“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Journal of Politics,2002.64(1):178-197.。
第三,选民的投票率。研究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选举的学者发现,由于候选人的提名受政府或政党的操控,选民的政治效能感不高,这些地方普遍存在着政治冷漠的现象。然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大选举的实际投票率在稳定增长。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相比于其他政治机构的运作,人大代表选举相对比较公正;二是人大机构的职权在不断扩大,在法律制定方面也扮演着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正是出于对人大选举过程的信任以及人大权力增长的信心,选民的人大代表投票率保持在稳定增长的水平④Kwong Julia,“Democracy in China:Voting for Beijing People's Congress Delegates”,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2008.35(1).pp.7-9,pp.10-11.。还有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普遍存在着政治动员现象,如果国家的政治动员不复存在,选民的投票率将如何变化?管梅与格林通过政治实验法研究了人大选举中非强制动员下选民的投票情况,结果发现非强制性动员可以有效地提高选民的投票率⑤Guan Mei & Green Donald,“Noncoercive Mobilization in State-Controlled Election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Beijing”,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6.39(10):1175-1193.。
第四,选民的投票策略。邝朱丽认为,北京选民采用了中国传统语境下的候选人选择策略。一开始他们倾向于选择有良好道德风范,不为金钱或权力所腐蚀的社会“能人”;之后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替其利益说话的候选人。更有甚者,他们在进行合乎民主选举的理性选择的同时,仍然会保持一些传统的价值理念。譬如,尽管个人关系会导致腐败,但它仍然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成为选举中的一项重要的政治选择考量⑥Kwong Julia,“Democracy in China:Voting for Beijing People's Congress Delegates”,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2008.35(1).pp.7-9,pp.10-11.。总之,选民的行为模式一方面受人大选举制度改革的影响和塑造,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变化又反过来推动人大在制度上作出回应,并以此推动人大的制度改革、建设和发展。
(二)权力范式
西方学者在对议会专门委员会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时发现,在议会的制度发展与其权力扩张之间,有着近乎完美的正相关关系:议会的制度化发展增强了它的立法权力,提高了它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⑦Lees John & Shaw Malcolm(eds.),Committees in Legislatures:A Comparative Analysis.Duke University Press.1979.。中国人大在制度发展的同时,其权力也得到明显增强,并由此重构了人大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而导致人大权力运作的某些变化。在此背景下,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的研究开始从制度范式转向权力范式,形成了关于人大权力运作的五种模式:合作模式、制衡模式、磨合模式、网络模式和垃圾桶模式。
1.合作模式
合作模式的提出源自欧博文对全国人大早期发展的研究。他发现,全国人大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来自既有体制的重重束缚,另一方面其制度也尚未健全,从而难以有效地履行职权。因此,它选择了以制度发展而非获得自主性来作为人大发展的优先目标。通过建立与其他权力组织之间的内嵌化联系,人大在没有与其他权力机构发生显著冲突的同时,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权威,从而实现了制度发展和权力扩张①O'Brien Kevin,“Chines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Legislative Embeddedness:Understanding Earl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94.27(1):359-380.O'Brien Kevin & Luerhrmann Laura,“Institutionalizing Chinese Legislatures:Trade-offs between Autonomy and Capacity”,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1998.23(1):91-108.。夏明进一步发现,省级人大在早期权力的扩张中也存在着类似全国人大权力运作的合作模式。在省级人大的早期发展中,由于与全国人大和普通公民相互隔绝,省级人大的资讯匮乏。为了求得政治生存,省级人大与全国人大等权力机构和普通公民之间建立起了复杂的制度联系以及资讯沟通渠道,从而大大提高了它们的信息收集、加工和传播能力,奠定了它们在上下各方之间的“信息经纪人”地位②Xia Ming,“Informational Efficiency,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 Linkages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1997.3(3):10-38.。可见,人大制度的发展需要是它们与其他权力机构之间建立合作模式的基础。无论欧博文的“内嵌化”合作模式,还是夏明的“信息经纪人”式合作模式,都是早期人大为了实现权力扩张而采取的缓和矛盾与冲突的策略。然而,随着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人大也越来越积极和活跃,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人大与其它权力机构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越来越频繁,合作模式已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因此,研究中国人大制度的海外学者开始关注人大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另一种权力运作模式,即制衡模式。
2.制衡模式
陈安提出一个“制衡模式”,用以解释人大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他发现,由于地方党委在选举地方人大代表以及提名政府官员候选人等方面的控制能力的减弱,政治权力在地方党委、政府和人大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地方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互锁的制度”,即地方党委、政府和人大都不能仅仅根据自身的制度偏好来制定政策,各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一种没有“政治反对派”的制约与平衡的权力关系③Chen An,Restructuring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Alliances and Opposition,1978-1998,Lynne Rienner Public,1999.p.194.。这种权力关系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地方人大与民众之间建立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其代表性得到增强,人大及其代表越来越敢于监督政府;另一方面,中央也有意通过地方人大的这种制约与平衡,推动地方政府改革,控制地方党政干部的渎职和腐败现象。
奥斯卡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在法治化背景下,地方人大成为地方党委制衡地方政府的有效手段,并且推动地方党委活动的法治化。在地方党委的支持下,地方人大常委会以评议和质询等方式对地方政府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和制衡。反过来,党委的行为也受到地方人大的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这就使党委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行使权力。在这种关系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党委、政府和人大之间扮演着缓冲区的角色,并形成人大、党委与政府三者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最终,地方人大对威权统治者的权力进行了限制,使看似不受限制的威权政体成为“受限制的威权政体”④Oscar Almén,Authoritarianism Constrained:The Role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Department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Ph.D.Dissertation:Göteborg University.2005.。佩拉则以《立法法》的立法过程为案例,诠释了现实政治中全国人大与国务院、地方人大等权力机构间的协商过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权力平衡关系⑤Paler Laura,“China's Legislation Law and the Making of a More Orderly and Representative Legislative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2005.182(6):301-318.。
导致这种制衡模式出现的原因,在于人大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首先,人大的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巩固与加强。经过多年的制度建设后,人大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着独立行动能力的权力机构,能够在一些关键议题方面发挥影响力。其次,党委进行了权力收缩与调试,其对下级党委与政府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迫使它需要赋予人大更多的权力,来制衡与控制下级党委与政府的腐败与渎职。比如,墨宁发现,由于中央与地方党委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更好地监督和控制地方党委以及选拔更加胜任的地方官员,在1995年的地方人大组织法改革中,中央赋予地方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权,以便让人大代表提名的候选人同地方党委提名的候选人相互竞争,从而产生了事实上的地方人大与地方党委在人事权方面的制衡关系①Manion Melanie,“When Communist Party Candidates can Lose,Who Wins?Assessing the Role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the Selection of Leader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008.195(1):607-630.。
然而,中国人大的这种权力制衡模式与西方议会的权力制衡模式相比,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中国人大并不存在类似西方议会中明确的行政—立法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其次,中国人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也不存在类似于西方议会的政党制度和多元竞争关系。人大与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党领导下的“劳动分工”关系。对此,麦克法夸尔在考察中国省级人大的作用时就认为,中国人大更像是明代的帝国监察机构,而与制衡模式下的美国议会迥然有别。这种类似于帝国检查机构的制度专门用于对其他机构进行监视和控制,之前其大部分官员都身居党政要职,这可以让他们以一种大致平等的地位与现任政府官员进行周旋②Mac Farquhar Roderick,“Report from the Field: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The China Quarterly,1998.155(9):656-667.。
由于人大制衡模式的这些特征,它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不会像西方议会那样,以一种不合作、不妥协、对抗性的姿态与其他权力机构进行博弈,而是以冲突与合作并存的方式与其他权力机构进行沟通与联系,这就引发了学者们对人大权力运作的第三种模式,即磨合模式的讨论。
3.磨合模式
在夏明看来,制衡模式并没能很好地理解中国政治的内在特点。中国政治在本质上极为重视政治的内在和谐和圆通,即使存在冲突和分歧,它也会试图将其最小化,以保持政治的和谐和稳定。由此,与这种政治特点相联系的磨合模式更能够解释人大权力运作的实质。他如此描述“磨合模式”的特征:
像开一辆新车或运转一种新的机器,所有的部件都需要“试运行”与“碾磨”,以便让彼此相互适应。不同的部分有着差异,于是分歧就产生了。但这是一个双向调试过程:每一个部分都抹去了不和谐的质性,而变得圆滑与灵巧。分歧最终促成合作而非冲突,“磨合”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合作竞争”的关系③Xia Ming,“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gime Transition(1978-98)”,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1998.4(4):122.。
首先,与制衡模式不同的是,磨合模式并不挑战党的权威,而是寻求党的支持。虽然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党逐渐改变了自身的统治策略,减少了对公民私人领域的干预,只关注一些关键的公共领域问题,对自身权力进行了相应的收缩和调试④[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吕增奎等译,俞可平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但是,人大并没有就此采取与党委对抗的权力模式,而是小心翼翼地处理它与党的关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比如人事任免、选举程序等,人大都向党委咨询、协商、请示和汇报,以争取党委的支持和信任,否则人大权力的正常运作便无法进行,权力扩张也就失去坚实的依靠。
其次,磨合模式的关键特征还在于地方人大面对不同的权力主体,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⑤Cho Young Nam,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在它与党的关系上,地方人大力图取得党的支持,而不是试图获得独立于党的权力;在它与政府的关系上,地方人大通常与政府合作而非对抗;在与两院的关系方面,它往往对权力相对弱势的法院和检察院采取比较强硬的姿态;在与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关系上,它鼓励和动员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参与人大的立法协商,并试图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由此构成了人大与其他权力机构之间既合作又对抗、既协商又冲突的丰富图景。
相对于合作模式和制衡模式,磨合模式的优点在于,它看到了人大权力运作中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也看到了人大在面对不同权力主体时采取的不同策略。然而,它还留下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这种磨合策略的运用为何能够奏效,它以怎样的组织形式进行运作?针对这个问题,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又发展出人大权力运作的第四种模式:网络模式。
4.网络模式
与磨合模式相比而言,网络模式既关注到了磨合模式中人大权力运作的行动者之间合作和竞争的复杂互动关系,也注意到了这种复杂互动关系建立的制度基础。
首先,在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上,市场模式强调权力主体之间的分歧与冲突、竞争与对抗;官僚模式强调命令与服从、协商与合作;网络模式则强调权力主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和谐的互动模式①Xia Ming,The People's Congres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Toward a Network Mode of Governance,Routledge,2008.p.15.。在人大的权力运作中存在着市场模式与官僚模式相混合的现象。比如一方面,人大内部已经逐渐形成了理性化的官僚科层结构;另一方面,各级人大之间又没有发展出类似政府组织的领导结构,而是形成了相对松散的“法律监督”、“工作指导”、“业务联系”等关系②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版,第253—257页。。因此,无论官僚模式还是市场模式都不能很好地描述与解释上述现象。相反,兼有市场模式和官僚模式优点的网络模式则能较好地解释人大权力的这种运作逻辑:一方面它继承了后共产主义体制的官僚权威结构,能够将分散的行动者整合起来,降低集体行动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它也能在市场模式下组织相对松散的各级人大跨越组织边界,进行制度学习、沟通、调试与渗透③Xia Ming,“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Power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A Network Explanation”,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0.24(9).p.192,p.187.。
其次,在权力互动的制度基础方面,合作模式将早期人大的制度发展看作优先选择。人大选择了牺牲自主性来换取制度的发展和能力的提高。制衡模式把争取获得权力与自主性作为优先发展的目标。不过,在夏明看来,人大的发展既不是制度优先,也不是权力优先,而是序列策略模式 (the strategy sequencing)。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期,制度建设与权力竞争呈现出交互发展形式,并没有截然分离开来④Xia Ming,“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Power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A Network Explanation”,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0.24(9).p.192,p.187.。人大通过权力运作的网络模式,既实现了制度发展的内嵌化,也在制度的内嵌化过程中与其他权力主体不断地发生冲突与对抗、沟通与协商、妥协与合作。
5.垃圾桶模式
上述几种模式存在着若干共同的理论预设:其一,人大的权力扩张建立在官僚制度的发展之上,无论这种制度发展是以内嵌化的方式进行,还是以网络化的方式进行;其二,人大与其他机构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目标和偏好,这导致人大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促使它们通过竞争与对抗、合作与协商等方式解决分歧。然而,这些模式也面临着某些共同的问题:首先,它们只关注人大与其他机构之间的意见和共识的缓慢达成以及制度的“边际性创新”⑤何俊志:《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33页。,具有强烈的渐进主义偏好;但在实际政治权力运作中,激进的制度创新和非渐进性政策创议也时有发生。其次,它们大多只对国家层面的制度行动者感兴趣,对社会层面的个体行动者则关注不足⑥Tanner Murray,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Institutions,Processes,and Democratic Prospec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5-35.。比如它们很少关注代表和选民的角色。由于组织政治模式有这些弊端,谭睦瑞提出用垃圾桶模式取代组织政治模式,用于解释人大在立法方面的权力运作。
所谓垃圾桶模式,即政策制定是一个“组织的无政府状态”(organized anarchy)⑦关于垃圾桶模式的论述请参阅 Cohen Micheal,March James&Olsen Johan,“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2.17(1):1-25。。在谭睦瑞看来,人大的立法过程非常契合于这样一种“组织的无政府状态”。首先,人大立法程序比较模糊。在国家层次的立法过程中,多个中央机构,如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以及最高法院等都有相应的立法权,但各自的正式立法程序、规则以及制度分工等并不清楚。与此同时,执政党的领导与人大立法之间也没有形成明确的规范,进而导致法律与党的政策之间的模糊①Tanner Murray,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Institutions,Processes,and Democratic Prospec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2-33.。其次,人大立法的关键行动者和参与者比较模糊。由于中央的制度化分权,党对立法过程的控制能力下降,削弱了党所扮演的关键立法行动者的角色②Tanner Murray,“The Erosion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over Lawmaking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8):381-403.。与此同时,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法制办承担了大量与经济事务相关的法案起草和审议。并且,在立法的不同阶段中,与政权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法团组织”也不断地参与到相关立法议案的起草和审议中来③Cho Young Nam,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3-142.。最后,人大立法目标比较模糊。人大立法处于多重目标的交叠冲突之中:一方面,它试图追求“依法治国”的目标,以此扩大自身的权力;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党的领导,以立法来体现党的政治意图和控制。一方面,它试图维持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以增强法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它又尝试与时俱进,根据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来修改和调整法律。
尽管垃圾桶模式在解释人大权力的运作方面,看到了人大立法过程中的非渐进性和政治参与的多元化,但它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党国体制中,党虽然有选择地进行了权力收缩,不直接干预人大的立法过程;但它在某些领域却强化了政治控制,比如选举和人事方面。因此,党依然是最重要的领导者。其次,中国政治中以精英为中心的决策模式依然是主要的权力运作模式,政治体制对外界的开放程度有限,普通的政治参与者无法参与诸如立法等政治决策过程。最后,人大的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无论正式的立法、选举、监督等制度或程序,还是非正式的如党与人大之间的制度性联系等,都在逐渐变得清晰化和规范化。这些情况的出现势必对垃圾桶模式的解释力构成有力的挑战与质疑。
三、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的趋势与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体现出了若干鲜明的特点与趋势。在理论建构方面,研究者运用了丰富的政治学理论和模式,对于解释人大的角色转变提供了多样的解释视角。在研究视角方面,他们大致经历了从制度范式向权力范式的演变。在研究对象方面,他们从早期的全国人大制度研究逐渐地转向了对地方人大制度研究,特别是省级人大和基层人大的研究。然而,在这些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比如,为何海外的人大制度研究会从制度范式转向了权力范式?这与地方人大的角色转变有着何种关系?事实上,如果不了解人大角色的历史演变、类型以及地区、层级差异,也就无法理解导致这种范式转换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中国人大的角色经历了历时性的演变。由于存在着与强势权力主体之间的强烈的政治依附关系,1979年以前的中国人大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1979年之后,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角色,人大在处理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时,通常会以制度建设作为优先取向,增强自身的能力和话语权,而不是急于摆脱政治依附关系。当人大制度建设已有所发展,人大已经崛起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时,它在面对其他权力机构的时候就会显得更加自信。此时,人大一方面会继续强化自身的制度建设,通过加强内嵌化和网络化制度建设来增强组织的复杂性,运用“依法治国”政策、基层选举制度、代表联系制度等政策或制度来巩固和扩大职权,从而形成与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相互竞争、抗衡和制约的场景。另一方面,尽管中央试图将人大打造成治理和监督地方政府的权力主体,地方党委也尝试让地方人大制衡和约束地方政府,预防、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党组织本身也在改革中进行了权力收缩和调适;但这些变化在扩张人大权力政治空间的同时,却并没有触动或者改变既有的政治依附关系。因此,人大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仍然只是一个权力变化的焦点,而非政治权力的中心。
其次,人大的角色类型开始趋向多元化。海外的中国人大制度研究者在分析人大的功能时,常常会以某种单一的维度审视人大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或者把人大看作仅仅提供政治合法性的象征机构,或者把它看作派系政治或非正式政治的权力斗争场所①Nathan Andrew,“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The China Quarterly,1973,(53):34-66;Dittmer Lowell,“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The China Journal,1995,(34):1-34.,而鲜有把它看作准民主机构或准官僚组织。事实上,随着中国政治内部的悄然变化,人大已成长为有着多重政治功能的角色。在制度合法性方面,一方面人大仍然在形式上保留着人民主权的仪式性象征作用,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民主资源;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人大选举的民主性、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和履职能力、选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等民主化指标都得到明显的提高。在制度结构方面,尽管在早期人大的发展中,尤其在全国人大的早期发展中,特殊政治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在人大的权力运作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随着人大制度化的不断演进,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越来愈依循正式的制度和规范②Bo Zhiyue,China's Elite Politics: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Balance.World Scientific Public,2007.,人大的发展也越来越按照一个准官僚机构的逻辑进行运作。在制度功能方面,人大既为精英提供了一个参政议政的论坛,以此平衡利益分化后的精英内部权力分配,强化精英同政权的依附关系;它也为行政机构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并督促其完善施政方案,提高其执政绩效。
再次,人大的角色呈现出地域与层级的差异性。在地域上,地方人大的制度发展与权力运作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状态,在行为模式上表现为先锋者、追随者和沉默者三种角色。有学者认为,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与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富裕程度没有特别的关系,而关键原因在于各地的领导结构。如果地方人大的领导有着强烈的监督意识,并且能够得到当地党委的坚定支持,那么人大的权力运作和行使就会比较活跃,反之则会无所作为③Cho Young Nam,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尽管这种解释仍有待通过案例和数据来进一步验证,但在现实政治中,不同地域人大的运作模式确实存在差异。另外,在层级上,较低层级的人大可能要比较高层级的人大更加活跃。换言之,基层人大要比省市一级的人大活跃,而省市人大要比全国人大活跃。选举法规定,县级以下的人大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级以上的人大由下一级人大间接选举产生。因此,相比之下,县级以下人大容易受选民的影响,在立法、监督和决定地方重大事件方面与地方政府的对抗和冲突可能会更多;省市一级人大在人大制度中处于基层人大与全国人大之间,发挥着“信息经纪人”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省市一级的人大必然会以某种更加缓和的方式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加注重在合作与竞争中找到平衡点。全国人大处于中央的核心决策层,任何政治改革或者创新都必然会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这就导致它在处理与党中央、国务院等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时更加谨慎和保守。
正是各级人大特别是地方人大的角色变化,引发了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者反思制度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制度范式简单地强调人大制度的渐进演变和制度行动者对制度的能动作用,忽视了制度背后人大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下人大权力扩张的策略,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权力范式所关注的问题。在权力范式看来,获取权力才是人大各种行为的根本动机。无论加强其自身的制度建设,还是对其他机构采取的种种策略,都是为了提高人大的机构运作效率,增强人大的影响力。在现实层面,自1979年的分权改革以来,地方人大的角色与作用日趋活跃与重要,这使得对人大制度化的研究已经不足以反映各级人大变化的全貌,尤其是反映地方人大的各种权力运作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对人大作深入且前沿的研究,就必须对地方人大的权力运作模式深入探索,以弥补制度范式研究的局限。在这种情况下,以地方人大权力运作模式为分析对象的权力范式也就成为海外人大制度研究的必然选择与发展趋势。
总之,制度范式可以为人大的制度化提供分析的框架,权力范式可以为人大的权力运作提供解释模型,两种范式各有所长。在地方人大的角色转型的推动下,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逐渐从制度范式转向权力范式,弥补了制度范式所存在的问题,而制度范式所提供的制度化分析框架依然对人大的制度分析有所帮助。由此可见,今后我国的人大制度研究应该吸取这两种范式的特长,对地方人大的制度化和权力运作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总结和分析了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的现状、趋势与问题。在现状方面,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存在着制度范式与权力范式两种主要分析路径。制度范式强调人大的制度建设和制度行动者的能动作用。权力范式强调人大与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的权力互动关系与模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合作模式、制衡模式、磨合模式、网络模式与垃圾桶模式等模型。在趋势方面,它经历了从制度范式向权力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与演变与地方人大的角色转变息息相关。它们在中国政治中的角色与地位越来越重要,其权力运作的活跃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使得单纯地从制度范式来解释和分析其角色变化面临着诸多问题。相反,权力范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范式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人大与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途径提供了可能解释的模型。在今后的人大制度研究中,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制度范式出发,对地方人大的制度化进行深入的考察,揭示其制度化过程中的特征与趋势;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权力范式下的权力模型对其权力运作开展深入研究,勾画出它们与其它权力机构的权力关系的丰富图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避免将这些范式削足适履地套用于人大发展之复杂现实。惟有在吸收海外政治科学理论与模式的同时,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对既有的理论与模式进行检验,才有可能对中国人大制度作比较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并将本土的人大制度研究进一步理论化,形成人大制度研究领域“从一个‘消费者’领域成长为一个‘生产者’领域”的转变①Perry Elizabeth,“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 Rel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9):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