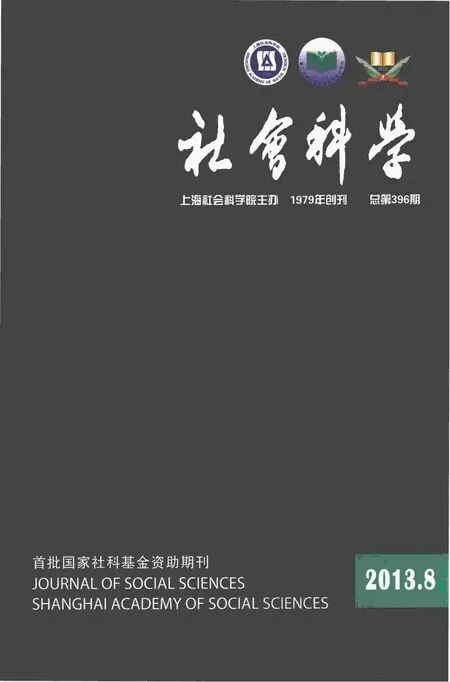论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的文学革命争论
高传峰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要从“八事”入手,来改良中国文学。胡适在文中明确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①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紧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②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陈独秀在文中同时指明“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③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在这样一篇言辞激烈的讨伐檄文中,陈独秀的这句话显得诚实中肯。
“文学革命”一词首次出现,是在胡适写于1915年9月17日送给梅光迪的一首诗里,名为《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后收在《尝试集》里)。在这首诗里,有“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的字样。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词。当是时,他自己也绝不会料到,这个词会在今后的中国文化界产生何等大的影响。“文学革命”一词,以及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都不是横空出世,而是胡适在和朋友们的讨论切磋中形成的。这一点,在胡适的《尝试集·自序》、《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等文章中都曾反复提到,在胡适日记、胡适与友人往来的书信中均留有他们当年讨论的痕迹。由于胡适有大量文字传世,再加上胜者为王的心理,多年来,人们偏信的是胡适的“一面之辞”,而对于当年和胡适热烈讨论的朋友们④当年参与或见证了这场讨论的朋友主要有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唐钺、朱经农、陈衡哲,均在本文论述之列。的意见进行研究的少之又少。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来重新讨论胡适当年与梅光迪、任鸿隽等友人关于文学革命的早期争论。
一、胡适与梅光迪诸人关系由来
胡适与朋友们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主要发生在1915年夏—1916年间,是他留美归国之前。(他1910年8月16日赴美,1917年6月启程回国)在讨论这场争论之前,有必要先对胡适与诸人关系由来做一考证,以便于论述。笔者把胡适与诸人关系分为三类:与梅光迪为旧友;与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为中国公学校友;与唐擘黄、陈衡哲为海外同乡。下文分别详细论述。
(一)胡适与梅光迪① 梅光迪 (1890—1945),字迪生,又字觐庄,安徽宣城人。1911年考取庚款留美资格,属第三届庚款官费生 (胡适是第二届)。梅光迪赴美后,先是在威斯康辛大学,后1913年转入芝加哥西北大学文理学院,1915年毕业。同年秋往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1919年获硕士学位回国。
梅光迪1911年赴美,胡适日记载:“见北京清华学堂榜,知觐庄与钟英皆来美矣,为之狂喜不已”②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2页。。可知梅光迪与胡适为旧友。1994年,安徽黄山书社出版耿云志主编的42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其中第33册收梅光迪致胡适信45通,并附梅光迪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一件。③后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除将此45通信及梅光迪的序全部收录外,另从别处录出梅光迪致胡适信1通,共收46通信。本文所引梅光迪文章及书信即参看的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在这篇小序里,梅光迪细述了与胡适的交情。梅光迪是“得由邵庭以介于适之”。邵庭,即胡邵庭,为胡适宗亲。1909年秋,胡适曾“与余与邵庭同舍而居”。1910年夏,梅光迪与友人同赴北京应庚款官费留美的考试,不期与同去应考的胡适在船上相遇。惊喜过望之余,“每浪静月明,相与扺掌扼腕,竟夜不少休止,令余顿忘海行之苦”④梅光迪:《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载《梅光迪文录》,罗岗、陈春艳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后来,胡适考上了,梅光迪落榜,于次年考取。
(二)胡适与任鸿隽⑤ 任鸿隽 (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省归安县菱湖镇,生于四川省垫江县。1912年12月到美国,1913年初进美国康奈尔大学,1916年获化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哥伦比亚大学,1918年获化学硕士学位。1918年10月回国。参看赵慧芝《任鸿隽年谱》,载《中国科技史料》第9卷,1988年第2期。、杨杏佛⑥ 杨杏佛 (1893—1933),名杨铨,杏佛为字,成年后以字行。祖籍江西清江,生于江西玉山。1912年12月到美国 (与任鸿隽同行),后选读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1916年夏,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18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年10月回国 (与任鸿隽同行)。参看许为民《杨杏佛年谱》,载《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1991年第2期。、朱经农⑦ 朱经农 (1887—1951),祖籍江苏宝山,生于浙江浦江。1916年春赴美,任留美学生监督处书记,并就学于华盛顿大学。1918年获学士学位,1919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辞书记职并转纽约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院。1921年回国。参看《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359—360页。
提起胡适与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的关系,不得不提“中国公学”。1912年12月1日,任鸿隽与杨杏佛乘车到达美国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城。当天的胡适日记载:“十二时下山,至车站迎任叔永 (鸿隽),同来者杨宏甫 (铨),皆中国公学同学也。……是夜,叔永、宏甫均宿余所。二君为谈时下人物,有晨星寥落之叹。所喜者,旧日故人如朱芾华、朱经农、王云五诸人,皆慷慨任事,可喜也。”⑧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2页。胡适与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的校友关系由此也可得到见证。
中国公学是“中国人自己一手创办的第一家私立大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停办”⑨[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07页。。中国公学创办的缘起是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是日本应清政府要求而公布的,实为戒备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力量。此项规则一经公布,便遭到了留日学生的反对。此后,一部分留日学生愤而归国,遂创办了中国公学。中国公学1906年夏举行招生考试,胡适即于这一年考入。1908年夏秋间,中国公学闹学潮,部分学生退出组建中国新公学。胡适亦在列,“便同其他坚持罢课的学生一起投入艰苦的创办新公学的活动中去了”[10]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中国新公学筹备完成后,教务干事李琴鹤请胡适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教员,胡适欣然同意。1909年冬,中国新老公学合并,胡适没有回去,后往华童公学担任教职。
1.胡适与任鸿隽、杨杏佛
任鸿隽与杨杏佛都是1907年进入中国公学读书①许为民《杨杏佛年谱》载杨杏佛1908年进中国公学,有误。此处参看杨宇清《杨杏佛传》,收《杨杏佛》,杨宇清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比胡适晚一些。任鸿隽进入中国公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剪去辫子,改换易装。秋瑾、章太炎等人在该校的活动,对其政治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课余常同张奚若、杨铨 (杨杏佛)等人谈论时政,向往革命,怀有推翻清政府的情绪。此时的要好学友除杨杏佛、张奚若外,还有胡洪骍 (后改名胡适)……朱经农 (朱经)……等”②赵慧芝:《任鸿隽年谱》,载《中国科技史料》第9卷,1988年第2期,第54—55页。。后“因该校课程较浅,不甘就此卒业,遂于年末离开中国公学”③赵慧芝:《任鸿隽年表》,载《任鸿隽陈衡哲家书》,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编,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1页。,1908年初东渡日本留学。这样,任鸿隽在中国公学仅呆了一年时间。
在《杨杏佛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杨杏佛与任鸿隽、胡适等人交往的记载。“1907年,杨杏佛进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读书。杨杏佛思想开朗,不但较早地剪去辫子,而且喜看《民报》,好发议论。课余常与同学……任鸿隽等人在江边堤道上散步,边吃花生,边谈时事,经常流露革命情绪,欲为推翻清王朝效力。”④杨宇清:《杨杏佛传》,载《杨杏佛》,杨宇清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杨杏佛在中国公学呆的时间比较长,且与胡适关系不一般。1908年中国公学闹学潮后,胡适在另组的中国新公学担任英文教员,“杏佛与……张奚若均为其受业弟子”⑤杨宇清:《杨杏佛传》,载《杨杏佛》,杨宇清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据说,胡适很看好杨杏佛,认为他是受业学生中“最有理想、最有出息的一个”⑥杨宇清:《杨杏佛传》,载《杨杏佛》,杨宇清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此后,“两人长时期以师生加朋友相待”⑦杨宇清:《胡适与杨杏佛》,《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杨杏佛至1911年从中国公学毕业。
由上述材料可知,胡适与任鸿隽、杨杏佛均为中国公学的校友,且与杨杏佛还有一层师生关系,三人在中国公学时已是好友。
2.胡适与朱经农
朱经农与胡适、任鸿隽、杨杏佛同为中国公学的校友,与后三人相比,朱经农的年龄虽不是最大,但资格最老。中国公学及后来的中国新公学的创办,朱经农都参与其中。“因留日学生遭日人之不平待遇,与同学数百人集体归国在上海自办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后来,“未几以同学中意见不一,别组中国新公学,经农膺选为教育干事,一面协同办理学校行政,一面按照课程听讲”⑧王云五:《我所认识的朱经农先生》,载《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140页。。1909年,朱经农毕业,中国公学与中国新公学合并,朱经农开始在中国公学任教。
胡适在中国公学是有名的少年诗人,据胡适《四十自述》里记载,当时“同学中如汤昭(保民),朱经 (经农),任鸿隽 (叔永),沈翼孙 (燕谋)等,都能作诗”⑨胡适:《四十自述》,载《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另据《任鸿隽年谱》中载,任鸿隽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要好的学友就有杨杏佛、胡适、朱经农等人。这证明他们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很出色,且关系要好。
1916年,朱经农赴美。胡适在6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朱经农新自国中来,居美京,为教育部学生监督处书记,将以馀力肄业于华盛顿大学。经农为中国公学之秀,与余甚相得……今闻其来,喜何可言?惜不能即相见耳。”[10]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这可看作是他们关系友好的又一个证明。
(三)胡适与唐钺[11] 唐钺 (1891—1987),福建闽侯人。胡适在文章中称唐擘黄。1914年留美,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后改学心理学。1917年毕业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心理学系深造,192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参见《唐钺履历》,载《唐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416页。、陈衡哲[12]陈衡哲 (1890—1976),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常州。英文名莎菲。1914年赴美,在PutmanHall学校读预科。1915年秋进入瓦莎大学学习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夏毕业,进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继续攻读西洋史和文学。1920年夏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被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参见赵慧芝编《陈衡哲年表》,作为附录收入《任鸿隽陈衡哲家书》,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编,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胡适与陈衡哲是在美国认识的,而笔者也未查到胡适与唐钺在1914年即唐钺出国以前交往的记录,故笔者把唐钺与陈衡哲归为一类,他们都是胡适在海外认识的中国同乡。
1.胡适与唐钺
胡适到美国后,1910年9月入康奈尔大学,1914年6月17日毕业。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6月启程回国。唐钺是1914年9月入康奈尔大学,1917年6月毕业。所以,并不像任鸿隽与杨杏佛那样——他们和胡适还有一年多的共同在康奈尔大学学习的经历,唐钺入康奈尔大学时,胡适刚刚毕业。不过,他和胡适算是校友,且胡适从1914年6月17日毕业到1915年9月进哥伦比亚大学,他的主要活动地点仍在绮色佳,他们应该有经常见面的机会。这样,1915年夏胡适和梅光迪、任鸿隽等人讨论中国文学,唐钺在列也是自然的事了。
2.胡适与陈衡哲
陈衡哲在美国是先和任鸿隽认识,然后才认识胡适的。据《任鸿隽年谱》载,“陈在一年前(即1915年,笔者加)曾将所著‘来因女士转’投寄《留美学生季报》,当时任鸿隽是该刊的总编辑,认为该作文词斐然,在国内外女学生中尤为难得”①赵慧芝:《任鸿隽年谱》,载《中国科技史料》第9卷,1988年第2期,第58页。,于是“心仪既久”②任鸿隽:《五十自述》,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任鸿隽著,樊洪业、张久春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5页。。1916年夏,任鸿隽与陈衡哲在美国绮色佳相遇,“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③任鸿隽:《五十自述》,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任鸿隽著,樊洪业、张久春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5页。。1917年春,任鸿隽已就读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再做校友。此时,因为任鸿隽的关系,胡适与陈衡哲之间已有书信往来。任鸿隽便约胡适一同前去瓦沙女子大学拜访陈衡哲。胡适日记1917年4月11日追记,“四月七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访陈衡哲女士……始得见之”④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此后,三人友情甚笃。1920年春,任鸿隽与陈衡哲在美国订立婚约。同年秋,二人在北大完婚。胡适于1920年曾作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鸿隽与陈衡哲,收在《尝试集》中。
二、梅光迪与任鸿隽的不同意见
胡适在《四十自述》附录《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等文中,提及1915年夏至1916年间他与朋友们关于文学革命的早期争论时,提到名字最多的是梅光迪与任鸿隽。二人都对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观持反对态度,尤以梅光迪为甚,“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⑤胡适:《四十自述》,载《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一)1915年夏——1916年4月
1915年9月20日,胡适在乘火车去哥伦比亚大学的途中,作诗《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诗中前两句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这是1915年夏胡适与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在绮色佳谈论中国文学问题,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后,首次提出具体的方案,即“作诗如作文”。
1916年1月25日,梅光迪致信胡适:
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 (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 (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 (Poetic diction)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于诗,即谓之改良,谓之革命,则不可也。究竟诗不免于“琢镂粉饰”。……一言以避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以其太易易也。吾国近时诗界所以须革命者,在诗家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知效其形式,故其结果只见有“琢镂粉饰”,不见有真诗,且此古人之形式为后人抄袭,陈陈相因,至今已腐烂不堪,其病不在古人之“琢镂粉饰”也。
至于该如何进行“诗界革命”,梅光迪指出:
究竟诗界革命如何下手,当先研究英法诗界革命家,比较Wordsworth or Hugo[华兹华斯或雨果]之诗与十八世纪之诗,而后可得诗界革命之真相,为吾人借镜也。①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载《梅光迪文录》,罗岗、陈春艳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0页。原信未标明具体时间,据《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2月3日日记“‘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可知此信作于1916年1月25日。
据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里称,此后任鸿隽也给他写信,说赞成梅光迪的主张。1916年2月2日,胡适复信任鸿隽,认为“不可不辨也”:
觐庄之意,以为适之所谓“作诗如作文”者,仅移“文之文字”以为“诗之文字”而已耳。此大误也。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须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日之诗 (南社之诗即其一例)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 (form)胜质 (matter)。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正复相同。皆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 (大家之诗无论古诗、律诗皆有文法可言);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②胡适:《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细读上述两封信,我们可知,胡适所说的今日诗歌“以文胜质”之弊与梅光迪说的“只知效其形式……不见有真诗”同义;他们的分歧在于梅光迪认为诗文两界,应互不干涉,而胡适则认为诗与文无明显界限,“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正复相同”,且提出“三事”来以质救文。第三点不避“文之文字”,最能解释他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
2月10日,任鸿隽复信:
要之,无论诗文,皆当有质。有文无质,则成吾国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然使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其行远,得乎?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③胡适:《四十自述》,载《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08、109页。
任鸿隽显然是站在梅光迪这边,他所说的“文人无学”与梅光迪信中说的“无古人学术怀抱”何其相似。他也提出了补救我国文学不振的方法,不过太显空泛,即弃文字形式上的讨论,从绩学入手。绩学,意为治理学问。
胡适自然无法认同,认为“他们都不明白‘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④胡适:《四十自述》,载《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08、109页。。也许正是受了任鸿隽这封信的启发,胡适文学革命的目标才明确,就是要“用白话替代古文”⑤胡适:《四十自述》,载《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08、109页。。胡适把他的想法写信告诉梅光迪 (据《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记述,时间是在1916年3月间,原信已失),梅光迪复信:
1916年3月14日
鄙意“诗之文字”问题,久经古人论定,铁案如山,至今实无讨论之余地……至于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欲得新文学或须俟诸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然以足下之奇才兼哲人、文人之长,苟努力为之,或能合康德、Wordsworth于一人,则迪当从旁乐观其成耳。⑥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载《梅光迪文录》,罗岗、陈春艳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原信时间仅标明“三月十四日”,据信中有“足下近遭两丧,甚望以哲人之胸境处人间伤心事”,此即指胡适1916年2月29日日记中载“大姐大哥于十二月二日三日先后死去”,可知此信作于1916年,准确时间是1916年3月14日。
1916年3月19日
迪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自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将来能稍输入西洋文学知识,而以新眼光评判固有文学,示后来者以津梁,于愿足矣。……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至于“诗之文字”问题,迪已不欲多辩。盖此种问题人持一说,在西洋虽已有定议,在吾辈则其说方在萌芽,欲宗于一是,必待文学革命成功之后……①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载《梅光迪文录》,罗岗、陈春艳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3页。
上述两通信透露出此时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一些观点,总结如下:
1.梅光迪是赞成文学革命的,他甚至“以创造新文学自期”,但他又认为这实现起来很难,得等“百年或二百年以后”,现在“已不作痴想”。
2.胡适致信梅光迪,谈到宋元白话文学,梅深受启发,亦认为当从“民间文学”入手进行文学革命。他预料到这样的话会和旧派文人之间有一番大战争。这里,他把胡适引为“我辈”。
3.关于“诗之文字”问题,梅光迪认为无须再讨论,要见分晓,只能等文学革命成功以后。在这一点上,他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且不会动摇。
梅光迪把胡适称为“我辈”,让胡适兴奋不已。这之后的胡适日记,有两处值得记录。一为4月5日夜所记,题为“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一为4月17日,题为“吾国文学三大病”。
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这篇日记中,胡适从自己所认定的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中寻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即把自古即有至元代时登峰造极却中断了的文学革命潮流继续下去,使我国文学成为“俚语的文学”,而我国语言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这方案让胡适信心更增。②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43、250、261—262、262页。
在“吾国文学三大病”这篇日记中,胡适指出现今中国文学的三大病:一、无病而呻;二、摹仿古人;三、言之无物。前文所提1916年2月2日胡适致任鸿隽的信中指出从三事入手来以质救文之弊,即一、言之有物;二、讲求文法;三、不避“文之文字”。两相对照,胡适后来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的“八事”已见“五事”,仅“三事”即“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还未提出。
(二)1916年6月——1916年8月
1916年6月,胡适往克利佛兰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去时经过绮色佳,与任鸿隽、唐钺、杨杏佛一起畅谈文学革命。胡适慷慨宣言,明确提出“白话可产生第一流文学”③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43、250、261—262、262页。。
这次宣言起到了效果,任鸿隽决定以白话作他们科学社的年会演说稿。由此也可见出,任鸿隽对于文学革命的反对态度并不像梅光迪那样坚决。胡适开完会回程途中,又过绮色佳,遇见梅光迪,再谈文学革命,但遭到了梅光迪的“大攻”。胡适“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梅光迪则“以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又以为偷得Tolstoi(托尔斯泰)之绪馀;以为此等十九世纪之旧说,久为今人所弃置”④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43、250、261—262、262页。。
1916年夏,任鸿隽已与陈衡哲相识。7月8日,他们和梅光迪、杨杏佛、唐钺一起在绮色佳凯约嘉湖上游玩。不料,船在近岸时翻了,还好最后有惊无险。此时天又下起大雨。事后,任鸿隽写了一首长诗《泛湖即事》寄给胡适。一番讨论之后,胡适开始用他“白话文学”的观点批判此诗。“‘泛湖’诗中写翻船一段,所用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浪之套语。足下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词套语之易,故全段一无精彩。足下自谓‘用力太过’,实则全未用气力。趋易避难,非不用气力而何?……再者,诗中所用‘言’字、‘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二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⑤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43、250、261—262、262页。
任鸿隽看此信后,尚可以接受,甚至要再作修改“奉呈审正”⑥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43、250、261—262、262页。。梅光迪阅后却大为不悦。7月17日,就在任鸿隽再次致信胡适以将修改后的诗作“奉呈审正”的同一天,梅光迪亦致信胡适,驳斥胡适:“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之价值……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一字之意义变迁,必须经数十或数百年而后成,又须经文学大家承认之。而恒人始沿用之焉。……足下所谓‘廿世纪之活字’者……并非廿世纪人所创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且字者代表思想之物耳,而廿世纪人之思想大抵皆受诸古人者……总之,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以锻炼之,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者也。(俗语白话亦有可用者,惟须必经美术家之锻炼耳。)……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①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载《梅光迪文录》,罗岗、陈春艳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65页。
虽然赞成文学革命,但梅光迪仍认为此非易事。7月22日,胡适作《答梅觐庄——白话诗》,其实是对梅光迪的观点予以反驳。诗中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从文字方面、文学方面说起。由于胡适在反驳的同时,又很明显地用了“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老梅牢骚发了”、“蠢才”、“老梅听了跳起”这样的句子或词,梅光迪看了自然大怒。
7月24日,梅光迪、任鸿隽均致信胡适,论及此诗:
梅光迪信: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Imagism、Free Verse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美术界如Symbolism Cubism Impressionism ets,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众徒,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今之美国之“通行”小说、杂志、戏曲,乃其最著者。而足下乃欲推波助澜,将以此种文学输入祖国,诚愚陋如弟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 (信末附,笔者加)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此早与足下言之,故不赘。②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载《梅光迪文录》,罗岗、陈春艳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68页。原信未标明具体时间,此处据《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7月13日补记“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可知具体时间为1916年7月24日。
任鸿隽信:
足下此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即如《三百篇》中各篇,何尝尽是当时人白话;下至汉魏唐宋人之诗,其非当时人白话抑又不问可知……乃至宋元人词曲,又何尝尽是白话!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 (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腔高调何一非诗……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今且假定足下文学革命成功,将另吾国作诗者皆京腔高调,而陶、谢、李、杜之诗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足下若见听,则请从他方面将文学革命,勿徒以白话诗为感矣。③杜春和、韩荣芳、耿金来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3页。
梅光迪在信中批评西洋诗界、美术界、当今美国文坛,显然已受到欧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比较梅光迪于任鸿隽的书信,他们此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观点一致④至于梅光迪与任鸿隽之间的不同,任鸿隽自己曾有一个说法:“迪生之反对白话盖为全般的,凡以白话为文者皆在其反对之列。吾则承认除白话有其用处,但不承认除白话外无文学,且于白话诗之能否成立,为尤龂龂耳。”(《五十自述》)。据笔者研究,这说法未必准确。如梅光迪,并非全般反对白话。在与胡适争论文学革命的高潮期,梅光迪与任鸿隽之间的同远大于异。异处仅在梅光迪反对白话入诗和文,要入也得极其地小心谨慎;任鸿隽则更强调的是诗,认为诗不可以用白话。另外,任鸿隽的态度要比梅光迪温和一些,不似梅氏那么咄咄逼人。本文未对此展开论述,特此说明。:
1.皆否定胡适所作《答梅觐庄——白话诗》,“如儿时听‘莲花落’”,“完全失败是也”。
2.皆认同文学革命,但不认同胡适的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革命观。梅光迪坚称诗文不可用白话,而任鸿隽则强调诗不可用白话。
3.均未提出自己心目中文学革命的具体方案。
之后,胡适于7月26日、8月4日两次致信答任鸿隽。胡适一方面为自己的白话长诗“戏台里喝彩”,一方面又针对任鸿隽的观点进行反驳,高唱白话文学的赞歌,并下决心“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且“不再和梅任诸君打笔墨官司了”①胡适:《四十自述》,载《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25页。。
但1916年8月8日,梅光迪再次致信胡适。在这封信中,梅光迪终于提出了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具体设想,所谓“文学革命之法有四”:
一曰摒去通用陈言腐语,如今之南社人作诗,开口燕子、流莺、曲槛、东风等已毫无意义,徒成一种文字上之俗套而已,故不可不摒去之。
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
三曰添入新名词,如科学、法政诸新名字,为旧文学中所无者。
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然须慎之又慎耳……②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载《梅光迪文录》,罗岗、陈春艳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这是现存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信中涉及文学革命的最后一封信,也是观点最为鲜明的一封。其实不仅仅是胡适被“逼上梁山”,梅光迪在这封信中关于文学革命的设想显然也是被胡适逼出来的。前言胡适已提出文学革命“八事”中的“五事”,而另“三事”之一“务去烂调套语”无疑是从梅光迪这里的“摒去通用陈言腐语”而来。后来胡适暴得大名,但他对早期和他讨论文学革命的这班朋友“只有感激,没有丝毫的怨怼”③张家康:《胡适“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文史精华》2005年第12期。,想来也是在情理之中。
三、其他在场者的意见
1915年夏至1916年间和胡适讨论文学革命“出力”最多的是梅光迪和任鸿隽。在胡适这段时间的日记、书信中,他们的名字也出现的较为频繁。然而,我们也不可以因此就把“功劳”全记在梅光迪和任鸿隽的身上,而忽视了当时在场的其他人的意见。其他人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观点,同样值得我们去研究。笔者在本部分内容中即对此做一梳理。
(一)杨杏佛与唐钺
杨杏佛与唐钺也亲身经历了这场关于文学革命的早期争论。1915年夏在绮色佳的讨论,1916年夏在绮色佳的讨论,以及1916年7月8日的翻船事件,胡适在文章中提起时,都提到他们二人的名字。但他们二人对于文学革命的态度,胡适却没有明说。
1.杨杏佛:支持
查看《胡适留学日记》,提及杨杏佛处与文学革命有关的仅见1916年7月6日追记的“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作者全文记录1916年6月底在绮色佳与任鸿隽、杨杏佛、唐钺所谈关于文学革命的观点,文末记:
余于二十四日自绮往克利弗兰城。后数日,得杏佛寄一白话诗,喜而录之:
寄胡明复 (白话)
自从老胡去,这城天气凉。新屋有风阁,清福过帝王。
境闲心不闲,手忙脚更忙。为我告“夫子”(赵元任也,原文注),《科学》要文章。④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杨杏佛作白话诗向赵元任索稿,这即是实践胡适“以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小说”①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244页。的观点,胡适评价此诗“胜南社所刻之名士诗多多矣”②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244页。。但杨杏佛对胡适的文学革命观点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仍不得而知。我们不能因为他作了一首白话诗,就判定他支持胡适的观点。
胡适与杨杏佛之间并无像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那般一样的书信往来争论,但笔者在《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中查到一封杨杏佛致胡适的信,这封信大概可以说明杨杏佛对胡适文学革命观的态度:
1916年10月
今日读致叔永函与经农诗甚佳,达意畅而传情深;虽然纯粹白话诗,然固白话诗中杰作也。《怀祖国诗》似为字累,此体至难作,必字简意深,然后能胜。《尝试篇》说理亦佳。兄白话诗进境颇速,不负此试。③杜春和、韩荣芳、耿金来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页。所标时间均据原书编者考证所加。
可见,杨杏佛对胡适的观点是持支持态度的,他不愧是胡适的得意门生。
2.唐钺:不反对
《胡适留学日记》中提及唐钺处极少。在这场文学革命的争论中,提及唐钺也只是提到其名字,未提他的态度。笔者在《胡适全集》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亦未发现这段时间内胡适与唐钺之间的通信。笔者在《唐钺文存》中查到一篇文章《文言文的优胜》,大概可以说明唐钺的态度。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名为“文言文的优胜”,实则是在反驳别人所认为的“文言文占优胜的地方”,全文最后几句话最能表明作者的观点:
我们不期望自己或人家因为个人有所忿愤,恐惧,好乐,忧患的缘故去反对文言文。同理,我们尽管有时“技痒”用“古文”或骈文作一两篇文或著一两部书,尽管有时“故态复萌”翻出一两篇名家的“古文”或骈文摇首咿唔,尽管一己所有世间可欲的东西,都从“古文”骈文得来,尽管为直接的或间接的题外的原因不喜欢白话文;但若是我们因为这些事就要我们和别人的小孩子一律学作“古文”骈文,或叫大家不要用白话文著作,那么,我们的心,恐怕有点“不得其正”罢!④唐钺:《文言文的优胜》,载《唐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46页。
唐钺的白话文并不好读。难能可贵的是,他说他不喜欢白话文,但却不因此就要求孩子一定要学文言,或反对别人用白话。我们可以猜测,在当年的那场争论中,唐钺对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大概也不会强烈反对。
(二)朱经农:先反对后支持
朱经农1916年赴美,正好赶上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朱经农对胡适文学革命观的态度是先反对,后支持。
有两封信可以说明初时朱经农对胡适观点的反对:
1.1916 年7—8月
白话诗所以 (不)如古诗者,盖缺一“美”字,故感人不深,达意不畅。此即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村歌山谣决不足以风行全国,传之后世,弟敢断言。且中国方言至不统一,所谓白话有能通于此而不能行于彼者。……故弟谓白话诗无甚好处,兄其毋以进化之说相难也。⑤杜春和、韩荣芳、耿金来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399页。所标时间均据原书编者考证所加。
2.1916 年8月2日
……弟意白话诗无甚可取。吾兄所作“孔丘诗”乃极古雅之作,非白话也。古诗本不事雕斫。六朝以后,始重修饰字句。……兄之诗谓之返古则可,谓之白话则不可。盖白话诗即打油诗。吾友阳君有“不为功名不要钱”之句,弟至今笑之。①胡适:《胡适留学日记》 (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据胡适1916年8月4日日记“答朱经农来书”,可知此信所作时间为1916年8月2日。
在这两封信里,朱经农还认为白话诗不如古诗,无甚可取,但没过多久,朱经农在致胡适信中的态度即起了变化:
1916年8月
“去国”已收到,拜诵一过,狂喜欲舞,除两律弟不赞成外,余均为上品,不但叙情写景栩栩欲活,且词意恳挚,格调苍劲,直逼古人 (此语兄不愿闻)甚矣,“死文字”之不死也。和杏佛诗仓卒为之,无律无韵,直类白话,盖欲仿尊格,画虎不成也。②杜春和、韩荣芳、耿金来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所标时间均据原书编者考证所加。
是什么原因使得朱经农在短时间内态度变化如此之大,甚至“仓卒”“欲仿尊格”,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查《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8、9月间,胡适与朱经农间书信往来频繁。8月4日有“答朱经农来书”、8月21日有“文学革命八条件”(作者寄信朱经农,谈新文学之“八事”,此即后来《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不过成文时顺序稍有变动)、8月27日有“打油诗戏柬经农、杏佛”、8月31日有“赠朱经农”、9月12日有“《虞美人》戏朱经农”、9月15日有“答经农”等。尤在9月15日日记“答经农”中,胡适记到:
余初作白话诗时,故人中如经农、叔永、觐庄皆极力反对。两月以来,余颇不事笔战,但作白话诗而已。……今虽无大效可言,然《黄蝴蝶》、《尝试》、《他》、《赠经农》四首,皆能使经农、叔永、杏佛称许,则反对之力渐消矣。经农前日来书,不但不反对白话,且竟作白话诗,欲再挂“白话”招牌。吾之欢喜,何待言也!③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0、292、294页。
朱经农态度的变化,让胡适无比欢喜,这是自然的事了。
(三)陈衡哲:胡适“最早的同志”
在1916年7月8日的“翻船事件”中,陈衡哲亦在场。此时的陈衡哲刚和任鸿隽认识,还不认识胡适。陈衡哲虽然没有参与到胡适与朋友们的争论中来,但可说也是亲历和见证者之一。
如前文所述,胡适和陈衡哲1917年4月7日才正式认识。不过,在此之前,二人之间已有书信往来。陈衡哲在《胡适留学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是在1916年10月23日,日记名为“打油诗一束”。其中二为“答陈衡哲女士”:
女士答吾征文书曰:“‘我诗君文两无敌’(此诗赠叔永诗中语),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吾答书有“细读来书颇有酸味”之语。女士答云,“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遭。④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0、292、294页。
因为陈衡哲在回复胡适信中称胡适为“先生”,胡适随后寄信陈衡哲: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⑤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0、292、294页。
陈衡哲回复:
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①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这回答使得胡适只能“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敢再驳回”②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我们注意到,陈衡哲与胡适最初交往时就互相写打油诗。可见,陈衡哲并不反感胡适的白话文学观。
不得不提的是,陈衡哲后来还以实际行动支持胡适。1917年6月,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白话小说《一日》,比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白话小说开山之作《狂人日记》还早。此文收入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中,胡适应邀为其作序,并在序中表达了对陈衡哲的感激之情:
民国五年七八月间,我同梅、任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方面。不久,我为了一件公事就同她通第一次的信;以后我们便常常通信了。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③胡适:《〈小雨点〉序》,载《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页。
陈衡哲对胡适文学革命观点的支持在这段话里得到印证。
四、结 语
在胡适文学革命观酝酿的早期,他和周围的朋友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些朋友当中,有反对他的,如梅光迪、任鸿隽;有不强烈反对的,如唐钺;有支持他的,如杨杏佛、陈衡哲;有先反对后支持的,如朱经农,但不管是曾经持了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他们都一起促成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产生。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说,“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④胡适:《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9页。。可以说,这些有系统的主张,是胡适对他和朋友们关于文学革命早期争论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