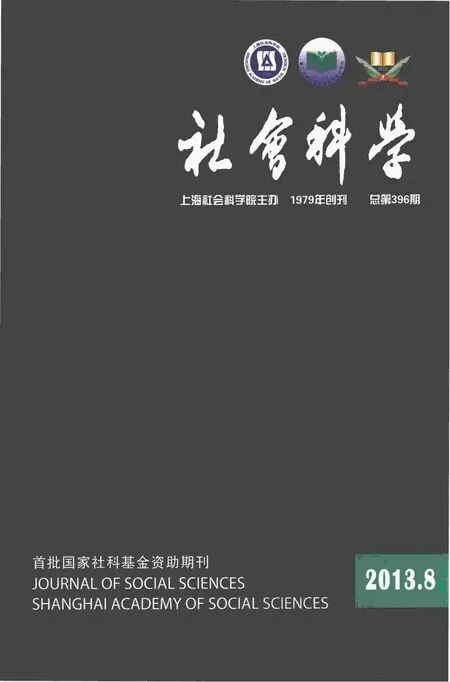论晚清兴学群体中的 “士”——以盛氏教育幕僚为中心
欧七斤
追本溯源,我国近代教育实发端于晚清——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发生正面碰撞之千古大变局中。面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社会现实,传统科举教育在与西方新式科学教育的竞争中明显处于下风,于是兴办新式教育的风潮自19世纪下半叶萌发,缓慢成长并最终击倒科举教育,成为教育形态的主体。在推动近代教育萌发与成长的过程中,由官、商、士凝聚而成的群体性兴学力量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以晚清大实业家著称的盛宣怀及其教育幕僚们就是鲜明的案例。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亦官亦商亦教”的重要人物,然而,学术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洋务实业、政治外交为主的“官、商”两个领域,对其近代教育的开创之功与教育思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空白点较多①关于盛宣怀研究主要成果有:美国学者费维恺 (Feuerwerker Albert)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 (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1958年);台湾学者谢世佳著《盛宣怀与他所创办的企业——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创造力之研究》(1971年);夏东元先生著《盛宣怀传》(1988年)、《盛宣怀年谱长编》(2004年);陈吉龙、易惠莉主编《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2002年)等重要著述,其中以夏东元、费维恺的研究最具学术影响力。然而,上述成果侧重直接影响近代化进程的洋务实业、政治外交领域,对于盛宣怀教育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为数不多的关涉其文化教育方面的相关专题论文,多将盛宣怀经办教育文化事业作为其实业活动的补充来观察,缺乏系统深入的整体性研究。。而且,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零星研究亦仅关注于盛宣怀个人,探析盛宣怀身后的教育幕僚这一重要兴学群体的研究尚付阙如,笔者即拟从探讨盛氏之教育幕僚入手,进一步深化盛宣怀研究,并管窥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主要兴学力量及运作机制。
一、盛宣怀兴学及其教育幕僚
盛宣怀 (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在近代史上以善于兴办洋务实业著称。盛本起家于幕僚,1870年先被荐入李鸿章的军幕,后由军务转为洋务,协助李鸿章创办经营轮船、电报、矿务、纺织等洋务实业,成为“李鸿章的经济事业的代理人”、 “中华帝国的工业家领袖”①[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吴乾兑校:《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 (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90页。。经济实力加上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等权臣的先后保举,盛逐渐得到清政府的垂青,先后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道、天津海关道、督办铁路大臣、办理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仕途上一路升迁,由一名出身佐贰之人,不经科第竟跃为清末政坛一位财权兼备、亦官亦商的实力派重臣。
与前述成绩相比,人们注意不多的是,盛宣怀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实力,曾经长期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从1880年创办天津电报学堂开始,先后主持创建或参与兴办了电报、轮船、铁路、矿务等学堂十余所,成为近代技术实业教育卓有成效的重要兴办者;甲午战争后又突破行业办学的局限,主持创建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三等公学堂等各级普通学堂十余所,并以遣留学生、设译书院、建图书馆相辅助,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的首创者②盛宣怀所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的标志,历来为多数史学家所认可。如周予同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印行,第190页)称:“普通分科大学的成立,当以光绪二十一年 (公元1895年)盛宣怀所奏设的天津西学学堂中的头等学堂为最早。……继天津西学头等学堂而设立的,是光绪二十三年 (公元1897年)盛宣怀所奏设的上海南洋公学上院。”陈旭麓亦曾指出:“南北洋学堂同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首倡。”(《陈旭麓文集》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建立我国近代普通教育体系的重要先驱③1895年设立的北洋大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级;次年开办的南洋公学分设外院、中院、上院三级,初步构成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清史稿》称南洋公学“学制分为三等,已寓普通学校及预备教育之意旨。”“中国教育有系统之组织,此其见端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25页)。著名教育家孟宪承亦称:“南洋公学是最早具有初等、中等、高等三阶级教育的雏形的。”(《新中华教育史》,中华书局1932年6月初版,第317页。),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新陈代谢。
台湾历史学者李守孔认为,盛宣怀一生事业成就“半由于时会,半由于人力”④李守孔:《杂谈盛宣怀的事功》,《传记文学》1969年第14卷,第3期。。确实,盛宣怀每办一事都注重选人用人,将用人作为办事成败的关键。1884年他与日本学者冈千仞笔谈时说:“办国事不在用人上发端,则事必败;用人不在实效上考究,则人不出。”⑤《盛宣怀与冈千仞笔谈》(光绪十年秋冬,1884年秋冬),载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次年又在总结办理电报经验时说:“大约筹款尚易,用人最难,得一人则一事成矣。”⑥《盛宣怀拟节略》(光绪十一年,1885年),载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版,第225页。随着官商事务的庞杂繁难,盛宣怀自辟幕佐,先后选用郑观应、陈遒、沈能虎、汪洵、经元善、谢家福、何嗣焜、李维格、王存善、杨学沂、吕景端等颇有才干者入幕,协办实业,佐理事务,成为盛宣怀经商为官的得力助手⑦盛宣怀自辟幕府具体年份与早期幕友情形不详,大约始于1880年代初创办电报总公司时期。1886年10月24日盛宣怀签发的《电报学堂劝谕文》内称:“局宪即是该管上司,于本局司事即是该管上司之幕友。”(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以下简称“盛档”:068395)又,1888年11月6日傅兰雅为盛宣怀代觅矿务学堂教员致旧金山矿务学堂总监院的信中说:“今有烟台道台盛大人之幕友到本馆,托余寄信查问美国有无矿学教习。”(盛档:000453)。
办洋务实业如此,办理新式教育也是如此,他曾致函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说:“窃偿谓中国少年子弟,聪颖英法,非不可教,但使教习得人,课程整肃,不难造就中西贯通之材。”⑧盛宣怀:《致张百熙、荣庆函》(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1903年10月10日),盛档:044186。办学过程中,他多方延揽才识宏通、留心时务者主持校务,礼聘精通中西、乐于育才的中外学者执掌教务。不少有识之士也因办洋务兴新学的抱负能够在盛宣怀那里得以施展,而投身于其所办教育活动。于是,盛宣怀逐渐聚拢了一批贤能精干之才,成为其办理教育的得力助手与推手,共同助推了其所办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实际受聘参与盛宣怀教育活动的人员,包括所办学堂筹办者、校务经营者、教务负责人,还有文化机构的主持人,笔者将之统称为盛宣怀的教育“幕僚”。
“幕僚”从狭义上指中国幕府制度下的幕府成员。幕府制度是对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重要补充,尤盛于明清时期。“幕僚”一般是由幕主礼聘的、在官署内协助幕主办理文案、刑名、钱谷等事务的非现职官员。但是,进入晚清这一新旧转型的过渡时期,幕府制度发生了从传统幕府向近代职官制度的过渡,无论是幕府成员的来源、幕主和幕僚关系、幕僚任职范围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黎仁凯教授对晚清幕府的论述:“在晚清,随着政治、军事的变局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幕主在衙署内外设立了一系列的政务、军务、经济或文化机构,如创建军队、办实业、兴学堂等,延聘、奏调和札委一批幕僚在其中任职、办事,这些人自然也就成为幕府的一员。”①黎仁凯:《晚清幕府制度及其嬗变》,《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据此,笔者将受聘参办盛宣怀教育活动的重要人员概称为教育“幕僚”。下面先将其主要教育幕僚的简况列表如下:

表1 盛宣怀之主要教育幕僚一览表

续表

续表
二、盛氏教育幕僚之身份考析
上表列举了盛宣怀教育幕僚共计32人。考察和分析这一教育幕僚群体的聘任薪酬制度、籍贯来源、身份背景及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盛宣怀教育活动实施与管理的具体细节,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新式教育兴办之初新旧杂陈的时代特征。
(一)盛氏教育幕僚之聘任和薪酬
盛宣怀对教育幕僚的聘任方式多种多样,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特点。一方面,延续了传统幕僚的“礼聘”方式,即通过私人关系邀请并约定。这些幕僚的身份一般比较高,与幕主的关系密切且相对平等。例如,盛宣怀对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的聘任。1896年4月,盛宣怀筹设南洋公学之际,亲临故里武进何嗣焜家中,以“时局艰危不当徒为洁身之士”①刘坤一、盛宣怀:《请将何嗣焜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光绪二十七年十月,1901年11月)。盛宣怀:《愚斋存稿》第6卷,第3页。等语,敦请退居乡野的名幕何嗣焜协助其办理洋务和教育。何感于时艰,欣然应允,被盛宣怀聘为南洋公学首任总理、全国铁路总公司参赞。又如,张元济、蔡元培任职南洋公学,分别通过李鸿章、刘树屏的举荐,获得盛宣怀礼聘而分任公学译书院主事、特班总教习。
另一方面,还有“奏调”或“札委”等形式,这些方式由于通过奏请朝廷调配或者通过下属机构内部委任,而带有了官方机构的职官色彩,因此不同于传统幕府。例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总办、提调等重要人选,先经盛宣怀择定再经禀明上级部门、奏请清廷派定的,如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总办伍廷芳、二等学堂总办蔡绍基、总教习丁家立,南洋公学总办沈曾植、汪凤藻等即是如此。盛宣怀还从其主管的电报、矿务、铁厂等实业部门中选拨人才,札委其为实业学堂的总办、提调等,如谢家福、俞书祥等,幕主和幕僚之间就有了明确的上下级的统属关系。
幕僚薪资由盛宣怀所办学堂、文化机构中公费支出。与传统幕僚主要由幕主个人的养廉银划拨也不同。这些学堂和文化机构的费用多由盛宣怀所掌握的洋务企业来支付。例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办学经费即由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按年捐付。由于盛宣怀经济实力雄厚,重视文教事业,给教育幕僚们开出不菲的薪酬。北洋大学堂总办、总教习月薪均银200两;南洋公学总理、提调月薪银200两,监院高达银350两,译书院主事银140两,特班总教习月薪银100两②《天津头等学堂经费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盛档:026511;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一卷1896—190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9、163、232页。。清末辜鸿铭曾比较盛宣怀与张之洞身边属吏的经济状况:“张宫保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 (指盛宣怀——笔者)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资,富雄一方。”③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分析盛宣怀教育幕僚的聘任和薪酬制度,可以发现其带有了近代职官制的特色。聘任制度中除了私人约定的“礼聘”外,“奏调”、“札委”等方式的引入增加了官方色彩,薪酬支付则改变了“自掏腰包”的方式,通过洋务企业的输血由学堂等文化机构直接支付。这些类似职官制度的新型管理方式,无疑更加高效,适应了规模日益扩大的新式教育机构对新型教育人才的大量需求。
(二)盛氏教育幕僚之籍贯分布
盛宣怀的教育幕僚中有中国籍幕僚27人,外国籍幕僚5人。
中国籍幕僚全部来自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其中江苏籍16人、浙江籍7人、广东籍4人。出现这样的地缘特征,与三省得新风气之先、人才盛出等地理文化因素有关,也与盛宣怀本人籍隶江苏、属江浙洋务集团首领有密切关系。盛宣怀在办学过程中特别倾向于启用武进和苏州同乡亲属。盛宣怀本人是江苏武进人,在江苏籍16人中,武进一县多达5人,而被盛自称“侨居数十年”的苏州有3人。当时有英文报道也曾说:“在他 (盛宣怀——引者注)的掌权时期内——绝不是官僚集团中的唯一例子——把所有赚钱的职位都授予他的亲戚、门徒和常州同乡的习惯。”④《北华捷报》1908年3月13日,第620—621页。转引自 [美]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 (1844—1916)与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123页。这种热衷于任用同乡门徒等私人关系的倾向,与传统幕府制度的典型特征也是一致的。黎仁凯曾指出:“幕府中人员不纳入国家正式行政机构之中,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由幕主的私人关系网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具有极强的私家性质和人情味。”①黎仁凯:《晚清幕府制度及其嬗变》,《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不过,传统幕府制度所具有的私人关系网络的特征,容易导致人事的派系化和人事斗争的多发化。例如,1901年南洋公学总理、武进人何嗣焜病逝后,浙江籍沈曾植受盛之奏调代行总理职位,但到校后他才发现:“梅生一席,近似盛氏私人,常州人希觑者甚多”,决意“止愿与孝章为寻常宾主,不愿为亲密朋友。”②沈曾植:《海日楼家书·第二十七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七日,1901年5月24日),载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6页。“梅生”系何嗣焜字,“孝章”即盛宣怀。沈任职半年后便挂职离去。
在5名外国籍幕僚中,有丹麦籍2人,英国籍1人,美国籍2人。特别是盛宣怀所办的最主要的两所学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总教习 (监院)丁家立、福开森均聘自美国,对两所学堂的起步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些人员的选择反映了盛宣怀办学时以欧美特别是美国学校为仿照对象,这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兴起的学习日本的风潮不同。1903年,他曾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函中,说到对学习日本和学习欧美孰优孰劣的认识:“论者谓取材日本或较泰西为易,不知求东文普通亦须二三年,且通商不止一国,何如竟讲西文西学更为直接。”③盛宣怀:《致张百熙函》(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廿四日,1903年19月14日),盛档:044187。这番议论表达了盛宣怀认为学习欧美更为直接的判断和倾向。这些外国籍人士在统计表总人数中占到16%,他们的出现充分地反映了在国门洞开的教育新格局下晚清幕府制度出现的吸纳外籍人士的时代特色。
(三)盛氏教育幕僚之知识背景
考察这些教育幕僚的求学与职业经历,又可以把他们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比较深入认识西学的新式知识分子。此类人物西学根基较厚实,后来多出掌盛宣怀所办学堂的教学事务。具体而言,有主要在西方学校中接受系统西方教育的,如伍廷芳 (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后留学英国,获伦敦学院法学博士)、蔡绍基 (留美幼童,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也包括外国来华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濮尔生、博怡生,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传教士傅兰雅、丁家立、福开森;有出身洋务学堂者,如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和京师同文馆的朱格仁、汪凤藻,或在洋务学堂学习后留学外洋者,如伍光建 (北洋水师学堂,留学英国)、李维格 (上海格致书院,留学英国);还有游历过欧美或参加过编译西学的人员,他们虽未直接接受西方教育,但多年身处西方或编译西学对西方文明和教育制度也有较深领悟,游历欧美者有张美翊、钱恂,参加上海制造局翻译馆编译工作的有钟天纬、赵元益。
第二类是长期从事洋务企业经营管理的实业人士。如轮船招商局参与创办者朱其诏,长期经办上海电报局的谢家福、俞书祥,招商局、电报局、汉阳铁厂主持者郑观应。他们多未有科举功名,长期追随盛宣怀创办经营洋务事业,同外国实际接触较多,对近代西方科技与文明感同身受,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以富国强民。他们多从办理实业的亲身体验出发,主动倡议并竭力办理技术实业型学堂。盛宣怀前期所办部门性技术学堂多归功于他们的倡导主持,他们是盛宣怀前期教育活动的中坚力量。郑观应、谢家福由实业出发,萌发形成维新改良思想,对盛宣怀办理新式教育多有影响。
第三类是出身旧学又倾向新学的新型知识分子。有从小饱读经史、获得过较高科举功名者,如有科举进士功名者9人:王修植、沈曾植、刘树屏、张元济、蔡元培、张鹤龄、费念慈、缪荃孙、劳乃宣;有淡于功名、留心经世之学的何嗣焜、张焕纶、罗振玉。他们参与盛宣怀教育活动时虽未出国,不识外文,然胸怀传统士大夫所具有的经世抱负,感于内忧外患,通过西学译作、报章等途径,主动吸纳西方新知,成为融会中西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少人又在中央、地方任过职,熟悉政务民情,是盛宣怀后期教育活动所倚重的中坚力量。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时,奉“中体西用”为办学方针,以培养精通中西的法政人才为目标,于是多延揽此类人才作为主体管理者以适应办学所需。
这三类教育幕僚,尽管知识背景有差异,身份来源多元,但其共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均或多或少吸收了西学,有志于通过引进西学实现教育体系的革新和新式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有别于传统幕僚的新型士人群体。
综观盛宣怀的教育幕僚,他们具有新旧杂陈的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聘任和薪酬制度上看,盛宣怀根据新式教育机构的需要,与教育幕僚间建立了超越传统私人约定的更加官方化和社会化的关系。从出生籍贯考察,一方面这一群体的籍贯结构仍然体现出传统幕府制度下的地缘特征,另一方面,有外籍人士的加入,为这一群体补充了不同于传统幕僚的新鲜血液;从身份上考察,尽管他们知识背景有差异,但他们均或多或少吸收了西学,是一个热心引进西学的新型士人群体。他们是中国近代教育大变革中具有革新性、创造性的一股力量,共同促成了盛宣怀教育计划的实施落实和办学活动的开展,推动着盛宣怀教育理念与实践的不断前行,是其文化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推手与助手。
三、教育幕僚:办学实践与理论倡导的结合
从盛氏教育幕僚一览表统计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教育幕僚多是盛宣怀所办新式学堂的筹建人和负责人,所担任的职位的一般名目有“总办”“总教习”“总理”“总校”“总纂”“监院”“监督”“主事”“提调”等。所肩负的职责和发挥的功用包括办学方向和宗旨的规划、办学章程的拟定、财务的管理、师资的聘任、教务的规划、招生和校园生活日常管理等。总而言之,他们是盛宣怀办学活动的实际操办者,学堂日常活动的主持人。
在筹办学堂或实施管理过程中,教育幕僚们能够依照办学经验和实际情况,主动地向盛宣怀提出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方案,实际上引导着学堂办学方向的走势。比如,南洋公学筹备之一张焕纶曾创立梅溪书院,对办学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在参与筹建公学时特别强调培养新式师资的重要性,他对盛宣怀说:“办学不易,师资尤难。师道不立,则谬说流传,其害甚于不学。……欲立兴学基础,必先造就师资。”①薛明剑:《南洋公学创办史实纪事》,载《薛明剑文集》(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页。盛对此十分赞同,所以在开办南洋公学时即首设师范学堂,这一师范学堂成为我国最早的师范教育机构。在修订筹定办学章程时,张进一步详细提出了11条意见,主张南洋公学除仿照北洋大学堂头等、二等学堂设立上院、中院外,应并设小学堂,“盖从小学堂升入中院者,将来造就易,为功维当以境诣为限,万不可以年岁为限”②张焕纶:《南洋公学教育事宜》(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盛档:044458-4。张在此函中以北洋大学堂“头等、二等名欠雅驯”建议改称“上院、中院”。盛亦从其议,遂有南北洋两学堂建制名称上的差异。。另对编纂教科书、中文教学、教员选聘、试读制度等有所建言,多为盛宣怀及其他筹备者所采纳并加以施行,遂促成了南洋公学四院建制的形成。
又如,1899年张元济受聘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时,该院以翻译兵书为主,社会影响不大。张即向何嗣焜、盛宣怀表示:“济思现有兵书均为学堂教授之本,译之无甚用处,……日本有《法规提要》,详载彼国行政之法,多有可以则效者。”③张人凤、柳和成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建议以翻译政法、经济类图书为主。他的建议被采纳,译书院遂改变译书方向,因译印出《原富》、《日本法规大全》等名著而声名鹊起。
1896年底,北洋头等学堂总办王修植到学校后发现,“通晓西学颇不乏人,惟于中国文字其斐然可观者殊觉寥寥”④王修植:《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1897年3月19日),盛档:044215。。认为如此不可能造就出中西兼全之材,于是函请盛增加中文授课时间,不及格者不予升班。与此同时,筹办南洋公学的何嗣焜北上考察该学堂,也发现该堂学生精通中文者为数极少,认为如此下去则学生难成大器。盛宣怀深以为然,一面批示王修植加紧中文教学,并亲选汉文教习2名北上;一面在南洋公学添设华文总教习,招考学生注重中学程度,以求中西并进。
教育幕僚们提出诸如此类对于学堂设置、办学目标等产生重大影响的具体措施,还有许多案例,在此不一一铺陈。
此外,这些教育幕僚中不乏对社会时局和教育制度有精深研究的教育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不拘于所承办的学堂校务本身,而是从发展近代教育的宏观角度给盛宣怀建言献策。其中以郑观应、钟天纬等具有早期改良主义的教育理论家建言最多,他们与盛宣怀关系密切,时常倡议盛创办新学,推动新式教育的普及。
郑观应是提出建立中国近代学制体系的最早创议者,他曾多次函促盛宣怀兴办新式教育。在给盛的一封信里,他提出了自己对于兴办新学的一些具体设想:
一、设文部,各省广开大、小学校及专门学堂,以开民智;
二、先选华文通顺已读西书数年者,资赴泰西学习专门,以储他日之用;
三、废八股取材,即在学校之中,俾人知趋向;
四、择有用之书次第翻译。①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年代不详),盛档:057758-1。
这些崭新的设想对于促成盛宣怀开设普通学堂、选派留学、设立译书院、倡设学政大臣等具有重要影响。郑在主持轮船招商、汉阳铁厂期间,又建言盛宣怀开设了轮船驾驶学堂、铁厂学堂。
奉盛为“业师”的钟天纬建言热心赈灾事务的盛宣怀不如移款兴学育才。他说:“养活数百万灾民无救于中国之灭亡,培植成数十辈英才总可以有俾大局也。” “如蒙吾师每年筹拨千金,专供新法教授之用,则其功德不在荒赈下矣。”②钟天纬:《致函盛宣怀》(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1896年5月14日),盛档:069926。说服盛宣怀资助其开办上海三等公学堂。
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也有劝其改赈灾为办教育的建议,意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义赈名意至美,特下走以为此可暂行,而不可以为经常。昔英国曾行赈贫,与今之义赈相类,阙后愈赈而贫者愈多,识者悟其非计,改而专重于教。夫以天下之大,水旱为灾,何岁能无,第敛钱以恤其饥寒,何如以此钱兴农学、教工艺为善乎。所为备赈愚意不同者此也。”③何嗣焜:《致盛宣怀函》(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载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版,第473页。此外,丁家立、福开森、伍廷芳、谢家福、刘树屏、缪荃孙等人在教育思想和理论方面也有相关建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盛宣怀与这些教育幕僚的互动关系。盛宣怀作为幕主无疑处于主导位置,他从自己的事业发展大局和办学观念出发,并不是全部或全盘接受教育幕僚们的提议。如钟天纬呈请盛宣怀资助其创办一所师范学堂,1902年汪凤藻建议扩建已名存实亡的师范学堂,1903年刚接任南洋公学总办的张鹤龄建议盛宣怀改用日文教学等,盛宣怀在仔细斟酌后都没有接纳这些建议。
但是,大致而言,盛宣怀与教育幕僚们在教育活动过程中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幕僚们以其对于新式教育的识见与实际经验,竭力倡导兴办新学,倾心主持校务,因地制宜地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办学措施,对办学过程上出现的弊端也能及时纠正。盛宣怀则能虚心纳言,集众人所见所长,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给以全局性指导和财力人力的支援。盛宣怀和教育幕僚们的通力合作和密切配合,使得一所所新式学堂相继建成,许多学堂办理得卓有成效,由于顺应了教育近代化的潮流,使得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④例如,盛宣怀所办的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
四、结 语
考察盛宣怀教育幕僚这一参与新式教育创办和管理的特定群体,从人员结构和运作机制上看,既有传统幕府的部分特征,又带有向近代职官制度过渡的特征,表现在:幕僚选用虽重用私人聘用,也多采用奏调、札委等方式;薪水不由幕主个人自掏腰包,而主要由幕主所掌管的教育机构来支付;来源更加广泛,除了原有儒生、非现职朝廷命官、同乡门徒,又新增新学堂学生、留学生以及洋人等;承办的事务由特定的衙门钱粮文案事务转为办理洋务中的新式教育。
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这些教育幕僚是盛宣怀办学活动的教育理论提供者,具体办学活动的落实者,而盛宣怀则是一个教育理论的吸收者,教育理论化为行动的指导者。盛宣怀与其教育幕僚们集体力量与智慧的结晶,理论与实践的较好结合,共同成就了盛宣怀的教育文化事业。而盛宣怀在其中的作用,正如时人陈三立所说:“能通天下之志,竭人士之力。”①陈三立:《盛宣怀墓志铭》,载《愚斋存稿》卷首。
最后将盛宣怀及其教育幕僚这一群体放置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就我国近代教育推动的大体时序和推动力量来说,发起洋务运动的开明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最早启动新式教育,自1860年代初起陆续创办了一些以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军事技术为主的西式学堂,继之而起的游走于官、绅、商之间,实际掌管经营近代工商企业的绅商阶层,盛宣怀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们在督抚大员的扶持下,适应近代洋务实业的发展,先是创设办理了一批技术实业学堂,进而在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留学教育、女子教育以及学制建设、西学翻译出版、图书馆等方面进行开创性的实践与示范,是提倡与推行新式教育的社会中坚阶层,在推动晚清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苏云峰评价绅商参与近代教育的作用与地位时所称:“绅商参与教育改革,于甲午战败后,亦达于高潮,以江苏、浙江与广东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最为显著。他们的贡献,往往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是不可忽视的。”②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 (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然而,绅商及督抚的办学活动与成绩离不开相互间奥援,离不开教育幕僚这一新型士人群体的理论建言与实践落实,由此三者构成推动近代教育发生、发展的“官—商—士”三角联盟。在这个同盟中,督抚予以政治权力的保障,绅商是实施主体,教育幕僚作思想倡导和落实推动,代表着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教育层面中具有革新性的三种力量,他们的相互融合与多年来的教育实践,共同推动了大致自1860年到1905年期间我国新式教育的产生与成长,影响了政府层面对于新式教育的态度,进而推动了政府全面广兴新式教育的决策,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全国学制的颁布与推行,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从此大步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