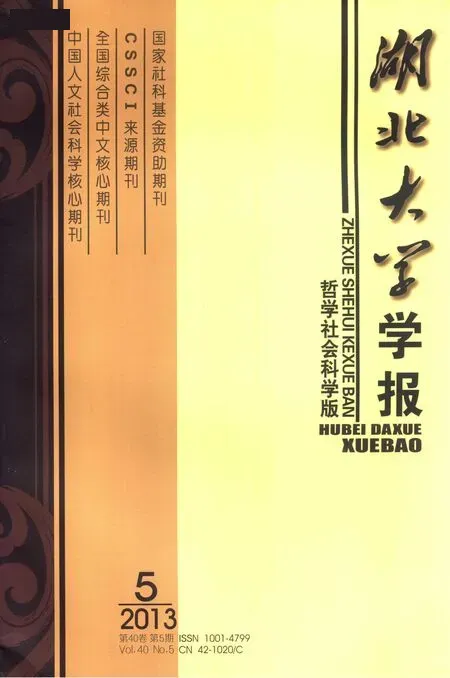论毛姆小说的自然主义特征
申利锋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是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作为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作家,毛姆一方面继承了英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因为时代风气和个人经历等原因接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1],因此,毛姆的小说从总体上可以归入现实主义的行列,但又具有较为明显的自然主义特征。
一
“自然主义”一词本为哲学术语,意指“除自然外,并不存在超自然的事物,一切都包括在自然的法则之中”[2]41。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1867年,左拉在《〈黛莱斯·拉甘〉序言》中对“自然主义”的借用使得该词正式进入了文学批评领域。此后,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迅速得以完善和系统化,使这一思潮在19世纪70至80年代达到高潮,并在当时的欧美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自然主义文艺观的核心是对文学的真实性、客观性的极度强调,认为“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2]501。而且,自然主义还十分重视人物形象的自然属性,主张在描写人物时,作家除应关注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之外,为了能够更为彻底地揭示人性的真实,还应该重视对人的自然品性和生理本能的刻画。同样,毛姆也将人之作为自然人的情欲视为人性正常的组成部分,认为欲望不过是“性的本能的天然结果”[3]193。因此,毛姆的多部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有对人物原始情欲的揭示和描写。
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开始,毛姆就把表现人的生理本能和自然情欲纳入了描写范围。小说中,年轻的姑娘丽莎被已有妻室的吉姆·布莱克斯顿所吸引,渴望与他亲近,为此,丽莎时时感觉有一种奇异的激情荡漾在心怀。在《克雷杜克夫人》中,伯莎年轻热情,情不自禁地喜欢那个“有修长的四肢和宽阔的胸膛”而且“口角很富有诱惑力”的雇工爱德华·克雷杜克,以致时时“感到一阵微微的、奇异的激动”;而当婚后她的澎湃激情不能为克雷杜克所理解时,伯莎又与同样充满青春热情的表弟杰拉尔德迅速碰撞出了爱的火花,并感到“她的肉欲在叫喊,想到她能把她肉体极宝贵的天赋给与杰拉尔德,她浑身颤栗”。在《人生的枷锁》中,一直在苦苦追寻人生意义的菲利普,在遇到相貌平平、人品平庸、喜怒无常的女招待米尔德丽德后,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情欲所指挥,欲罢不能地爱上了她——尽管这种爱给他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心灵上的饥渴,是痛苦的思念,是极度的苦恼”,因为善于解剖自我的菲利普明白:“他的痛苦乃在于肉欲得不到满足。”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向来端庄、温柔、娴静的勃朗什,面对思特里克兰德这个“身体高大、壮硕”、“生得粗野不逊,眼睛深邃冷漠,嘴型给人以肉欲感”的人,面对他给人的强烈生理欲望的召唤,最终屈服于肉体的诱惑而抛弃了她的丈夫戴尔克·施特略夫。在《剧院风情》中,已届中年的女演员朱莉娅·兰伯特,因不满丈夫迈克尔对她的冷淡,而委身于一个“性欲旺盛”、“最喜交欢”的青年会计师汤姆·芬纳尔。在《刀锋》中,健康活泼、漂亮果敢的伊莎贝儿虽然并未从精神上把拉里舍弃,但还是与格雷·马图林结了婚,这不只是为了方形钻石和貂皮大衣,还因为格雷能很好地满足她的肉体需要。显然,在毛姆笔下,人性和情欲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除了长篇小说之外,毛姆的短篇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这可从《雨》一篇中见出一斑。小说主人公之一戴维森是个狂热的传教士,他本打算用宗教教义使妓女汤普森小姐改邪归正,为此甚至不惜采用种种手段胁迫她。但是,这个有着“丰满而性感的双唇”、“有一团火在身里被抑压”且“这团火含而不露却又蠢蠢欲动”的传教士,尽管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在汤普森充满轻蔑、傲慢和憎恨的咒骂声中,最终暴露出了卑鄙的嘴脸,从而成为毛姆小说中一个伪善、淫恶的典型。
由此可见,毛姆在描画人物时,除了写人之作为社会人的思想感情外,还真切表现了人之作为自然人的生理冲动与原始欲求。他不回避男女关系中的肉欲成分和生理原因,这与自然主义所要求的真实描写客观现实、真实描写人性和人类机体的主张显然是相契合的。
二
毛姆在他的多部小说里都真实地描绘了下层民众的贫寒生活境况,并在此基础上表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他的这种写作特征与自然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流行同样具有内在的关联。正如柳鸣九先生所言:“由于自然主义,人类的文学才完全超出了沙龙、舞会、林荫道、乡间别墅的天地,才有了矿井、坑道、小酒店、贫民窟、洗衣房、工场里的车间、农村里的市集、大城市中的菜市场,以及农民在地头的劳动、工人的操作技术、乡间酿酒的程序……十九世纪末的自然主义思潮中,作家们……将目光注视到社会底层,把社会矛盾与劳苦大众的生活带进了文学领域。”[2]4的确,只有将下层人民的凄惨生活与上流社会的觥筹交错并重,对生活场景做更加广泛的描绘,才能达到真实表现整个社会现实的目的。
毛姆对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描写体现在很多细节上。如在《兰贝斯的丽莎》中,毛姆就真实地勾画了一幅19世纪末伦敦东南部贫民窟的真实生活图景。在这里,贫苦的下层人民居住的是单调而灰暗的房子,阴沉寒冷的夜晚常有“无家可归、又没钱找个地方投宿的可怜人,蜷缩在角落里……死人般地沉睡着”,妇女们谈话的资料只是“那些刚生下和即将生下的婴孩们和附近小客栈里正好发生的杀人事件”,人们靠饮酒来暂时忘却日常的悲苦,靠肉欲的满足来暂时逃避现实的凄楚,偶尔的苦中作乐也不过是给他们灰暗沉闷、浑浑噩噩的生活添加几声空洞的笑声罢了。这一切,都是兰贝斯贫民窟的真实写照,是毛姆对现实的忠实再现。毛姆自己也曾明白地指出:“这是在兰贝斯贫民区九天的见闻……这儿的住户们有的是一种破破烂烂的生活,也有他们的那种爱情,死起来也和别的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本来什么都是无所谓的,而在兰贝斯,那就更无所谓了。”[4]53~54这种近乎“实录”的写作方式在当时即引起了英国评论界的重视,《每日邮报》上的评论文章认为:“全书充满着小酒馆的气息,颇为沉闷,但毕竟写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不能不认为是一部成功之作。”[4]57《文艺协会》评论说:“那些希望看到对生活的真实描写、而不是粉饰生活的人,倒也觉得不难从书中看出社会真情来。”[4]58《学术》杂志的《小说副刊》更是明确地提出,这部小说所描绘的内容“都不啻为生活的真实再现”[4]58。而毛姆这种不带任何修饰的真实正是为自然主义所要求的。
毛姆不仅真实地勾画了伦敦底层的生活图景,而且对自己游历世界各地时亲见的贫困也给予了如实的描绘。如在墨西哥,有“身材矮小、衣衫褴褛的印第安妇女,每人都用布包着孩子,驮在背上,伸出皮包骨头的手,用颤抖、啜泣的声音不停地行乞”;有“营养不良、衣不蔽体的孩子,没完没了地吵着向别人讨钱”;有“要是从你那儿没有得到点儿施舍,就会不停地苦苦哀求”的大量乞丐(《乞丐》)。在中国,有挑着担子而“衣服就只是一件短褂和一条裤子”的年轻苦力;也有“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形容枯槁,……瘦削的脸上猴子似的满是皱纹,头发稀薄斑白,蹒跚在他们的负担之下,一直走到坟墓,他们最后休息的边缘”的老年苦力;还有身着打了补丁的背心、赤脚裸踝去敬神的贫寒老妇人(《在中国屏风上》)。……所有这一切,都是毛姆观察所得,这些小说无不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矛盾与劳苦大众的生活”,难怪有评论家指出:
如果你害怕直视生活,那你最好把毛姆搁在一旁,而去那些几乎没有立足基础的、想象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未必会有的浪漫故事中寻找安慰;但是,如果你想通过一些重要的事情反映真实的生活,如果你要扩大知识面并增强对现实人性的同情——那么,毛姆就是一个能满足你这些需要的小说家。[5]34~35
众所周知,自然主义文学理论非常重视环境对人物所起的作用。左拉就宣称:“近代文学中的人物不再是一种抽象心理的体现,而像一株植物一样,是空气和土壤的产物。”[2]510因此左拉主张作家要“在准确地研究环境、认清和人物内心状态息息相关的外部世界的情况上做功夫”[2]511。也许正是受到了左拉这一观点的影响,毛姆也将环境展示置于小说创作的重要地位,他常常有意无意地通过许多细节,把自己所观察到的道德、婚姻、宗教等方面的社会因素具体地再现于读者面前,让他笔下人物的故事皆与具体环境密切相关,从而使读者明了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支配他们作出种种决定的环境影响。在毛姆的小说中,人物性格和环境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和谐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姆小说的成功与他出色的环境描写是分不开的。
三
不过,尽管毛姆的小说有着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但这只是特征的相似而非本质的相同,他仍然应归属于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毛姆对于“客观”、“真实”等写作原则的理解和把握与自然主义作家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比如,自然主义提倡创作的客观性,强调作家情感的“零度介入”并应原汁原味地描绘现实。与此相关,毛姆在创作中也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眼光,他也不主张作家在小说中灌输自己的思想:“小说家应该让人物自己解释自己,而且要尽可能地把人物的行为描写成人物性格的自然结果,……如果小说家出面来指点你如何赞美主人公的魅力或者如何憎恨反面人物的恶行,如果他一面对你说故事一面又在故事中充当某种角色,那你很可能会觉得讨厌。”[6]203~204这是二者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不同的是,虽然毛姆极少在作品中进行说教,也喜欢使用白描的手法,但他并非对作品中的人和事进行情感的“零度介入”,而是将自己的情感和态度巧妙地包蕴在文字之中,读者也很容易透过毛姆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内容丰富的故事,洞悉作家对人与物的褒贬、爱憎。
还是以《兰贝斯的丽莎》为例。在小说中,作者对两个主要场景——丽莎与布莱克斯顿太太扭打时的情景、肯普太太与霍奇斯太太在奄奄一息的丽莎面前边喝酒边讨论丧葬事宜的情景——的描写,都是极为客观的。在第一个场景的描写中,读者能看到的是两个女人的怒目相向、唇枪舌剑、拳脚相加,以及围观人众的幸灾乐祸、火上浇油;在第二个场景的描写中,读者也只看到两个满脸麻木、生活贫寒的中年妇女在病人病榻前的冷漠而无知的言行举止。直至丽莎惨死的那一刻,毛姆都是以一个超然的、客观的叙述者身份,不动声色地宣告死亡的来临:“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一阵大声的哮吼。它从床上发出来,震动整个房间,打破了沉寂。医生揭开丽莎的一只眼睛,碰碰它,然后把他一直握着的她的那只手按在她胸口上,拉起床单,遮没了她的头。”自始至终,作者都没有对这两个场景作任何评论。对此,毛姆是这样解释的:
在《兰贝斯的丽莎》中,我没有多加渲染或夸张地描写了那些我在医院门诊部遇见的人和我作为助产医生在服务街区遇见的人,描写了那些在我工作时从一家到另一家遇到的触动了我的事情,还有在我无事可做随意漫步时看到的事情。……我相当直截了当地写下了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东西。[7]109
从字面上来看,这似乎表明作者在写作时并没有情感介入,但仔细分析就可发现,由于作者所描写的内容大都是“触动了我的事情”,因此,这些貌似客观展示的情节实际上已先在地蕴涵了作者的情感,作者“没有多加渲染或夸张”的写作方式,反而能够将自己心中已不自觉地筛选过的镜像更多和更逼真地陈列开来,从而赋予作品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并引发读者的审美感受。
同样,在短篇小说《午餐》中,女食客和年轻穷作家的性格特征,毛姆也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来展现的。这个女食客一边三番五次故作姿态地声称自己“中饭只吃一道菜”,一边却毫不客气地点着一道道昂贵、稀有的佳肴并“纵情大嚼”;一边装腔作势地说“中饭从来不喝什么酒”,一边却津津有味地品味着法国白葡萄酒;一边说“一个人吃饭时一定要只吃八成饱”,一边却在吃掉了鱼子酱、鲑鱼、大龙须菜并“消灭”了一份香槟酒后,又为自己要了一份冰淇淋加咖啡和一个大大的桃子。而且,她在鲸吸牛饮的同时,却对身为穷作家的“我”所吃的那份“菜单上价格最便宜的菜”大发议论,一本正经地责备“我”中饭吃得太多,训诫“我”说吃“羊排这类油腻的东西”很不好。而“我”则被恭维话说得飘飘然,结果,本以为“一顿便餐不会超过十五个法郎”,却不料这一次午餐竟耗光了他当月仅有的八十个法郎的生活费。整篇小说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行文简洁流畅,作者未加任何评论,却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一个虚伪的、堪称饕餮之徒的妇人形象,并把经济拮据的年轻作家为要面子而身处窘境的状况描绘得生动有趣。再如《舞男舞女》中,毛姆同样以客观的态度和白描的手法,描写了资产阶级富婆阔佬们穷奢极欲、觥筹交错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为求刺激找乐子而无视艺人生命的彻骨冷酷嘴脸,同时也描写了穷苦舞女斯特拉为了生计而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从六十呎高台跳入燃着烈焰的水深仅五呎的水箱中的表演。这些描写同样是语气平静、喜怒不流于笔端,但这种强烈的对比显然是包含着作者丰富的潜台词的,读者也不难从中体会出作者对于资产阶级生活奢华与残忍自私心态的揭露与批判,以及作者对下层人民贫困生活的同情。而这些正是毛姆在本质上仍属于现实主义作家之列的原因。
四
综上所述,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在毛姆的小说创作中只是部分和倾向,而非全部和主流。而且从根本上而言,自然主义也并不是现实主义的对立面,而是与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正如柳鸣九先生所言:“自然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是现实主义的演变与发展。”[2]5毛姆小说创作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善于观察生活的毛姆,以犀利的笔触对人的生理欲求、下层民众的贫寒生活境况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作了真实的、淋漓尽致的描写,这种描写既扩大了其作品的表现范围,也增强了其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另一方面,自然主义倾向也给毛姆的小说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与萧伯纳、高尔斯华绥、阿诺德·本涅特等同属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作家相比,毛姆对社会的批判显然要少一些。而且,毛姆常常满足于描写个别人而非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人物,醉心于人们行为中的反常现象,却很少更深地思考那个反常现象的道德基础,或为之寻找社会的解释。而这两方面的影响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自然主义倾向正是毛姆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
[1]申利锋.毛姆小说创作自然主义倾向的缘起[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4).
[2]柳鸣九.自然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毛姆.刀锋[M].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特德·摩根.人生的挑剔者——毛姆传[M].梅影,舒云,晓静,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5]Anthony Curtis,John Whitehead.W.Somerset Maugham——the Critical Heritage[M].New York:Routledge,1997.
[6]毛姆.毛姆读书随笔[M].刘文荣,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7]W.Somerset Maugham.The Summing Up[M].London:Pan Books Ltd.,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