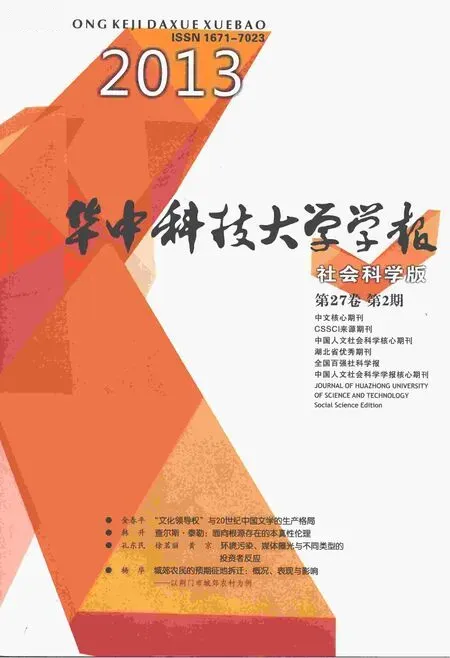超越之思:沟通在与言的知识论之桥——评高秉江的《西方知识论的超越之路》
梁上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副编审
综观整部西方哲学发展史,不难发现它的主流形态是围绕在、思、言及其关系问题逐步形成并拓展开来的,对它们的研究分别产生了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哲学)三种最基本的哲学形态。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虽然人们习惯性地以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和当代语言哲学来简单地概括整个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段的主流哲学形态的嬗变,但是这仅仅就不同历史时段哲学所关注的基本主题和核心问题而言才有其合理性。事实上,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哲学思考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涉及在、思、言及其关系问题。因此,可以说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哲学)并非分别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固有哲学形态,而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段的哲学思考都必然会涉及的带有普遍性的共同论域。同样地,当人们习惯于用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来概括地说明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时,它并非仅仅简单地意味着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和当代语言哲学之间的历时性统一,而且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三种基本哲学形态之间所具有的共时性统一。西方哲学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处于哲学思考两极的分别是本体论和逻辑学(语言哲学),前者探讨的主题是“在”,它作为对终极存在进行追问的形而上学,曾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乃至中世纪哲学的核心话题,后者探讨的主题则是“言”,它是作为技术操作的语言分析学,当代哲学将其关注的重点转移至此,以致出现了人们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沟通本体论和逻辑学(语言哲学)两极的则是认识论(就认知的动态过程而言)或知识论(就认知结果和对象的静态结构分析而言),认识论或知识论所探讨的主题则是“思”,它是作为认知主体如何认知世界的主体主义哲学或意识哲学,近代哲学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始就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于此。在、思、言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统一性,在必须对思显现才能作为对象被认知,思作为认知活动只有思及在才不是空洞的;言为心声,思作为认知结果必须对言显现才能作为心声被谈论。因此,在本体论与逻辑学(语言哲学)之间有一座沟通两者的知识论之桥:只有知识论意义上的本体论才是可以显现和谈论的,否则本体论就会成为独断论和自然科学话题;同样地,也只有知识论意义上的逻辑学(语言哲学)才能关涉存在和真理,否则逻辑学(语言哲学)就会完全消融为修辞术,甚至沦落为诡辩论。这才是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这一古老话题所具有的基本意蕴。
既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中,认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那么从知识论出发并且通过知识论的探讨去把握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总体走势必定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选题之一。高秉江教授的新作《西方知识论的超越之路——从毕达哥拉斯到胡塞尔》(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正是一部探讨这一重要选题的高水平学术专著,颇值一读。该著既对西方知识论的总体发展路径和基本走向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宏观梳理,又对从毕达哥拉斯到胡塞尔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家在知识论上的基本观点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微观分析;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既有对西方知识的独特洞见,又有对中西思维方式的精妙比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善于使用优美的文学性语言来表达近乎枯涩的哲学观点,而且与书中随处闪耀着的灵动的思想火花交相辉映,读起来常常给人一种仿若在西方哲学史长廊中信步观景的轻松愉悦之感。作者在该著中所要表达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是一种超越论,即把西方知识论的演变历程从总体上理解为一条超越之路,正如作者在其导论中所言:“西方知识论从一开始就是走一条超越之路,一条从感觉的当下性、私人性和模糊性,超越到知识的永恒性、公共性和明晰性之路。这条超越之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着一条十分清晰的脉络,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确定性的超越,巴门尼德的语言确定性的超越,到苏格拉底的定义追求,柏拉图的idea超越,再到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超越,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超越观念论体系,为西方文化打下了演绎逻辑的理性基础。这条超越之路在中世纪走向天国,而在现代笛卡尔之后回归到主体的内在先验之思。”[1]19作者紧密结合本体论、语言哲学的基本语境对这条超越之路进行了全面论证和深刻分析,每一位认真细读过全书的读者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其论证和分析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当然,这种超越论也为读者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即便读者对它给予某种程度的赞同也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解释,因为作者不仅没有对“超越”一词的基本意涵予以界定,而且没有在同一意涵上使用“超越”一词。因此,在对西方知识论的这种超越论解释架构中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询问西方知识论所走的超越之路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超越?它又向何处超越?
从该著以超越论为核心线索对西方知识论的学术历程进行的梳理来看,作者提出的这种超越论基本上可以在新康德主义者所区分的“超验”(transcendent)和“先验”(transcendental)两种不同意义上加以理解。
首先,西方古典知识论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在“超验”意义上的超越之路,即从经验世界向超验领域的跃升。超验与经验无关,超验领域是与经验世界相对的形而上学领域,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本身就意味着知识论意义上的哲学开端之学。从柏拉图转述、黑格尔评述的泰勒斯的望天之举的喻意中可以感受到西方哲学一开始就孕育着这种形而上学诉求。当以泰勒斯为代表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从流变不居的经验世界出发追寻作为其统一本原的始基时,他们就已经开始了超验的形上致思。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追寻经验世界的超验本原的形上致思也不自觉地体现在一种概念化语言的努力之中,也就是说,当他们用表达某种具体物质形态(水、气、火、土)的语词去解释经验世界的统一性时,实际上是用某个语词(实词)本身蕴含的普遍性超越经验世界的特殊性,虽然一个语词(实词)所指称的是经验世界中某种具体的东西,但这个语词(实词)本身却蕴含着普遍性,因为语词(实词)本身能把其意谓颠倒过来使感性的经验具体转变成理性的超验共相。由此可见,作为知识论意义上的哲学开端之学本身就不自觉地与语言纠缠在一起。当赫拉克利特用“逻各斯”(logos)充当经验世界的变中之不变的“尺度”时,古希腊哲学才开始自觉地以语言的普遍性、确定性去超越感性世界的特殊性、流变性。但是,完成古希腊哲学史上第一次知识理性的系统超越的不是赫拉克利特,而是毕达哥拉斯,他率先完成了从感觉实在论向数字确定性的超越。知识理性所需的确定性、可分析性、普遍性、必然性、可言说性等在其数本论中已初具雏形。但是,毕达哥拉斯所说的数毕竟不是在,而仅仅是在的某种本质规定性。在巴门尼德的being学说中才正式触及在。巴门尼德所说的being不仅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而且是一种可以内化于人的思想意识中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具有语言逻辑特征的规定性。因此,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一开始就是与知识论、语言逻辑融会贯通的。此后的智者学派虽然重点关注巴门尼德学说中的语言逻辑性,但是由于切断了知识论之桥对语言与存在联接,使得语言逻辑丧失了对存在和真理的言说,最终只能片面地强调修辞术,甚至不可避免地陷入诡辩论。苏格拉底批判智者学派,倡导寻求普遍性的定义,是向巴门尼德在、思、言三者融合的回归。柏拉图继承了乃师的基本理路,以其相论将世界二重化,只有超验的本体世界才是客观存在的独立王国,而经验的现象世界则被视为超验的本体世界的摹本。因此,他的idea不仅是一种语言逻辑的共相概念,而且是一种形而上的客观存在,打通两者的关键便是“知识即回忆”这一经典论述。至此,古希腊哲学从作为感性对象的水、气、火、土等到作为观念对象的数、being、idea等,都试图以语言概念的形式超越当下感性经验的流变性而通达一种观念的永恒确定性,并将其设定为形而上学的实在性。亚里士多德虽然批判了柏拉图将idea客观实在化的做法,但是他仍然坚守着以往哲学家们对超验世界的理想追求。不仅他的“第一哲学”肯定了作为终极存在的“第一推动者”,而且当他以“知识始于经验”的论述修正柏拉图的“知识即回忆”的论述时,他实际上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对柏拉图的超验思想的经验诠释和方法论补充。他虽然强调知识的个体经验基础,但是他所描述的个体经验仍然是idea共相光照下的殊相经验,作为第一推动者的“思想的思想”始终高悬于个体经验知识之上的终极理想;他的经验科学关注仍然是在逻辑确定性架构下的理性描述。亚里士多德对西方哲学的最大贡献不是别的,而是他建构起来的具有科学方法论意义的形式逻辑系统。亚里士多德之后,不管是斯多亚学派还是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是在沿着这条超验之路继续前行。总之,古希腊知识论是向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超越,虽然有亚里士多德试图为其奠定经验基础,但是其所追求的占居主导性地位的知识论目的仍然是一种超验意义上的客观观念论或观念实在论。
古希腊知识论的超验理想在中世纪得到了传承和进一步强化。众所周知,中世纪是宗教主宰的时代,中世纪知识论的探讨是在基督宗教语境中展开的。宗教信仰与自然理性的关系问题构成了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直接决定了中世纪知识论的总体走向。正统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对这个基本问题的总体回答是信仰高于理性,同时也承认两者的和谐一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和“信仰寻求理解”就是回答这一中世纪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信仰和理性两者在知识论上意义上密切相关。信仰作为一种相信和认可的态度,其本身就是构成知识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作为知识起点的第一原则是知识理性自身无法提供和辩护的,只能被相信为自明而无需被证明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信仰为知识的原则和基础提供了某种终极的存在论辩护;同时,知识乃是理性运作的结果,理性的运作不仅体现为自我意识自觉主动的寻求,而且体现为理性本身能够对其意识过程进行反思和辩护。因此,信仰和理性在知识论意义上相互关联,信仰本身就是一种经由理性而最终又超越理性的认知,是理性的存在论预设,而理性则是信仰的认识论基础。基于对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这一基本理解,中世纪哲学和神学在承认人的自然理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高扬了信仰的绝对优先性。作为信仰对象的上帝不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存在,而且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终极基础和根源。知识所追求的普遍性、必然性、永恒性和绝对性在追求对上帝的信仰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强化。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两大体系,不管是以柏拉图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奥古斯丁主义,还是以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托马斯主义,都传承和强化了古希腊知识论的超验理想,它们共同开启了对信仰、直观、天启乃至灵魂自身的内在体悟等诸多超越层面的探讨。奥古斯丁以其“光照论”传承了柏拉图的“洞喻”思想,强调神圣之光对于获得真理性知识的极端重要意义。托马斯虽然继承亚里士多德“知识始于经验”的思想,但是他认为人凭借其自然理性以经验为基础所获得的知识是不完善的自然真理,只有在神圣理智之光照耀下获得的启示真理才是完善的最高真理。人凭借其自然理性所获得的自然知识虽然不能达到对神圣者完美认知程度,但是它与启示知识并不矛盾。“即使人类心智的自然理性之光不足以使由信仰所启示的东西被认知,由信仰神圣地教授给我们的东西仍然不可能与由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发生冲突。”[2]43托马斯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就是从经验世界通达超验领域的最好例证。中世纪知识论的超验追求同样与其语言哲学紧密相联。基督宗教语言哲学不仅补充和提炼了古希腊形式逻辑,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古希腊语言哲学的论域。对超验的神圣语言及其与人的自然语言的关系的探讨构成了宗教语言哲学特有的论题。作为基督教信仰对象的上帝不仅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存在,而且也是语言哲学意义上的“道”。圣经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1)上帝原本就是藉着话语(“道”)来创造世界的。人虽然是最肖似上帝的受造物,但是人作为受造物与上帝之间毕竟有着无限的距离,有限的人类语言何以理解作为无限的神圣对象的上帝及其话语始终是一个宗教语言哲学的难题。不管是奥古斯丁对“三位一体”奥秘的言说,或者否定神学的否定性描述理论,还是托马斯的类比性谓词理论,甚至是神秘主义的个体性情感言说,都是试图为人类有限的理性语言得以言说无限的超理性的神圣对象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中世纪语言哲学与中世纪知识论所追求的超越知识理性的神秘体悟、超越逻辑推理的直观洞见、超越实证法则的澄澈意境正相契合。总之,中世纪知识论的超越是向信仰启示和理性形而上学的终极性的超越,把古希腊知识论的观念实在论在神学语境中推向了极端。
其次,西方近现代知识论所走的则是一条在“先验”意义上的超越之路,即从经验实在性向先验主体性跃进。先验与经验虽然属于不同层次,但是它与经验密切相关。按照新康德主义者的理解,先验不仅意味着先于经验,一切先验的东西都是先天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因素,而且意味着渗透在经验之中而使经验提升为普遍必然性的先决条件,即“可能性的条件”(condition of possibilities)。西方古典知识论与近现代知识论本质上都属于超越的观念论,但是观念论有客观与主观之分。如果说西方古典知识论超越到了一个与经验无关的超验的客观观念领域,那么西方近现代知识论则超越到了一个与经验密切相关的先验的主观观念领域。推动西方知识论从超验的客观观念论转向先验的主观观念论的始作俑者是笛卡尔。与古希腊知识论向作为宇宙理性的逻各斯寻求知识建构的基础或中世纪知识论向作为神圣理性的上帝寻求知识建构的基础不同,笛卡尔哲学以其“我思故我在”转向了理性与主体自我的结合,一切知识都必须建立在自我明见性基础上,否则便被当作独断论加以拒斥。他把知识的基础和起点转化成为一个纯粹意识能够普遍直观的“我思”,这个普遍意识能够直观的“我思”就是自我意识观念直接明晰而确定的呈现,不以任何假定前提为根据,一切去蔽的纯粹意识都能够直观到它。从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开始向主体主义哲学或意识哲学的道路阔步挺进,自我主体成为其关注的重大主题,直观呈现的意识内容以及意识结构是其探讨的核心内容。继笛卡尔之后,康德系统地建构起了主体主义的先验哲学。他以“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口号确立了其主体主义的基础立场,为人的理性划定了界限,坚决反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僭越理性的界限而仅凭概念的演绎和理性的推理就能通达既不可知又无法言说的超验领域。如果说笛卡尔把西方哲学从关注本体论转向了关注认识论,那么康德则在认识论上完成了先验转向,即把关注的焦点从客体的认识对象转向了主体的认知结构。在康德看来,知识不过是主体的认知结构整理经验材料的结果。他在主体的感性经验与先验结构之间谋求达成某种平衡。一方面,康德向外寻求意识内容的经验来源,他反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认为知识的内容始于经验,没有来源于认识对象的经验表象的充实,就不会产生任何知识内容;另一方面,康德又向内寻求先验自我的先天意识结构及其功能,认为先验主体的认知结构是使经验表象成为可能的先验根据,知识是先验主体的认知结构主动整理经验材料的结果。在认知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感性经验,而是主体的先验结构,前者是主体被动的接受,后者是主体主动的整理。主体的先验结构表现为在感性直观中以“时间”、“空间”为先验形式,在知性中则以“十二范畴”为先验图式。一切知识都是主体的感性经验与先验形式配合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他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3]52胡塞尔所开创的先验现象学延展了笛卡尔和康德的主体主义哲学。胡塞尔虽然不以探讨知识论为其口号,但是由于他的现象学对呈现在主体意识面前的现象加以描述,因此他的现象学在本质上仍然与知识论是密不可分的。胡塞尔以“意向性”作为其现象学探讨的出发点和核心问题,而“意向性”又意味着“意识是对自我之外的某物的意识”,因此他的现象学必然要深入人的意识结构去反思人对外物的认知。从知识论角度来看,重视主体性以及寻找不容置疑的知识之出发点构成了从笛卡尔哲学到康德哲学再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特色。当然,在主体问题上,这三位哲学家有着一定的差别:笛卡尔由“我思”的逻辑非自足性而导向了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自我实体,康德把笛卡尔的“我思”转换成自我表象,将其实体自我改造成功能性的逻辑自我,胡塞尔则认为康德的逻辑自我仍然具有人本主义倾向,他进一步把自我纯粹化为一种非人身的纯粹意识的先验主体。对主体意识的探讨必然要涉及到意识终极之处的存在问题,在追问意识的终极存在基础时,笛卡尔借用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康德虽然在自我功能方面把笛卡尔式的自我实体当作可疑的先验幻相加以拒斥,但是他在对象意义上设定了作为直观内容的终极基础的“物自体”;胡塞尔虽然使用了一个空括号来悬置存在问题,但是他以“意向性”突破笛卡尔式唯我论式的封闭的自我实体,因为它意味着先验主体的意识是一个向外在的对象世界开放的意识,先验主体作为意识体验的自我极统摄诸多的我思内容,被思的对象世界的统一性从先验自我的统觉中获得其构成性基础。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又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转向了存在现象学。总之,近现代知识论为了避免古典知识论陷入超验的形而上学独断论困境而转向了主体先验论,但是这种主体先验论自身也面临着知识在起点上的自明性与在结论上的普遍必然性之间的矛盾。如何从自我意识的明见性出发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而不陷入唯我论是近现代知识论需要化解的理论难题。不管是由笛卡尔开启而由康德所完成的先验转向,还是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或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都是为了克服这一难题而付出的理论努力,他们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仍然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延续,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理论圆满性。
不管读者对高秉江教授提出的超越论作出何种理解都会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这本谈知识论的专著实际上是对西方知识论史的纲要性梳理。知识论作为关于知识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因对何为知识这一问题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不同形式的知识论述。高秉江教授所理解的知识比“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更加宽泛,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古典和欧陆哲学在存在论视域下的知识论问题,并且紧密结合语言哲学来考察知识论问题,表现出它明显不同于只关注语言技术处理的英美哲学的知识论特点。此外,读者不难发现,该著所作的知识论史的考察虽然逻辑主线清楚明了,但它不是严格按照哲学史的时间秩序逻辑化地展开的,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知识论史,例如对于洛克、休谟以及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知识论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作者显然根据自己的主题需要进行了剪裁取舍,我们只能期待他将来有更加深入的拓展。
[1]高秉江:《西方知识论的超越之路——从毕达哥拉斯到胡塞尔》,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Thomas Aquinas,“Faith,Reason and Theology,QuestionsⅠ-Ⅳ of the Commentary on Boethius’De Trinitate”,St.Thomas’Introduction,tran.by Armand Maurer,Toronto: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1986,Q 2 A 3 Body.
[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51/B75,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 吴兰丽
——访陈嘉明教授